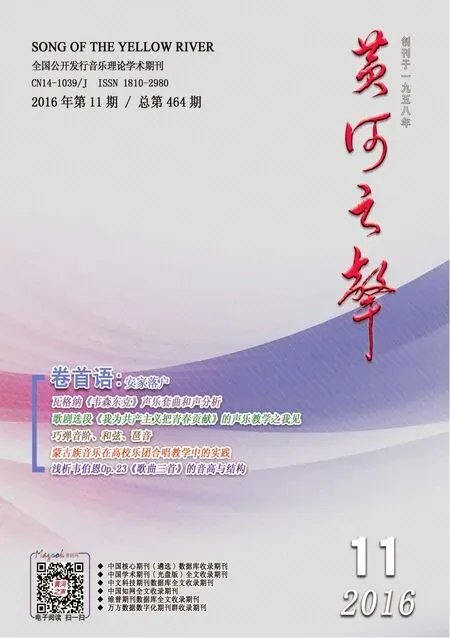以樂顯仁德
——孔子樂教思想探微
丁潤今
(河南大學藝術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以樂顯仁德
——孔子樂教思想探微
丁潤今
(河南大學藝術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孔子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樂教思想作為其思想體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人們認識音樂社會功能及教化功能的重要途徑。孔子樂教理論雖距今已有兩千余年歷史,然其樂教理論思想對現代音樂教育事業的發展,仍有著較為積極的方面。本文通過五個方面闡述孔子主要的樂教思想,希望對當代音樂教育工作者提供一定的借鑒與參考。
孔子;樂教思想;音樂功能
一、孔子其人
孔子,春秋末期人,作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不僅是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同時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音樂家。據歷史材料記載,孔子不單善歌,還善操琴、鼓瑟、擊磬,對樂舞也有較為深入細致的研究,特別是在創作方面,更是達到了隨事、隨詩賦曲的高度。此外,孔子的音樂教育思想是其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樂教方面,孔子將道、德、仁、禮等深刻思想與樂結合起來,體現出其“由道統樂,以樂體道”的樂教觀。雖然孔子的音樂教育思想并沒有形成專論,只是在其弟子所編撰、整理的《論語》一書中略見一二,但這也可見其樂教的主要思想。
二、孔子的樂教思想
(一)“游于藝”與“成于樂”——孔子的樂教基礎
在如何成為綜合素質比較全面的人的問題上,《論語·憲問》中提到:“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在這句話中,孔子把“藝”與智慧、克制、勇敢并列提出,說明了孔子認為藝術教育對人全面發展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那么在如何利用音樂藝術在培養人材方面發揮作用上,孔子則認為:“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這短短的十二個字實則在講一個人修身治學的順序,即由勵志發端,把仁德作為目標,通過學習六藝來涵養德行,從而達到教育的最終目標——成人。孔子認為樂教的終極目標在于以樂體道,是在“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的實踐過程中實現道、德、仁、樂合一,使人們臻于生命的理想狀態和本然。而從美育的角度來看,“游于藝”還意味著在學習中使學生獲得審美的自由、快樂的感受,在“游戲”性質的快樂氣氛中,既學習到了技能又能獲得審美上的深刻體驗,我們尚可把這一點看做“寓教于樂”的意思,在一定程度上來講,這與現在新課程改革的理念是相通的。在《論語·秦伯》中,“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則反映出詩教、禮教、樂教之間的關系,強調了藝術教育的重要性。
(二)“有教無類”——孔子的教育公平
孔子門生三千,賢者七十二人,此中絕大多數人屬于“貧而賤”階層的成員,在這種情況下,孔子“有教無類”的思想一反過去“禮不下庶人”的規定以及周代樂教的等級制度,實現了教育思想上的一次革命,孔子強調在教育對象上沒有貴族與平民之分,也沒有華夏與戎狄之分,這種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社會的受教育層面,適應了當時文化更新、學術下移的時代潮流,這也類似于我們當代社會所提倡的精英式教育轉向大眾式教育的觀念。
那么孔子真的就突破了等級制度了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其樂教思想在教育對象方面突破了等級的局限,是適應了當時文化發展的要求。而在春秋時期,孔子代表的是奴隸主階級的利益,從本質上講他還是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篇》)體現出孔子對封建禮樂以及等級制度的維護。
(三)“放鄭聲,遠佞人”與“盡善盡美”——孔子的“以樂顯仁德”
在孔子的思想中,并不是所有的音樂都適合人們去聽。在春秋時期的都市娛樂圈中,流行著一種供貴族富豪們聲色娛樂的音樂,在當時人們稱之為“鄭聲”或“鄭衛之音”,這類音樂活動不遵從任何禮樂規范而以縱情享樂為主要目的,過分強調感官刺激。針對這種情況,《論語·衛靈公》中有這樣一段記錄:“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武。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由此可見,孔子在音樂價值取向上具有明顯的道德屬性。此外,孔子在觀樂舞《韶》與《武》之后,也有不同的評價,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矣”,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這即強調了孔子要求好的音樂要達到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在這里的“內容”,即有一定的道德評價標準。故孔子的樂教思想由此也具有了社會學與倫理學方面的意義。
(四)“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樂教的最高境界
孔子在其樂教活動中,經常和學生談及生活中應該具有的一種精神境界,即一種樂觀愉悅而具有審美意義的精神境界,也就是“樂”這一美學思想范疇中的最高境界——“人生之樂”。這一點,我們可以通過《論語·先進篇》中的一個故事加以佐證。
有一天,孔子問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四人的志向,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冉求說道其志向:“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可使足民。”隨后公子華回答:“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愿為小相焉。”最后曾點舍瑟而作,對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在這里,孔子的“吾與點也”道出了其心中所贊賞的“樂”的境界已經超然于任何物質與權力之上,是一種真正無拘無束的人生境界,通過這一認知,來使人們獲得內在的審美愉悅的體驗。
三、結語
孔子的樂教思想促進其學術下移之風的形成,可以說,在整個先秦時期,孔子不但承繼、完善了周公的禮樂制度,而且把禮樂推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使禮樂成為中國文化的精神坐標、禮樂教育成為當時最為重要的教育手段。當然,孔子對樂教所賦予的道德評價標準以及仁德的思想內涵,在現代音樂教育體系中仍有很多借鑒意義。
[1] 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1.
[2] 田小軍.孔子樂教思想論略[J].中國音樂,2008.
[3] 吳丹.由道統樂,以樂體道——孔子樂教思想研究[J].益生文化,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