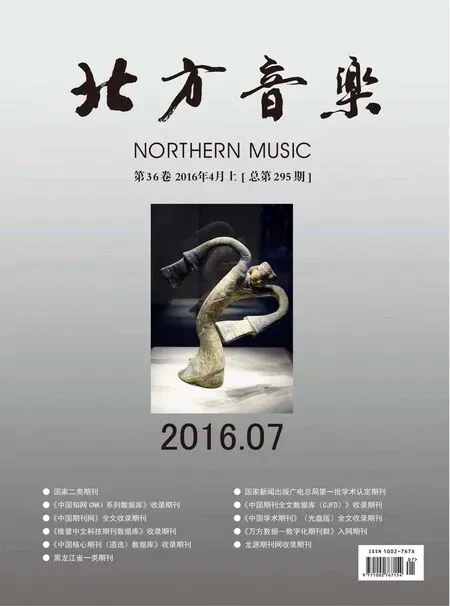二胡成為“道器”的文化演變
趙若希(西南民族大學,四川 成都 610000)
?
二胡成為“道器”的文化演變
趙若希
(西南民族大學,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從古至今細說二胡音樂的發展,近百年歷史的行程中二胡藝術不斷發展, 二胡作品的已有上千首, 通過二胡的發展史以及二胡的脈絡如獨奏曲的出現與教會音樂相關聯,慢慢演變成道器,也將禪宗文化與胡琴音樂相結合,現在也有一些二胡禪宗風格的作品出現,通過這些途徑,將其演變過程、現有曲目、影響與發展展開論述。
【關鍵詞】二胡;道器;演變;如來藏;三寶佛
一、“道器”與二胡的歷史淵源
在傳統音樂文化里,很多以“道”名之,稱之為“琴道”,最早在東漢桓譚著作《新論》中就專門有“琴道”篇了。“道”與“器”是中國傳統的一對哲學范疇,前者指抽象的、精神層面,后者具體的器物、制度、方法。借用這對哲學范疇,“道”也指音樂作品的情感、內涵,“器”指二胡、指法、音域、調性等。
中國歷史文化源遠流長,樂器種類繁多,二胡是我國最具代表性、流傳最廣、最富民族特色的一種拉弦樂器,中國傳統音樂在其漫長的演變和發展過程中,互相交錯的民間音樂與宗教音樂是有著深層根源的。例如:佛教音樂最初就是隨印度教在東漢時期傳入中原的,民間音樂和宗教音樂在慢慢歷史長河中相互影響、相互吸收、相互結合,形成了其雙重而又模糊的特點。兩者經過各種族、各地區、各樂種的長期的發展流變,取長補短,互通有無,既在橫向上保持了連貫性,又在縱向上發展了兼容性。在宗教音樂里,我們常見到民間音樂所用的曲牌,聽到似曾相識的民間音樂旋律,在民間音樂表演中,宗教音樂題材、體裁、標題也不斷出現,二者水乳交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已經沒有辦法人為地為它劃分界限。在近代的二胡發展中,已經有人漸漸把二胡與禪宗相聯系,試圖借鑒禪宗智慧解釋二胡演奏之道,如趙寒陽教授著作《二胡金剛論》就闡釋了這個觀點。之后也出現了較多禪宗與二胡的研究性論文。二胡音樂藝術由最初的獨奏曲出現就沿襲了教會音樂,如劉天華的《病中吟》。二胡的精髓與底蘊在于它比一般音樂文化藝術有著更深層次的內涵。這也是歷代文人墨客、士大夫與修道之士喜歡它的原因。
二、二胡“道器”之相關曲目分析
二胡最初主要是為戲曲、說唱、歌舞伴奏和參與某些小型傳統的樂隊合奏。之后由劉天華先生將其引入了學院派,開創了首功,慢慢的獨奏曲目就多了起來。而近現代與禪宗相關的二胡曲目也不斷增加,二胡就從意見簡單的“樂器”想“道器”進行著文化的演變,比較著名的如《三寶佛》、劉文金的《如來藏》套曲等等。
(一)《三寶佛》是漢族民族器樂曲中不可多得的傳世之作
原是廣東音樂里一支流傳已久的傳統民間曲目, 用《三汲浪》《倒卷珠簾》和《和尚思妻》三首短小的曲子作為引子收編在《南胡曲選》中,于上世紀初在廣東地區流行起來。三寶,即佛、法、僧或者覺、正、凈。三寶就是佛寶、法寶、僧寶。宗家各派將佛寶視為釋迦牟尼佛,法寶視為四諦圣法,僧寶視為最初被度的五比丘,皆為執掌天地、統領精神的大要。此曲將宗教音樂和佛教音樂結合在一起,二者相互影響,相互襯托又相互制衡。所以我們在聽奏二胡曲《三寶佛》時,總有一種虛靜、空靈的超脫之感。
(二)《如來藏》套曲
劉文金先生根據文學巨匠愚溪先生的《袍修羅蘭》(瓔珞姑娘的故事)為原本創作出了著名二胡套曲《袍修羅蘭——如來夢》。
這部里程碑式的二胡作品將“以和為美”“美善同一”的中國傳統音樂美學思想滲透其中。把其意境美、崇高美的表現特,以及博大精深的佛學哲理,征用情景交融的音樂表達方式體現的淋漓盡致。
這部作品有著獨特的創作性,運用現代與傳統相結合的創作手法和新穎的演奏技巧等高超藝術表現手段使得作品有了豐富的藝術價值,為二胡藝術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開創了更廣闊的空間。
值得強調的是本曲運用了“以和唯美”的審美取向,這一點與道家學派創始人老子在《道德經》提出的“大音希聲”這個觀點不謀而合。即最美的聲音就是無聲,用一種祥和的感覺讓人得到升華與享受。劉文金先生創作套曲時追求了“真善美”,傳達了人內心與自然的和諧。此曲運用高燒的藝術手段和作曲技法,用二胡一樣樂器,無伴奏的形式創作出來,塑造了純凈的音樂,凈化人們的心靈。“袍修羅蘭”乃梵文“多寶”之意,出自于藏經,是佛學哲理中覺悟者終其一生所追求的生命的頂峰境界。劉文金先生將這樣崇高的佛學哲理用音樂作品來表達,這樣的思想內容賦予作品一種內在的力量,有內在力量的藝術作品給人以生命振作的韻律感,給人以心靈的震撼。有著這樣一種思想內涵的音樂作品無疑是崇高的。其內部滲透出的精神力量拉近了音樂與聽眾靈魂的距離。打開聽眾心靈大門的同時,又重重沖擊并填滿著聽眾內心對純粹音樂的渴望。真實、平凡而又偉大的情感被滲透在了音樂里,高深莫測而又近在咫尺。這種對生命精神的表達才是人類藝術最核心最崇高的哲學境界。
三、二胡“道器”的發展與展望
“如何把一部廣泛傳閱的文學名著,用一件樂器所具備的音樂語言、技法,重塑于音樂舞臺,使之與世俗題材相區別?”其難度非同一般。宗教題材是‘一難’;篇幅長大是‘二難’;從頭到尾一人演奏,是 ‘三難’。”喬建中先生在“中國弓弦藝術節·劉文金作品專場音樂會研討會”上這樣說到。二胡也慢慢從計發月起變味了“道器”,這種改變是一個好的發展方向。在嘈雜的社會中,人們正需要“道器”的演奏來慢慢凈化心靈。
中國宗教文化也是滋養中國胡琴成長和發展的環境必不可少的,若要真正演奏好二胡,也要做到以和為天、美善統一的審美價值,擴大了民族音樂的審美范疇,并提升了人們對民族器樂作品的審美品位。這些以其立意新穎的音樂題材、宏大的敘事方式和獨特的創作性大大提升了二胡作品的藝術價值。
參考文獻
[1]成公亮.古琴套曲《袍修羅蘭》創作后記[J].新原人,1998,(25).
[2]孫博.二胡套曲《袍修羅蘭——如來夢》演奏與研究[D].中國音樂學院,2011.
[3]周戀.論中和之美在二胡藝術作品中的體現[D].湖南師范大學,2012.
作者簡介:趙若希,女,西南民族大學,碩士,研究方向:二胡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