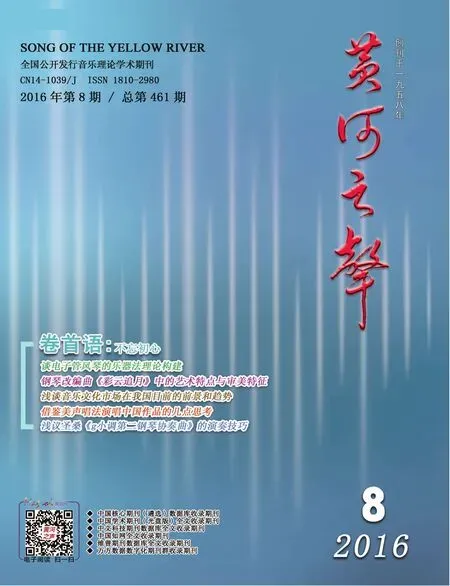彝族舞蹈體語與在不同語境的語意分析*
楊 俊
(西南科技大學文學與藝術學院,四川 綿陽 621010)
彝族舞蹈體語與在不同語境的語意分析*
楊 俊
(西南科技大學文學與藝術學院,四川 綿陽 621010)
在彝族悠長的歷史發(fā)展中,舞蹈藝術永遠伴隨著彝族人民生活的轉變而成長與發(fā)揚。藝術形式的演變往往揭示著一個民族社會的進化狀態(tài),而舞蹈藝術恰好最能充分展示一個民族的基本風貌和民族精神,所以舞蹈已經成為一種民族社會思想的一種具體表現(xiàn)形式。眾所周知,舞蹈的呈現(xiàn)是綜合性的,身體作是它的主體媒介,運用身體語言(動作律動)來進行舞蹈活動,同時結合身體輔語言(舞臺、燈光、布景、服裝等)元素共同呈現(xiàn)舞蹈表達的特色風貌。
彝族;彝族舞蹈;舞蹈體語;舞蹈文化
彝族作為我國古老的少數(shù)民族之一,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貴州三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的西北部。涼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區(qū),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川滇交界處,也是一個多民族的聚居區(qū)。該地區(qū)的彝族人民素以能歌善舞著稱于世,其傳統(tǒng)舞蹈豐富多樣,獨具特色。
一、彝族舞蹈及其類別
彝族人民能歌善舞,其舞蹈風格古樸凝練,種類繁多,民族特色鮮明而濃郁。追根溯源,這與古羌文化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可以說源自于古羌。彝族及其先民進入涼山之后,其舞蹈文化即在相對封閉的社會環(huán)境中長期延續(xù)。因此,涼山彝族傳統(tǒng)舞蹈既有悠久的歷史,又有當?shù)厣鐣螒B(tài)的痕跡。彝族舞蹈的形成期約在公元8到10世紀,那時廟會舞、巫舞、佛舞以及各類樂舞頗為盛行,至今有些歌舞還留存在彝族人民的生活中。據(jù)統(tǒng)計,有超過170多種彝族民間舞蹈,以及1900多種跳躍方法。
根據(jù)舞蹈的表現(xiàn)形式來分,彝族舞蹈主要分為集體舞與獨舞,此中以集體舞為主,如“跳月”“跳歌”“跳樂”“鍋莊舞”和“打歌舞”等。彝族民間舞蹈,按史學源流可分四類,即征戰(zhàn)舞、勞動舞、宮廷舞與祭祀舞。從藝術表現(xiàn)可分為花燈、樂舞和歌舞三種類型(樂舞包括銅鼓舞、煙盒舞、阿細跳月等,歌舞包括羅作舞、打歌、四弦舞等)。從內容上可分為:娛神驅鬼舞、送靈舞、虎舞等。
二、語境中的舞蹈體語
人是環(huán)境的人,作為一種場景動物,所有的人的行為都不能脫離特定的環(huán)境。人在不同的語境下說不同的話,而同樣的話在不同的環(huán)境中又傳達著不同的語意信息,所以,要確切無誤會意人們語言傳達的切實內容,必須結合其語言表達時所處的具體環(huán)境——語境。猶如美國語言學家Gilles Fauconnier所言:“語言表達形式本身是沒有意義的,確切地說,它有一種意義潛能,只有在完整的話語和情景中意義才能產生。”[1]語言如此,身體語言亦如此,舞蹈身體語言自然也概莫例外。
(一)身體語言
人類伊始,人與人的交流是由語言和非語言兩類構成的。研究顯示,人類在傳播信息的時候,語言(口述的字和詞)傳播占信息總量的7%,聲音(音量、語調及其變化)傳播占38%,另外由無聲的面部表情、動作、姿態(tài)等傳遞的占55%的比例。我們把這種無聲的、非口頭表達的“能夠傳遞信息及觀念的顯意符號系統(tǒng)”稱為身體語言(Body Language)[2]。
身體語言,也叫肢體語言(簡稱體語),指非詞語性的身體符號。從語言學的視角說,身體語言其實是副語言(paralanguage)的一種類型,表示使用姿勢、動作與動作群、表情來替代或作為口頭言語、聲音以及其他交流方式的輔助,以達到交流目的的方式的一個術語。從藝術欣賞的角度對身體語言進行研究,具體的任務是研究身體語言與審美之間的關系,重視的是身體語言的美是怎樣產生的,如舞蹈身體語言研究。
(二)舞蹈身體語言
身體語言作為人類獨特語言的一種,也與上述所受影響的因素一致。在通常的理解中“身體語言”僅指人的肢體,而在舞蹈身體語言中與舞蹈表演息息相關的因素,諸如服飾、道具與音樂等也是舞蹈身體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共同形成合力為最終的舞蹈作品傳達思想與情感。
“舞蹈身體語言”即“舞蹈體語”,其概念的提出也是近代以來舞蹈理論和實踐觀念變革的結果。盡管“身體語言”很早就已經以一門獨立的學科存在,可是把這門學科引入舞蹈理論界卻還是在現(xiàn)代舞蹈觀念產生以后。上世紀初,以“現(xiàn)代舞之母”鄧肯為代表的現(xiàn)代舞前驅們從批判古典芭蕾程式化,反對足尖技巧對舞蹈表現(xiàn)情感能力的約束,主張把人類的情感表現(xiàn)放在舞蹈的首位之始。現(xiàn)代舞使舞蹈重新回歸到服務人類情感意義上的原初動作本身。
(三)彝族舞蹈體語
在舞蹈藝術中,要正確理解舞蹈身體語言所傳達的含義,同樣離不開對其具體語境的聯(lián)系與判別。舞蹈身體語言的語境不單表現(xiàn)于運動人體的姿式、動作及其服飾、道具等物質載體上,還同時表現(xiàn)在不同舞蹈類別的審美和感知氛圍等綜合體驗當中。
彝族舞蹈體語是彝族舞蹈特有的身體語言,同時也是針對彝族舞蹈的種類、特點以及生態(tài)學意義的舞蹈研究的方法。不管是在傳統(tǒng)還是現(xiàn)當代的彝族舞蹈中,由于舞種、語境、舞者性別差異等而展示出來的身體語言都始終保持著那份神秘與不可或缺的地位,彝族的舞蹈動作以獨具特色、別有意味的樣式展現(xiàn)了其特有的身體語言的魅力。
三、彝族舞蹈體語在不同語境中的語意
談“語言”就離不開“語境”,將舞蹈身體語言放置于具體的“語境”中進行研究,才能讓我們更準確的把握傳達者的語意。[3]身體作為傳達媒介時,會因為這種表達方式的抽象性而顯得多意,就需要我們從多角度去理解,方能獲得更全面的信息。彝族舞蹈身體語言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藝術風格中所承載的文化傳達、審美意義與歷史價值均有不同。在不同語境中,彝族舞蹈身體語言的語意也自然會發(fā)生著變化,要正確理解交流對象語言的全部含義,就必須結合對方的語境因素,合理運用推理能力才可能獲得對該舞蹈作品最準確的解讀。
(一)彝族舞蹈遠古時代的語意
舞蹈作為表現(xiàn)人的生活和情感的有節(jié)奏的運動形式,產生于原始社會時期。先民們用舞蹈來慶祝豐收、歡慶勝利、祈求上蒼或祭祀祖先。從圈舞這種人類古老的舞蹈形式就可窺見一斑。圈舞歷經千年蛻變,在許多民族中已改頭換面,漢族的鼓子秧歌以多種形式的跑場顯示風采,傣族以雙人對舞的形式獨樹一幟,維族、蒙族豪放多姿,不拘一格。而彝族舞蹈跟所有藏緬語族一樣,仍保持著原始古樸的圈舞風貌,以連袂踏歌的方式訴說著他們悠久的歷史文化。古老的圈舞文化在千百年中流傳,奠定了彝族舞蹈文化的基礎。透過彝族聚居區(qū)的火把舞,我們看到諸多原始舞蹈的特質,彌漫著強烈的原生態(tài)氣息。火把舞在彝語中稱為“米疊騰”,就是舞動火把的意思。通常火把舞是在火把節(jié)才跳。每年的火把節(jié),彝族人民身著盛裝,家家吃盛宴,紛紛聚集荒原,點燃篝火,唱著火把歌兒,聯(lián)袂起舞,場面非常壯觀。對于火把舞的源起,傳說是很久以前一個叫阿史阿娜的彝家姑娘,因為美貌而聲名遠揚,被當時的一個漢人官員知道后,就把她的情哥殺害,搶走阿史阿娜,但是阿史阿娜寧死不從,最后點火自焚。后來彝族人為了紀念這位以身殉情、堅貞不屈的姑娘,就把六月二十四(她死的這天)定為火把節(jié),每年到這一天家家都點起火把,亦歌亦舞,祈望與阿史阿娜的不死之靈魂相通相息。
凡是到民族地區(qū)參加過圈舞活動的人多少會有這樣的感受,連袂踏歌、攜手而舞的形式很容易給我們現(xiàn)代人一種強烈的內心沖擊。在攜手同舞的過程中,不知不覺的化解了人與人之間或多或少的“潛在的敵意情結”。彝族舞蹈聯(lián)袂他哥的這種形式也不例外,當相識或不相識的人圍著篝火攜手而舞時,能喚起現(xiàn)代人對團結、信任、互助、協(xié)作的和諧大同社會的原始理想。釋放自己、回歸自我,人類最純真、最質樸的一面悄然流露,一片和諧祥寧之氣。
(二)彝族舞蹈的田園農耕語意
舞蹈在傳承的同時也繼承了該民族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習俗,在很多彝族舞蹈中都有生動形象地表現(xiàn)田園農耕生活的場面與語意。從發(fā)生學的角度講,舞蹈的誕生絕非純精神的產物,它具備與精神合為一體的實用價值。
彝族舞蹈動作的形成必然有其獨特的客觀環(huán)境和人文因素。彝族人民大多長期生活在山高坡陡之地,由于生產力低下,勞動和生活資料的運輸主要依賴于人力,沉重的背負必然會限制上肢的活動。因此他們的腿部變得堅實而有力,腿和膝部變得非常靈活。我們通過彝族舞蹈體語中的分析,很多腳部動作都含有許多生產勞動的影子,舞蹈的表演也起到了傳授生產勞動技能的作用。譬如織氈舞、蕎子舞、包谷舞等,基本就是表現(xiàn)生產過程和模仿勞動動作。在撒麻舞中,直接再現(xiàn)了從開墾到耕耘,從播種到出苗,從鋤草到田間管理,從收割到紡線,從織布到縫衣這一系列的完整的勞動過程,人與人之間的團結互助以及男女情感都在這個勞動過程中得以互融,勞動改變著生活的品質。
(三)彝族舞蹈的當代舞臺語意
社會的變化對民族民間藝術的影響不可估量,跟所有民族民間舞蹈一樣,根植于民間,帶著厚重的樸素的民間色彩一路走來。而在田野院壩和劇場表演,舞蹈的身體語言需要根據(jù)環(huán)境的改變而改變。當民族舞蹈走進劇場,就已經不再是原初田園舞蹈的意義了。即使將其最大化的還原為“原生態(tài)”的形式,但由于時空的改變,整個氣場也隨之改變。也正因如此,舞蹈的劇場表演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演繹風格與表演樣式。近距離、互動性和親和力作為民間舞蹈表演的優(yōu)勢和特點,這時候在劇場中就很難得以實現(xiàn)。所以,在劇場表演中,由于舞臺和空間的客觀性將舞者和觀者放在了對立的兩面,形成欣賞與被欣賞的關系,這使得舞蹈編導家們不得不從新的視覺入手去進行藝術創(chuàng)作。
20世紀50年代,當彝族舞蹈進入都市舞臺后,冷茂弘先生創(chuàng)作的彝族劇場舞蹈《快樂的啰嗦》、《阿哥追》《翻身農奴把歌唱》、《紅披氈》等,舞蹈皆因該時期的政治訴求所致,強烈的帶著顯明的時代特點,作品的審美意蘊也被意識形態(tài)的觀念消失殆盡。最后僅僅依靠舞蹈編創(chuàng)者的擇取吸納手法,得以巧妙的將其與時政嫁接。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電視的普及,彝族舞蹈也逐漸通過視頻與觀眾見面。觀眾通過現(xiàn)場與電視影像的接受也是完全不一樣的情感體驗。而另一方面,彝族舞蹈也在悄然的發(fā)生著重大變化,譬如馬琳的《阿惹妞》、《阿嫫惹牛》,蘇冬梅的《心之翼》等。通過對比這個時間階段涼山彝族舞蹈的創(chuàng)編作品,發(fā)現(xiàn)有兩個重大的轉向:一是舞蹈從彝族人自己編創(chuàng)轉向為他族人編創(chuàng)彝族舞蹈;二是彝族人自己跳彝族舞蹈轉向他族人跳彝族舞蹈。彝族舞蹈的創(chuàng)編角度也多元化起來,從而豐富了涼山彝族的當代舞蹈精神與內涵。可以說,這是彝族傳統(tǒng)舞蹈在面對現(xiàn)代族群觀念變化后的一次重要革新。
四、結語
引發(fā)彝族舞蹈體語語意變化的因素很多。二十一世紀以來,伴隨網絡數(shù)字技術的普及與運用,我們發(fā)現(xiàn)通過現(xiàn)場、電視、網絡看到的各種舞蹈大賽中的彝族舞蹈作品,均在表現(xiàn)形式、內容、服飾搭配、細節(jié)處理等方方面面作出了很大的變化。在社會整體逐漸進入現(xiàn)代文明的過程中,不斷主動或被動的吸收著現(xiàn)代社會的文明成果,從鄉(xiāng)村走向都市,從田野院壩走向華麗炫目劇場舞臺,融合科技可能的輔助表現(xiàn),將現(xiàn)代人的人文與生活訴求均納入其作品表現(xiàn)的內容。同一個作品不管是表現(xiàn)內容還是表現(xiàn)形式都發(fā)生了很大變化,甚至根本性的改變。因此,唯有將作品放在具體的語境中去研究彝族舞蹈體語,我們才能夠更好地承傳并發(fā)揚這門獨具魅力的舞蹈形式。
[1] 亞倫·皮斯、芭芭拉·皮斯,王甜甜、黃佼譯.身體語言密碼.中國城市出版社,2003.
[2] 安德魯·斯特拉桑.身體思想.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
[3] 朱永生.語境動態(tài)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彝族文化研究中心”項目研究成果(YZWH1209)
楊俊(1980-),女,四川仁壽人,西南科技大學文學與藝術學院講師,碩士,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民間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