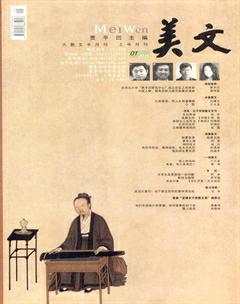塵封的光芒
宋旭紅
本世紀(jì)初,一部名為《達(dá)·芬奇密碼》的小說成就了暢銷奇跡。這本書不僅刷新了美國有史以來的書籍銷售紀(jì)錄,還在短短數(shù)年間被翻譯成42種不同語言。2006年,由該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更是火遍全球。這部小說當(dāng)然有著眾多暢銷書的特質(zhì):層層懸疑的情節(jié),緊張刺激的氛圍,高超的敘事技巧和簡練卻表現(xiàn)力極強(qiáng)的語言等。不過,僅僅這些并不足以制造奇跡。讓這部小說超越一般懸疑故事的是它的隱秘主線:基督信仰真正的傳承者和守護(hù)者不應(yīng)該是羅馬天主教會(huì),而是耶穌的妻子及其后裔。在漫長的歷史進(jìn)程中,后者成為教會(huì)極力隱藏和抹殺的對(duì)象……這個(gè)結(jié)論無疑是非常驚人的,因?yàn)樗嵏擦巳祟愑惺芬詠碜顬閺?qiáng)大的傳統(tǒng)之一。《達(dá)·芬奇密碼》走紅以后,人們很快發(fā)現(xiàn):這種顛覆絕非小說作者丹·布朗的獨(dú)創(chuàng)——它的主題早在上世紀(jì)80年代的另一部暢銷書《圣血與圣杯》已經(jīng)面世,并且同樣引起了巨大的爭議與反響。
其實(shí),歐洲人對(duì)天主教會(huì)歷史的質(zhì)疑以及對(duì)基督信仰統(tǒng)緒的揣測(cè)從未間斷過,上述兩本小說的產(chǎn)生也正是基于古老相傳的各種傳說。然而到上世紀(jì)后期,圣杯傳說再度甚囂塵上、尤其是關(guān)于耶穌婚姻家庭的顛覆性設(shè)想借現(xiàn)代傳播手段之力傳遍世界,卻是與女性主義圣經(jīng)學(xué)術(shù)的成就密切相關(guān)的。1895至1898年,美國女權(quán)運(yùn)動(dòng)先驅(qū)之一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出版了《女性的圣經(jīng)》一書,對(duì)大量圣經(jīng)章節(jié)進(jìn)行女性中心的解讀,從此開女性主義圣經(jīng)研究之先河。1970年代以降,伴隨著西方女性主義運(yùn)動(dòng)第二次風(fēng)潮的來臨,女性主義圣經(jīng)研究蓬勃興起,其中最有影響力的作品就是當(dāng)今西方女性主義神學(xué)領(lǐng)軍人物伊麗莎白·舒斯勒·菲奧倫查的學(xué)術(shù)著作《以她為念》。
《以她為念》出版于1983年,與小說《圣血與圣杯》幾乎同時(shí)。不過,與后者不同的是,這是一本嚴(yán)肅、嚴(yán)謹(jǐn)?shù)膶W(xué)術(shù)著作。該書副題是《一種對(duì)基督教起源的女性主義重構(gòu)》,顧名思義,它的目的是從女性主義角度對(duì)基督教最初的歷史進(jìn)行重新解讀。所謂女性主義的角度在文本中的主要表現(xiàn)有二:一是關(guān)注一切與女性相關(guān)的內(nèi)容,二是暗含“(圣經(jīng))文本都是以男人的視角寫就、對(duì)女性存在一定程度偏見”的預(yù)設(shè)。當(dāng)然,學(xué)術(shù)著作不是小說,所有預(yù)設(shè)都必須經(jīng)由嚴(yán)密的論證。為此,伊麗莎白·舒斯勒·菲奧倫查通過比對(duì)、解讀大量的相關(guān)文獻(xiàn),從社會(huì)學(xué)、歷史學(xué)等方面對(duì)《圣經(jīng)》中與女性問題相關(guān)的章節(jié)進(jìn)行批判性解釋,從而試圖揭示出女性曾經(jīng)在基督教早期歷史中占據(jù)活躍而重要地位的歷史真相,以及《圣經(jīng)》(《新約》)作者們以各種手段隱瞞或歪曲這一真相的過程。相比于驚險(xiǎn)刺激、引人入勝的小說,滿篇文獻(xiàn)引注、各種概念術(shù)語的學(xué)術(shù)著作自然是枯燥的。然而,正因?yàn)槠鋰?yán)謹(jǐn)?shù)膶W(xué)術(shù)風(fēng)格,《以她為念》對(duì)基督教發(fā)軔時(shí)期女性形象的重塑具有根基性的意義——它將小說家們的大膽設(shè)想落到實(shí)處。更重要的是,它所關(guān)注的是基督教早期女性的群像,而非某一個(gè)有話題有看點(diǎn)、能夠引起當(dāng)代人娛樂興趣的人(如被影射為耶穌妻子的抹大拉的馬利亞)。嚴(yán)謹(jǐn)繁瑣的論證猶如利鑿,一點(diǎn)點(diǎn)撬開了那些蒙蔽在古老文字和人們思想上的塵垢,從兩千多年的歷史深處,透出了女性智慧與功績的奪目光芒。
在這些女性當(dāng)中,讓人印象尤為深刻的是曾經(jīng)拯救了以色列民族的朱迪斯。據(jù)《朱迪斯書》記載,朱迪斯是一位美麗而富有的以色列寡婦。當(dāng)敵國巴比倫王的手下大將敖羅菲乃率大軍壓境、以色列的男人們束手無策之際,朱迪斯挺身而出,憑借非凡的勇氣、巧妙的智謀和出眾的美貌色誘敖羅菲乃,最終成功解救出自己的族人。凱旋歸來的朱迪斯受到族人們的盛大歡迎,功成名就之后,她拒絕了無數(shù)的求婚者,獨(dú)身生活到百歲高齡后方才離世,身后事也極盡哀榮。根據(jù)伊麗莎白·菲奧倫查的分析,《朱迪斯書》大約作于公元前一世紀(jì),在敘事和主題上都有意模仿《出埃及記》。這表明在原作者心目中,朱迪斯的功業(yè)甚至堪比摩西率領(lǐng)以色列出埃及。這個(gè)故事流傳頗為廣泛,后來的“七十子譯本”以及天主教和東正教的正統(tǒng)基督教《舊約》版本都包含有這個(gè)故事,可是偏偏猶太教從未將之接受為正典。究其原因,無非是正典編撰者們(自然是男性)認(rèn)為朱迪斯以美色誘敵,與英雄行徑相去甚遠(yuǎn),因而難登大雅之堂。同時(shí),也有很多學(xué)者質(zhì)疑朱迪斯故事的歷史真實(shí)性,甚至認(rèn)為它只是以色列最早的一部小說。然而在現(xiàn)代女性主義者眼中,朱迪斯的色誘成功恰恰證明了男性的缺陷和女性的智慧,而對(duì)其歷史真實(shí)性的懷疑更是男性中心主義抹殺女性在歷史中的存在與作用的表現(xiàn)。我們可以設(shè)想,在以對(duì)耶和華上帝的信仰為基本歷史邏輯的古代以色列,這樣一個(gè)故事即使不是完全真實(shí)地發(fā)生過,也一定有其歷史依據(jù)或原型。而這樣的一位女性,只要她在歷史中存在過,她的光芒就是不可遮蔽的,所有讀到她的故事的人,有誰不會(huì)為她的聰明、勇敢、美麗、堅(jiān)定以及她對(duì)祖國的愛所折服呢?她不是女扮男裝的花木蘭,也不是徒然指責(zé)“寧無一人是男兒”的深宮婦人。與中國歷史上被嵌入典型的男性中心主義話語的女性形象相比,朱迪斯閃耀著完美的女性光彩,并且用這種光彩戰(zhàn)勝了最強(qiáng)大的男人。
然而朱迪斯的例子只是伊麗莎白·菲奧倫查用來證明作為基督教誕生語境的猶太教具有男性中心主義偏見。與之相比,《圣經(jīng)》中另一個(gè)女人被忽視的命運(yùn)更加令作者憤慨不已,這就是《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和《約翰福音》都提到的一個(gè)“用香膏膏耶穌”的女人。在《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中,這個(gè)故事都發(fā)生在“最后的晚餐”前夕,猶大出賣耶穌之前。耶穌和眾門徒出席宴會(huì)時(shí),一個(gè)無名的女人進(jìn)來,把一瓶極珍貴的香膏澆在耶穌頭上。門徒們立刻站上道德高地、指責(zé)那女人浪費(fèi)錢財(cái),不如用它周濟(jì)窮人,但耶穌制止了他們,并且當(dāng)眾肯定了女人這一行為的重要價(jià)值:她是“為我安葬作的。我實(shí)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論在什么地方傳這福音,也要述說這女人所行的,作個(gè)紀(jì)念。”據(jù)福音書記載,耶穌親口如此贊許并設(shè)立為紀(jì)念的行為,這是唯一的一次。這是因?yàn)椋讵q太教傳統(tǒng)中,用膏油澆頭通常是先知確立以色列王權(quán)的一種神圣儀式。《圣經(jīng)·撒母耳記上》就記載了以色列先知兼領(lǐng)袖撒母耳將膏油倒在掃羅頭上,立他為以色列王的儀式(撒上10:1)。后來他又以同樣的儀式膏立大衛(wèi)為王(撒上16:13)。因此,這個(gè)女人其實(shí)是第一位確認(rèn)耶穌神圣地位的門徒。相比于在“最后的晚餐”之夜背叛主的猶大以及三次不認(rèn)主的彼得,這個(gè)無名女人的行為更顯得彌足珍貴、無比重要。然而可惜的是,正如經(jīng)文中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的那樣,以彼得為首的圍繞在耶穌身邊的男性使徒們完全不理解這女人的行為,他們對(duì)她的指責(zé)透露出強(qiáng)烈的男性中心主義的傲慢與偏見。因此可想而知,他們不會(huì)真正地看重和執(zhí)行耶穌親口為她設(shè)立的紀(jì)念。相反,正如伊麗莎白·菲奧倫查所指出的那樣,在耶穌受難后,負(fù)責(zé)編撰福音書的男性使徒們有意無意地淡化和抹殺了這個(gè)膏立耶穌的女性門徒的地位,以至于到今天,三次不認(rèn)主的彼得成為教會(huì)的磐石,人們提到“最后的晚餐”時(shí)想到的反倒是那個(gè)罪人猶大,而主耶穌要求紀(jì)念的女人卻被歷史遺忘了。
時(shí)至今日,伴隨著《達(dá)·芬奇密碼》的流行,人們總算記住了《圣經(jīng)》中一個(gè)女人的名字,可她不是這個(gè)膏立耶穌的女人,而是抹大拉的馬利亞。但是,人們記住她不是因?yàn)閯e的,而是因?yàn)樾≌f明確地將她的身份確定為耶穌的妻子、即傳承耶穌王室血脈的工具、真正的圣杯。很顯然,這種定位遵循的仍然是典型的男性中心主義原則:女性的尊榮完全來自于她與男性的關(guān)系。當(dāng)然,小說家的想象未必全然沒有依據(jù),因?yàn)閺母R魰鴣砜矗ù罄鸟R利亞的地位的確非常重要和特殊:她是耶穌受難時(shí)的見證人,名列眾女性門徒之首,又是耶穌復(fù)活的第一見證人。復(fù)活后的耶穌先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xiàn),并且命她向眾使徒傳達(dá)福音。由此可以推斷,她的確是耶穌身邊最重要、最親近的追隨者之一。但是,沒有任何證據(jù)表明她與耶穌有夫妻關(guān)系。在見證受難和復(fù)活時(shí),她也不是單獨(dú)出現(xiàn)的,而是作為女性門徒的首領(lǐng),在男性門徒紛紛避難的生死關(guān)頭仍然追隨在耶穌身邊,為他料理后事。可以想見,如果這位抹大拉的馬利亞確有其人,她必定在耶穌的傳教過程中貢獻(xiàn)良多,并占有重要地位。福音書的編撰者們沒有記載她的其他事功,但也無法從那驚人的歷史事件中徹底抹去她的名字。事實(shí)上,在未被列入正典的基督教早期文獻(xiàn)中有一部《馬利亞福音》,相傳即為抹大拉的馬利亞所作。這部福音書除了記載耶穌生平言行及教導(dǎo)之外,也反映出了馬利亞與彼得之間的尖銳矛盾,而這一矛盾的實(shí)質(zhì)就是男性門徒基于男性中心主義的偏見而否定,乃至嫉恨女性門徒之權(quán)威和功業(yè)。在小說中,這一矛盾披上了一層男性中心主義話語的外衣,并且被衍化為一場長達(dá)兩千年的迫害與陰謀,變成了當(dāng)代人的娛樂盛宴。
然而,對(duì)于我們而言,基督教世界對(duì)“圣經(jīng)中的女性”這一話題的探索絕不僅僅是一場有噱頭的娛樂。它巨大的勇氣和深刻的批判應(yīng)該帶給我們反躬自省的覺悟,讓我們把目光轉(zhuǎn)向自己的傳統(tǒng),去正視我們的歷史中那積壓在萬千女性身上的厚重而令人窒息的塵埃,并嘗試用批判的武器挖開這些塵埃,讓女性燦爛的智慧重新閃耀在文明的巔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