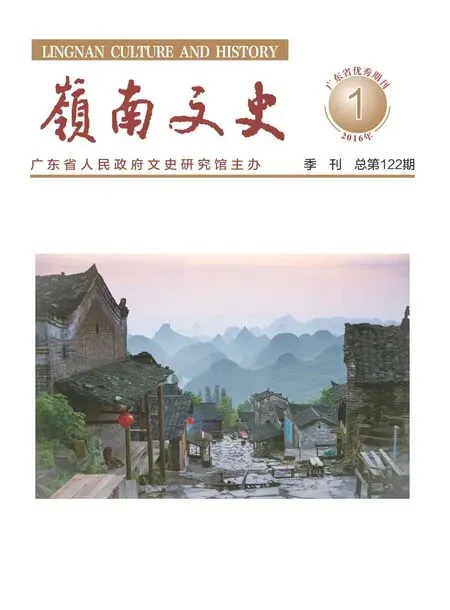本地域名稱沿革主線探析
韓 強
?
本地域名稱沿革主線探析
韓 強
一、四個概念辨析
地域文化主概念的確定是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任務。主概念的基礎在于地域名稱的沿革及其文化積淀。
(一)地域
文化學框架中的地域,并非指各時代的行政區劃,而是指稱國家之下的文化空間分布。它包含了漢文化的空間劃分和各大少數民族文化如藏族文化、維吾爾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等的空間劃分。中華漢文化版圖中歷史生命力最強的是原創性的、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大區分布。秦晉文化、燕趙文化、齊魯文化、楚文化、吳越文化、閩越文化、滇越文化、巴蜀文化、嶺海(嶺南)文化等,它們都是于春秋戰國始逐步成型的地域文化,共同構成華夏傳統地域文化版圖,其各自的文化傳統延續至今仍清晰可辨,既具有歷史的悠久性,又具有文化的延續性和穩定性。以后各時代不管行政區如何分割,各省(區)文史學者都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依此追溯自己的文化之根,將自身歸入某個文化大區中。廣東、廣西、港澳、海南的根都在于嶺南或嶺海文化,這基本上已成共識。
本地域文化研究首先要確定地域的最寬范圍。現學界普遍認同本地域陸地的最寬范圍包括廣東、港澳、海南(含南海諸島)、廣西大部分地區和越南紅河三角洲一帶及以北地區。[1]以南宋隆興二年(1164)朝廷封交阯郡王為安南國王為標志,越南部分劃出,本地域的陸地最寬范圍則包含今中國境內廣東、廣西(大部分地區)、海南三省(自治區亦省建制)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約略可簡稱“三省兩區”。嶺海名稱在完整領土意義上包含了海上國土南海,范圍最廣,是一個疆域范圍的概念;在指稱陸地時也包含南海,歷史上多以北倚五嶺南瀕南海,或依山帶海等描述之。筆者傾向于采用嶺海這一名稱指稱最寬范圍。
(二)名稱
嶺海地域從整個歷史來看產生過眾多的名稱。從文化學的角度探討,地域名稱包括自然—人文名稱、種族性名稱、政制區劃名稱三類。前兩者統稱為人文名稱。
自然人文名稱以自然空間為表,人文為里的命名,是生態系統與地域內人們的歷史實踐結合的名稱。它分為五類:以地理位置名之的如南交、交阯、交阯部、交州、南裔、南徼;因海而名的如南海、南服;以氣候名之的如炎洲、炎方、與南海結合的炎海、與地理相聯的炎徼,與嶺合一的炎嶠;以嶺名之的如陸梁、領南、嶺南、嶺嶠、嶠嶺、嶠南、嶺表、嶺服、與地理方位結合的嶺外;嶺與海兼稱的嶺海。它們都在歷史中積淀了不同程度的人文意蘊。
種族性名稱是指以種族及其特征為主要內涵對該地域的指稱。包含民族、種族、族群、民系等大小不等的含義,但均帶有較濃重的種族印記,反映地域文化的種族屬性。從陶唐至趙佗所建南越國時期是以越、粵之種族名直接作為地域名稱,以后則進入以“廣”代粵(越)時期。[2]嶺海地域種族性名稱眾多,如揚越、楊越、揚粵、楊越、蠻越、百越、百粵、交州屬的東越和西甌、越裳、南越、南粵、大越、粵、廣州,廣南,兩廣。自然義涵與種族性含義結合的名稱有越嶺、粵海、越嶠等。
政制區劃名稱是史載歷代統治者對各行政區劃的命名,它們大多數是人文名稱。“必也正名乎”影響深遠,歷史上中央統治者命名行政大區很少是隨意的,一般都經過大臣和飽學之士的考證和斟酌,多選取嶺海地域積淀較深的人文名稱。但也有四次例外,即藩服、荊州、番州和南漢。這是主觀認定的名稱,反映統治者的政治、經濟、軍事需要和文化意識,簡稱為“純政治名稱”。本文所采三類名稱都是從歷史典籍中選取的,都可稱為典籍名稱。
(三)沿革
首先,地域名稱沿革,即以地域為基點進行完整的名稱梳理,政制區劃和地域范圍是兩個主要參照。政制區劃名稱方面,一般史書以此為沿革主要依據,有些稱之為建置沿革。本文不用建置概念,因為先秦時代本地域對于華夏各帝只是隸屬或納入疆域,歸入其九服、九州政制框架中,也有沒歸入的情況,大多數時期并未在本地域設置直接管轄的政權機構,即沒有行政建置。如稱南交、揚越等就是這種情況。秦后各朝代建置名稱又有不少小于本地域最寬范圍。以政制區劃名稱,特別是以嚴格的建置概念,難以呈現完整的本地域名稱沿革。如漢武帝在本地域范圍置獨立行使行政職能的九郡,設交阯部統一監察,此期宜用“交阯部”作為地域名稱。所以,“政制區劃名稱”概念具有較大的包容性。
地域范圍上,應盡量采用較為恰當地指稱本地域空間范圍的名稱,這就需要比較歷史上空間盈縮不一的名稱,以確立各個名稱的涵義,盡量不采用范圍過大或過小的名稱。本文以秦統一中國時成型(秦三郡)、南越國時定型的本地域最寬范圍為參照選取名稱。但歷史情況十分復雜,大于和小于這一最寬范圍的時期都會出現統治者沒有對本地域進行政制區劃命名;或政制區劃名稱大于或小于本地域最寬范圍的情況。這樣,作為整個地域名稱沿革在歷史上就會出現空白。本文這樣處理:(1)先秦時代名稱所指地域一般大于上述最寬范圍,因而其名稱的意義是指本地域之所屬,另加說明。(2)小于此范圍的名稱一般不入沿革。(3)南宋時朝廷封交阯郡王為安南國王,雖明永樂五年(1407)以其地置交阯省,但時間短暫,宣德二年(1427)又復獨立建國,[3]此后我國大多數典籍都稱之為安南而非中國地域。因而宋代后本地域范圍多用“兩廣”這一典籍名稱相指稱,約略相當于現今“三省兩區”。
其次,沿革的一個重要標準是完整,主要歷史時期不能遺漏。梳理完整的沿革要求將政制區劃名稱、人文名稱與典籍補白三者進行綜合運用。地域名稱中,政制區劃名稱起主導作用,人文名稱則是主流。嶺海地域政制區劃名稱有兩種:一種是統治者在當時社會文化環境中,結合前朝命名并根據文獻典籍的命名,反映其對地域文化某些特征的確認。這種綜合作用使政制區劃名稱包含著許多重要的種族性名稱和自然-人文名稱,并且以這兩類人文名稱為主流。另一種則是統治者主觀認定的四個純政治名稱。所以政制區劃名稱包括三類:種族性名稱、自然-人文名稱、純政治名稱。政制區劃名稱依歷史順序排列已基本構成地域名稱的沿革,以后文獻典籍多采用之,其主導作用是歷史事實。
地域名稱沿革還應包含“典籍補白”一類。政制區劃沿革在本地域歷史上時有中斷,不能構成完整的線索。這是因為本地域最寬范圍與政制區劃所轄范圍常不吻合,在上述政制區劃名稱大于或小于本地域最寬范圍時,史載便沒有當時統治者對本地域的政制區劃名稱。對政制區劃的空白,本文根據文獻典籍所記載的本地域名稱即人文名稱予以填補,以還本地域名稱一個完整系列。所有地域名稱都曾列入過典籍,都可稱為“典籍名稱”,典籍名稱表征整體,典籍補白則只在政制區劃名稱空白時作為本地域名稱完整沿革的補白。
(四)主線
地域名稱沿革還有個主線與輔線的關系處理問題。任何時代除政制區劃名稱外,還存在眾多典籍名稱,主線的梳理須舍棄許多名稱,選取最重要的。種族性名稱和自然-人文名稱的絕大部分未入政制區劃名稱中,即當朝統治者對其并未認同和確認,或在多種名稱中并未選擇它們而是選取了文獻典籍中積淀深厚,運用較多,更加符合統治者意志的那一個。典籍補白也不可能將歷史上存在的所有相關典籍名稱都列入,而只能選取其中文化內涵更豐富,最典型地反映時代特征的那一個,并且它在典籍中被廣泛采用,延續時間較長。否則枝蔓橫生,地域名稱沿革的主線就無法清晰顯現,不利于從中發現地域主概念的變遷規律。但它們仍然屬于本地域名稱沿革的范疇,作為輔線共同反映著本地域的自然環境特征和歷史文化內涵。如在“專言嶺”的一組名稱中,本文只選取嶺南和嶺海之名納入主線,嶺嶠、嶠嶺、嶠南、領南、嶺外、嶺表等只是輔線,為使主線清晰,輔線各名稱均不納入。這樣的處理,根據主要在于上述人文名稱文化涵義的厚薄。
二、本地域名稱沿革主線
根據以上原則和方法,筆者嘗試梳理本地域名稱沿革主線如下:
(1)交阯。顓頊帝時稱交阯,為本地域最早名稱。屈大均認可“交趾自高陽時已砥屬”,《史記·五帝本紀》曰:“帝顓頊高陽者……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2)南交。堯帝時稱南交,以《墨子·節用篇》、《韓非子·十過篇》所云“帝堯之地,南至交趾”,故稱南交。《尚書·堯典》亦曰:“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
(3)南交。“舜帝 南交 按:《舜典》:‘肇十有二州。’揚州如舊。”[4]以上三時期本地域在政制區劃上均屬揚州南境。
(4)南海。“禹 南海 按:《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又:‘淮、海惟揚州。’海,南海也。”[5]其時淮地和南海地都屬揚州,南海為今東海與南海合稱,直至周末。
(5)揚越。夏朝時本地域屬揚州。《五經正義》曰:“夏禹九州本屬楊州,故云楊越。”但屈大均認為“揚越”指本地域:“故越號揚越,謂揚州之末土,揚之越也。”[6]
(6)南越。商湯時稱南越,對原揚越地域中所含“百越”已有進一步細分。“商 湯 南越 始定南越獻令。”[7]
(7)南海。周武王時稱。“然史稱周武王巡狩,陳詩南海,又詩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則舉南海,又可以概粵矣。”[8]“武王十有三年 南海 按:《通歷》:‘王既滅殷,乃正九服。’徹法:以南海地在東南揚州之裔,定為藩服。”[9]藩服為純政治名稱。
(8)東越和甌。周成王時對本地域的分稱。“成王十有四年 東越 按:《汲冢周書》云:成王定四方貢獻:東越蚌蛤、甌人蟬蛇。”注云:“東越、甌人皆交州屬。”[10]
(9)揚粵。周彝王時稱揚粵有彝王八年“楚熊伐揚粵時事楚,有楚庭”[11]之事為證。后世以“百粵”、“南粵”、“兩粵”約略指稱本地域,以“粵”專稱廣東,從史載看均溯源于此。
(10)南海。周宣王時稱南海。宣王二年王命召公虎平淮南,“于疆于理,至于南海”。[12]
(11)南海。春秋時仍沿此稱。“惠王六年南海 楚成王惲即位,布德施惠,使人獻于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彝越之亂,毋侵中國。’于是楚地千里,南海臣服焉。”[13]
(12)百越(百粵)。戰國時期政制上一般將越族之地概稱為百越或百粵。
(13)南服。戰國楚威王起稱南服。“楚威王滅越,兼有南服,楚庭之名遂以傳焉。”[14]此記載顯示當時本地域在大的范圍上屬百越地,典籍具體指稱為南服,約略同于最寬范圍。
(14)陸梁。秦始皇時本地域分為三郡,無統一政制區劃名稱,典籍補白有陸梁、楊越、秦三郡,《史記·秦始皇本紀》曰:“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陸梁為主稱。
(15)南越(南粵)。秦末至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本地域稱為南越。高祖元年(前206)趙佗據南海郡,擊并桂林郡和象郡,建立南越國,自立為“南越武王”并曾短時間內自稱“南越武帝”。在《報文帝書》中趙佗又自述為“南粵王”。南越作為地名,前史記載之地域范圍寬窄不一,地界模糊,其明確指稱本地域最寬范圍乃定型于南越國時。
(16)交阯部。漢武帝元鼎六年平息南越叛亂,在本地域置九郡,設交阯部刺史統一監察,至獻帝都為刺史監察的郡治而非管轄意義上明確的州建制,但已是中華明確的地域即國家下一層次的政制區劃名稱(十三刺史部)。后世典籍以交阯部為本地域名稱。此前所稱交阯,地域模糊且廣大,并未明確,此階段才確指本地域最寬范圍。
(17)荊州或交阯。漢末本地域曾屬荊州,亦稱荊州地。“十有八年 荊州 時復禹貢九州,故并廣屬荊。然是時廣州實為孫權所據。 南海郡。”[15]此為漢末行政區劃的短暫調整,屬統治者主觀認定的純政治名稱。但典籍中仍主要稱為交阯,以確指本地域最寬范圍。
(18)交州。交阯部正式列入州建制而改稱,明確的史載是漢獻帝建安八年(203)改交阯刺史部為交州刺史部,轄境相當今廣東、廣西大部和越南承天以北。交州歷14任刺史,其中有稱為廣州的時期,至隋初“交”稱、“廣”稱交錯;稱為交廣期后文補充說明。
(19)廣州。建安“二十二年(217)交州刺史步騭遷州治于番禺(今廣州)。”[16]交州改稱為廣州,管轄的地域范圍與交阯部相同,即嶺海最寬范圍。
(20)交州。223年又復稱交州。“后主建興元年、吳黃武二年(223)交州 吳復置交州。”[17]
(21)交廣。次年交、廣分置,本地域范圍一分為二,至隋初典籍均稱交廣,為兩州之合稱。“建興二年、吳黃武三年 廣州 因呂岱言交阯治遠,乃分合浦以北為廣州,交阯以南為交州。”[18]另有一說:“三國吳黃武五年(226)提出交廣分治,一年后復合。”[19]
(22)交廣。魏晉之交,吳元興元年(264)分交、廣兩州后未再合一。此時離晉武帝泰始元年(265)僅一年。晉沿襲吳國區劃,未見另外命名。“晉 成帝咸和元年(326) 廣州。”[20]
(23)交廣。南朝宋以后,仍是交廣兩分,但交州不斷縮小。其南界移至今越南廣平省界,東界移至今廣西南流江口。齊襲宋制。因廣州地域大,典籍常用廣州約略指稱本地域。
(24)交廣。南朝梁時廣州又有分置。“武帝天監五年廣州分廣州置桂州,即今廣西桂林府也。廣分東西,實始于此。”[21]陳襲梁制。典籍稱本地域為交廣。
(25)交廣。隋開皇年間襲陳制,至隋文帝仁壽元年(601)改為番州為止,交廣期結束。
(26)番州。601年,隋文帝因避太子晉王廣諱始改廣州為番州,至隋亡均未變。
(27)嶺南。唐代從唐太宗到懿宗前期以嶺南為政制區劃名稱。嶺南政區范圍約當今廣東(含海南)、廣西大部和越南北部地區,治所均在廣州。
(28)嶺南、嶺海。懿宗咸通三年(862)始分嶺南政區為嶺南東道和嶺南西道,初具后來兩廣的大致格局。典籍簡稱嶺東和嶺西。因嶺南政區劃分為東西兩道,本地域無統一名稱,唐代典籍中開始稱本地域為“嶺海”,同時嶺南也成為典籍補白名稱,已非政制區劃名稱。
(30)廣南、兩廣。宋太祖開寶五年(972)本地域置廣南路。宋太宗晚年將廣南分為東西兩路,典籍稱為兩廣。南宋隆興二年(1164)封安南國王始,越南部分劃出本地域。
(31)兩廣。元代沿襲宋代名稱,但分稱為廣東道和廣西道,典籍合稱為兩廣。
(32)嶺海、兩廣和官職名“兩廣總督”。均為明代時本地域名稱,非官方政制區劃名稱。
嶺海是典籍補白名稱。“太祖洪武元年(1368)廣東省置行省參政及嶺南道、嶺西道、嶺東道、海北道、海南道,省會屬嶺南道。”[22]以嶺名之三道,以海名之兩道,典籍合稱嶺海,或單指廣東,或與兩廣并行指稱本地域,作為無統一政制區劃名稱的一種補充。
兩廣。因明代依前朝分廣東廣西,本地域無統一名稱,典籍合稱兩廣。
兩廣之稱獲得政制上的權威性起于設置職官“兩廣總督”。明代宗景泰三年(1452)“以兩廣宜協濟應援”為由設兩廣總督。初為因事暫設,非正式官名,后來逐漸成為封疆大吏,政制上節制所有地方文武官吏。[23]職官制是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就獲得了典籍和政治名稱的雙重性質。此期兩廣之稱結束了宋末至元本地域完全沒有官方統一名稱的歷史。
(33)兩廣。清代分置廣東、廣西,府縣皆因明代舊制。沿襲明“兩廣總督”之職設。
(34)兩廣。中華民國仍分廣東和廣西。
(35)兩廣。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廣東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
三、幾點補充說明
(1)以上地域名稱沿革主線中,對選取各歷史時期地域名稱的根據,因篇幅所限本文只列出其主要的典籍依據,更多論證請參閱拙著:《嶺海文化:海洋文化視野與“嶺南”文化的重新定位》(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上篇“地域名稱與文化主概念考辨”。所列自然-人文名稱、種族性名稱的詳細考辨亦見此篇。
(2)上列35條中分為三類:其一,藩服、荊州、番州和南漢四個是純政治名稱。其二,典籍補白有南越國之前的各名稱;宋太宗晚年將廣南路分為東西兩路后本地域沒有統一的政權建置,典籍稱為兩廣;此外唐懿宗時分本地域政區為嶺南東道和嶺南西道,唐代典籍或稱嶺南,或稱嶺海。這些典籍補白填補了本地域名稱完整沿革的空白。其三,上兩類外的名稱是以自然-人文名稱和種族性名稱這兩類人文名稱命名的政制區劃名稱。上文所列兩類人文名稱未入主線的均為輔線名稱。
(3)交廣期問題。漢末本地域名稱進入交廣期,至隋朝結束。此期中央政權頻繁更迭,政制區劃名稱十分復雜,文獻典籍以“交廣”主稱本地域。地方史志有《交廣春秋》(又名《交廣二州春秋》)一書,學術論斷上有屈大均《廣東新語》中之“晉之交廣”說。交廣并非政制區劃名稱,而是典籍中學者史家對交州和廣州之稱復雜交錯情況的一種概略稱謂。交州或廣州則是政制區劃名稱。這種復雜情況以本地域最寬范圍為標準分為三種:一是時稱廣州,時稱交州,這種情況下廣州或交州均轄本地域,為本地域政制區劃名稱;二是這一地域內分置為交、廣兩個州,各為小區域之稱,非本地域名稱;三是分置與合一又交錯發生,合一的時候又或稱廣州,或稱交州。這一時期以“交廣”之典籍統稱來延續本地域沿革較為合適,是古代學者在政制名稱混雜期的一種具有文化智慧的統稱,屈論“晉之交廣”不能涵蓋這整個時期。屈大均“晉之交廣”說法,可能受晉時王范《交廣春秋》一書問世之影響概略述之,并非嚴格的史學稱謂。按朝代劃分,隋文帝開皇九年才進入隋朝,廣州之稱在隋朝只有12年,[24]按概略的說法交廣期劃至晉也勉強說得過去,但嚴格來說應將隋初包括在內,交廣期應是結束于隋朝開皇年間,準確地說是601年改廣州為番州。交廣期的起始我傾向于按明確史載為漢獻帝建安八年(203)改交阯刺史部為交州刺史部,開始進入以州制為準的“交廣期”。即此期起于203年,終于隋文帝仁壽元年(601),長達將近400年。所以將屈論改為“漢隋之交廣”或更準確。王范所撰《交廣春秋》又名《交廣二州春秋》和《十三州記》,交廣、十三州之稱將本地域看成一個整體,十三州記之名更將本地域納入中國政制的13個州之一,使“交廣”之稱成為權威的本地域名稱。
(4)本課題的意義首先在于填補空白。雖然本地域地名變化很多,其中的地域名稱在歷史記載中也很豐富,但地域名稱和文化概念的梳理卻很缺乏,至今無一部著作對地域名稱和文化概念進行過完整的梳理。很多史籍有建置沿革,但都是以政制區劃為準來排列的,這樣勢必出現沿革的斷裂。仇巨川在《羊城古抄》卷四中做過廣州的沿革梳理,包含不少人文名稱,是本地域所有典籍中最為詳細的;但因局限于廣州這一只在短暫時期指稱本地域,而多數時期僅用于指稱小區域的名稱,并非本地域名稱和文化概念的梳理。由于缺乏地域文化名稱的完整梳理,地域文化主概念的確定便缺乏基礎,文史學家們一般采取兩條路徑:一是根據歷史典籍和約定俗成原則選取人文名稱,如種族性名稱的《南越志》、《粵大記》、《百越先賢志》等,自然-人文名稱的《嶺南風物志》、《嶺表錄異》、《嶺外代答》、《嶺海名勝志》、《嶺海見聞》等。二是以政制區劃為命名方式。如《交州記》、《交廣春秋》等。屈大均編撰《廣東文集》,在命名文集所括地域時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為此整理過不少本地域名稱或文化概念,并進行了一些分類,還是無法找出合適的地域文化主概念,于是采取最簡單的,即用當時的政制區劃名稱的辦法:“凡為書必明乎書法,生乎唐,則書嶺南,生乎宋,則書廣南東路,生乎昭代,則必書曰廣東,此著述之體也。以尊祖宗之制,以正一代之名,而合乎國史,其道端在乎是。”[25]本文梳理地域名稱沿革主線,優先選取政制區劃名稱,空白處則用人文名稱做典籍補白。這樣一種對沿革完整系列的梳理雖屬首次,但卻反映歷史的真實存在,是歸納吸收歷史上地域文化研究之智慧的有益嘗試。其次,梳理地域名稱沿革主線的目的是挖掘其文化含義,發現文化發展的規律。只有完整梳理了地域名稱的沿革,才能從中篩選出具有較深文化積淀的名稱即地域文化概念,進而才能從眾多文化概念中選出文化含量最大,最能全面涵括地域文化內涵的那一個含金量最高的作為主概念,以統轄、概括和突出本地域的文化特色。這種文化學方法是客觀歷史過程的反映和抽象。本文作為初次嘗試,希望引起文化學界對此問題的重視和爭鳴,故斗膽拋磚引玉。
注釋:
[1]李權時、李明華、韓強主編:《嶺南文化(修訂本)》第一章,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以“廣”字代粵,含有種族根源和意蘊,以及先人對本根文化的執著。參看韓強:《嶺海地域的種族性名稱考辨》,《廣東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
[3][24]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縮印本),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版,第1001、2106頁。
[4][5][7][9][10][11][12][13][14][15][17][18][20][21][22]仇巨川纂,陳憲猷校注:《羊城古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302-303、303、303、303、303、303、303、569、306、306、306、307、308、312頁。引文空格遵原版。
[6][8][25]屈大均:《廣東新語》,見李默校點:《屈大均全集(四)》,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7、288頁。
[16][19]《嶺南文化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6年版,均見第28頁。
[23]《明史·職官二》。
(作者單位:廣東省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