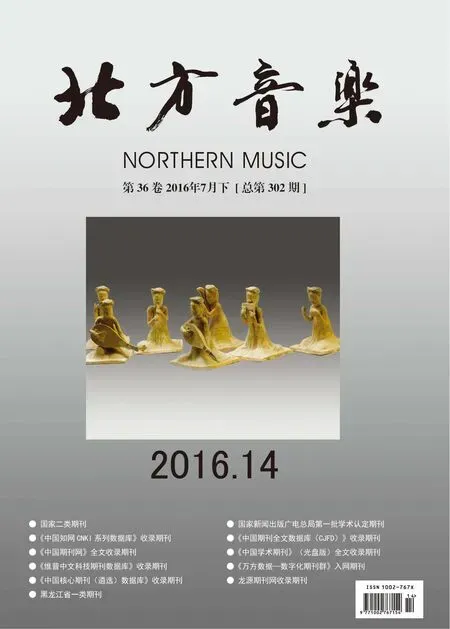論歌唱意境營造中的兩個(gè)主要因素
董永強(qiáng)
(呂梁學(xué)院,山西 呂梁 033000)
論歌唱意境營造中的兩個(gè)主要因素
董永強(qiáng)
(呂梁學(xué)院,山西 呂梁 033000)
歌唱藝術(shù)是表情的藝術(shù),但又不止于表情,因之產(chǎn)生于一定的歷史文化背景,打上了深深地時(shí)代烙印;具有強(qiáng)大藝術(shù)感染力的聲樂作品,除了對聽者情感的直接沖擊外,更多是一種沉靜之后的反思,審美的,社會(huì)的,文化的等等。而要達(dá)到這個(gè)效果,就需要綜合情感、風(fēng)格與時(shí)代精神等因素,共同營造出情景交融、曲味悠長的意境。
歌唱;意境;情感;風(fēng)格
意者,志也,意識(shí)、意念、意境等心態(tài)也。在歌唱藝術(shù)中,作曲家為演唱主體提供了譜面,但是,譜面只是該作品的基本特征的綜合體,在文本中存在著許多“潛在的”不定點(diǎn)或“空白”。有待于歌者去填補(bǔ)去實(shí)踐,即是“得意”的過程。
李漁《閑情偶寄·演習(xí)部·解明曲意》中也說:“口唱而心不唱……此所謂無情之曲”。“唱(奏) 曲”的前提是“心中有曲”。一個(gè)完整的聲樂作品的闡釋,首先是在歌者“心”中完成的。包括速度的快慢,力度的強(qiáng)弱,樂句之間的連接,樂段之間的對比,整體的情緒情感、風(fēng)格特征把握等等。對這些音樂語言的掌握過程就是意境的營造過程。本文擬就情緒情感和風(fēng)格與時(shí)代精神兩個(gè)主要因素在意境營造過程中的作用進(jìn)行探討。
一、情緒情感
“情緒:是指有機(jī)體受到生活環(huán)境的刺激時(shí),生物需要是否獲得滿足而產(chǎn)生的暫時(shí)的較劇烈的體驗(yàn)[1]”。
“情感是指人對客觀事物的態(tài)度體驗(yàn),是和人的社會(huì)性需要向聯(lián)系的一種復(fù)雜而又穩(wěn)定的態(tài)度體驗(yàn)[2]。”
從情緒情感兩者的定義我們不難看出:情緒體驗(yàn)是情感態(tài)度的基礎(chǔ)。在情緒體驗(yàn)的基礎(chǔ)上加入認(rèn)知性部分就是情感。但是,音樂的非語義性使其不能直接表達(dá)概念。因?yàn)橐魳繁磉_(dá)模擬對象具有極大的偶然性。它所引起的歌者和觀眾體驗(yàn)主要是情緒性體驗(yàn),這是音樂審美活動(dòng)的必然。當(dāng)這種情緒性體驗(yàn)持續(xù)刺激感官神經(jīng),形成相對穩(wěn)定、明確的體驗(yàn)時(shí),認(rèn)知性活動(dòng)就會(huì)滲入進(jìn)來,人們通常會(huì)由這種情緒聯(lián)想到自身生活中相似的場景、情緒,這就轉(zhuǎn)化為復(fù)雜的情感體驗(yàn)。
音樂是一門表情的藝術(shù),情感對音樂的重要性在古今文獻(xiàn)中不勝枚舉,二十世紀(jì)杰出的女高音歌唱家卡拉斯就說過:“首先,美聲是表情,而單有一個(gè)美麗的聲音是不夠的,你必須將你的聲音分碎成千塊,作曲家為你寫下了音符,而歌唱家必須把音樂和表情放進(jìn)這些音符[3]。”這,就是得意的過程。這也說明,歌唱技術(shù)固然重要,但終究是要為“表情”服務(wù),為意境的營造服務(wù)。
然而,音樂中情感的產(chǎn)生不是一蹴而就的,其經(jīng)歷了一個(gè)由情緒到情感的轉(zhuǎn)變過程。聲樂表演更是如此:聲樂是詩情、曲情,聲情的統(tǒng)一。旋律、伴奏呈現(xiàn)給我們的首先是一種情緒體驗(yàn),在加入具體指義性的歌詞的指引下,喚起了我們心中類似的情緒體驗(yàn)和觀念性聯(lián)想。從而轉(zhuǎn)化為情感。以舒伯特的藝術(shù)歌曲《鱒魚》為例,這首歌曲中有兩個(gè)形象,小鱒魚和垂釣者。小鱒魚無疑是主角,舒伯特模仿小鱒魚甩動(dòng)兩三下尾巴,然后輕柔的滑動(dòng)的動(dòng)作,創(chuàng)作出以小節(jié)前一半輕甩的十六分音符音型和后一半靜止的滑行這一節(jié)奏型。這一處理馬上會(huì)讓我們內(nèi)心產(chǎn)生一種活潑、愉悅的情緒體驗(yàn),隨著這一音型持續(xù)穩(wěn)定的刺激,激發(fā)了我們內(nèi)心深處類似的經(jīng)歷,混合著歌詞的概念性解讀,使我們的這種情緒性體驗(yàn)上升為對小鱒魚的“憐愛”,對垂釣者的輕微怨恨以及如旁觀者一樣的平和。把握了這幾種感情基調(diào),在演唱的過程中就能夠有效地營造歌曲所需的意境,把對樂段樂句的處理和作品中的角色緊密聯(lián)系起來,平衡詞、曲、情之間的關(guān)系,如此,一個(gè)栩栩如生的小鱒魚便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
二、音樂風(fēng)格與時(shí)代精神
音樂風(fēng)格是音樂藝術(shù)歷史發(fā)展中的階段。在長期的社會(huì)實(shí)踐和審美活動(dòng)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時(shí)代的人要求和主張著不同的聲樂表現(xiàn)形式和內(nèi)容,由此形成了不同語言、不同音階音調(diào)特點(diǎn)的聲樂藝術(shù)。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了帶有各自屬性的表演風(fēng)格和審美觀。對于此,音樂美學(xué)家漢斯立克曾有過精彩論述:
一切音樂作品是人創(chuàng)作的,是一定個(gè)性、一定時(shí)代、一定文化的產(chǎn)物,雖然各個(gè)時(shí)期照例都有對可惡的時(shí)代精神的咒罵,而衰亡過程并不因此而停頓下來,時(shí)代真可說是一種精神,………[4]。
漢斯立克的這段話對今天的我們同樣有借鑒意義。作為音樂表演主體,必須對作曲家所處的時(shí)代、內(nèi)心深處的思想意識(shí)、生活閱歷、民族特征等等做到客觀細(xì)致的分析把握。因?yàn)椋耙魳凡粌H是審美現(xiàn)象,而且也是社會(huì)事實(shí)。”
對于歌唱家來說,最重要的是個(gè)人的演唱風(fēng)格。一個(gè)歌唱家成熟的標(biāo)志,就是形成了自身獨(dú)特的演唱特性。在聲樂表演活動(dòng)中,對于同一部聲樂作品。同時(shí)代的不同歌唱家,甚至不同時(shí)代的不同歌唱家由于其個(gè)人出身、生活經(jīng)歷、文化教養(yǎng),思想感情的不同對作品的闡釋也大不一樣。
那波利民歌《我的太陽》,帕瓦羅蒂的表演激情四射,音色明亮通透,高音輝煌震撼,而吉利對這首作品的演繹則大不相同,他充分運(yùn)用自己的技術(shù)特點(diǎn),大量用半聲,音色變換層層推進(jìn),速度也做慢處理,使整首作品意蘊(yùn)深長,如春雨般滋潤審美客體,同樣讓觀眾蕩氣回腸。這除了二人的個(gè)性差異外,也反映了不同時(shí)代聲樂審美標(biāo)準(zhǔn)的變化,在每一個(gè)歷史階段,審美觀一經(jīng)形成,便相對穩(wěn)定下來,人的審美活動(dòng)也會(huì)潛移默化受到影響。但在社會(huì)歷史生活中,隨著時(shí)代的變遷以及經(jīng)濟(jì)因素、政治因素的改變,審美觀也有可能被不同的審美因素異化和重新建構(gòu)。五六十年代的歌唱家們技巧超群,但他們很少賣弄嗓子,對作品的處理既有整體性風(fēng)格的把握,又在細(xì)節(jié)處細(xì)微、精致。哪怕是戲劇性極強(qiáng)的威爾第的作品也聽不到聲嘶力竭的吼叫,他們更多時(shí)候是觀眾的朋友,是鄰家男孩(女孩),近代,隨著瓦格納、威爾第等作家作品要求蓋過龐大管弦樂隊(duì)的大音量,以及聲樂技術(shù)的退化,表演者在舞臺(tái)上似乎更加‘專制’,觀眾也只是務(wù)須多言的被動(dòng)聽賞。少了幾分親切、舒服,多了幾分感官刺激。
同樣,同一個(gè)歌唱家在詮釋不同歷史階段,不同作曲家的聲樂作品時(shí),也存在著一個(gè)風(fēng)格把握的問題,演唱十七世紀(jì)作曲家斯卡拉蒂的《紫羅蘭》和十九世紀(jì)藝術(shù)歌曲大師舒伯特的《菩提樹》是完全不一樣的,需要對聲音狀態(tài)、演唱心理、語義語勢甚至不同時(shí)代審美觀念進(jìn)行大幅度調(diào)整、把握。特別是語言,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發(fā)音部位,不同的美感,很多時(shí)候,演唱風(fēng)格的形成就是由于不同語言的發(fā)聲特點(diǎn)決定的,這也解釋了美聲歌唱在不同國家進(jìn)行傳播時(shí)為什么會(huì)形成那么多不同流派。
總之,歌唱藝術(shù)是一門表情的藝術(shù),但情感不是唯一,中間混合著經(jīng)過長期實(shí)踐而表現(xiàn)出來的個(gè)性、風(fēng)格和時(shí)代精神;怎么樣讓這些因素積極作用,互相契合,共同參與到歌唱意境的營造中,這是一門大學(xué)問,有待我們努力鉆研,積極實(shí)踐。
[1]朱智賢,主編.心理學(xué)大辭典[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89:503.
[2]朱智賢,主編.心理學(xué)大辭典[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89:498.
[3]馬克·蕭勒.冰山理論.對話與潛對話:上[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174.
[4]愛·漢斯力克.論音樂的美[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0:95.
[5]阿多爾若.美學(xué)理論.北京[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70:334.
董永強(qiáng)(1978-),男,甘肅天水人,碩士,呂梁學(xué)院藝術(shù)系助教,研究方向:音樂表演、教學(xué)與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