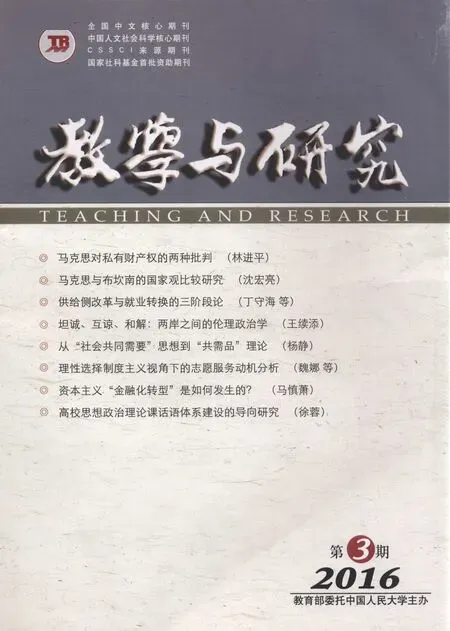馬克思對私有財產權的兩種批判
林進平
?
馬克思對私有財產權的兩種批判
林進平
馬克思;私有財產;批判;歷史唯物主義
馬克思對私有財產權的批判既有哲學批判,也有歷史唯物主義批判,前者主要存在于《德意志意識形態》之前,后者主要存在于《德意志意識形態》及之后,特別是《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它們共同揭示了私有財產權不是自然權利,而是基于市民社會的權利。以私有財產表現人性意味著人的關系的全面異化,私有財產權則是這種異化的法權確認,它無法兌現其人道主義承諾,在實質上它是有產者針對無產者的權利。在私有財產權問題上,馬克思的兩種批判并不存在截然的斷裂,后者是前者的進一步推進和具體化。馬克思對私有財產權的批判在總體上不屬于道德批判,但如果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批判排除了對私有財產權、人權理解的道德維度,也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誤解,特別是將其誤解為“歷史相對主義+經濟一元決定論”。
在洛克、邊沁等開創的自由主義傳統中,私有財產權與自由、平等堪稱自由主義人權的三位一體。[1](P362)其中,私有財產權更是穩居基礎地位,被視為自由主義人權的基石,以至有“沒有財產權就沒有正義”一說①參見哈耶克:《致命的自負》,馮克利等譯,第3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原英文為“W here there is no property there is no justice”其中的財產權主要指私有財產權。。然而,正是這種被視為古典自由主義正義基礎的私有財產權②Privateigentum(private property)在不同的語境中有不同的譯法,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一般譯為“私有財產”、“私有制”,偶爾也譯為“私人所有”或“私人所有權”。比如,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可能是為與“異化”相呼應,主要是譯為私有財產;在《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等文本中,則可能因為指向的主要是一種社會制度,譯為私有制相對多見。雖然在中譯本中,較少有譯為私有財產權的,但考慮到在馬克思的批判中,也有針對作為人權的“Privateigentum(private property)”,就譯為“私有財產權”,雖然這一譯法在實質上是與中譯本的“私人所有權”是一致的,但不采用“私人所有權”而采用“私人財產權”是考慮到與“私有財產”、“私有制”相呼應。在本文,私有財產與私有財產權都是指同一個語詞,不同的表述只是為了適應不同的語境。卻受到了馬克思一貫的犀利的批判,以至于羅爾斯、哈耶克和諾齊克等人不得不回應馬克思的批判③哈耶克:《致命的自負》,馮克利等譯,第25、54、56、10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羅伯特·諾齊克:《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何懷宏等譯,第25426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羅爾斯:《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姚大志譯,第289292頁,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正是基于馬克思對私有財產權批判的深刻與影響,本文試圖考察馬克思對私有財產權的兩種批判——哲學批判與歷史唯物主義批判,并就其批判所延伸出來的問題談點看法。
一、馬克思對私有財產權的哲學批判
馬克思對私有財產權的思考、批判較早可以追溯到《萊茵報》時期,在那段時期,馬克思因作為編輯之便有機會接觸到了關于貧民拾撿枯枝是否合法、貿易自由和保護關稅等大量的物質利益問題,這些問題給他產生了這樣的強烈印象:法律保護的是權貴階層的財產權,而弱勢群體的權利卻受不到法律的保護;本應體現理性、正義、人道的法,卻使弱勢群體沒有尊嚴、正義、人道可言;本應體現普遍利益、正義的國家捍衛的卻是特殊利益、私人利益。現實與理念的沖突困惑把馬克思帶向了對國家、法及其副本(即黑格爾法哲學)的質疑,并由此通向了對國家、法、法哲學的對立面——市民社會和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研究。這種質疑和批判性反思的早期成果就是《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及其導言、《論猶太人問題》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神圣家族》等系列作品,而馬克思對私有財產權的早期思考也表露在這一系列作品中。
1.私有財產權并不是一項自然權利,而是市民社會成員的權利。馬克思肯定了黑格爾關于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分離是現代社會的標志的思想,從黑格爾式的歷史觀出發,以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二元對立的分析框架取替并批判從思辨哲學出發的自然狀態與政治國家二元對立的分析框架,把自然法學者從自然狀態中推演的自然權利還原為市民社會的人的權利。在他的分析中,人并不是“生來”就自由、平等和擁有私有財產權的,而是“生在”市民社會之中才擁有自由、平等和私有財產權的,或者說,這些被認為是“自然”所賦予的人權,并不是“自然”所賦予的,而是基于市民社會才獲得的;相應地,人權的主體也不是“自然人”,而是“市民社會的成員”;[2](P40)且由于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和劃界,市民社會的成員也相應地成了“封閉于自身、封閉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為、脫離共同體的個體”,成了“利己主義”的人。[2](P42)既是如此,那人權就“無非是利己的人的權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體分離開來的人的權利”。“自由是可以做和可以從事任何不損害他人的事情的權利”,“是人作為孤立的、自我封閉的單子的自由”。平等則成了這種自由的平等,即“每個人都同樣被看成那種獨立自在的單子”。[2](P40)而私有財產就成了這種自由的具體運用,是“任意地、同他人無關地、不受社會影響地享用和處理自己的財產的權利;這一權利是自私自利的權利”。[2](P41)因此,人的權利就成了一種通過否定性的自由和平等來實現的人道追求,但這種人道追求卻因其是建立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上和以孤立的、封閉的利己主義的個人為出發點,最終使其追求成為幻影,成為一種現代神話。[2](P43)
2.私有財產是人的異化、生命的異化、勞動異化的結果。這一觀點充分地體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在這一手稿中,馬克思透過對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的分析,指出私有財產是異化勞動的結果,且就勞動的異化也意味著人的異化來說,私有財產也是人的異化的結果。[2](P166、168)這呼應了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已經指出的,私有財產的主體是孤立的、封閉的、利己主義的人,也即異化的人。論至此,馬克思是可以大書特書,指出私有財產的“原罪”根源,比如,可以模仿《舊約》中亞當、夏娃如何受誘違背上帝命令而踏上發現“自我”的原罪路徑來探討人是如何經由“未曾異化的人”而演化出人的異化、勞動的異化,并最終把私有財產界定為一種原罪——勞動的異化——的結果,或者可以像盧梭那樣,把私有財產的產生推演為人的一種不斷完善化能力的結果。但經歷了費爾巴哈宗教批判洗禮和對自然法持批判態度的馬克思不會采用這樣的一種路徑。[2](P5-6、112)他要做的是從私有財產的當下事實出發去剖析私有財產所關聯的一系列悖謬和從中可以看到的解決問題的出路。因而,在指出了私有財產是源于生命的異化、人的異化和異化勞動之后,他筆鋒一轉指出,“后來,這種關系就變成相互作用的關系”,“私有財產一方面是外化勞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是勞動借以外化的手段,是這一外化的實現”,[2](P155、166)繼續探討私有財產所關聯的問題,而沒有落入對人的異化、勞動的異化等的抽象思考之中。但盡管如此,指出私有財產和勞動的異化的內在關聯,從而循著私有財產直指人的本質的異化。這有助于透過私有財產問津人的解放的問題,因至少在亞當·斯密之前,“人們談到私有財產時,總以為是涉及人之外的東西。而人們談到勞動時,則認為是直接關系到人本身”。[2](P168)而借助斯密把勞動由人的外在行為詮釋為人的存在方式、人的本質,視為財富的唯一源泉,也揭開解決人的解放的路徑。[2](P60、178-179)既然私有財產隱匿著人的本質(異化的人的本質),那從批判這種建立在私有財產基礎之上的國民經濟學就能揭開人的解放的路徑。[2](P168)
3.既然私有財產意味著人的異化、生命的異化、勞動的異化,那人權所推崇和捍衛的是一種全面的異化關系。首先,私有財產權意味著對有產與無產的區別的漠視,意味著人與物的混同。因私有財產權的確立有一前提,就是把勞動視為人的內在生命的存在方式,并將其視為人人能夠擁有的私有財產,從而實現了人人皆有私有財產,私有財產權是人一項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利的理論預設和現代宣稱。但是,不論私有財產權的出場如何“神圣”,都掩埋不了私有財產權在另一維所隱含的對人的貶抑。對此,馬克思可以說是洞若觀火,他認為“私有財產的關系潛在地包含著作為勞動的私有財產的關系和作為資本的私有財產的關系,以及這兩種表現的相互關系”,并深信這種關系的充分展開,是“整個社會必然分化為兩個階級,即有產者階級和沒有財產的工人階級”,必定是“工人降低為商品,而且降低為最賤的商品”,并“把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本質變成僅僅維持自己生存的手段”。[2](P172、155、162)因扮演“一視同物”、“公平競爭”的市場會無視人與物、人與人的天然差別,無視市場天生就是資本的戰場,而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馳騁,放飛夢想的天堂。其次,在私有財產被尊崇為社會的基石、人的基本權利時,私有財產帶來的是人的關系的全面異化。私有財產盡管是異化勞動的產物,但它一旦產生就反過來成為異化勞動借以運作的手段。因而,在私有財產被尊崇為人的基本權利和確定為社會的“正義追求”時,異化勞動也帶來了人的關系的全面異化,不僅使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自己的生命相異化,而且使個人生活與類生活相異化;不僅使人與自然界的關系相異化,也使人與人的關系相異化。[2](P163)最后,由于私有財產(借助于異化勞動)僭越了人的本質,成為人的存在方式,私有財產也必然使人的其他生命活動擺脫不了異化的命運,因“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2](P186)既然作為“人的生命的物質的、感性的表現”的私有財產已經標示人的異化,那以私有財產為依托的一切生命活動方式——不論是精神生活,還是現實的物質生活——都不可避免地擺脫不了被異化的命運。[2](P186)
4.人類的出路在于從私有財產對人性的僭越與“普適性統治”中解放出來。既然人的異化源于勞動的異化或私有財產,那回歸合乎人性的存在方式,就必須從異化勞動或私有財產入手,但異化勞動既已被視為異化了人性,那從異化勞動入手去解決人性問題,就無異于同義反復。因而,有希望的方式也許就是從那種使異化勞動成為現實的私有財產入手。而這恰是馬克思的主張,早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就已指出“猶太人的社會解放就是社會從猶太精神中解放出來。”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更是強調要破除人的一切關系的異化與扭曲,回歸人性,就必須破除私有制及其對世界的感受與思維方式。在他看來,“私有制使我們變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個對象,只有當它為我們所擁有的時候,就是說,當它對我們來說作為資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們直接占有,被我們吃、喝、穿、住等等的時候,簡言之,在它被我們使用的時候,才是我們的。”[2](P189)私有財產也在培養我們形成扭曲的需要,[2](P223-224)私有制使我們無法開放我們的感官去自由地、美地感受世界。[2](P190)“因此,對私有財產的揚棄,是人的一切感覺和特性的徹底解放”。[2](P190)而這樣的一種解放狀態就是他筆下的共產主義,因“共產主義是對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復歸,是自覺實現并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范圍內實現的復歸。”[2](P185)當然,這種揚棄的歷史任務的只能是由無產階級來承擔,因無產階級不論是在外在財富還是內在的人性的豐富性上都給剝奪得一無所有,他們是私有財產權的受害者,他們最有理由起來宣稱:“我沒有任何地位,但我必須成為一切”。[2](P15)或者說無產階級起來擔當揚棄私有財產權的歷史任務只不過是把社會施加在他身上的“無產”的原則上升為社會的原則——廢除私有財產權,或者說,“無產階級作為無產階級,不得不消滅自身,因而也不得不消滅制約著它而使它成為無產階級的那個對立面——私有財產。”而且還因為無產者的解放包含著普遍的人的解放,因他蘊涵了整個人類的苦難與奴役。[2](P17、260、167)
私有財產的種種悖謬似乎在暗示著一個問題:一切都是私有財產的錯!資本主義的種種罪惡都可以算在私有財產的頭上。盧梭、蒲魯東和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就有過這種看法。但是,馬克思在這個問題上的深刻之處就在于他不是把私有財產視為人類的一件“原罪”,而是在看到私有財產所帶來的種種災難的同時,也像黑格爾那樣看到了私有財產所隱含的人的力量。因此,馬克思不是像蒲魯東那樣主張消滅私有財產,[2](P183、257-259)而是主張揚棄私有財產,實現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不是簡單地從道德上否棄私有財產,而是試圖揭示它在歷史上生滅的緣由和作用。這一點在歷史唯物主義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
二、馬克思對私有財產權的歷史唯物主義剖析
進入歷史唯物主義時期,馬克思依然批判私有財產權,但馬克思的批判已經主要不是哲學批判,而主要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剖析。這種剖析更為具體地揭示了私有財產權的歷史真相和諸多悖謬。
1.私有財產的存續不是人類歷史的永恒事實。對于自然法學者來說,私有財產稱得上是與人類歷史相伴隨的永恒事實,他們或是從人性出發,或是從生產出發論證私有財產對于人類的普適性與永恒性。但在馬克思看來,不論是從人性還是從生產來論證私有財產的普適性與永恒性都不可避免地以特定歷史境域中的“人性”或“生產”為依據,并抽象掉“人性”或“生產”所賴以存在的歷史條件或歷史境域,并進而將特定歷史境域中的“人性”或“生產”泛化為人類的一般生產。[3](P-6)但是,這樣的論證不僅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不可跨越的鴻溝——先驗論的預設一旦尋求歷史的經驗論論證,就注定在邏輯上是無法周延的,而且也有悖于歷史的真實。
歷史的真實是:私有財產的存續不是人類歷史的永恒事實。當然,我們可以說占有是人類的永恒事實,假如我們把一切生產都看作是“個人在一定社會形式中并借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對自然的占有”的話,人類的確一刻也離不開生產。但占有并不等于私有財產,[3](P11)更不等同于作為人權的私有財產權。正如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所說的,“占有,是一個事實,是無可解釋的事實,而不是權利。只是由于社會賦予實際占有以法律規定,實際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質,才具有私有財產的性質。”[4](P137)況且,私有財產要上升到作為人的權利的地位,更必須發展到勞動淪為商品的資本主義世界中才有可能,才會將私有財產尊奉為人的神圣的基本權利。
就占有(即生產)來看,它從來不是在虛空中進行,而是“在一定社會形式中并藉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占有。“實際的占有,從一開始就不是發生在對這些條件的想象的關系中,而是發生在對這些條件的能動的、現實的關系中,也就是這些條件實際上成為的主體活動的條件。”[3](P144)在資本主義之前的社會中,個人的占有必須在部落、部落聯盟、家庭等社會共同體中方能進行。[3](P123)“每一個單個的人,只有作為這個共同體的一個肢體,作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3](P124)至于私有財產也不是人類的永恒事實。私有財產意味著個人把他賴以占有的條件看作為自身的前提和存在方式,[3](P142)看作為個人的所有。但是,“在亞細亞的(至少是占優勢的)形式中,不存在個人所有,只有個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實際所有者;所以,財產只是作為公共的土地財產而存在。①特別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47349頁,人民出版社,2002年。只是共同體的解除,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有個人所有和私有財產,因此,試圖從人類的一般占有(即生產)離析出私有制觀念,不是試圖跨越一道不可跨越的鴻溝,就是在做概念游戲。[3](P132、121 136、11)
2.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是作為人權的私有財產權賴以存在的現實基礎。對于馬克思來說,揭示作為人權基礎的私有財產權并不是人類的永恒事實還不足以揭示其實質,而只是做到了一個否證,要做到揭示私有財產權的實質,還必須剖析出它的“出身”。
如我們所知,作為人權的私有財產權潛藏著這樣的邏輯:人的身體(或生命)及其能力(勞動)既是人的私有財產,也是其他私有財產的基礎。這一觀念如從邏輯來推演也可以這樣理解:作為人權的私有財產權如被視為具有普遍性,就意味著這個被視為“財產”的東西是人人都能夠擁有的。然而,一旦是人人都能夠擁有的,那這個“財產”就最好理解為是與生俱來的,理解為人的身體(或生命)及其能力(即勞動力)。因此,人的勞動在人權理論中被設定為私有財產權的出發點就可以說是邏輯的必然。[1](P349)
私有財產權的這一特定內涵為我們理解馬克思對私有財產權的“歷史出身”的揭示提供了方便。因為,馬克思正是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透過對生命和勞動力何以淪為個人的私有財產,為我們揭開了附著在私有財產權之上的普遍性面紗:私有財產權并不是人類社會的普遍觀念,而是歷史演進的結果,是商品化時代的觀念。馬克思把它概括為“一方面是封建社會形式解體的產物,另一方面是16世紀以來新興生產力的產物”。[3](P5)
首先,作為人權的私有財產權是封建社會形式解體的產物。“雇傭勞動的前提和資本的歷史條件之一,是自由勞動以及這種自由勞動同貨幣相交換,以便再生產貨幣并增殖其價值,也就是說,以便這種自由勞動不是作為用于享受的使用價值,而是作為用于獲取貨幣的使用價值,被貨幣所消耗;而另一個前提就是自由勞動同實現自由勞動的客觀條件相分離,即同勞動資料和勞動材料相分離。”[3](P122)馬克思在談到“勞動客觀條件與勞動本身的分離,資本的原始形成”時,又作了更為詳細的說明。[3](P154-155)
正是由于封建社會形式的解體,才使得勞動者擺脫了人身依附關系,使個人成了支配自己勞動的主人,成為了自己的所有者。
其次,作為人權的私有財產權是資本主義經濟時代的必然要求。對于這一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有著相當細致的論述①特別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47349頁,人民出版社,2002年。。馬克思的觀點主要是,商品所有者對其被用來交換的“商品”(如考慮它尚處于交換之前,也可以將其稱為產品)擁有所有權,而這一“商品”在沒有成為商品之前的原初占有只能是來自于勞動。因此,如果追溯商品的最初的所有權,就“必須承認自己的勞動是最初的占有過程”。這就是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們把勞動視為最初的私有財產權的依據。[1](P348、349)但是,勞動者如果不是生產勞動產品用于交換(即為商品交換而生產),而僅是為勞動而勞動,那很難說勞動者的勞動就是私有財產權的依據,或者說勞動者在生產某種他必須在其上宣稱具有所有權的產品。因為,勞動者只是生產了自己可以占有、使用的東西,而無關乎他者的承認與否。因此,關鍵在于,勞動者所進行的勞動并不是為生產而生產,而是為了商品交換而生產,即他生產的產品必須通過商品交換來獲得“社會承認”,并在交換時確認自己對被用來交換的產品擁有所有權。因此,勞動產品和勞動本身并不必然是私有財產,它可以只是表達一種占有的事實,只是在商品交換中才被確定或追認為勞動者的私有財產。這正如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所說的,某人圈了一片土地,最多只能表明他占有了該片土地,而當它獲得了“他人的承認”時,該片土地才成為他的私有財產一樣。[5](P111-112)
因此,使勞動產品成為私有財產的不在于勞動產品,而在于具有“社會承認”功能的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使勞動者的產品必須接受“社會承認”的裁判,從而使勞動產品失去其自在的價值。但是,勞動者的產品必須接受商品經濟這個“社會承認機制”的裁判,還不足以產生作為人權意義的私有財產權。只有商品經濟發展至極致,將一切都視為商品,則不論是勞動者的勞動,還是勞動者的生命本身都會被視為商品,都會失去其“自在的價值”,那時,一切都被視為商品,一切都必須接受貨幣的裁定。此時,“萬般皆商品,唯有貨幣高”。此時,任何商品都可等價于貨幣,都是資本,任何商品也都可回溯至人的勞動,生命與貨幣、勞動與資本都可以等價齊觀。人,不論其“有產”抑或“無產”,都有“資本”可以出賣的,都對這“可以出賣的”擁有所有權,都是“私有財產”者。
3.作為人權的私有財產權無法兌現其人道承諾。在馬克思看來,雖然附著在商品經濟之上的自由、平等和私有財產權等人權圖景給人們留下了一種讓人為之神往的外觀,但這種外觀在馬克思看來卻是“海市蜃樓”式的“現代神話”。這是因為,私有財產權似乎是體現了對人的本質和尊嚴的肯定與捍衛,但同時也是對人更為徹底的否定。
(1)在“貨幣=勞動”的等價關系中,潛藏著對人的價值的否定。在“貨幣=勞動”的等價關系中,勞動這種內在于人自身的價值需要借助貨幣這種萬能的等價物來為之界定,這本身已是對勞動自身價值的僭越。這正如在“上帝=理性”的等價關系中,我們所看到的不是上帝的偉大,而是理性對上帝的質疑與審視。假如在“上帝=理性”的等式之下,上帝已如尼采所說遭受了理性的質疑而死,那在“勞動=貨幣”的等式之下,我們將會見到的是人在貨幣這種萬能的等價物之前,同樣也已經死了。人,這種以自由自覺的創造性活動作為標識的存在,已經身不由己地為貨幣所支配。人在貨幣面前覺醒的同時,也“賣身”于貨幣。從理論上,在“勞動=貨幣”的這一等式中,人通過貨幣這一中介有可能支配貨幣所能夠支配的世界,在這意義上,人的世界明顯地被拓寬了,但是,這種可能也僅在于能夠支配貨幣的人才能夠做到,如果考慮到在馬克思的經濟學文本中,能夠支配貨幣者即為資本家的話,那世界也只是為資本家的存在而展開。而對于未能支配貨幣而只能為貨幣所支配的無產者來說,他們的生活世界并沒有因之而拓寬,相反,由于他們未能支配貨幣,貨幣有可能通達的多樣性世界對他們來說與其說是敞開著,不如說是封閉著。無法成為貨幣的主人的命運使他們只能封閉于自身的世界之中,封閉于個體生命之中。因此,在“貨幣=勞動”的極端情形之中,假如勞動者一無所有的話,那他就只有一種命運:為個體生命的生存而活著,作為貨幣的附屬物而活著。
但是,“淪為貨幣的奴隸”對于長袖善舞的資本家來說,也未能幸免。因為資本家在對貨幣的支配之中,雖然體驗了貨幣的“神通”,感受了貨幣的魔力與親切,但也身不由己地為貨幣支配,成為貨幣的追逐者。而在其追逐貨幣的過程中,競爭已在所難免,競爭又反過來加重了對貨幣的追逐。資本家就如同被帶入了一條難以掉頭的追逐貨幣的“高速路”之中,在這條路上,追逐資本增殖成為驅使資本家在這條路上狂奔的動力。因此,“貨幣的主人”并沒有成為真正貨幣的主人,而只是貨幣的表面上的主人,依然不是在操縱貨幣,而是為貨幣所操縱。資本家同樣是貨幣的奴隸。
也許,資本家與無產者的區別在于,貨幣所通達的可能世界對于無產者來說是封閉的,而對于資本家來說,卻是敞開著。如是而已。
在把人權立基于私有財產之上,而又把人的生存條件看作為私有財產之時,還隱藏著一個更為致命的邏輯:一旦認為人的一切都可以待價而沽時,人的一切就將臣服于貨幣,即貨幣將支配人所擁有的一切。這就意味著一切自許為有著自在價值的靈光的東西,都給削去了“頂上靈光”,都淪為或俗化為貨幣的附庸,美貌、良知、生命、信仰等一切據說有自在價值的東西,都成為可以估價、可以出賣的東西。
如是的話,被標榜為人道關懷的人權就在其深層處卻隱含著對人的踐踏,在其似乎離人最近的地方,卻又離人最遠。
(2)私有財產權在實質上是有產者的權利。既然私有財產權也意味著把自己的生產條件看作為屬于自己的東西,那私有財產權在無產者和有產者面前就展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前景。
從私有財產權觀念來看,在簡單商品交換中,商品所有者的所有都得到了法律的確認,而在資本購買勞動力的商品經濟中,作為無產者和有產者都同樣能夠享有私有財產權,至少是自己生命的主權者和生命活動能力的主權者。但這些對于馬克思來說,都僅僅是表象。
首先,從簡單的商品經濟來看,商品所有者和貨幣所有者的內在差異消失了,我們沒有必要去注意商品所有者和貨幣所有者的內在差別,我們需要注意的是二者之間的等價與否。在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中,一切商品都必須接受充當了交換價值的貨幣這一外在尺度的估價;也是在貨幣面前,一切商品都同時獲取了平等的外觀,[1](P15-166)達到了“在貨幣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在貨幣面前的這種平等未曾不是對商品的內在豐富性的忽視。“兩個東西只有當它們具有同樣性質的時候,才能用同樣的尺度來計量。”[3](P176)既然我們以同樣的尺度來審視,就意味著貨幣以其獨特的視角抽象化了一切商品的內在豐富性,而在貨幣傲視一切的社會中,一切無非都是商品,連人也不能例外。[3](P55)因此,人在貨幣面前的所謂平等,無非是人在被商品化之后的平等,是類似于在上帝面前的原罪的平等。
其次,從“貨幣=勞動”的等價交換來看,勞動者的私有財產權難以得到有效捍衛,能得到有效捍衛的無非是資本家的權利。因為對于一無所有,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勞動者來說,無所謂外在的財產需要捍衛,需要捍衛的也許就是具有自在價值的生命。但是,就是這一具有內在價值的生命,勞動者有時也是難以捍衛的,因為在一切都被化約為商品,一切都被卷入競爭的社會中,作為勞動者“內在財產”的生命及其活動能力也有可能因為競爭的緣故而被逼至難以維系,甚至有可能出現為了活著而被迫出售自己生命的荒謬。[2](P163)
但對于有產者來說,私有財產權就有了實質性的意義。它不僅體現為有產者的生命這一“內在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也體現為有產者的“外在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而更為重要的是體現在外在財產上面,因為只有這一財產才表現出有產者之為有產者。因此,私有財產權在這一層面上成了有產者的特權,成了有產者針對無產者的權利。結合馬克思關于資本家所擁有的財產主要是來自對他人勞動的占有的思想,[6](P449)我們不難理解馬克思在私有財產權上的重要揭示:私有財產權“在資本方面就辯證地轉化為對他人的產品所擁有的權利,或者說轉化為對他人勞動的所有權,轉化為不支付等價物便占有他人勞動的權利,而在勞動能力方面則辯證地轉化為必須把它本身的勞動或它本身的產品看作他人財產的義務。所有權在一方面轉化為占有他人勞動的權利,在另一方面則轉化為必須把自身的勞動的產品和自身的勞動看作屬于他人的價值的義務。”[6](P450)
因此,既然私有財產權“表現為占有他人勞動的權利,表現為勞動不能占有它自己的產品”的權利,[6](P450)那么奠基于私有財產權之上的人權就不可能是無產者所能擁有的人權,而是資本家用以占有他人勞動的人的專有的權利。而且,把私有財產作為人的基本權利,從而作為裁斷正義的準則,意味著私有財產是市民社會中的君主,誰得到她的“青睞”將不僅可以主宰市民社會,而且可以在事實上挑戰法律所劃下的邊界或讓法律為其劃界。那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所看到的法只是強者的利益和弱者的苦難與無奈就可能是私有財產權“治下”的社會的常態。
三、對馬克思批判私有財產權的幾點思考
關于馬克思批判私有財產,需要進一步探討和反思的問題有很多,比如:(1)馬克思對私有財產權的批判有沒有一貫性?是否存在阿爾都塞所說的“意識形態”與“科學”的“斷裂”?(2)馬克思對私有財產權的批判是否屬于道德批判或是否存在道德批判?(3)馬克思對私有財產、人權的剖析與批判是否會在彰顯其歷史性的同時遮蔽了人權的普遍性,彰顯經濟維度時,遮蔽了道德維度?(4)馬克思對古典自由主義的私有財產權、人權的批判是否能夠適用現代形態的人權,甚至是適用于人權一般?(5)馬克思為近代人權開出的“藥方①參見林進平:《馬克思以何批判資本主義辨析》,《社會科學輯刊》,2014年第5期。是否依然有效?
對于這些問題,筆者認為都值得思考,但限于篇幅,這里只是略為蜻蜓點水地探討前三個問題。
1.馬克思對私有財產權的批判是否具有一貫性。關于馬克思對私有財產權的批判是否具有一貫性的問題,只要比較前后的批判就可以大致明了。
首先,就批判對象來說,馬克思的批判顯然具有一貫性。不論是早期還是晚期,私有財產一直是馬克思批判的對象,在這里,看不到“批判對象上”的斷裂,而是批判對象上的連貫性,特別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資本論》及其手稿中更為明顯。也許正是借助這種批判對象的一致性,盧卡奇能夠透過馬克思的《資本論》探析出他未曾看過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異化思想。
其次,就批判所做的一些揭示來看,二者也存在著顯然的連貫性。這表現在前期哲學批判中馬克思所揭示的——私有財產不是人的自然權利,是市民社會成員的權利,私有財產是人的異化、人權是人的異化當為人性,捍衛的是異化的關系等——在后期的批判中都得到了呼應和強調。如要說有不同的話,是后者的批判更為具體和深化。前者對作為人權的私有財產權的批判不多(主要集中在《論猶太人問題》中),而后者則以較多的篇幅剖析、批判了這種人權,特別是作為人權觀念和機制上的批判;前者只是道破私有財產潛藏的勞動與資本的對立,后者則對這種對立給以了細致的剖析,直接道明私有財產權就是資本家針對無產者的權利,自由、平等也無非是資本家剝削無產者的自由、平等,以及無產者在受剝削上的自由與平等。
最后,假如存在不連貫性的話,就是在批判方式上。因早期的哲學批判與后期的歷史唯物主義批判似乎存在著“認識論上的斷裂”,[7](P3、13-15)比如對于早期的哲學批判,一些學者傾向于將其視為道德批判、意識形態批判,而后期則是不同于道德批判或意識形態批判的“科學剖析”(即歷史唯物主義批判),且馬克思自己也明確表述過他不滿意早期的哲學批判而尋求歷史唯物主義剖析。但是針對阿爾都塞等人所說的“認識論上的斷裂”,已有不少學者指出這是對馬克思前后的思維范式的差別的夸大,以致否定了前后期之間的連接。事實上,我們從馬克思自己指出的歷史唯物主義思維方式與黑格爾的思維方式的承接關系,也可以推想他前后期之間不可能是一種“楚河—漢界”之間的關系,因表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哲學批判相較于黑格爾的思維方式來說更為接近歷史唯物主義,且他借此發現了他更為明確的批判對象和方法——市民社會及政治經濟學。緣于上述,我認為至少在批判私有財產這一對象上,馬克思前后期的批判具有高度的連貫性,只不過后期的批判更為徹底和具體而已。
2.馬克思對私有財產的批判是否屬于道德批判。對于此問題,我認為首先要弄清“道德批判”所指,假如“道德批判”指的是運用一定的道德規范或道德準則去進行批判,那我認為至少在歷史唯物主義時期,馬克思是避免運用道德規范或道德準則去批判資本主義社會。因此不認為馬克思存在或明或暗地以某種道德規范去批判私有財產權①參見林進平:《馬克思以何批判資本主義辨析》,《社會科學輯刊》,2014年第5期。。這不僅是因為道德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中屬于意識形態,是馬克思所要拒斥、批判的對象,也是因為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時期的文本中很難找到直接的文本支持,找到的反而是馬克思對海因岑、蒲魯東等人的道德批判的批判。
對此,也許會有人不以為然地質疑:那馬克思指認資本主義剝削為盜竊、掠奪、盜用等,又該作何解釋?
這的確有一定的挑戰性,但這里有必要區分兩種情形:一種是馬克思對剝削(包括對私有財產與剝削的關系)的分析是一種事實分析,而這種事實分析卻吻合人們的道德判斷;另一種是依據某一種道德準則去分析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與剝削。馬克思對剝削的剖析宜理解為前者,而不是后者。[8](P242-263)至于為什么會認為資本主義剝削是不道德的,我認為這與其說是馬克思的觀點,不如說是我們以自己的道德準則去統攝馬克思所剖析的事實得出的道德研讀。
因此,在總體上,我不認為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時期,存在著以道德規范或道德準則去批判私有財產權的情形。
至于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之前的情形則相對要復雜些。對于這一段時期,較多的學者傾向于認為馬克思存在著某種道德批判①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科學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幾乎在這個問題達成了共識,阿爾都塞、塔克爾、布倫克特和國內學者俞吾金等都認為馬克思這一時期的批判屬于道德批判。,甚至將他這一段時期視為道德批判時期。但是,當我們想具體地探問馬克思究竟是以何種道德規范批判資本主義、私有財產時,答案卻是五花八門,有人認為馬克思是以正義準則批判資本主義的,有人認為馬克思是以自由準則批判資本主義的,也有人認為馬克思是以平等準則批判資本主義的,更有人認為馬克思是以費爾巴哈式的人本主義批判資本主義的,甚至認為馬克思是以資本主義的道德規范批判資本主義的。答案的五花八門和彼此沖突常常暗示著這些“答案”并不是真正的答案,而情形極有可能是我們持有某種道德判斷去統攝馬克思對私有財產權的批判所致。他們或者從馬克思的批判中推演出私有財產會導向不自由或不正義等,就推斷馬克思是以自由原則或正義原則等批判私有財產權,批判資本主義②參見George G.Brenkert.M arx,sethics of freedom,Routledge&Kegan Paul plc,pp .1517、86、124、131163.認為馬克思是以平等原則或人道原則批判私有財產權的也與此相似。。但是,諸如此類的推斷未曾不是“瞎子摸象”,一方自以為是的推斷為另一方所否證。不過,相對而言,在諸多認為馬克思是以某種道德準則批判私有財產權,乃至批判市民社會的觀點中,我認為較有說服力的是推斷馬克思是以費爾巴哈式的人道主義去批判私有財產權,批判市民社會。這一推斷至少能夠得到幾個理據的有效支持:(1)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及其導言、《論猶太人問題》和《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在相當程度上是借費爾巴哈式的人本主義介入了對黑格爾法哲學、國民經濟學、市民社會(包括私有財產權等)等的批判;(2)馬克思在此一時期對費爾巴哈的宗教批判是充分肯定的,在馬克思對私有財產權的批判中,隱隱約約能夠感受到費爾巴哈的宗教批判是馬克思對私有財產權的批判的“仿用①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科學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幾乎在這個問題達成了共識,阿爾都塞、塔克爾、布倫克特和國內學者俞吾金等都認為馬克思這一時期的批判屬于道德批判。。(3)馬克思常常將揚棄私有財產與真正的人道主義相提并論,人道主義成為他這一時期顯然的人道訴求。
不過,盡管我認為馬克思對私有財產權的批判存在著人道主義的訴求,但我不認為由此就可以斷定馬克思對私有財產的批判就是道德批判。
3.馬克思以歷史唯物主義批判私有財產、人權是否有潛在的理論風險。對此,我認為有風險,就是被誤解的理論風險。其中的理論風險之一就是將歷史唯物主義簡單機械地理解為“歷史相對主義+經濟的一元決定論”。這也是我在這里想探討的一個理論風險。
應該說,從馬克思對私有財產、人權、正義的拒斥和批判來看,他的確拒斥、批判了投射在這些問題上漫無邊際的普遍主義和泛道德主義傾向,這種拒斥和批判較多地反映在他對蒲魯東、拉薩爾和魏特林等人的批判上,這種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批判他們忽視了問題的實質,遮蔽了解決問題的真正路徑。
但是,這種批判本身并沒有使馬克思否定合理抽象和道德訴求的正當性,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對合理抽象的肯定,[3](P9-12)對工人通過權利訴求謀求工作日的縮短和工作條件的改善的肯定都可以說明這一點。甚至馬克思在以其歷史唯物主義視角審視人類社會時,它的背后也有某些可以視為“普遍主義”的影子——在一定程度上他是把在近代突顯出來的歷史精神和經濟學走向凝練為歷史唯物主義視角,并把這一視角推演為審視人類社會的視角。在這一點上,他的歷史唯物主義就帶有濃厚的“普遍主義”傾向。他甚至比黑格爾和斯密更為徹底地把握了現代性的精神實質和推進了普遍主義。他不像黑格爾把以往的思想理解為一個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環節,而把自己的思想卻理解為終結的傾向,而馬克思則從不把他的思想設想為終結。在斯密和布魯諾等學者的抽象理解中,經濟似乎是利己主義的,道德是利他主義的,道德與經濟就像斯密的《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一樣存在著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的割裂,而馬克思則以歷史唯物主義審視私有財產、人權,避免了人性的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經濟學與政治學、倫理學的割裂。在他看來,不應該抽象空洞地談論人性,而應該研究現實的個人,人性無不體現在現實的個人之中,體現在人們的行為之中。經濟行為見證的并不只是人的利己性,只是在具體的商品經濟下所見證的才是人的利己性;道德見證到的也不一定是人的利他性,如把道德理解為是對人的制約,那道德似乎是利他的。但是,道德在現實上不是表現為對人的共同規定,而毋寧是人與人之間博弈的結果,是表現為共同性外觀的利己而已。假如沒有利己的因素在起作用,道德又何以能夠存在。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他避免了僅從政治、道德的角度理解人權,而從經濟學的角度理解私有財產、工商業的缺陷,在否定了道德和經濟之間的抽象斷裂的同時,也溝通了二者之間的聯結,道破了道德的純粹的利他性外觀。
誠然,歷史唯物主義包含有強烈的“經濟學維度”,但是,這一“經濟學維度”不宜簡化為“經濟學的一元決定論”,一旦做出這種簡化,就會認為馬克思僅僅是從經濟的視角去看待私有財產和人權,就會認為馬克思否定了私有財產、人權所隱含的“道德維度”。事實上,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即使是談論最具有經濟學特色的私有財產,馬克思也一直留意私有財產背后的“人道主義訴求”;在談論人權時,他雖以“經濟學”的視角審視,但并沒有由此否定人權背后也存在道德、文化維度。[9](P435)正如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和《神圣家族》中對鮑威爾的批判那樣——批判其把宗教問題僅僅視為宗教問題——,在思維方法上,他一直反對把“經濟”問題僅僅看為“經濟”問題,把“人權”問題僅僅看為“人權”、“道德”問題,看不到“經濟問題”背后的“人性”,“人權問題”背后的“經濟”。
出于對時代的把握,出于對那些奢談“人性”的反感,馬克思并沒有大談特談“經濟問題”背后的“人性”,而是談論了“人權問題”背后的“經濟”。當然,“經濟學視角下的人權”意味著它所能窮究的也基本上是作為狹義的人權,即特指市民社會成員的權利,而不包括公民權在內。因此,在《資本論》時期的馬克思所指的人權也基本上作為市民社會成員的權利,而不包括公民權。
既然馬克思談論人權,只是從“經濟學”的視角談論人權,而沒有否定從人性、道德視角談論人權的合理性,那對馬克思談論人權的視角就不宜做泛化的理解,不應該強調從經濟學視角審視人權的合理性而否定從其他視角審視人權的合理性。一旦做泛化的理解,則容易淡化人權的人道主義追求,窄化人權的可能意義。
再者,假如我們注意到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的當務之急是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10](P8)而不是人權研究,即論及人權只不過是馬克思的“乘便之作”,那我們就沒有理由要求馬克思在從經濟學視角揭示人權的局限之時,還要時不時回過頭來提醒:這種從“經濟”視角理解人權的方式本身也是有缺陷的,是會貶低人權的價值的。因此,這種“窄化”與其說是來自馬克思,不如說是來自我們,是我們忽視馬克思言及人權的具體語境,是我們“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窄化了人權的意義空間。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答布洛赫的信中就指出:“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11](P591)
辯證法本是消解對歷史唯物主義誤解的“解藥”,但當我們放棄歷史唯物主義本身所內含的辯證法時,誤解就會接踵而至。比如,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視角”審視人權意味著它突顯了人權的時代性,彰顯、強化了人權的歷史性的一面,撥開了籠罩在人權之上的過多的普遍主義的迷霧,使人權坐實在現代性上,從而暴露出其歷史限度;但如把投射在人權之上的“歷史視角”作泛化的理解,就存在遮蔽人權的超越歷史性、追求價值、傳遞人性化追求的危險,甚至最終陷入相對主義、虛無主義的深淵。同樣,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視角”剖析人權,能夠揭示人權的社會經濟條件,用現代性的手法揭示了人權之謎,但如把這一“經濟視角”做泛化的理解,從而認為人權無非是利己主義或經濟利益的外在表現,否定人權的人道主義維度,那也容易使人忽略人權在人道主義上的價值導向作用以及人權自身的建設,從而否定人權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潛在的改造作用。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 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M].李常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M].顧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8] Allen W ood.Karl M arx[M].2nd edition.London:Routledge,2004.
[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責任編輯 孔 偉]
M arx's Two Kinds of Criticism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
Lin Jinping
(Department of M arxism Studies,Central Compi 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Bei j ing 100032)
M arx;private property;criticism;historical materialism
M arx made both philosophicalcritic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riticism on private property right.Private property showing human nature means the comprehensive alienation of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and private property rightis the confirmation of this kind of alienation.Itis unable to deliver humanitarian com mitment and itisin fact the right of the haves against proletarian.On theissue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thereis no distinctfracturein M arx,s two kinds ofcriticism.M arx,s criticism ofthe private property rightsin general does not belong to the moral criticism,but it is also a mis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think that the criticism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ruled outthe moral dimension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nd human rights.Itis especially wrong to misunderstand it as the theory of“historical relativism+ unary economical determinism”.
林進平,中央編譯局馬克思主義研究部研究員(北京10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