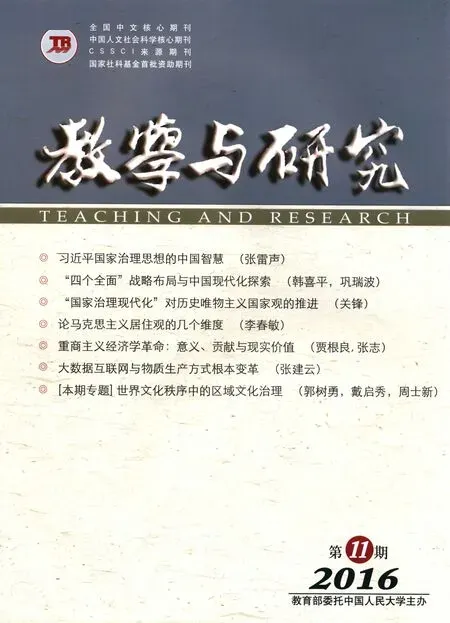論馬克思主義居住觀的幾個維度*
李春敏
論馬克思主義居住觀的幾個維度*
李春敏
馬克思主義;居住;空間
“居住”是“生活世界”的重要維度,它不僅關涉身體對空間的占有,更展現著人的生命形態和本質力量,指向了人的精神家園和生命寄托,人在“居住”中建構意義世界;同時,居住空間也日益成為一個社會變遷的“場所”。馬克思主義的居住觀為理解“居住”與“生活世界”的關系提供理論啟示:即作為一種“生活實踐”的居住、作為一種“空間生產”的居住、作為一種“政治規劃”的居住、作為一種“社會理想”的居住。
“居住”是“生活世界”的重要維度,它不僅關涉身體對空間的占有,更展現著人的生命形態和本質力量,指向了人的精神家園和生命寄托,人在“居住”中建構意義世界,也在意義世界中“居住”,人類追求“詩意的棲居”之努力從未停歇。在當代,由“棲居之所”的爭奪引發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斗爭如火如荼,“居住的政治”正在深刻地塑造著每一個“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與此相適應,“居住”被賦予更為豐富的內涵,居住空間也日益成為一個社會變遷的“場所”。如何理解“居住”與“生活世界”的關系,如何走出一條體現空間正義、促進空間和諧的居住空間生產之路,通過對馬克思主義居住觀幾個維度的探討,我們可以獲得重要的理論啟示。
一、作為一種“生活實踐”的“居住”
在馬克思的視野中,“居住”不僅僅意味著給“身體”一個“居所”,更是理解“感性世界”的一種基本方式,關涉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架構和“新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源頭。如果我們按照實踐場域的不同,將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范疇分為“生產實踐”和“生活實踐”,那么,“居住”總體上屬于后者,是被馬克思稱之為“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的活動。馬克思指出:“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這樣的歷史活動,一切歷史的一種基本條件,人們單是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去完成它,現在和幾千年前都是這樣。”[1](P79)這里的“住”同“吃”、“喝”、“穿”一起構成馬克思“生活實踐”的基本領域。它們是人類存續所必需的“現實的生活生產”,是使“歷史”成為“歷史”的東西,“新唯物主義”歷史觀必須對上述事實及其全部意義給予足夠的重視。如果把這些領域從歷史觀中剝離出去,歷史就會淪為“某種脫離日常生活的東西”、“某種處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東西”,必然造成“自然界和歷史之間的對立”。[1](P93)馬克思對費爾巴哈進行了批判,“他從來沒有把感性世界理解為構成這一世界的個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動”。[1](P78)不難理解,區別于形形色色的“思辨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更加關注“現實的人”的“現實生活”,“生產實踐”和“生活場域”不僅不是割裂的,恰恰相反,“生活場域”在這里成為“生產實踐”的緣起,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向現實世界注入人文關懷的特有方式。
“居住”在本質上是人的一種對象化活動。在這種對象化活動中,主體的需要被注入其中,作為居住活動物質載體的居住空間呈現為人自身的“他在”,是“他的作品”、“他的自然”。馬克思指出:“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1](P47)在這里,作為一種“生活實踐”的“居住”體現人的價值訴求,承載日常生活世界的意義建構,是人與自身的“對話”,是人作為一種“生活者”的一種“合目的性”的活動。與其他的生活實踐范疇相比,“居住”又表現出自身的獨特性。其體現在:居住活動的目標指向是“安居”。后者創造了一種生活情境:“身體”被安置其中,其多元性被打開了,成為“萬物的尺度”。這個“身體”不是某種給定的客體,而是不斷生成的“身體”;不是“溫順的身體”,而是“解放的身體”。在這個意義上,“居住”是一種讓身體休憩舒展、讓心靈平靜喜樂的活動。因此,不是房屋賦予人以“居住”,而是人為“居住”建造房屋,人與房屋的關系始終應被理解為一種對象化的過程。
“居住”作為一種“生活實踐”具有社會歷史性。人類的居住活動源遠流長,不同的時空語境下人類的居住面貌是各自相異的,每一個時代的居住活動受到特定的物質生活條件的制約,展現出鮮明的時代性。農業時代的居住活動不同于工業時代的居住活動,封建時代的居住活動又有別于資本時代的居住活動,在這個意義上,“居住”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構造物。以資本時代為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辟了一種新的人與土地的關系模式,與前資本主義時代相比,“它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權從統治和從屬的關系下完全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又使作為勞動條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權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離,土地對土地所有者來說只代表一定的貨幣稅,這是他憑他的壟斷權,從產業資本家即租地農場主那里征收來的;[它]使這種聯系遭到如此嚴重的破壞,以致在蘇格蘭擁有土地所有權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度過他的一生。這樣,土地所有權就取得了純粹經濟的形式,因為它擺脫了它以前的一切政治的和社會的裝飾物和混雜物”。[2](P539)土地經營的資本化運作瓦解了籠罩在房屋上的封建宗法關系,使人與房屋之間主要呈現為一種消費關系,為棲居之所的流動以及生存空間的轉移創造了條件。
二、作為一種“空間生產”的“居住”
“居住”本質上是一種有自身域界的“空間體驗”,具有空間屬性,不管這個空間是“家”、“臨時居所”還是我們賴以生活的“星球”,“居住”的意義在于不斷生產“屬人”的空間。
首先,作為一種“空間生產”的“居住”著眼于日常生活的空間繪制,在其中,生活、交往、工作及享樂得以有序展開。一個地理空間一旦被納入到人的居住活動中,它的“自在”狀態就被改變了,它不再是僵死的、刻板的“容器”,而成為一個“表征的空間”、“人化的自然”,“人們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同時間接地生產著自己的物質生活本身。”[1](P67)作為一種“空間生產”的“居住”是社會過程的“空間表達”,我們以何樣的方式生活,就會展現何樣的居住空間面貌。舉例來講,有的居住空間帶給人寧靜,有的居住空間帶給人躁動,有的居住空間生產和諧,有的居住空間累積憤怒。在這里,作為一種空間生產的“居住”根植于日常生活的經驗體系,連接著現實的歷史地理條件,它可能是自由意志的生成地,生活旨趣的實驗場,也可能是文化對峙的溫床、資本權力的災區,它始終代表著一種可觀的地理力量。作為一種空間生產的“居住”是感性的、多姿的、綺麗的,充盈著波瀾壯闊的日常生活之流,它是現實社會空間的一種隱喻,在其中,我們每個人都扮演著“建筑師”的角色。
其次,作為一種“空間生產”的“居住”著眼于一種“場所精神”的建構。馬克思指出:“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想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2](P178)人的居住活動展現的是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1](P46)的過程,反映著居住者的精神特質和文化屬性。居住活動創造了一個由“自然環境”和“人為環境”共同組成的一個有文化屬性的場所,人在其中進行自我闡釋、建構自我認同。這種“場所精神”抑或浮夸,抑或節制,抑或張揚,抑或內斂,不一而足。“當人為環境充滿意義時,便讓人覺得在家般的自在”。[3](P23)作為一個古老的社會范疇,人類對“居住”的探尋是多維的,從住宅的建造到“居住”的文化視野的開辟,如果說前者關涉的是技術層面的“居住”,那么后者關涉的則是更為深刻的“存在之根”的追問。一種“我們從哪里來,我們是誰,我們要到哪里去”的惶惶然,相對于身體的居住困境,靈魂的“無家可歸”則更為深遠,這也是為什么在人類的居住想象中充滿了對精神棲居的渴求。居住活動就是建構這樣一個場所:人在其中注入情感、投射需要、關照身體、安放心靈,在其中體驗生之愉悅、編織意義之網、建構意象世界。
最后,作為一種“空間生產”的“居住”著眼于一種象征性空間的建構。 這種象征性空間是一個由居住想象建構的空間,這種想象聯結著特定的時空秩序,它使“居住”從實在的場所、地理的藩籬中抽離開來,成為一種滋養思想的動力空間。比如,同樣是“居住”,“家”與“旅店”代表著完全不同的空間體驗,相對于“地理-物理”空間的概念,“家”更是一個親情的空間、意義的空間和倫理的空間,“家”代表了一個獨特的居住景觀,一個只有家庭成員才能解讀的空間符號體系,在其之上籠罩著溫情的烏托邦面紗。“家”是心靈的歸依處,具有非功利性,再簡陋破舊的“家”,也是游子心中溫暖的港灣,“家”建構了一種“居住情懷”,其象征意義遠遠高于它的物質存在。相比之下,“旅店”則代表的是一個過渡空間、共享空間和消費空間,它具有暫時性,是標準化、快捷化的開放空間,居住者往往不會將過多情感和意義加諸其上。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賦予了象征意義的“家園”,它不僅僅是以實體形態存在的地域空間,更以一種想象空間的方式鮮活地存在于人們的心中。在這個意義上,居住空間從來不是喪失了意義的技術機器,無論在場與缺場,這個空間作為一種象征性景觀都會對現實的生活實踐產生影響,即使是無家可歸的“游蕩者”,也會通過空間的烏托邦想象來實現“居住”。在這里,“街道成了游蕩者的居所,他靠在房屋外的墻壁上,就像一般的市民在家中的四壁里一樣安然自得。對他來說,閃閃發光的琺瑯商業招牌至少是墻壁上的點綴裝飾,不亞于一個有資產者的客廳里的一幅油畫。墻壁就是他墊筆記本的書桌;書報亭是他的圖書館;咖啡店的階梯是他工作之余向家里俯視的陽臺”。[4](P56)
三、作為一種“政治規劃”的“居住”
“居住”很早就被納入人類的政治視野。“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民生思想代表著一種古老的政治智慧。“居住”作為一種政治元素聯結著人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正義的建構,圍繞“居住”的“地理政治學”廣泛存在當代的政治話語體系中。
首先,居住空間作為一種空間產品,其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都滲透著政治價值觀,是現實政治秩序在日常生活世界的表達,呈現為一種“微觀政治學”。在資本主義社會,這種“微觀政治學”的核心是“資本”,“資本”是一種現實的運動。在其中,居住空間不僅具有使用價值,同時創造剩余價值,后者使居住空間成為資本逐利的對象。那些在資本的鏈條中處于優勢地位的階層成為資本的“寵兒”,他們炫耀著資本的權力;相反,那些弱勢階層別無選擇地成為資本積累的“被剝奪者”。兩者的居住面貌呈現出巨大的空間差異:一邊是優質居住空間的占有者,一邊直接導向了被壓榨的身體,兩種居住景觀代表著兩種生存境遇。馬克思這樣描述一個城市雇傭工人的棲身之地:“這也許是一座破落的茅屋,只有一間臥室,沒有火爐,沒有廁所,沒有可以開關的窗戶,除了水溝而外沒有任何供水設備,沒有園圃,但工人對這種虐待也無可奈何。”[5](P750)同時指出:“由于無意識的默契,也由于完全明確的有意識的打算,工人區和資產階級所占的區域是極嚴格地分開的”。[2](P326)在這里,居住空間生產聯結著資本積累和階級對抗,它是資本開辟的一種“空間政治”,社會權力格局通過居住空間得以確認、保障和呈現。
其次,“居住”是一項基本的“空間權利”。這項權利應當涵蓋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有平等、不受歧視的居住空間獲得渠道;二是可支付性,即居住空間是通過合法勞動可以支付的,如果這種支付昂貴到已經事實上剝奪了房屋購買者其他方面的基本需求的滿足,這種居住權就只是形式上的;三是居住空間是適宜居住的,有安全健康的基礎設施,保證居民的個人隱私不受侵犯;四是居住的自由遷徙權,這四項權利保證了居住尊嚴的實現。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資本主義條件下雇傭工人居住權利的缺失,指出:“勞動生產了宮殿,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棚舍。勞動生產了美,但是使工人變成畸形。”[1](P43)雇傭工人的居住權利是讓位于資本的,這源于資本主義的土地占有與資本權益之間的緊密關聯,馬克思指出:“這種土地所有權,在和產業資本結合在一個人手里時,實際上可以使產業資本從地球上取消為工資而進行斗爭的工人的容身之所。在這里,社會上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人要求一種貢賦,作為后者在地球上居住的權利的代價,因為土地所有權本來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剝削地體,剝削地下資源,剝削空氣,從而剝削生命的維持和發展的權利。”[2](P572-573)在這里,居住權利的缺位加劇了雇傭工人的空間焦慮,直接導致了“居”的喪失,“居住”成為對生活的顛覆、拒絕和否定,城市的居住空間樣態是非正義的結果,同時,這個結果又進一步加劇了居住的非正義。
最后,“居住抵抗”是政治訴求的重要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關注資本主義條件下雇傭工人的居住困境,指出:“城市人口本來就夠稠密的了,而窮人還被迫更其擁擠地住在一起。他們除了不得不呼吸街上的壞空氣,還成打地被塞在一間屋子里,在夜間呼吸那種簡直悶死人的空氣。給他們住的是潮濕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閣樓。給他們蓋的房子蓋得讓壞空氣流不出去。”[6](P382)當“居住”成為一種社會壓迫的力量、一種對自我存在的貶損,而且這樣的居住體驗不是發生在個別的雇傭工人身上,而是代表著某種普遍性的階級生存狀況,“居住抵抗”就不可避免,這使居住空間成為了一個動蕩的戰場。“居住抵抗”的形式是多樣的,從介入居住規劃到參與公共政治,從保持空間想象的權利到建構生活世界的“詩性”。“居住抵抗”的實質是重建居住權利,促進居住空間生產的多元、民主和公正,實現空間解放,抵抗資本對于生活世界的宰制,在這里,重建居住秩序的努力只有與整體的社會變革結合起來才能有的放矢。
四、作為一種“社會理想”的“居住”
“居住”是實現人的自由與解放的重要維度,作為一種“社會理想”的“居住”既是美好的愿景,又是一種現實的運動,在馬克思的視野中,這一社會理想就是共產主義。“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7](P120)共產主義開辟了全新的居住境界。
首先,作為一種“社會理想”的“居住”是對居住普遍物化的揚棄,回歸“居住”的本質。資本文明帶來的居住普遍物化使人的精神世界呈現種種病理狀態,人的主體性在“居住”中被消解了,居住空間反過來成為確定和支配人生活世界的“主人”,人們不顧一切地陷入居住空間的追逐中,不斷地沖向新的居住空間目標,居住空間的“拜物教”成為人們無法揮去的生之重荷,一條沒有終點的欲望之鏈。“貨幣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貨幣的特性就是我——貨幣持有者的特性和本質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夠做什么,這決不是由我的個性來決定的”。[7](P152)在這種居住體驗中,人的精神生活樣式的豐富性被遮蔽了,生存困境不斷累積。居住空間普遍物化的實質是“異化”,它是“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1](P40)的資本邏輯的一種“空間實踐”,是資本文明無法克服的痼疾。“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存在的時候,企圖單獨解決住宅問題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運有關的社會問題都是愚蠢的。”[8](P197)在一種理想的“居住”中,私有制將被消滅,在全社會范圍內高效而有序地進行居住空間的生產和分配,居住空間不再作為商品,而是一種勞動產品,不再是一個斗爭的場所,而是一個愉悅身心的安居之地。
其次,作為一種“社會理想”的“居住”能夠滿足人的多樣化的居住需要,這些需要關涉休息、安全、私密、健康、學習、娛樂、交往等多方面。以交往需求為例,理想的“居住”是一種和睦共居的狀態,居住密度是適宜的,既不密集,也不稀疏,能夠促進自由、真誠、多維的交往,個人與鄰里、社區和諧共處,共居的目的是建構有意義的“對話”,促進個體實現更深刻的自我理解,人們在居住空間中進行有益身心的健身活動和娛樂消遣,分享精神成長的成果,承擔共同的道德義務,體驗彼此之間深刻的社會聯系。作為一種“社會理想”的“居住”著眼于建構一種“居住美學”,將美的元素、美的態度注入到居住活動中,從居室美化到居住區設計,這種建構過程是自發的、非功利的。理想的“居住”致力于開辟一種全新的居住境界,在其中,人的“感性”得到更為豐富的展現,獲得了全面的解放,居住活動成為生機勃勃、充滿律動的跳躍音符,人的居住體驗是愜意而美好的。在一種理想的“居住”中,居住空間的流動是自由的,人們不再受制于特定的地理地域,人們流動到哪里,就可以在那里獲得優質的居住空間。在這里,“居住”的意義在于滋養人的心靈,建構精神家園,把“人”和“人的世界”還給人自身。
最后,作為一種“社會理想”的“居住”的核心要義是對人的關懷。在一種理想的“居住”中,“生產”與“生活”的對峙消解了,“生活本身僅僅成為生活的手段”。[1](P46)人們能夠在居住空間中度過充足的自由時間,居住本身的功能更加多元,成為一個開放的世界,人在其中耕耘自己的身體和心靈,享受美、歡樂和親情,進行智力思考和追求審美體驗。在這里,居住空間不僅僅是“容器”,更是精神的搖籃、生命的綠洲。人們對存在的覺知和領會在居住中更加主動,人與居住空間之間將呈現能動的多重聯系。人的生命活動在居住空間中被轉化為藝術形式,展現出靚麗多姿的生命形態。“居住”本身成為一種生活美學的表達,“創造著具有豐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覺的人”,[7](P126)通過“居住”人完成了人的本質的自我確證。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諾伯格·舒爾茨. 場所精神——邁向建筑現象學[M].施植民譯. 臺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4] 本雅明. 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修訂譯本)[M]. 張旭東, 魏文生譯. 北京:三聯書店, 2007.
[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責任編輯 孔 偉]
On the Dimensions of Marxist Views of Residence
Li Chunmi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Marxism; residence; space
“Residence” i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the living world. It not only involves the space occupancy of a human body, but also demonstrates forms and nature of human life. It points to people’s spiritual home and life sustenance, people construct a meaningful world in “residence”. At the same time, living space has become a place of social changes. Marx’s view of residence provides theoretical enlightenment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sidence” and the “living world”. This revelation includes: residence as a “life practice” , residence as a “space production”, residence as a “political planning” and residence as a “social ideal”.
*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居住空間正義研究”(項目號:14BZX019)和2014年上海市陽光計劃的階段性成果。
李春敏,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上海20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