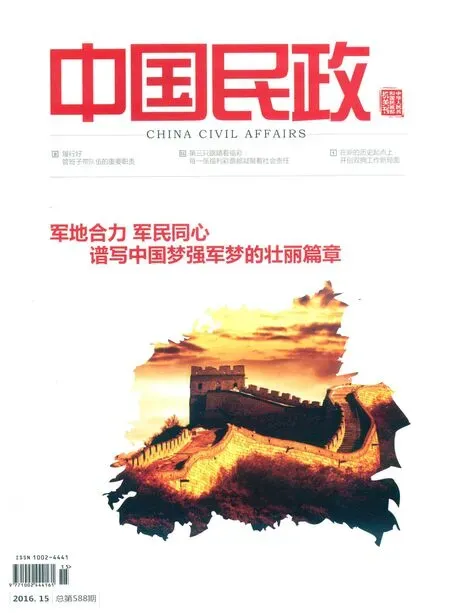社會救助程序法治化路徑探析
李鄂輝 唐政秋
社會救助程序法治化路徑探析
李鄂輝 唐政秋
一、我國社會救助程序存在的主要問題
1. 社會救助程序法制化不足,實踐中輕程序現象突出。一是專門的救助程序法規極少,“重實體、輕程序”。據統計,自1999年頒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以來,國務院共出臺社會救助相關法規、政策近五百余件,地方性規范性文件數以千計,但專門的程序性規定只有兩件(2006年修訂的《民政部應對自然災害工作規程》、2008年的《受災人員冬春生活救助工作規程》)。學者將此現象概括為“縱向結構失衡” 。二是現有程序規定設計簡單。《社會救助暫行辦法》(以下簡稱《辦法》)總則中沒有統一設立程序條款,除低保救助的程序比較詳細外,其他救助程序規定簡單。三是缺乏對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救助的程序規定。現有法規鼓勵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救助,但對其準入、監管以及退出程序等方面的規定缺位。四是限制政府濫用救助權力的程序,如救助資金的確定、變更程序或救助資金濫用責任的追究程序仍屬于原則性條款。
2. 申請、審批、實施程序設計不完善,約束力不夠。申請程序方面,大多規定以書面方式向戶籍所在的基層政府提出,不利于農民工獲得及時有效的救助,家庭經濟情況調查核查程序不明確、不統一,家庭收入和財產狀況計算步驟和程序不透明,公信力不足。實施程序方面,我國暫未建立社會救助標準制定與調整的法定規程,救助標準制定調整以地方政府為主,民政部僅出臺了低保標準的指導意見,導致部分地方主要根據地方財力確定救助標準。另外,現有救助程序的規定內容模糊籠統,約束力不夠,缺乏強制性和追究責任的規定,一些基層政府往往將受理、審核等職責交給村、社區行使,導致“人情救助”“關系救助”。
3. 部分基本程序性制度缺位。現有的救助法規中沒有回避程序、聽證程序以及監督程序等規定,弱化了救助的公平公正。社會救助程序直接關系到社會資源的公平配置和收入的合理分配,回避制度的缺失將大大降低救助制度的可信度和公平性。舉行聽證能夠聽取救助對象的意見,有利于接救助對象更好的參與到社會救助事項中來,也可以讓民眾更好的了解行政決策的過程,有利于保證社會救助的公正性。監督程序(包括對救助資金、救助物質發放程序的監督)的缺失,讓法律有關監督權的規定形同虛設。
4. 權利救濟程序不明確。廣義的社會救助權利救濟程序包括事先救濟和事后救濟。事先救濟主要包括公示程序、聽證程序、監督程序等,事后救濟則主要為司法救濟和行政救濟。我國的社會救助行為包括國家救助、民間救助,還有行政審批等行為。現有的社會救助法規有關救濟權利和救濟手段的規定很少(《辦法》只在第六十五條規定了依法提起行政訴訟或行政復議的權利),事先救濟程序的規定除了公示程序外,其余均缺失,事后救濟程序也不明確不規范。行政復議法、行政訴訟法等也分別只對依法不發放社會保障金、撫恤金糾紛等做出了規定。
二、社會救助程序法治化的必要性分析
社會救助程序,又稱社會救助法程序,是社會救助法規定的,社會救助行政主體實施救助以及行政相對人申請和獲得救助的步驟、方式、時限等。社會救助法屬于實體法與程序法兼具的法律,國外的社會救助立法均含有程序法制的內容。
依據社會法法理,社會救助程序法治化的必要性體現為:一方面,正當合法的程序是公民的社會救助權利得到保障和獲得救濟的基礎。程序本身就是對社會救助的前置性救助或稱預防性救濟,同時也為事后救濟提供了依據,再者,規范的救助程序設置是防止政府救助資源配置異化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社會救助程序是實體法價值實現的工具,是社會救助工作正常開展的必備條件。通過社會救助法規定救助主體和對象的權利義務,救助主體必須依程序行使職權、履行義務,救助對象也必須借助于相關程序機制獲得救助利益,使法定權利成為現實權利。
從我國社會救助現實情況來看,社會救助法規定程序法治化的必要性在于:社會救助的實施實際上是國民收入的再分配,而分配主體是掌握公權力的行政機關,被分配的主要是社會弱勢群體,因此必須通過規范程序保證救助資源分配的合理與公正,同時限制公權力的恣意行使;現有的救助資金、救助資源遠遠“供小于求”“僧多肉少”,容易導致救助的不公平甚至權力尋租,需要嚴格的程序予以制約。更重要的是,社會救助程序的合理創設,有利于被救助主體在維護自身利益、實現被救助權益的過程中,感受到各方主體行使權利(力)過程的公正性,以培養其遵循合法程序來行使權利的習慣。
三、法治化社會救助程序的主要路徑
1. 加強社會救助程序立法,完善救助程序的頂層設計。必須通過加強救助程序的立法,改變“重實體、輕程序”的狀況,保證各項救助程序有法可依。根據目前情況以及立法實踐,單獨制定一部綜合性社會救助程序法規并不可行,比較可行的立法模式是修訂《辦法》,或制定《社會救助法》時,在其總則中設立社會救助程序條款,也可以設立專章規定社會救助程序。要通過救助程序立法,完善救助程序的整體設計,彌補救助程序法治化的不足,協調生活救助、特困人員救助、專項救助、臨時救助等救助程序,規定社會力量參與救助的準入、監管、退出等程序,同時,要特別規定救助標準制定程序、救助資金確定與發放程序等,并保證公民的信息知情權。
2. 規范社會救助的啟動、審核、實施程序,強化程序的強制力。社會救助啟動程序方面,應確立書面和口頭相結合的形式,并克服二元化結構帶來的申請限制,建議增加特殊情況下救助機構依職權啟動和公益組織啟動救助的程序,完善救助申請對象權利和受理機構義務的法律規定。審核程序方面,建議在全國范圍內統一規定救助部門受理、審查、公示、批準的時限,要統一、規范家計調查程序,并保證其操作性;可以借鑒英國等經驗,針對不同的救助設置不同的家計調查程序,并設置特殊情況下的簡易程序。實施程序方面,要通過立法規范救助標準的制定、調整程序以及救助資金(含實物)發放程序,設立專業且中立的救助資金發放機構,以保證救助行為的透明、公開公正。要改變現有法律制度中救助程序規定約束力弱化的現象,賦予救助程序更大強制力,要在“法律責任”一章中規定違反救助程序、變相“簡化”程序等行為相應的法律責任。
3. 設置公民參與程序和監督程序,保證救助行為的公信力。要通過立法,將現有救助法律缺失的公民參與程序予以確立。一是建議在救助審核程序中規定對相關利害關系人的回避制度及其程序。二是在在救助對象的審批、救助標準的制定與調整、社會力量參與救助的準入審核等程序中,引入聽證程序,一方面可以保證公民的信息知情權,從外部約束公權力,防止暗箱操作,同時也可以保證上述程序的合法性以及相關結果的權威性。三是在健全監督權的同時完善監督程序。現有社會救助法律制度規定的監督包括政府部門的監督、社會監督和救助對象的監督等。各類監督在監督主體、監督對象、監督事項等方面不同,程序也不相同。特別是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對救助資金以及救助部門救助行為的監督、救助部門對救助對象(家庭經濟情況等)的跟蹤監督、有關部門及民眾對救助資金發放情況的監督等必須有相應的程序規定,以保證監督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4. 完善社會救助權利救濟程序。權利救濟是憲法規定的公民的社會救濟權實現的保障和基礎。如果僅依靠《辦法》第六十五條規定的行政復議或訴訟手段,難以實現對申請人或救助對象的權利保護。一方面,建議修訂《辦法》或制定《社會救助法》時設立“權利救濟”專章或專門條款,明確可以提起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的情形以及相關救濟方式等。另一方面,整合現有的權利救濟手段和救濟資源,通過完善《人民調解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等,拓寬法律受理范圍,確立不同程序的救濟方式。在上述基礎上,建立一套匯集民間調解、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三個層次的立體化救濟程序體系,明確各類主體在救濟程序中的權利和義務。
(李鄂輝系湖南省民政廳政策法規處處長;唐政秋系長沙民政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