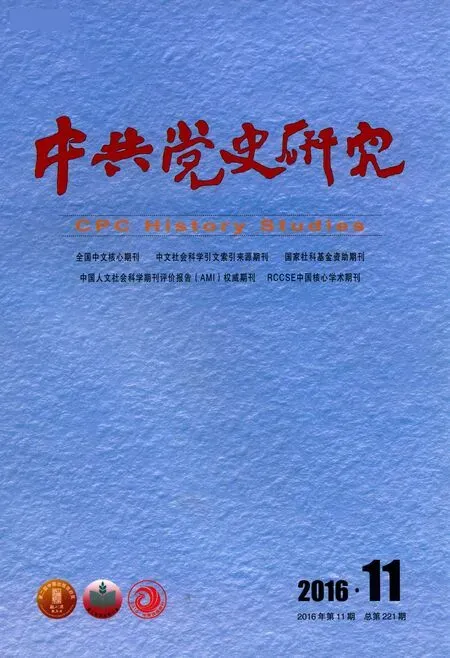路徑依賴:新時期鄉村史研究的新路徑*
辛 逸
?
路徑依賴:新時期鄉村史研究的新路徑*
辛 逸
著名經濟史學家諾斯指出:“路徑依賴意味著歷史是重要的。不去追溯制度的漸進性演化過程,我們就無法理解今日的選擇。”①〔美〕諾斯著,杭行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8頁。理解和研究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社會經濟的制度創制與變遷,不可能也不應該不追溯人民公社制度及其技術與慣習等文化因素,并將改革開放前后的鄉村社會視為一個持續演變的過程進行研判。正如馬克·布洛赫所言:“這種真正的時間,實質上是一個連續統一體,它又是不斷變化的。”②〔法〕馬克·布洛克著,張和聲譯:《歷史學家的技藝》,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1頁。
黃宗智曾在《中國研究的規范認識危機——社會經濟史中的悖論現象》(《近現代中國》第17卷第3期,1991年7月)一文中指出,近40年來,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研究的“理論體系實際上具有一系列的共同的基本信念。這些信念一般被認為是不言自明的,無須討論也不受人注意……然而,數十年累積的實證研究實際上已揭示出一系列的與這些信念相悖的現象”③轉引自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2000年,第413頁。。早在新時期“三農”問題研究創立之初,學界就已形成若干先入為主的所謂“基本信念”,如認定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改革開放后農業發展的主要動因,而改革開放之前數十年農業停滯、農村落后的主因是人民公社制度固有的結構性弊端。這一至今仍不容置疑的“基本信念”,不僅否定人民公社為新時期農業發展在制度、技術以及農業基本建設等方面所做的儲備,也基本阻斷和否定了兩個“三十年”農村社會經濟演變的內在聯系。
學界較早對上述成見提出挑戰的是黃宗智對松江鄉村經濟變遷的研究。他早在1990年就指出:“松江縣的作物畝產在1978至1979年集體生產時已達到頂點。自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到80年代末,單位面積產量實際上一直停滯不前。它真正促進的不是作物產量,而是作物生產中勞動的節約。”也就是說,“80年代真正意義重大的變化是農業外就業”。質言之,聯產承包制更重要的意義是允許社員自由擇業。鄉土精英脫離土地進城經商務工或到鄉鎮企業就業,帶來農村產業結構的質變和農民人均收入的大幅增加。1983年,該縣“華陽橋公社的工業占總產值的三分之二,而10年前僅為三分之一;同時農業產值由二分之一下降到僅為五分之一”。全國農村的產業結構同期也發生相同的結構性變化,“農村工業的比重在1973年至1984年間由不足10%上升到40%以上”。黃宗智由此對聯產承包促進農業顯著發展的“基本信念”提出質疑:“農業家庭責任制到底有沒有,以及在何種程度上起了作用是不容易推測的。”④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第319、287、286頁。這與主流“三農”問題專家的見解形成對照。
松江的個案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聯產承包是改革開放后農業增產主因的成說,還提醒我們,松江縣以解放農民為特征的反“過密化”發展模式并非孤案,在其他資源稟賦、人文傳統類似的地區很可能發生過類似于松江的故事。這就像小崗村在實行聯產承包的第一年,糧食產量是1966年至1970年五年產量總和⑤凌志軍:《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與失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2頁。的奇跡并非個別,在其他推行聯產承包的產糧區也曾出現產量大增一樣。這就提醒我們,若以個案為基礎研討聯產承包,研究者很容易選取對自己有利的材料和個案進行抽樣作證。這不僅難以對這一新的農業經營制度作出相對客觀的評價,更不要說在新時期“三農”問題的性質及其發展路徑上達成共識了。
對新時期各地農村社會進步與經濟發展的解讀,經濟學家大都關注各地農產量的突飛猛進、副業的大發展或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等不同的增長方式,主流史學則將農村這個時期的快速發展歸功于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實施。筆者則更加關注各種發展模式的歷史成因及其路徑依賴。各地農村既有的自然條件和人文習慣,規定和限制了當地的資源配置方式和勞作習慣,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當地的發展方式與路徑。我們發現,這種傳統的慣性與力量是難以通過人為的制度設計、行政干預和所謂“戰天斗地”的精神而加以改變的。具體言之,新時期農村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與人民公社時期的物質儲備、文化習慣與精神遺產有著很大的關聯性和繼承性。因此,從路徑依賴的角度研判改革開放前后中國農村的社會變遷與經濟增長,不僅是一個新的研究視角,更有助于理解當下的鄉村社會及其未來的演進方向。
筆者所理解的鄉村變遷史中的路徑依賴:一是農村基本制度(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和農作技術的源流及其演變方向,很大程度上會受到以往制度和技術的規定和限制;二是當下的新制度和技術不可避免地包含著舊制度和技術的某些因素,換言之,后者的某些要素一定會頑強地哪怕是歪曲或變形地反映在前者之中;由此可以得出鄉村發展史中路徑依賴的第三個含義,即僅憑領袖的理想而設計和創制的新制度,尤其是與既有的鄉村文化傳統和農作技術幾乎無關聯的制度(如“大躍進”時期的大公社制度),是很難在鄉村社會扎根和發展的。這種依靠行政力量推行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很難撼動鄉村社會的文化根基,其興起的隆盛與衰落的快速往往均超出人們的想象。
本文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農村經濟制度史研究,只是試圖借鑒路徑依賴的理念與視角,研判新時期鄉村社會的變遷,提出若干不同于既有研究的初步意見,期待有關專家的評判。
第一,新時期普遍推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非改革開放后才出現的新鮮事物,而是對集體化時期各種包產到戶制的繼承與揚棄,是一種比較典型的誘致性制度變遷。所謂誘致性制度變遷是“由個人或一群(個)人,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必須由某種在原有制度安排下無法得到的獲利機會引起”*〔美〕科斯等著,劉守英等譯:《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第384頁。。在人民公社剛性制度的束縛下,農業剩余的絕大部分由國家掌握,社員之間的分配又幾乎平均,使農村基層和農民幾乎沒有獲得更多收益的機會。這就迫使農村基層自發地創制一種將社員勞動與農產量直接聯系的管理制度,以便在狹小的體制空間內實現多勞多得。永嘉縣首倡的“包產到戶”,湖南、河南和福建等地的“借田(地)渡荒”,安徽的“責任田”等各種各樣的包產到戶,與新時期的聯產承包在本質上有明顯的繼承關系,“制度變遷過程中,大多數制度安排都可以從以前的制度結構中繼承下來”*〔美〕科斯等著,劉守英等譯:《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第390頁。。筆者在相關研究中甚至發現,集體化時期以自留地為核心的家庭副業,“已經包含了后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最主要的制度因素”,為后者“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準備、改革思路和豐富的經驗。可以說,家庭聯產責任制,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家庭副業的完善和擴大化”*辛逸:《農村人民公社家庭副業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5期。。包產到戶在人民公社體制內醞釀、實驗長達30多年,其命運多舛,三起三落*包產到戶三起三落的演變過程可參見徐勇:《包產到戶沉浮錄》,珠海出版社,1998年。。在農民的預期收益大于推行包產到戶的風險及其交易成本的驅動下,包產到戶最終演變為后來的聯產承包。改革開放后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從公社時期的社隊企業進化而來的。有學者甚至肯定:“大多數成功的鄉鎮企業都是由‘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生產隊創辦的企業發展而來的。”*高默波:《高家村:共和國農村生活素描》,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87頁。所以,新時期農村各種新制度的創制與演變,“類似于一種進化的過程”*〔美〕科斯等著,劉守英等譯:《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第390頁。。
第二,人民公社時期尤其是在20世紀70年代,為新時期的農業發展打下了較為堅實的物質基礎,形成了農業基礎條件和技術的路徑依賴。改革開放前中國農業的生產條件已經有了很大改善。1957年至1982年的農村用電量增加282.6倍、農業機械總動力增加136.9倍、化肥用量增加40.6倍、機耕面積增加13.3倍、灌溉面積增加61.9%*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84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第169、175頁。。據陳錦華回憶,70年代,在李先念的主持下,“經請示周總理同意,增加到引進13套化肥項目。以后,又繼續引進,結合國內的國產化設備配套,大化肥項目總數達到33套,年產尿素1593萬噸。按照1比4—5的增產效果計算,1593萬噸尿素可增產稻谷近6500萬噸—8000萬噸”*陳錦華:《國事續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72頁。。在新時期糧食增產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雜交水稻,早在1964年就在湖南開始研究,“1975年,在數以百計的縣同時進行地區性的生產試驗;1976年,雜交水稻開始大田生產”*林毅夫:《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第138—139頁。。另外,現在很多地區的農田水利設施大部分也是集體化時代修建的。人民公社后期農業生產條件和農業技術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規定和限制著新時期“三農”制度與技術變遷的路徑與方向。
第三,創制新制度一定得考慮歷史上已有的制度因素與文化傳統,在此基礎上進行的制度創新才有可能扎根、生長。新時期的許多制度創新比如村民自治,其實際運行效果與制度設計的初衷相去甚遠。現在農村基層村委會及村民小組已基本被納入正式的政治制度及其運行邏輯之中,扮演著國家地方正式權力機關下派機構的角色。
主流史學將黨史劃定為革命、建設和改革三個歷史時期。對歷史學家來說,三者是一脈相承的,其連續性遠大于間隔性,后一階段承續著前一階段的方方面面。尤其是1949年絕不應該是中國革命的終結。有學者指出:“了解1949年前的中國是研究當代史的前提”,“對50年代進行歷史學的研究,應跨越1949年的間隔。所謂‘間隔’,即是將20世紀的歷史截為兩段,視彼此毫無關聯,而實際上一些歷史性的長時段因素仍在繼續發揮作用,并沒有因1949年而中斷”,因此,“研究歷史肯定需要關照兩個方面:變革是從何處出發的;延續在變革中的流變及其走向”*高華:《敘事視角的多樣性與當代史研究:以50年代歷史研究為例》,《南京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最近也有學者從不同視角強調1949年后中國革命在當代中國的延續及其路徑依賴*王奇生:《中國革命的連續性與中國當代史的“革命史”意義》,《社會科學》2015年第11期;張濟順:《國家治理的最初社會空間——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前期的上海居民委員會》,《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10期。。如果說將1949年作為中國革命的終點,很難理解新中國前30年以政治運動治理社會、促進經濟建設的話,那么將1978年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終結,也同樣無法透徹地解讀改革開放時期鄉村社會的制度變遷。本文主張,應該打破以1978年為界將新中國鄉村史截然劃分為兩個歷史階段的理念與范式,注重改革開放前人民公社的制度安排、社會建設和技術儲備對新時期鄉村社會經濟發展的深刻影響,將兩個歷史階段作為一個延續發展的完整演變過程進行研究。這應該是歷史學界研究新時期鄉村史的一個學術路徑。
(本文作者 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教授 北京 100872)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人民公社制度史稿”(10ADJ002)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