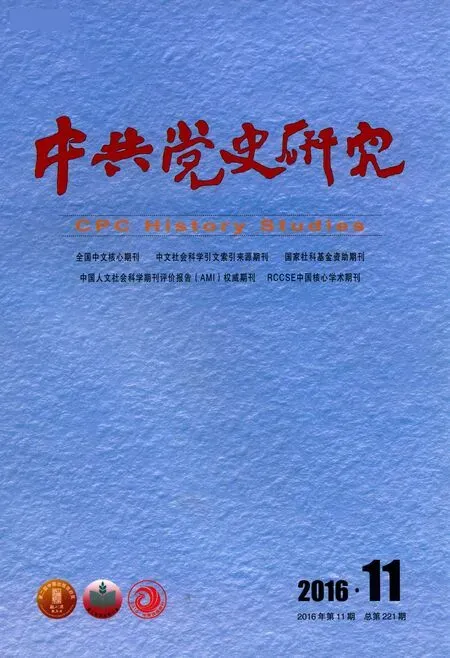國民革命語境中的中共政權口號及其階級意蘊
——兼與《從“平民主義”到“革命民眾政權”》一文商榷
于 化 民
?
·探索與爭鳴·
國民革命語境中的中共政權口號及其階級意蘊
——兼與《從“平民主義”到“革命民眾政權”》一文商榷
于 化 民
中共政權主張在大革命進程中幾經變更,其實質是對國民革命中階級關系和未來政權性質及階級構成判斷的變化。“平民政權”口號并未將資產階級排除在革命陣營和未來革命政權之外。“革命民眾政權”與前者在階級規定性上亦無原則上的不同,也稱不上黨內不同政權思想的整合。真正摒除資產階級于未來政權構成的標志,是中共五大“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權獨裁制”口號的提出。資產階級在五卅運動中的妥協和國民黨新右派的形成,是引起中共政權主張變化的主要政治因素,共產國際的有關指示則是導致變化的直接原因。
國民革命;平民政權;革命民眾政權
大革命時期中共政權口號的變化,實際上折射出黨內對于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特別是階級關系的不同認識。也可以說,客觀如實地分析考辨中共政權口號的內涵,可為準確理解大革命時期中共關于中國革命的基本思路與內在邏輯提供一把鑰匙。拙文《國民革命時期中共“平民政權”思想的演進軌跡》(《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12期)正是基于上述認識,對中共在國民革命中提出的“平民政權”口號作了初步的梳理考察,認為這一多階級聯合專政的政權主張,不僅是對中共二大所提出“民主共和國”的延展和深化,還成為中共從簡單照搬蘇俄式的無產階級專政轉向探索適應中國國情的國家政權理論的重要標志。新近讀到周家彬《從“平民主義”到“革命民眾政權”——大革命初期中共黨內政權思想的分歧與整合》(《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5期,以下簡稱周文)一文,亦是通過分析陳獨秀與瞿秋白政權思想的異同,提出黨內存在“國民本位”和“平民本位”兩種革命邏輯,最后在“革命民眾政權”名義下整合了分歧。周文對拙文某些觀點有所質疑,讀后多有啟發,細思之后仍有難以茍同之處,歸納為以下三個問題略作申說,以期引起學理上更為深入的討論。
一、“平民”與“平民政權”中是否包含資產階級?
周文主要質疑拙文的,是認為瞿秋白提出的“平民政權”為四大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階級、工人階級)聯合執政,并把瞿秋白的“平民政權”等同于中共三大提倡的“平民的民權”。既然要討論“平民政權”的問題,就有必要回歸歷史語境,簡要追溯一下“平民”概念的緣起與流變。
在中國傳統政治語匯中,“平民”被用來泛指與世族官宦相對應的黎民百姓。在歐洲近代資產階級革命中,則是指除貴族騎士以外的社會下層,主體是第三等級即資產階級。新文化運動以后,作為一個與“民主”密切關聯的近代政治術語,“平民”概念才真正在中國流行開來。在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中,李大釗是較早較多使用“平民”概念并提出“平民政治”口號的人。他在五四運動前發表的《平民獨裁政治》一文便提出:“平民政治的真精神,就是要泯除一切階級,都使他們都化為平民。”*《平民獨裁政治》,《李大釗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0頁。此后,又陸續在《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平民政治與工人政治》《平民主義》等文章中闡發自己的觀點。李大釗指出,“平民主義”源自“Democrocy”一詞,原意是指“人民的統治”。平常所說的平民政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乃是中產階級的平民政治。它是為中產階級裝潢門面,而特權政治卻在內幕中施行。中產階級的平民政治將發展為無產階級的平民政治,即“工人政治”。只有無產階級的平民政治,才是真實的純正的平民政治,而“純正的‘平民主義’,就是把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一切特權階級,完全打破;使人民全體,都是為社會國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須用政治機關以統治人身,政治機關只是為全體人民屬于全體人民而由全體人民執行的事務管理的工具”。*《平民主義》,《李大釗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70頁。由此看來,李大釗所說的平民政治就是民主政治,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涵義自不相同,而“真實的純正的‘平民政治’”是階級差別完全消滅之后才會有的一種理想政治。
繼李大釗之后,瞿秋白是中共領導人中較多談論“平民”問題的。剛剛回到國內的他,在1923年1月17日為《晨報》所寫的雜感中說:“中國真正的平民的民主主義,假使不推倒世界列強的壓迫,永無實現之日”,“全國平民應當亟亟興起,——只有群眾的熱烈的奮斗,能取得真正的民主主義,只有真正的民主主義能保證中國民族不成亡國奴”*《最低問題》,《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3頁。。他還指出,帝國主義出于吞滅中國的野心,與軍閥官僚等封建勢力相勾結,“決不愿有平民的民權運動建成真正的獨立國家”,而中國的平民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消滅封建制度,才能間接地給帝國主義以打擊,建立“平民的統一國家,平民的地方自治政體”。他把這種新的國家政權稱之為“平民的政權”“平民的共和國”。*《中國之地方政治與封建制度》《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各種方式》,《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33—34、81頁。由此可以看出,在瞿秋白所說“平民的民權”與“平民的政權”“平民的國家”之間,存在著緊密的內在聯系:一方面,平民通過爭取民權的斗爭去創建平民政權和平民國家;另一方面,平民政權和平民國家為實現平民民權提供政治和法律上的保障。
要準確地理解這一問題,還應當特別注意瞿秋白與1923年6月召開的中共三大和1924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一大的關系。中共三大的主要貢獻是確定了與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黨的工作中心此后轉向國民革命運動。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張太雷、瞿秋白三人負責中共三大的文件起草和會議籌備工作,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就是由瞿秋白起草的,其中明確提出“以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權”。黨綱草案既指出資產階級“茍且偷安”,極易向列強和軍閥妥協,同時又強調,在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軍閥壓迫之下,“大多數的中產階級和大多數的勞動平民便一天一天失掉了他們生活的保證”,“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與國際帝國主義及軍閥根本上不能不沖突;而勞動平民及無產階級的解放,尤其與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根本上不相容:國民革命之進行,是必不可免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139、136、140頁。。這個草案雖然經過陳獨秀修改,但出自瞿秋白筆下的“以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權”一句話得以保留。可以說,它反映了瞿秋白本人對政權問題的思考和認識。1923年8月,共產國際派鮑羅廷來華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瞿秋白成為鮑羅廷的翻譯兼助手,并且參與了國民黨一大宣言的起草。他在宣言起草委員會討論三民主義時提出:“國民黨的民主主義來源于其他一切先進國家民主運動的經驗,同時作了相應的修改。因此,除了所謂直接的人民權利之外,我們還實行直接的人民民主。就是說,全體公民不僅有選舉權,而且有倡議、否決和召回國家官員的權利。”*黃修榮:《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史》上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209頁。他的提議亦為正式文本所采納。
在此前后,瞿秋白接連發表文章為新三民主義造勢。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平民”成為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比如,他把國民黨稱作“平民的政黨”*《國民黨改造與中國革命運動》,《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288頁。、“代表大多數平民的利益而奮斗的政黨”*《國民黨與下等社會》,《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392頁。,把新三民主義稱作“現實的革命原則”,“是平民意志的結晶,是平民反對軍閥,反對帝國主義,農民、工人反對地主、資本家的意志之表示”,它“代表全中國平民的利益”,是“平民組織團結力量以達到革命的旗幟”*《中國革命史之新篇》,《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384頁。,把未來的革命政權稱作“真正的平民共和國”*《國民黨改造與中國革命運動》,《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288頁。。他還最先把新三民主義與平民政權聯系起來,主張民權主義就是要建立“中國平民群眾的政權,使政府真能代表全民族”,“國民黨所提出的三民主義是代表全中國平民的利益的,所以能組織平民,集中革命勢力,和反革命勢力作戰,這是國民黨應有的責任,也是平民應有的責任”*《中國革命史之新篇》,《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384頁。。為此,他號召“商人、農民、工人、學生、教育界”都來參加作為“平民的政黨”的國民黨,“凡是平民都應當為我們的將來——真正獨立自由的中國而奮斗”*《國民黨改造與中國革命運動》,《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288頁。。
在瞿秋白這一時期所寫的文章中,“平民”是個較為寬泛的概念,內涵也不固定。除了“平民”,瞿秋白還經常使用“勞動平民”一詞用以代指工人階級*《帝國主義的傭仆與中國平民》,《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18頁。,有時又把“勞動平民”與無產階級并提*《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117頁。。在大多數情況下,“平民”被他用來泛指處在被統治地位的“下等社會”,亦稱“下等階級”,以對應于“上等社會”和“治者階級”“智識階級”“上等階級”。在他看來,“各國的革命都是下等階級(平民)反抗上等階級的行動,所以革命黨必定是代表下等階級利益的政黨”,“國民黨始終是下等階級的政黨,是革命的政黨,是代表大多數平民的利益而奮斗的政黨”*《國民黨與下等社會》,《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390、392頁。。如此反復地強調國民黨的“平民”特色,強調建立“平民政權”,其用意不外乎配合國民黨對三民主義的重新解釋,拉近中共政權主張與新三民主義的距離,以適應國共聯合進行國民革命的現實需要。無論是“平民的政權”還是“平民共和國”,都與中共三大黨綱草案中的“平民的民權”是相通的,并非如周文所認為的那樣,是兩個“完全不同”、互不相干的東西。
政權口號的背后是對階級關系的分析與認定。“平民政權”是否包含資產階級,僅僅字面上的解析是不夠的,還要看瞿秋白是如何看待資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作用的。在寫于1923年6月的《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一文中,瞿秋白對近代以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現狀與特征,以及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態度及與國民革命的關系等問題作了深入分析,指出:“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導源于帝國主義的侵入,亦就不得不成為帝國主義的對抗力。這些對抗力之中,勞動階級固然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種種特性而尚弱,現時只有民族主義的覺悟;然而資產階級之弱更甚于勞動階級。外國資本的侵略卻正在日益加緊,自然而然促成反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中國的民族運動,得最宜于組織最易有團結的無產階級之猛進,當能聯合小資產階級,督促資產階級而行向民族革命;以至于與世界無產階級攜手,而促成偉大的長期的世界社會革命,徹底顛覆帝國主義”*《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108、90頁。。在中共三大關于國共合作的討論中,他把資產階級區分為小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兩種,指出盡管現在小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是不革命的,但為了自身利益,他們將會革命。不要害怕資產階級的壯大,因為與此同時無產階級也在壯大,我們不能采取與他們分離的辦法阻止他們的發展*《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468頁。。現在看來,這種區分方法過于簡單化了。所謂大資產階級主要是指依靠帝國主義的買辦勢力,這部分人本來就是革命的對象。在他們與以小商人、小作坊主、自由職業者為主體的小資產階級之間,還有著一個主要由工商企業主組成的中等資產階級。對后一部分人,還是要聯合他們一起從事國民革命。
三個月后,瞿秋白在《自民權主義至社會主義》一文中系統闡述了自己的國民革命觀。文章主旨在于肯定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也說到了資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瞿秋白指出,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制度,只有資本主義的發展能生出社會主義來,只有它能造成社會主義公有生產資料的技術基礎,能造出數量多而覺悟深的革命無產階級。因此,在資產階級社會還沒有成就的地方,“資產階級還能做革命的進取”的地方,無產階級應當和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君主諸侯及軍閥”,同時為工人階級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爭——建立資產階級的社會。民權革命的社會及經濟的內容,本來就是資產階級的,然而并不因此而對于無產階級沒有很大的利益。民權革命不但不消滅資本主義的基礎,而且擴充、推廣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民權革命不但代表勞工平民的利益,而且代表全資產階級社會的利益。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之下,資產階級之統治工人階級是不可免的。因此可以說,民權革命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多,而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少。然而,說民權革命絕對不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那卻是蠢話。*《自民權主義至社會主義》,《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194—195、201頁。此文發表于《新青年》季刊第2期,原題為《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收入作者自編論文集時,改為現標題。后來他還更加清楚地說過,平民中“包含了利益相反的種種階級”*《孫中山與中國革命運動》,《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3卷,第84頁。,分明就是指處在剝削者地位的資產階級和處在被剝削者地位的工人階級。
那么,民權革命對無產階級的利益體現在哪里?瞿秋白認為,沒有別的途徑可以使無產階級得到真正的自由,只有經過資產階級的自由和資產階級的進步。在封建軍閥之下沒有別的方法行向社會主義,只有完全的政治自由,民權主義的共和國。“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民權主義)的基礎上,社會主義的種子才能開始萌動”,“在民權主義的資產階級社會之中,無產階級方才有活動之自由及廣泛的政治運動之可能,——這是無產階級的成熟及經驗之必要的前提”,“參加并促進國民革命——是現在中國無產階級的職任,——在原則上,在實際應用上,在國內政治經濟上,都是絕無疑義的”。無產階級和農民階級在民權革命中愈有組織系統,愈集中,愈徹底,就能愈多地保證他們的利益。他還說,無產階級與其他平民在民權政權和共和主義方面是有統一意志的。無產階級應當引導最大多數的農民和小商人實行堅決的民權革命,以嚴厲手段鎮服君主派或軍閥派的反動,并且遏制資產階級的畏怯妥協,應把“平民之革命民權的獨裁制”作為民權革命的最近目標。無產階級的最后目標是社會主義,隨著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日益取得重要地位以至于領導權,到國民革命的最高度,很可以與世界革命合流而直達社會主義。*《自民權主義至社會主義》,《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195、222、207—209、221頁。
由此可見,在反帝反軍閥的國共聯合戰線醞釀和建立初期,瞿秋白是最早認識并始終堅持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發揮領導作用的中共領導人之一,也是他較早地看到中國資產階級在外國資本和封建軍閥面前有著“畏怯妥協”的天性。但是,至少在這一階段,他并未因此否定國民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并未否定資產階級是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的組成部分。斷言他此時已將資產階級排除在“平民”和“平民政權”之外,既缺少充分的文獻依據,也明顯有悖于中共三大確定的聯合戰線政策,邏輯上是很難說得通的。
二、“五卅”前后中共對資產階級認識的重大變化
如果說,中共領導人對于國民革命是反帝反軍閥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認識達到高度一致,那么最令他們感到困惑和糾結的,還是如何看待資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作用的問題,看法存在明顯分歧。就其基本傾向而言,仍以正面肯定居多,以強調團結和聯合為主。這種情形在孫中山逝世到五卅運動期間發生了明顯變化。
從性質上看,平民政權是包括無產階級在內的多階級聯合專政的政權,這是沒有疑問的。中共期冀通過國民會議的召集來實現這樣一種新式政權,認為舊的國會制“或者對于資產階級可以將就,而對于勞動平民絕對不能相容”,可以通過國民會議創造“代表真正大多數勞動平民的制度”,進而創造出“真正的民主政治”*《現代中國的國會制與軍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58、60頁。。中共設想的國民會議不是單純的議事機構,而是一種政權的組織形式,通過國民會議產生的政府是一個由工農商學各階層共派代表組成的聯合政府。在1923年8月、1924年9月、1924年11月發表的關于時局的宣言和主張中,中共一再號召社會各界迅速召集國民會議。北京政變后,孫中山決定接受馮玉祥邀請北上,并在《北上宣言》中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召集國民會議兩大主張。中共隨即發起大規模的國民會議促進運動予以配合。國民黨本來就是由不同的階級和利益集團構成,成分龐雜。還在孫中山在世時,張繼、謝持等國民黨老右派即蓄意生釁,排擠中共。孫中山遽爾病逝,不但使方興未艾的國民會議運動失去了一面旗幟,更讓國共聯合戰線的內部危機凸顯出來。以孫中山學生自居的戴季陶,接連發表《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個小冊子,公開質疑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以維護“純正的”三民主義為名,向共產黨人發起攻擊。除來自戴季陶主義的理論挑戰,資產階級在五卅運動中的表現同樣引起共產黨人的警覺。五卅慘案發生后,上海人民在中共的組織領導下,實行全市的總罷工、總罷課、總罷市,迅速發展成為席卷全國的反帝愛國運動。起初對運動抱同情和支持態度的上海上層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和軍閥的鎮壓面前開始妥協和屈服,無條件地結束總罷市,還通過扣壓各地捐款逼迫罷工工人復工。資產階級在五卅運動中的所作所為,讓中共不得不重新審視資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實際作用。
作為中共最活躍的理論家,瞿秋白積極投身于同國民黨右派的論戰,加大了對資產階級的批判力度。他重申,在反帝反軍閥的國民革命中,基于共同的利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能夠建立聯合戰線,“這種共同利益若仍舊存在,敵人的離間利誘是難于破裂這聯合戰線的。國民革命尚未成功,則各階級間的共同利益尚屬存在,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自然能夠維持下去”*《三論階級斗爭——甚么是階級?》,《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4頁。。“中國的國民革命是各階級的,城市中的小商人(有時大商人也來參加)、工人、農民,以及革命的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各階級的人們都需要這樣的革命”,當然,“革命的隊伍里也有民族資產階級參加,他們是與買辦階級不同,需要反對帝國主義的,可是與工人、農民大不相同……他們恐怕工農的力量大了,他們將因此受害,不能盡其所欲地來剝削工農,因此他們對于革命終有些疑懼”。工人并不怕資本主義的強大,資產階級卻在怕工人勢力的增高。所以,“在國民革命中資產階級參加,工人也參加,但是國民革命的指導權必定不能使之落入資產階級的手里”。*《國民革命中之農民問題》,《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4卷,第391、392頁。這是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妥協性有很深的經濟基礎,如果資產階級來領導革命,很快便會和敵人妥協,而客觀上工農群眾已經要求革命,積聚實力,準備決死的斗爭,自然而然只有工人階級和農民聯盟來做國民革命的先鋒和領導者。因此,這一革命雖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卻不會是資產階級的。*《北京屠殺與國民革命之前途》,《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4卷,第39、40頁。
國民黨右派認為階級斗爭學說不適用于國民革命,工人階級的斗爭會把資產階級嚇得走向反動,進而分裂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瞿秋白反駁道,國民革命中的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的,中國工人階級承受著外國資本家和本國資本家的雙重剝削,自然不能不開始斗爭,這種斗爭從一開始便是革命的階級斗爭。難道中國工人階級應當忍受中國資本家的剝削,同時又能反抗外國資本家的剝削而參加國民革命?中國資產階級要利用工人的力量爭民族的解放,便應當犧牲自己的目前利益:工人反抗外國資本家的剝削,當然也反抗中國資本家同樣的壓迫;中國資本家不能自動的減輕壓迫,便只有受反抗。假使中國資本家因受反抗而竟反動,以至于勾結軍閥、帝國主義,那工人階級的階級斗爭就尤其必要。他還指出,共產黨在國民革命時代并未主張無產階級獨裁制。真正的民權主義,只有擁護保障真正平民的政權。共產黨所主張的,正是在國民革命時代必須革命的,各革命黨聯合的,對于保皇黨、帝國主義黨、軍閥黨、買辦黨、土豪黨,對于一切反動勢力的獨裁制——國民革命的革命派獨裁制。*《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國民黨右派與國家主義派之分析》,《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3卷,第467、469、479—480頁。瞿秋白認為,中山艦事件表明代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內新右派的形成,提醒有出現新的軍事專政的危險,“中國稚弱的資產階級,現在既然還留在革命營壘之中,始終需要軍力來代表他。新右派暫時和帝國主義妥協之可能較少;他在既得相當的領袖地位之后,為求鞏固此地位起見,不得不向前進取幾步——北伐。因此,北京屠殺后在全國范圍內之革命聯合戰線之中,自然還包含著民族資產階級,甚至于民族資產階級竟還保持著部分的領導權。于是,北伐的革命戰爭,便可以說是代表這一聯合戰線反抗買辦階級統治的戰爭”。他有意識地使用“革命平民”一詞,將其他革命階級與資產階級區別開來,“革命平民——小資產階級、農民、無產階級之參加、贊助革命戰爭,其傾向必然與民族資產階級不同。平民是要以實現國民會議為旗幟而戰;革命平民不但反對軍閥買辦的專政,并且反對民族資產階級之新式的軍事專政”。*《北伐的革命戰爭之意義》,《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4卷,第376、378頁。在瞿秋白看來,資產階級與其他革命階級的政治分野日趨明顯,其妥協性會給革命造成嚴重危害,他對可能出現國民黨新軍閥的警示更是有預見性的。
與瞿秋白看法類似的還有鄧中夏和惲代英。鄧中夏鮮明地主張,無產階級參加國民革命不是附屬于資產階級,應當通過斗爭爭取自己的階級利益。這不僅包括政治上的民主權利和生活待遇的改善,還包括政權的取得。在這個過程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是不可避免的。他還是把以帝國主義和軍閥為對象的國民革命和以資產階級為對象的社會革命作了區隔:“資產階級固然是我們的仇敵,而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尤其是我們目前最厲害的兩個仇敵。我們必得參加國民革命先打倒這兩個最厲害的仇敵,得到初步的解放,再進而實行社會革命,打倒資產階級,以得到全部的解放。”*《勞動運動復興期中的幾個重要問題》,《鄧中夏全集》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38頁。在國民革命階段,基于“某一共同目標即共同利益”而“共同行動”的各階級聯合戰線是必不可少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國際帝國主義一面摧毀中國的手工業與農業,一面又阻止中國實業的發展,工農商學各階級均受其困,各階級因其民族境遇之相同,各階級利益又不期然而然有趨于共同之一點,因此我們可以斷言必不因其階級間部份特殊利益之故,而致限制與障礙此一聯合戰線之建立與成功”*《工農商學聯合戰線問題》,《鄧中夏全集》中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81頁。。惲代英也提出,無產階級要為建立真正的平民革命政權而斗爭,“我們心目中的國家,是為抵御國際資本主義的壓迫而存在的;我們心目中的政府,是為保障無產階級平民的利益而存在的”*《答〈醒獅周報〉三十二期的質難》,《惲代英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1頁。。無產階級要聯合資產階級反抗帝國主義及軍閥,“現在我們不問資產階級是否一定要反動的,我們應該聯合他們反抗帝國主義者及軍閥,所以資產階級只要在不壓迫農工的時候,在國民革命的運動上總是友軍。這一點,共產黨也是看得很清楚的。有人說共產黨不要聯絡資產階級來實行國民革命,然而過去的事實證明最努力聯合資產階級的,還是共產黨”*《孫中山主義與戴季陶主義》,《惲代英全集》第7卷,第364頁。,不過,“大商人,資本家,名流,學者,律師,教職員,一切在社會上所謂比較有地位或者自以為有地位的人,常常是反革命的”*《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惲代英全集》第7卷,第195頁。。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也對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及其根源進行了剖析,強調要對資產階級開展有原則的斗爭。毛澤東指出,中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出發點完全不同:“他們的革命是為了發財,其余階級的革命是為了救苦;他們的革命是為了準備做新的壓迫階級,其余階級的革命是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將來永無壓迫自己的人。”他們的目的是“能夠于革命成功后發展成壯大的資產階級,建設一個一階級獨裁的國家”。*《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革命前途的影響》,《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頁。為此,他們對民族革命采取了矛盾的態度,“他們在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但是當著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于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頁。。劉少奇認為,中國資產階級因受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壓迫,有參加國民革命的可能,但資產階級參加國民革命終究是妥協的,不能徹底的。當無產階級起來參加革命時,或要求生活改良時,資產階級就馬上反動起來了,“工人階級在某一個時候,即在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沖突最厲害的時候,應與資產階級合作,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以增強反帝國主義運動之勢力。但當資產階級一有妥協之傾向,或壓迫工人運動時,工人階級應極力反對,以防備資產階級騙賣自己”*《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地位與職工運動方針》,《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頁。。周恩來著重強調:“在革命的長期爭斗中,民族資產階級總是富于妥協性,小資產階級也常搖擺不定,只有無產階級是最不妥協的革命階級。”在工農與資產階級發生矛盾和斗爭時,共產黨必須站在工農方面,代表工農利益,“共產黨領導工農群眾參加國民革命,其目的是在打倒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半封建勢力,其要求不能超過民主政治的范圍。但當著資本家壓迫工人謀生活改善的正當要求,或是地主聯合一切舊勢力摧殘農民謀解放的運動時,共產黨必須站在工農群眾方面,為解除他們的痛苦奮斗到底……這并非超過國民革命,而實是推進國民革命”。*《現時政治斗爭中之我們》,《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頁。
就連一向十分看重資產階級的陳獨秀,也對資產階級的表現感到極度失望。他坦承,“五卅運動起時,我們絕不死守成見,我們頗幻想在此次全國民族運動奮起大潮中,中國資產階級或不能不相當的與一切革命的民眾合作了。可是在事實上,中國資產階級對于此次民族運動的態度,使我們的幻想終于是一個幻想”,“幼稚的中國資產階級,在原則上,他被壓迫在帝國主義及國內軍閥兩重勢力之下,應該有革命的要求;然而在實際上,他已是全世界反動的資產階級之一部分,他所有應有的革命要求,很容易被他階級的反動性消滅下去”*《中國民族運動中之資產階級》,《陳獨秀著作選編》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1頁。。國民黨右派不承認階級斗爭,陳獨秀在《給戴季陶的一封信》中針鋒相對地加以批駁:“不但不能否認中國現社會已經有比前代更劇烈的階級爭斗這個事實,也并不能否認中國民族爭斗中需要發展階級爭斗這個矛盾的事實。”他列舉歷史事實證明,真正的革命力量是工農階級。工農群眾的力量,只有通過階級斗爭才能集中和發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張停止階級爭斗,便是破壞民族爭斗之主要的力量”。*《給戴季陶的一封信》,《陳獨秀著作選編》第3卷,第504、505頁。以戴季陶為代表的國民黨新右派“一開始既帶有反動的傾向”,“反對階級爭斗,反對蘇俄,反對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左派,并且反對國民政府,客觀上便實實在在的幫助了反革命和帝國主義者”。當然,陳獨秀還是沒有把新右派和老右派(指西山會議派)等量齊觀,他認定老右派已經“背叛了國民革命,站在敵人那邊了”,而對于新右派,仍“應與之在每個行動上聯合作戰”。*《國民黨新右派之反動傾向》,《陳獨秀著作選編》第3卷,第550、552頁。
與此同時,中共對于政權問題有了一個新說法,即受到周文格外重視的“平民的革命政權”。這個提法最先出現在陳獨秀1925年8月下旬發表的《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斗》一文。文章說:“反帝國主義爭斗的過程,不能和力爭民權自由的爭斗分開;民族的建立正在反帝國主義爭斗的過程中;而反帝國主義的爭斗,沒有平民的革命政權,不但不能得著勝利,并且連爭斗的力量都不容易集中。”工人階級應聯合一般平民和同情民族運動的軍人,與用武力破壞民族運動、蹂躪民權的奉系軍閥斗爭,“一直到平民的革命政權之實現”。*《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國主義的爭斗?》,《陳獨秀著作選編》第3卷,第500頁。不久他又作了進一步闡說,強調共產黨取得政權,乃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事,在國民革命時代,不會發生這類問題。不但在國民革命中中共不會有向左超過民主主義的傾向,即使是國民革命成功后轉入建設時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眾政權,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并且還不是工農政府。那時,在革命的民主的民眾政權之下,中國的資本主義當然要發展起來。也只有到那時,真正中國的資本主義才能夠自由發展。*《我們現在為什么爭斗?》,《陳獨秀著作選編》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3頁。10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確認了“平民的革命政權”的口號。會議決議指出:“最近的革命運動,當然不僅是反對帝國主義,而且是力爭革命民眾政權的實現”,“現時這一歷史的時期”已是“全國民眾起來爭中國解放和民眾政權實現時候”*《中國現時的政局與共產黨的職任議決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463—464頁。。中共作為無產階級的指導者,應當提出包含“革命民眾政權”的政綱,為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指出前進的道路。仔細體味陳獨秀的文章和中央的決議,其立論的邏輯還是從國民革命反帝反封建兩大任務著眼的,強調要把兩者結合起來,并非表達未來政權階級構成的變動。決議同時使用“革命民眾政權”與“平民政權”兩個概念,沒有著意加以區別,也可從側面證明這一點。
對中共而言,即便已經認識到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也并不代表馬上與資產階級分道揚鑣,基于策略上的考慮,還是要盡可能地拉住資產階級,將其留在聯合戰線內。1926年2月的中共中央特別會議指出,資產階級在“漸漸的脫離民眾的國民運動”,然而他們希望以出賣群眾運動換取帝國主義的讓步,只能是自己騙自己,“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真正妥協,暫時還沒有可能。所以以后資產階級的對抗帝國主義,還是不可免的”*《關于現時政局與共產黨的主要職任議決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53、54頁。。7月,陳獨秀在中共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上所作的報告,對此有更加詳盡的分析。報告指出,國民革命的前途不外乎兩種:要么是工農階級領導小資產階級,推動資產階級,以革命手段達到民族的資本主義之建設;要么是買辦性的資產階級拿住小資產階級,并聯合買辦階級,與帝國主義妥協,撲滅革命運動。中共要力爭第一種前途,就不能不“從帝國主義奪取中國的資產階級”,“鞏固民族運動的聯合戰線”。資產階級不過是想用改良的方法向帝國主義要點東西,一旦他們的要求得到滿足,便存在著與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妥協的可能性。可是,資產階級“在民族民主的革命運動中,乃站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依現時世界政治環境,中國的國民革命若沒有資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必陷于異常困難或至于危險。我們應該明白了解現時中國的革命,毫無疑義的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民族民主革命,因此在估計革命運動之社會的力量中,便非要不要資產階級參加的問題,而是資產階級是否參加及是否參加到底的問題”。鑒于此,中共應當采取的策略是:“一方面努力拉住小資產階級,使之接近工農群眾,而不完全為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所統治,以與資產階級爭此革命運動的領導地位,以防其將來之妥協;一方面極力鞏固各階級的聯合戰線,促進資產階級之革命化,明知其為將來之敵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敵人,而現在卻不可不視為友軍,且為有力之友軍,以共同打倒國外的敵人(帝國主義)和國內的敵人(半封建勢力)。”*《中央政治報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第170—171、168、169頁。既不能“妄信”資產階級可以革命到底,不預防將來的危險,也不能過早地敵視他們,逼他們為帝國主義利用。換句話說,就是對資產階級既要聯合,又要斗爭。
三、曇花一現的“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權獨裁制”
戴季陶主義的出現,資產階級在五卅運動中的妥協,中山艦事件和國民黨新右派的形成,國內政局發生的這一系列嚴重變化,加劇了共產黨人對資產階級的疑慮和不滿,促使他們不得不重新評估資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作用,并不得不重新思考資產階級在未來政權中的位置。但是,直接推動中共決定對政權主張作出重大變更、對未來政權的階級構成加以新的界定的,卻是來自于共產國際的指示。
中國革命是1926年冬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的中心議題。此時布哈林已取代季諾維耶夫,實際主持共產國際的工作。他在會議上的發言系統闡述了關于中國革命的三階段理論,要點是:在革命的初期即第一階段,在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等隊伍中尋找支點的一部分資產階級,即開明的民族資產階級、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大學生,是革命的極其重要的動力之一;第二階段,無產階級成為最重要的政治力量,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結合在一起;目前是第三階段臨近的時刻,標志是大資產階級被排除在外,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之間結成聯盟*《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4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第18—19頁。。斯大林在會議上發表《論中國革命的前途》演說,專門談到中國未來政權的性質問題:“我以為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就其性質來說,大體上將類似我們在一九○五年所說的那種政權,即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之類的政權,然而有一個差別,這主要將是反帝國主義的政權。這將是中國走向非資本主義發展,或者更確切些說,走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渡政權”,“中國共產黨可不可以參加未來的革命政權呢?不僅可以而且必須參加。中國革命的進程、它的性質、它的前途都雄辯地說明中國共產黨必須參加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張仲實、曹葆華譯:《列寧斯大林論中國》,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99、100頁。。會議通過的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貫穿了斯大林、布哈林的觀點,指出中國革命的結果,不一定造成使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政治環境;這個革命國家,不會是純粹的資產階級的民權國家,而將成為無產階級、農民以及其他被剝削階級的民權獨裁制的國家,將成為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發展之時期中的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政府*《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體會議關于中國問題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第671—672頁。。
國際新決議1927年1月送達上海后,引起了中共中央內部的不同反應。彭述之對決議內容表示反對,陳獨秀的態度有所保留,只有瞿秋白“無條件接受決議”*《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4卷,第131頁。。依據決議的基本精神,瞿秋白寫下了7萬余字的長文《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系統闡述對中國革命一系列根本問題的看法。瞿秋白反復強調,中國革命并不是無條件的資產階級性的革命,而是有條件的資產階級性的革命,“中國革命雖是資產階級的中國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然而農民的徹底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性的革命要求,必定和世界的中國的無產階級之社會主義要求相結合,而形成直接從國民革命生長而成社會革命的革命”,“就是‘一次革命’直達社會主義,‘從民權主義到社會主義’!”*《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4卷,第487、484頁。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角色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基于自身利益,民族資產階級有參加革命的可能,并且會力爭革命的領導權,以造成與帝國主義和地主階級妥協的資格。民族資產階級一旦爭得領導權,就會停止革命,造成一個形式上的獨立國家。可是,帝國主義仍能繼續支配中國的一切經濟,中國經濟就會變成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庸,民族資產階級就會代替現在的官僚地主階級,做帝國主義的“政治買辦”。為了避免這種結果的出現,無產階級就要與民族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要爭取工農小資產階級的群眾以至城市貧民及兵士,不斷打擊民族資產階級妥協主義的影響,隔離民族資產階級而使之孤立,“要用‘勞工階級的方法實行國民革命’,以蘇維埃的方法創造國民會議制度的平民共和國”。*《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4卷,第527頁。鄧中夏則指出,中國的革命政權即非土耳其式的資產階級政權,也不是俄羅斯式的無產階級政權,而是“中國自己的第三種形式”,這就是“一個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聯合的民主主義的專政。這個專政是將一切被壓迫階級——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聯合在一塊,一方面要消滅一切封建殘余,另一方面繼續反帝國主義的奮斗,成一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政權。這個聯合政權的建立,使革命不落在資產階級領導向資本主義的道路發展,而在無產階級領導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發展”*《一九二六年之廣州工潮》,《鄧中夏全集》中卷,第1260頁。。陳獨秀也不由自主地受到國際新決議的影響,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國民革命的前途,一種“是由工農及其他被壓迫剝削階級之手實現國民革命而行向社會主義”,另一種“是由資產階級之手聯絡一切反動勢力,在國民革命的假招牌之下,回復到帝國主義的統治”,而“只有工農及其他被壓迫剝削階級統治的國家,才能夠真正脫離帝國主義之統治,才能夠力圖非資本主義的經濟建設,才能夠不一定經過再度革命方式而行向社會主義的社會”*《答沈濱祈、朱近赤(國民革命之歸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4卷,第268頁。。這個表述顯然與他之前主張的“二次革命論”有所不同。
受共產國際委派,羅易率代表團前來傳達貫徹執委會七大決議,指導中共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五大召開距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已經過去半個月。由于共產國際和中共一直把蔣介石看作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其公開叛變似乎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觀點,即民族資產階級已經背叛革命。國際代表團實際上成為中共五大的主導。羅易在大會上多次發表講話,對國際新決議的相關問題作出說明。他在談到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時說,殖民地革命的發展不可避免地要超出資產階級的領導,革命領導權要轉到非資產階級人物手中。在資產階級領導下,國民革命將同帝國主義妥協而告結束,中國會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基地,從而有利于穩定資本主義。要取消資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把領導權轉到更加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聯盟)手里。當消滅封建主義的任務不是由資產階級分子而是由更加革命的階級領導的殖民地革命所完成時,那么消滅封建主義的目的就不再是為了建立資本主義。它開創了一個直接走向社會主義的非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時期,“中國革命客觀上只有一個前途:非資本主義發展前途。只有當革命的主觀力量不能發揮他們的作用時,才會失去這個前途”。*《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5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第397、399、405頁。在講到中國未來的政權形態時,羅易又說,中國革命“是一種嶄新的革命方式,將建立一種新型的革命政權。因為革命是在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聯盟領導下進行的,在一定時期革命政權就不能是無產階級的政權。它將是小資產階級政權,確切地說,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政權”。革命所建立的以這三個階級為基礎的政府,就不是一個階級的專政工具,而是三個階級的專政機關,是民主專政的機關。這種政權的性質與無產階級專政有區別,是一種介乎民主主義(即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之間的政權形式。無產階級是這個政權中的決定性因素,它將防止民主主義變質的危險。革命的發展已建立了一個客觀上具有民主專政性質的政府,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都要負責切實運用這個革命政權機構,為加強非資本主義發展和實現社會主義而斗爭。*《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5卷,第403—404、412—413、405頁。他所說的這個“客觀上具有民主專政性質的政府”,顯然是指由國民黨左派主導的武漢國民政府。
陳獨秀所作的大會政治報告,是根據羅易提供的提綱起草的,自然遵從了國際新決議的基調,但從中很容易發現在對待資產階級問題上的自相矛盾。報告一方面揭示了民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妥協性,斷定“資產階級不僅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甚至也不會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只要帝國主義者和軍閥作出某些讓步,資產階級左派就會叛變革命”,并且判定,四一二政變后大部分資產階級叛變了革命;但另一方面又說:“雖然資產階級是反革命的,但我們要吸收他們參加民族運動,不僅要吸收小資產階級,而且要吸收大資產階級。”*《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5卷,第351頁。可以看出他在執行國際決議和堅持個人觀點之間左右為難的窘迫。他還說,現在還不應把武漢政府看成是工農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專政,這個政府只是走向工農和小資產階級民主專政的途徑。我們必須利用這種機構,以便今后建立起工農和小資產階級的政府,并進而走上工農和小資產階級民主專政的道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5卷,第358頁。這也顯現他與羅易對武漢政府性質判斷上的差異。涉及資產階級與未來革命政權的關系問題,中共五大通過的文件和決議主要闡明了以下觀點。
第一,靠中國的資產階級不可能實行徹底的土地革命。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任務之一,也是國際新決議對中共提出的要求。這個任務靠資產階級是無法完成的。原因有二:一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國,資產階級并未形成一個反封建勢力的成分;二是資產階級是從地主階級產生出來的,依然同地主階級保持親密的結合,甚至變成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民眾的工具(如買辦)。由于中國的資產階級與剝削農民的勢力有密切的聯系,他們仇視農民革命,不但不能為民權自由而奮斗,反而作民權自由的敵人,更不能完成土地革命以促進反帝國主義的斗爭。*《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64—65頁。
第二,革命發展到一定階段時,資產階級的妥協與背叛是必然的。從五卅運動起,無產階級開始為反帝國主義斗爭的領導權而斗爭。這個斗爭建立了廣州革命的國民政府,獲得暫時的成功。封建的及資產階級的分子,看見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反帝國主義斗爭將走得太遠,客觀上危害了他們的階級利益,于是開始用全力使民族解放運動移轉到他們的指揮之下。目前中國革命已經進入到第三階段,即封建分子、大資產階級已經成為帝國主義的工具,與帝國主義勾結起來反對革命。*《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第50、49頁。資產階級因不能阻滯無產階級和民權勢力所推動的國民革命運動,終竟破壞了革命的聯合戰線。蔣介石所領導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就是想用軍事的勝利統一中國,然后與帝國主義妥協,使中國大多數民眾仍被剝削。*《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第101頁。
第三,今后的革命動力將是無產階級、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在中國革命的第三階段,“革命勢力之社會基礎是無產階級,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的聯盟。在這革命的聯盟之中,無產階級將實行其領導權”。中共過去忽略了與資產階級爭取革命領導權的斗爭,今后的迫切任務是繼續爭奪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建立一個左的包含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第49、50—51頁。革命要在堅決反抗反革命聯盟的斗爭中,更加向前發展。共產黨必須領導勞苦群眾反對封建資產階級等反動派,“中國革命將要在工農小資產階級聯合政權之下,向非資本主義前途發展”*《職工運動議決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第74頁。。
第四,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權獨裁制的政權。“中國的國民革命已經沖破了資產階級式的民權主義之限制”*《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第100頁。。現在革命階段的特質是需要建立一個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權獨裁制。只有這個政權以無產階級做領導,才能解決現在革命中的重要問題,并引導革命向非資本主義之發展方面進行。*《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體會議關于中國問題決議案〉之決議》,《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第47頁。國內外的客觀條件都利于中國革命發展到工農小資產階級民主獨裁制的階段。依工農小資產階級三個階級的本性,國民革命的政體應當是民權的,可是對其他階級必須是獨裁的。凡是不和革命站在一起,并且反對革命的,都應當以無情的手段加以對付,這是國民革命中的唯一原則。*《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第106頁。
至此,“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權獨裁制”的政權主張,通過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決議的形式,得到正式確立。這表明,中共徹底拋棄了曾經是革命同盟者的資產階級,將其歸入反革命的陣營,從而否決了在未來國家政權中給資產階級保留位置的可能。中共五大對當時階級關系的分析是不科學和不符合實際的,其中最大的問題,正如李維漢后來所指出的,是“沒有把叛變革命的大資產階級和雖處于動搖中而仍然應該盡可能爭取的民族資產階級區分開來,將蔣介石的叛變看作‘是代表了一個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將中等商人劃入小資產階級,并將小資產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同大資產階級混同看待,這種階級劃分是錯誤的”*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第85頁。。這固然與中國資產階級來源和成分復雜、經濟利益和政治面目差別極大,客觀上又無法提供一個科學的劃分標準有關,更主要的原因則是中共當時的革命理論和實踐水平不高,在階級分析中常犯“公式化”“定型化”的毛病,易為資產階級不同派別代表人物的言論迷惑,而忽視了他們轉變政治立場和態度的可能。據此制定的政權主張,包含了自身難以克服的缺陷。就在“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權獨裁制”提出后兩個月,曾經的國民黨左派代表汪精衛在武漢發起“清共”,與蔣派實現合流,由是小資產階級也被認為背叛了革命,從革命陣營中剔除出去。革命動力從廣州時期的四個階級聯合,變為武漢時期的三個階級聯合,到南昌起義再變為兩個階級的革命,進入創造工農蘇維埃政權的時期。由于從提出到完結只有區區兩個月的時間,很難說“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權獨裁制”口號在客觀上發生了多大作用。
四、幾點認識
綜上所述,對于國民革命時期中共政權主張的變化,筆者與周文有些看法是相同或相通的。其一,都承認中共主要領導人陳獨秀和瞿秋白的革命思路是不同的。姑且不論是不是如周文所說存在國民本位和平民本位的兩種革命邏輯的區別,兩人在革命路徑選擇上的確表現出明顯差異。其二,都認可中共政權主張在大革命中有逐漸激進化的傾向。其三,都同意對資產階級看法的變化是導致中共政權主張變化的基本因素。至于與周文的歧異,可大要歸納為如下幾個方面。首先,“平民的民權”和“平民政權”并非“完全不同”,其階級內容是一致的,資產階級是包括在“平民”和“平民政權”范疇中的,“平民政權”就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權。其次,中共對資產階級看法的變化不是始自平定廣東商團,商團早就被判識為買辦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從一開始就是國民革命要打倒的對象。中共四大已經清楚地指明了這一點。能夠表明中共對資產階級看法陡變的征象,是對戴季陶主義的批判和五卅運動后對資產階級兩面性的揭露。再次,中共將資產階級排除在未來政權構成之外的想法,不是萌生于1923年6月的中共三大前后,亦不是確定于1925年10月的中共中央擴大執委會會議,中共政權主張的實質性改變發生在1927年四五月間召開的中共五大,其標志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權獨裁制”的提出。最后,筆者以為,并不存在如周文所說的在“革命民眾政權”口號下的政權思想“整合”。周文的觀點能夠成立,至少需要幾個前提:一是“革命民眾政權”與之前的“平民政權”(有時也稱作“平民革命政權”)性質尤其是階級規定性有所不同,屬于另外一種政權主張;二是“革命民眾政權”與之后的“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權獨裁制”性質尤其是階級規定性相同,屬于同一種政權主張;三是“革命民眾政權”口號提出后,為全黨普遍接受,全黨認識都統一到這個口號上,并通過一定形式(如中央正式決議、宣言、文告等)表現出來。從史實和文獻看,這幾個方面的證據都不充分,斷定發生過這樣的“整合”未免有些言過其實。
(本文作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北京 100006)
(責任編輯 吳志軍)
The Slogan and Class Implication of the CPC’s Political Power in the Context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nd A Discussion with the ArticleFromthe“CivilianDoctrine”tothe“RevolutionaryPeople’sPoliticalPower”
Yu Huamin
The claim of the CPC’s political power experiences many changes in the revolution process, and its essence is the change of the judgment on class relations in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the nature and class constitute of the future political power. The “civilian power” slogan doesn’t exclude the bourgeois from revolutionary camp and the future revolutionary regime. The “revolutionary people’s political power” has no differences of principle in the provisions of the class from the former, and can not be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political ideas in the party. The mark of excluding the bourgeoisie from future regime is the proposal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and the small bourgeoi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slogan in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bourgeoisie’s compromise and the form of the new rightist in the May 30th Movement, is the major political factor causing the changes of the CPC’s political power claim an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s instructions are the direct cause of changes.
D231
A
1003-3815(2016)-11-01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