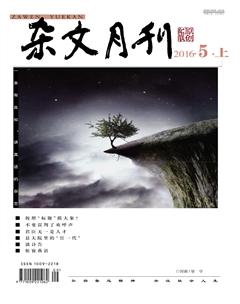我們如何對待遺產
柳士同
遺產通常指的是人死后留下的可以繼承的財產及其相關權益。不過,遺產這個詞的詞義也時常延伸和擴大,還泛指國家、民族乃至全人類留下的財富。這類遺產往往以文化遺產命名,而文化遺產呢,又可分作有形與無形兩種,通稱為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按此說法,個人和家庭的遺產是否也應有有形與無形之分呢?對于個人和家庭來講,除了財產之外,還有好多非物質的東西,比如家世、教養、名聲等等。當然,這類遺產,除了著作權尚有五十年的期限外,其余的則可由整個社會繼承。倘若是公眾人物,特別是名人,這類“遺產”乃是屬于整個社會的,它們已然是“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所謂的傳統文化,說白了也就是由無數群體和個人的文化遺產融匯而成。
那么,對于祖輩留下的遺產,無論是屬于個人的還是社會的,無論是物質的還是非物質的,都存在一個如何對待的問題——是否值得繼承,又該如何去繼承?
對于私有財產的繼承,由財產的主人來決定,當是無可非議的。像巴菲特和比爾·蓋茨那樣宣布將遺產的絕大部分捐贈給慈善事業,還有扎克伯格,為祝賀自己的第一個孩子降生而將股產的99%(約450億美元)捐給慈善事業,這些善舉無疑最值得世人的敬重。而有些富豪把自己的財產留給家人,那也無可厚非。
公共財產可就不容某個人或某些人隨意處置了。比如人類歷史文化遺產,像古代的建筑、名人的故居等等,不是說想拆就拆、想改建就改建的。這些物質文化遺產一旦毀掉,即使復制了也都是贗品,根本就不能再稱其為“遺產”。至于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繼承,無論個人家庭的還是國家民族的,情況就更加復雜了。比如當今最為某些人所津津樂道的傳統文化,作為這種文化的載體,典籍、文物之類,當然要一個不少地保存下來,但對它們所承載的文化內涵,卻不能不認真地加以鑒別和挑選,既不宜輕言“乏善可陳”,也不能“言必稱傳統”。就像魯迅先生所比喻的“祖上留下的大宅子”,我們既不能“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燒光”,更不能“欣欣然的蹩進臥室,大吸剩下的鴉片”。
但凡遺產,無論是物質的還是非物質的,往往是家世越顯赫、財富越多、名聲越大,遺產也就越大越豐厚。不過,就無形的非物質遺產來講,則未必與有形的物質遺產成正比了。這種無形的非物質遺產我們姑且稱其為“精神遺產”吧。正因為它屬于精神層面,即使時代變了身份變了,其精神遺產依舊可以代代相傳,自覺或不自覺地被后人承繼下來。比如貴族精神,盡管自周代“三世削爵”以后,傳統貴族就幾乎不復存在,但其精神卻并未泯滅。尤其是近百年來,隨著東西文化的交流,受歐美貴族精神的影響和熏陶,這一珍稀的精神在相當一批人當中都不同程度地得以傳承。當然,這其中也不乏“偽貴族”,自以為出身名門,祖輩曾是當地豪紳或封疆大吏,便人模狗樣地“貴族”起來,還時不時以所謂的家風家教自詡。殊不知即使錢多到七八位數,官升到廳局級省部級,其文化內涵也未必能跟“貴族精神”搭得上界。與“貴族精神”相對的是“流氓精神”,這種精神也并非只有流氓才具備。流氓繼承了祖輩父輩的流氓精神并不奇怪,怕的是不是流氓,或者祖輩父輩曾經是流氓,到他這一代早就闊起來了,或成為土豪或成為官員或成為所謂的專家教授,可那渾身的痞子氣實在令人不齒!不過,對于國人來講,普遍的倒是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精神”,那些偽貴族真流氓大致也可歸于這一類。
遺產再多再好也未必能一代又一代地繼承下去,遑論發揚光大。物質遺產很可能被后人揮霍一空,精神遺產也往往被忽視,以致不知好歹。比如中國新文化的兩位巨匠魯迅和胡適,無疑給我們整個民族留下了極其寶貴的精神遺產,但我們珍惜了嗎?繼承和發揚了嗎?
那種吃老一輩的飯,打著名人后代的旗號四處招搖、博取名利的做法,顯然是不可取的,最終只能令人鄙視。況且有的還不惜文過飾非,為推崇老一輩而遮蔽和篡改歷史!在這個問題上,魯迅先生的長孫周令飛就頗值得我們學習。他于2002年在上海設立了一個“魯迅文化發展中心”,以“公益文化終生義工”的名義,“繼承保護魯迅文化遺產,弘揚魯迅思想精神,發展魯迅先進文化,促進社會文明發展”。這恐怕才是真正地完好地繼承了先輩的精神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