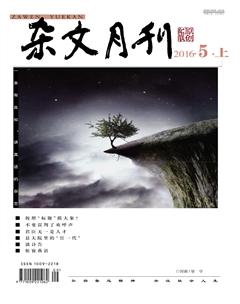日語是不是很貧乏?
楊建業(yè)
首先聲明一句,這里絕無貶低日語的意思。作為一個(gè)泱泱大國的國民,我不屑于玩弄這些不入流的小動作。這只是我讀了高低先生的《倘若馮英子先生健在……》(《雜文月刊》2016年第2期原創(chuàng)版)后心里產(chǎn)生的疑惑。
其實(shí)這個(gè)疑惑已伴隨了我四十多年。憶及年少時(shí),看過一本日本作家寫的《沖繩島》。作家的大名,早已忘卻,書中寫的什么,當(dāng)年也壓根兒就沒有看進(jìn)去。那時(shí)正是愛看小說的年紀(jì),怎么會看不進(jìn)去呢?只因沒看幾頁就感到語言干癟,味同嚼蠟。既無中國小說常見的起伏跌宕的故事情節(jié),亦無歐美小說豐富細(xì)膩的心理描寫和俄羅斯小說身臨其境般的場景敘述,當(dāng)然更談不上語匯的生動、豐富、風(fēng)趣和幽默了。不只我一人的感覺如此,身邊的小讀友們也大都是如此感覺。后來又看到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作品,語匯的單調(diào)無味,情節(jié)描述的刻板單一,如出一轍。據(jù)說,日本人古時(shí)候有語言無文字,公元三世紀(jì)時(shí)漢人王仁渡日后,漢文字才傳到日本。現(xiàn)在,日語的文字由漢字和假名兩套符號組成,混合使用,恐怕有時(shí)難免詞不達(dá)意。因此,莫不是日語本身在表述上不夠豐富才造成上述的感覺呢?
因?yàn)檫@個(gè)印象,所以1982年日本文部省審查通過的教科書中說上世紀(jì)三十年代日本軍隊(duì)“進(jìn)入”“進(jìn)出”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時(shí),我也只當(dāng)是日語本身詞匯的貧乏之故。后來得知,田中首相訪華說日本當(dāng)年的侵華戰(zhàn)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麻煩”,受到周總理的嚴(yán)厲批駁,一時(shí)竟懷疑我們是否有些小題大做了?沒準(zhǔn)兒日本人一直耿耿于懷的挨原子彈轟炸一事,他們可能也只會說“唉,你們美國人真是給我們帶來了麻煩”吧?前些年,福田首相的“迎春之旅”,中日和國際輿論均好評如潮,福田在北大演講時(shí)表示要“勇敢反省歷史”,更是贏得了北大學(xué)子雷鳴般的掌聲。可他在談及中日間那段銘心刻骨的歷史時(shí)也只是說,“必須對自己的錯(cuò)誤進(jìn)行反省,以及帶著不傷及被害者感情的謙虛……”。應(yīng)該說,在我們眼里,福田還算是一位主張中日友好的首相,所以他把日本侵華罪行說成“錯(cuò)誤”,我們也只是認(rèn)為日語詞匯里壓根兒就沒有“罪行”或“罪惡”這兩個(gè)詞,對他停止對被害者感情傷害的底線行為,也只會用近似贊揚(yáng)般的“謙虛”一詞表述罷。沒準(zhǔn)受害人還要感謝加害者這種“謙虛”的美德?
不過,若說日語貧乏,又怎么會走出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那么多的世界級大作家?我們中國的語匯,也有很多是來自于東瀛。比如“干部”這個(gè)詞,據(jù)說就是來自于日本。而“科學(xué)”一詞,我們中國從前壓根兒就沒有,明治維新時(shí)期日本著名科學(xué)啟蒙大師、教育家福澤渝吉把“Science”譯為“科學(xué)”,我們中國的康有為才首次引進(jìn)并使用“科學(xué)”二字。翻譯家嚴(yán)復(fù)在《天演論》等著作中,也用“科學(xué)”。此后“科學(xué)”才在中國廣泛地“科學(xué)”起來。可見,日本人并不缺乏語言表述的智慧。當(dāng)中國慰安婦要求日本政府對當(dāng)年日軍的侵害賠償時(shí),日本法庭判決受害者敗訴時(shí)稱“國家無答責(zé)”。這個(gè)“無答責(zé)”,就用得很妙,意即日本政府不只沒有賠償?shù)呢?zé)任,而且也沒有作任何回應(yīng)的義務(wù)。我們中國就沒有這個(gè)詞。只是,這樣絕妙的詞語為何卻不廣泛應(yīng)用于日本國內(nèi)呢?前些年,日本200多名受污染血制品影響而導(dǎo)致丙肝感染的國民向日本政府、日本企業(yè)索賠,當(dāng)時(shí)的日本首相福田不僅鞠躬道歉,而且日本政府也很痛快地“答責(zé)”了:先給受害者支付1.23億美元,再拿出0.26億美元作為“幫助款”,支付給調(diào)解計(jì)劃外的受害者。
如此看來,在日本政府正式的書面文件吐不出“道歉”二字前,我們沒準(zhǔn)還得一直困惑下去。我們也不想困惑,因?yàn)檫@種由困惑而帶來的對日隔膜總是不大好。但當(dāng)我們硬是參不透日本語匯的某種曖昧?xí)r,就很難不困惑下去。不過,有這種困惑也不是壞事,它會提醒我們,當(dāng)今的日本仍不乏其當(dāng)年“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的侵略美夢,因此我們必須居安思危,常備不懈,時(shí)時(shí)關(guān)注玩火者的新動向,把馮英子先生未完成的事情繼續(xù)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