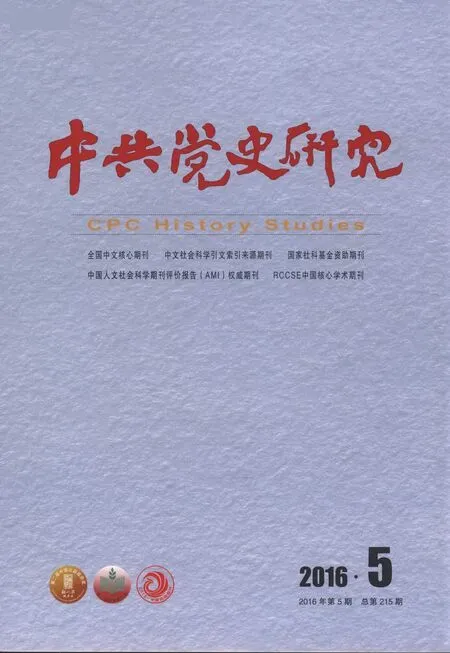中共黨史論文論點摘編
當代史研究中的圖像研究方法及其史學意義
中共黨史論文論點摘編
當代史研究中的圖像研究方法及其史學意義
李 公 明
視覺圖像資料在當代中國史研究中的價值不言而喻。常見的現當代圖像資料大體分為攝影圖像和作為藝術創作的圖像。就攝影圖像的史學研究價值而言,既可以從圖像入手研究人物與歷史背景、事件、群體等關系,也可以直接用作歷史證據。藝術創作品在實現圖史互證研究中的運用主要體現在“圖像學”方法,亦即在圖像志基礎上結合歷史學、心理學和批評論等對藝術品進行解釋。但是在當代史研究領域,圖像學方法易被忽視,許多作為圖像資料的藝術作品往往僅作為一般的歷史背景而使用,如作為著述中的插圖等。而事實上,關于圖像學的研究是“對一種方案的重建”的觀點使圖像解釋超越了僅僅是“對現成原典的直接圖解”的層面,在圖像與題材之間建立起更深層次的聯系,因此需要通過對確定的上下文理解來厘清圖像所表現的故事的意義。在與當代政治史研究相聯系的藝術作品課題中,所謂“原典”就是各時期的重要文獻和決議等,“方案”就是各時期現實情境的具體需求(即革命敘事話語中的“目前的革命斗爭需要”)。對于這些“方案”的認識必須以實證性的史料研究為基礎,重建歷史語境中具有特定意義的“方案”與“圖像”的聯系。當然,在圖史互證的研究中到處充滿了誤讀和過度詮釋的陷阱,但這并不是運用“原典”和“方案”分析方法本身的錯誤,而是論證過程中對實證材料掌握的準確性和闡釋的合理性可能存在問題,因此只有通過不斷的“試錯”分析才能使“方案”與所見的圖像不斷匹配。此外,還需要高度關注圖像考證過程中極容易發生的“碎化”問題,需要避免失去圖像與時代之間的整體性聯系。進一步而言,不能僅僅把“藝術品”作為藝術來研究,應該同時把握“視覺文化”(將作品視為文字與圖像的結合)與“物質文化”(將作品視為一種物品)的研究取向,應該在“物品”與“藝術品”之間尋求更豐富的闡釋空間。從此角度審視,圖像研究在當代史研究中的史學意義并非僅僅擴大了研究視野或強化了藝術與社會歷史的聯系,更重要的是關注和反思視覺文化在整個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從而更全面地展現歷史研究的廣闊視野和深刻內涵。準此而論,更深邃的學科之間的聯系與相互挑戰,也構成了圖像研究在當代史研究中的深層意義,亦即它深刻地體現了新文化史的潮流,它關注的是范疇、喻義和符號。(吳志軍摘自《社會科學》2015年第11期,全文約6400字)
60年代初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當代中國思想史上被忽略的一個片段
曹 光 章
20世紀60年代初期,在《紅旗》《新建設》《文匯報》等一批報刊上曾開展了一次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學術討論,主要局限于自然科學領域,涉及真理和錯誤的關系、實踐標準的相對性和絕對性、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區分、邏輯證明和實踐檢驗的關系等問題,基本上遵循了“高教六十條”關于百家爭鳴“一般只適用于自然科學”的原則規定。到1964年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因可能觸及社會科學領域的真理問題以及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等問題而變得敏感,因而迅速停止。直到“文革”結束,除1966年《新建設》《光明日報》各發表過一篇文章外,類似文章幾近鮮見。這次討論對于貫徹教育、科技、知識分子政策的調整具有積極意義,是學術界對中央調整政策的積極響應,使新中國的哲學工作者和一些自然科學工作者經歷了一次馬克思主義真理論的深入學習與研究,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真理論在當代中國的發展,為1978年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做了知識、思想方法和人才方面的準備。長期以來,這次討論很少為黨史或國史學界所關注,因而對這一歷史事件的研究,不僅能夠展現被思想史所忽略的歷史片段,而且有助于揭示當代中國思想史發展的連續性。(吳志軍摘自《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5年第11期,全文約8500字)
蘇聯經濟核算制與中國計劃經濟
林 超 超
經濟核算制是蘇聯(俄)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形成,并在計劃經濟時代發展成熟的經營和管理企業的基本方法,核心價值就是喚起企業對生產業績的關心,刺激其不斷改善生產。中共對蘇聯經濟核算制的借鑒可以追溯到30年代的根據地時期。1942年12月,毛澤東還對經濟核算制的主要內容作出較為全面的規約。1948年后,東北行政委員會(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發布文件,具體說明推行經濟核算制的內容和步驟,但同時將開展群眾性的創造新紀錄運動和反浪費斗爭放在首位。新中國成立后,中央要求參照東北人民政府關于經濟核算決定的原則,有步驟地推行經濟核算制,使企業減少浪費,實現盈利。經濟核算制在1951年被正式納入財經工作重點。從制度建設的層面看,國家對于推進經濟核算制下了很大決心,但在制度環境培育和成效等方面存在很大問題,尤其是廠長負責制的缺位以及50年代末“一長制”被徹底否定,導致黨政干部對于群眾運動的貫徹能力遠高于經濟制度建設的能力。在“大躍進”中,“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制度得到推廣,顛覆了并不完善的既有企業制度。從1960年底開始,《工業七十條》重新強調經濟核算的重要性,經濟核算制還一度被國家經委確定為管理社會主義企業的一項根本原則。但隨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文革”的開展,《工業七十條》遭到批判,“鞍鋼憲法”再次成為企業管理的主導原則。可見,新中國并未嚴格執行和切實落實包括經濟核算制在內的一系列計劃經濟制度。中國缺乏訓練有素的執行計劃管理的行政干部,政工干部更傾向于通過群眾運動式的生產動員以達到增效降耗的經濟效果,諸如增產節約運動、反浪費斗爭、反對官僚主義乃至勞動競賽等都應該被視為國家實施經濟監督、彌補激勵不足的一種表現。非制度化管理帶來的有形和無形的物力與人力損耗,是計劃經濟難以成功實現資本良性積累的短板。(吳志軍摘自《史林》2016年第1期,全文約21000字)
從“婚姻自由”到“婚姻自主”:20世紀40年代陜甘寧邊區婚姻的重塑
叢 小 平
“婚姻自由”是五四時期的重要議題,倡導從封建家長制的壓迫下和沒有愛情的婚姻中解放婦女。中共在革命根據地也開始注意婚姻問題的重要性,陸續頒布了一系列法律條文,其中尤以1939年《陜甘寧邊區婚姻條例》為典型,這一條例將婚姻改革的原則簡化為“婚姻自由”,但在具體實踐中遭遇挫折,導致根據地的離婚率上升。由于沒有考慮到訂婚所帶來的財產轉移(主要指彩禮),以女方及其家庭提出的退婚情況急劇增多,物質利益成為父親引誘女兒配合退婚再嫁的重要籌碼,給很多男性家庭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基層法律工作者逐步認識到,在家長制仍然主導婚姻習俗的情況下,父母從家庭利益出發扭曲了“婚姻自由”原則,實施婚姻改革就需要得到婦女配合以及打破父女聯盟。因此,邊區婚姻改革原則逐步轉向“婚姻自愿/自主”,強調在婚姻糾紛中當事婦女的個人意愿和她對于婚姻對象的選擇權。這一原則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婚姻自由”所隱含的任意性,賦予女性當事人選擇婚姻的決定權,并排除父母和第三方對婚姻問題的干涉,從而適應了邊區的社會文化生態,被相繼寫進《修正陜甘寧邊區婚姻暫行條例》和《陜甘寧邊區婚姻條例》,50年代后繼續推行,并進一步擴展為全國性的司法原則。從“婚姻自由”的政治口號到“婚姻自主”的法律權利的演變,反映了20世紀中國通過法律實踐探索適合中國社會的變革方式。(吳志軍摘自《開放時代》2015年第5期,全文約31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