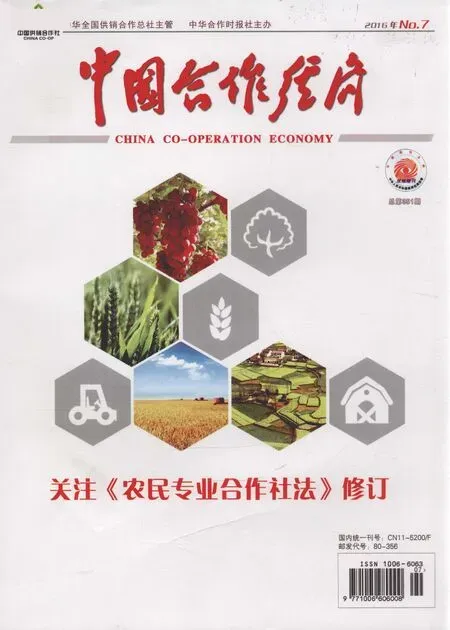關于《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修法名稱問題的思考與建議
韓長江
思考
關于《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修法名稱問題的思考與建議
韓長江
在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調研活動中,筆者對《專業合作社法修改對照表》進行了認真分析研究,認為修改后的新法(草案)內容更加豐富,更具操作性,其中最大的修改當屬增設了有關“聯合社”一章和立法名稱的變更。法律名稱的變更屬于立法思路的重大調整和根本性改變,確立一個新法名稱首先要考慮的問題是,這個新法名稱能否與其法律規范調整的具體內容相適應、相協調、相配套,并具有充分的法理和事實依據。
一、新法(草案)名稱可能存在的問題
各國合作社立法模式不盡相同。按照各國立法傳統,大致有以下幾種立法模式,即統一綜合立法、分業立法、混合立法和民商法典附屬立法等。我國農民合作社立法模式,從理論上講既可以采取統一綜合立法,也可采取分業單獨立法或“統一綜合立法+特別立法”,關鍵是能否做到名副其實、立法有據和便于執行。我國2006年頒布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屬于按居民身份實行分業單獨立法。而新的修法建議將法律名稱暫定為《農民合作社法》屬于按居民身份實行統一綜合立法(或統一綜合立法+特別立法)。這一動議的初衷可以理解,但可能存在“寬打窄用”、名不副實之虞,也缺乏事實依據和政策法理支撐。
一是“法小名大”、“大題小做”。由于歷史原因,我國形成了多種合作經濟組織形式并存的發展格局,其中“受到農民群眾普遍歡迎的一種十分重要的組織形式,就是農民專業合作社”。為此,國家通過頒布《農民專業合作社法》這一單行法規規范其組織行為,這也是立法的根本目的。將其更名為《農民合作社法》屬于立法思路由單項立法到綜合立法的根本性轉變,要使《農民合作社法》名副其實,就應該相應擴展該法調整和規范的對象和具體內容。特別是需要將法律調整對象擴展到所有以農民為成員主體的各種合作社,至少應該包括供銷合作社和資金互助社。但實際上,新法(草案)調整的對象幾乎沒有什么變動。
二是賦權不足,對經營服務范圍規定過于狹窄。按照“非禁即允”的原則,至少應將農民合作社的經營服務范圍擴大到農業生產以及生產性服務和生活性服務等多環節、多要素和諸多方面。而新法(草案)仍局限在農業生產(副業生產)和生產性服務的狹小領域。
三是概念模糊,將不同性質的合作經濟形式混為一談。我國現行憲法從1982年至今歷經多次修改,但對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定性和分類基本沒有改變。《憲法》規定,“農村中的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應該說,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建立在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之上的一種新型農業合作社,是農村集體經濟的一種有效實現形式。從《憲法》的角度講,盡管新興專業合作社、資金互助社與傳統的供銷合作社、信用社的終極所有權都屬于農民所有,但在管理體制機制制度等方面存在重大差異,不能一概而論,也難以實現“一部法律定天下”。我們知道,這很可能不是立法起草者的初衷,但既然如此,就不應該強拉硬拽,將其勉強連接在一起,更不應該名不正言不順地將立法名稱確定為“農民合作社”。
四是法律關系不順,以單行法駕馭單行法。本來,《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和正在研究起草中的《供銷合作社條例》均屬于單行立法,為同位并行關系,其共同的上位法為《憲法》。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抓緊研究修訂農民專業合作社法”。2015年中發11號文件明確提出要“確立供銷合作社的特定法律地位”,同時指出,“為更好發揮供銷合作社獨特優勢和重要作用,必須確立其特定法律地位,抓緊制定供銷合作社條例,適時啟動供銷合作社立法工作。”新法(草案),不論叫什么名稱,如果能夠按照中央〔2015〕11號文件精神,從正面將供銷合作社特定法律地位納入該法規范之中,可謂一大創新、一大突破。實際的情況是,新法(草案)只是在附則第七十四條原則規定“法律法規對供銷合作社等農民合作社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這種以一個單行同位法統御另一個單行同位法的想法,似乎是實現了形式上的“駕馭”和法名上的統一,實際上仍是“駕而不馭”、“統而不一”,不足為取。
二、立法名稱的新提議
修法可采取兩種形式,一是存續性修訂,二是廢舊立新。根據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抓緊研究修訂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按存續性修訂和廢舊立新兩種思路對新法(草案)名稱及相關問題提出如下建議:
留法名改法條。一是修改專業合作社的定義,由強調成員的同類性轉向強調經營的專業性。可將其定義為“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在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農村居民(農民)為了共同的利益,自愿聯合、民主管理、專業化經營的互助性經濟組織。”二是擴展對專業合作社經營服務范圍選擇的規定。新法(草案)已經這樣做了。三是放松對合作社注冊登記的“專業”字樣的限制。命名由“五段式”改為“四段式”。在執行或司法解釋中可明確規定“已經登記注冊的合作社是否辦理更名登記手續,由合作社自主決定。”實際上,即使新法取名《農民合作社法》也沒有必要強制更名,以保持法律的嚴肅性,降低執行成本。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只是適用于新型合作社的一個立法名稱和注冊登記的企業類型。更名與否,對合作社發展并不會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改法名換角度。從新法(草案)對合作社經營服務范圍的法律規定看,都是一部從農業角度或大農業的角度提出來的,因此,建議可考慮將新法名稱確定為《農業合作社法》,聯合社應定名為“農業合作社聯合社”。需要強調的是,這里提出的《農業合作社法》屬于單項立法,專門用于規范按本法注冊登記的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和農業生產性服務的合作社。這個法律名稱,不僅有《憲法》依據,符合現實情況,避免出現法律名稱與調整對象、范圍錯位和不對稱的問題,而且可以避免與將來可能出臺的《供銷合作社法》等單項立法出現概念沖突和混亂。如日本除有《農業協同組合法》外,還有《水產業協同組合法》(1948.12)、《森林協同組合法》(1948.5)、《消費生活協同組合法》(1948.7)以及《中小企業協同組合法》(1949.7,用于規范企業協同組合及信用協同組合)。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鑒。
河北省供銷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