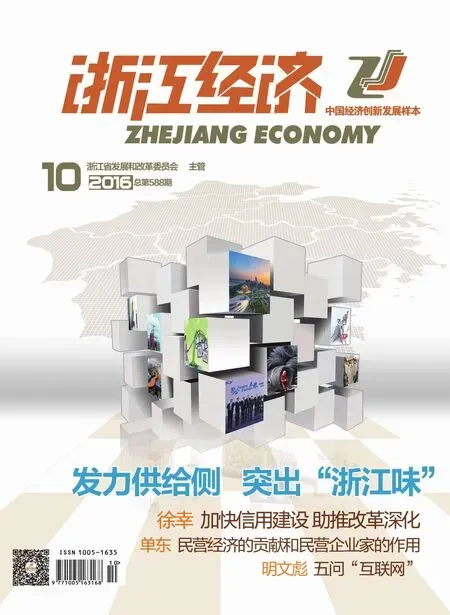供給側改革:破冰與攻堅
——2016京都論壇專家觀點綜述
本刊記者/馮潔
供給側改革:破冰與攻堅
——2016京都論壇專家觀點綜述
本刊記者/馮潔
從“新常態”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對于經濟發展現狀的認識和出路的探索不斷在深化。作為“十三五”時期經濟工作的主線,中央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供需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率。在4月23日-4月24日舉行的2016京都論壇上,來自國家各經濟研究部門的專家們就“十三五”開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何破冰與攻堅進行了一場深度討論,本刊對部分專家觀點進行了綜述,供讀者參閱。
深化供給側改革釋放新動力
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已成為一種必然趨勢。如何在增速放緩的同時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顯然,解決結構性矛盾是當務之急。當前,供給和需求不平衡、不協調的矛盾和問題日益凸顯,突出表現為供給側對需求側變化的適應性調整明顯滯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恰恰是從這一深層次的矛盾入手尋求新動力。
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院長、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常務副秘書長李新創認為,“供給側”是與“需求側”相對應的。需求側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三駕馬車決定短期經濟增長率。而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條件下所實現的增長率即中長期潛在經濟增長率。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應簡單復制供給學派的“供給管理”,而應通過改革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從而避免潛在增速的大幅下行,其實質是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在要素領域的延續和聚焦。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怎樣的背景下提出的?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鄭京平提出,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建立在一系列發展新趨勢和經濟新結構之下。
“十三五”時期,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國際環境依然嚴峻,企業和個體勞動者都將面臨新的生存壓力。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將顯現幾大新趨勢:一是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二是產業將邁向中高端水平,三是民生跨入中高收入階段。與之對應,新的經濟結構也正在形成。對此,鄭京平解釋,“從三次產業看,服務業將繼續崛起。從三大收入看,居民收入占比也將繼續上升,或將提高到65%,這也符合共享發展的理念精神。”
在新趨勢和新結構的作用下,“十三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也將面臨新舊動力轉換,新的發展動力亟待激活。鄭京平認為,目前需集中力量釋放以下幾大新動力:首先,要向改革開放要動力。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開放力度尤其是要推動金融服務業領域的開放。其次,要推進新型城鎮化。提升城鎮化水平,是激活經濟增長潛力的重要途徑。第三,要以科技創新為引領。作為五大發展理念之首,“創新”是今后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動力之一。不創新就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產業進入中高端水平和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都將無法實現。第四,加快提升信息化水平。要以云計算、大數據、“互聯網+”為依托,推動中國經濟轉型進程。第五,要充分釋放人才紅利。第六,要積極發揮京津冀一體化、長江經濟帶、“一帶一路”及中國制造2025等發展戰略的作用。第七,要充分發揮縣際政府間競爭性模式的作用。在繼續加強執政紀律的基礎上,進一步建立健全激勵機制和容錯糾錯機制。
在鄭京平看來,新的發展環境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恰恰抓住了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命門,抓住了中國供給側的短板,同時對過去扭曲的資源配置誤區進行了撥亂反正,強化了投入產出意識。不過,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仍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既要充分發揮好政府作用,又要防止其越俎代庖。政府必須要以全球化的視角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全球化的眼光來優化資源配置,并統籌運用好財政和貨幣政策。與此同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與需求側管理齊抓并進。通過刺激需求將潛在的需求激發出來,從而帶動供給,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
在增速放緩的新常態下,如何最大限度發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作用,以提高潛在增長率?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蔡昉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著眼于勞動參與率、生育率、人力資本、企業成本、全要素生產率,以達到提高潛在增長率的目的。
現代服務業引領新升級
發達的服務業是推進結構轉型升級、經濟中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保障。“十三五”規劃建議對現代服務業發展高度重視,第一次提出了“開展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行動”。還提出要“放寬市場準入,促進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務業向精細和高品質轉變,推動制造業由生產型向生產服務型轉變”。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過程中,關注產業結構變動,推動現代服務業發展,已成為一條重要通途。
國家發改委服務業專家咨詢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夏杰長介紹,“十二五”時期,服務業已成為經濟發展的最亮點,占據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2012年,我國產業結構調整迎來重要拐點,第三產業(服務業)占比首次超過二產,之后三產占比不斷提升,與二產的差距越拉越大,到了2015年服務業更是超過了50%,與此同時,服務業增長速度也明顯快于二產和GDP增速。
夏杰長認為,我國正處在邁向服務經濟時代的“窗口期”,并將成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動力。到2020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比重、勞動就業和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將分別達到58.80%、46.91%和54.36%,服務業主導地位將進一步鞏固;服務業開放有望邁出新步伐,再上一個新臺階,服務業利用外資規模可能達到872億美元,服務貿易有望突破11000億美元。這些數據變化,意味著“十三五”時期我國服務業發展迎來難得的機遇期,離“服務經濟時代”的步伐越來越近,國民經濟服務化的格局將初步形成。
現代服務業發展如何為經濟結構升級帶來新動力?夏杰長對此提出六大對策。第一,激勵服務創新。鼓勵制度創新,創新人才政策和金融支持政策,完善容錯機制;鼓勵技術創新,以“互聯網+”“人工智能+”培育新業態、新服務、新模式,推動“新經濟”大發展。第二,推動跨界融合。鼓勵“1+2+3”,即六次產業的發展;鼓勵農業與服務業跨界融合,發展農業產業化服務體系;鼓勵工業(尤其是制造業)與服務業深度融合,推進制造服務化。第三,引導空間集聚。順應集聚發展的趨勢,鼓勵服務業園區自然形成和有機成長。要在已有的制造業產業集群內部或者附近,建立起各種為其服務的公共平臺,包括研發設計、試驗驗證等公共技術支撐平臺,咨詢、評估、交易、轉化、托管、投融資等知識產權應用服務平臺,集交易、物流、支付等于一體的綜合電子商務服務平臺等,以降低制造業集群的交易成本,優化投資環境。第四,培育市場主體。鼓勵服務業企業專業化發展,推動優勢服務企業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兼并重組,打造跨界融合的產業集團和產業聯盟,培育若干有特點、有品牌、有控制力的服務業龍頭企業或企業集團。第五,改善營商環境。建立自由公平競爭、科學適度監管的營商環境。第六,堅持雙向開放。在開放型體制上實現較大突破:打破管制和壟斷最為關鍵;積極推進服務業便利化改革;由政府生產服務走向民間生產政府購買;按照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著力推進金融、教育、醫療、文化、體育等領域的對外開放;放寬服務貿易的準入和投資限制,實現服務要素在全國、全球范圍內的互聯互通;破除行政壁壘和畫地為牢的桎梏,力爭服務要素在全國范圍內無障礙流動和服務資源的最優配置;大力發展服務外包,推動服務業企業“走出去”。在積極參與全球化與國際分工中做大現代服務業,培育服務業新優勢。
完善金融供給促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在眾多改革領域中,進一步增加和完善金融供給無疑是整體供給側改革的關鍵環節。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加和完善金融組織、市場、產品、調控、治理等方面的供給,對于推動供給側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至關重要。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副局長劉向耘指出,當前,單純的金融總量擴張已滿足不了經濟轉型發展的需要。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推進的新環境下,我國的金融體系仍存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為:金融體系的市場化程度仍不高,金融結構仍不合理,滿足不了經濟轉型的需要;金融產品與服務仍不夠豐富,滿足不了多樣化的金融服務需求;在互聯網技術快速發展、金融創新日新月異的情況下,金融監管體制已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
金融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著力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和支持經濟轉型的能力,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具體而言,推進金融要素供給側改革,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加快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建設,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建立均衡的社會融資結構,滿足經濟發展和轉型過程中多元化的融資需求;建立覆蓋廣泛的中小微金融組織,發展普惠金融和多業態的中小金融組織,規范發展互聯網金融;擴大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建立一個更加多元的金融機構股權結構,促進金融機構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
談及當前金融如何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劉向耘進一步提出一系列對策: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更加注重松緊適度;繼續發揮貨幣政策定向調控的作用;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降低社會融資成本,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充分發揮信貸政策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能動作用;進一步完善證券市場和保險市場功能;規范發展互聯網金融、小額貸款、融資擔保機構等;守住風險底線,為供給側改革創造穩定的金融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