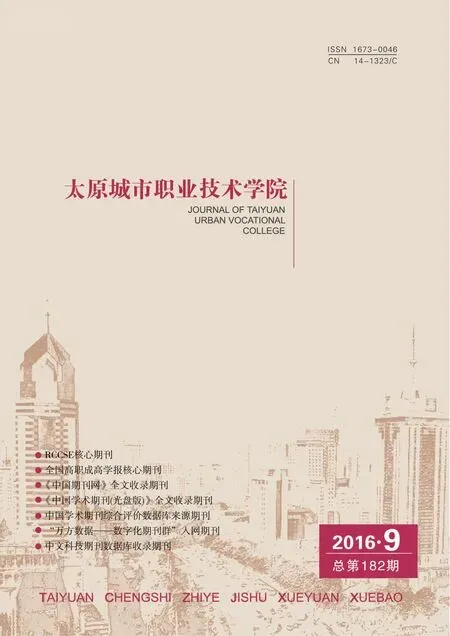蘇軾寓言作品創(chuàng)作初探
陳黎
(無(wú)錫機(jī)電高等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校,江蘇 無(wú)錫 214000)
蘇軾寓言作品創(chuàng)作初探
陳黎
(無(wú)錫機(jī)電高等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校,江蘇 無(wú)錫 214000)
蘇軾才華橫溢,一生仕途坎坷,在寓言創(chuàng)作上深受佛教寓言、柳宗元寓言和宋代理性思想等因素的影響,表現(xiàn)出獨(dú)特的藝術(shù)特點(diǎn):寓言形象鮮明、獨(dú)特;善用生動(dòng)的對(duì)話(huà),表達(dá)人物個(gè)性;汪洋恣肆的的浪漫主義色彩;將自己作為人物形象融入情節(jié);智慧的苦笑。
蘇軾;詼諧幽默;形象;理性思想
蘇軾是北宋后期文學(xué)成就最高文學(xué)家,他以其杰出的文學(xué)成就在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史上占據(jù)了一席之地。他的詩(shī)題材廣闊,風(fēng)格獨(dú)具,與黃庭堅(jiān)并稱(chēng)“蘇黃”;詞開(kāi)豪放一派,與辛棄疾并稱(chēng)“蘇辛”;書(shū)法又自成一家,與黃庭堅(jiān)、米芾、蔡襄合稱(chēng)為“宋四家”,代表宋代書(shū)法的最高成就。在諸多光環(huán)之下,蘇軾的寓言作品鮮少被人關(guān)注,但其在寓言上的成就極高。他的作品詼諧超然,思想獨(dú)具,繼承了唐代寓言的針砭時(shí)弊的社會(huì)作用,又帶有個(gè)人超然物外的灑脫和幽默。蘇軾的寓言在中國(guó)寓言史上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而他在宋代寓言上的地位可堪與柳宗元在唐代寓言中的地位比肩。
縱觀整個(gè)中國(guó)歷史,宋代在隋唐的物質(zhì)財(cái)富積累的基礎(chǔ)上,加之商品經(jīng)濟(jì)在此間快速發(fā)展,成為一個(gè)集經(jīng)濟(jì)、文化教育、科學(xué)技術(shù)高度繁榮的時(shí)代,達(dá)到了封建社會(huì)的巔峰階段。在思想意識(shí)上,賣(mài)弄淫巧、淫靡浮艷的駢儷文風(fēng)再起。蘇軾與歐陽(yáng)修、蘇洵、蘇轍等人繼承并發(fā)揚(yáng)中唐時(shí)期古文運(yùn)動(dòng)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在社會(huì)上掀起了古文革新的巨浪,使得詩(shī)文發(fā)展面貌為之一新,文風(fēng)轉(zhuǎn)向平實(shí)曉暢、清麗優(yōu)雅,取得了北宋中期古文運(yùn)動(dòng)的勝利。隨著北宋中葉古文運(yùn)動(dòng)的興起,宋代寓言的創(chuàng)作也逐漸達(dá)到頂峰。
蘇軾所著的《艾子雜說(shuō)》是中國(guó)文學(xué)史上的第一部寓言專(zhuān)著。他的寓言作品主要收集在《艾子雜說(shuō)》、《雜記》、《雜著》和《東坡志林》中。由于其生活經(jīng)歷豐富,影響其創(chuàng)作的因素眾多,因此其寓言作品在內(nèi)容上較為博雜,但藝術(shù)成就高超,語(yǔ)言簡(jiǎn)潔凝練,風(fēng)格輕松幽默,于嬉笑怒罵中,彰顯出深刻的寓意和獨(dú)有的藝術(shù)性。
一、影響蘇軾寓言創(chuàng)作的因素
(一)受佛經(jīng)寓言影響。
在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印度佛經(jīng)寓言以一種完整、獨(dú)立的姿態(tài)進(jìn)入了中國(guó)寓言史,從此成為中國(guó)寓言史上的一個(gè)重要的寓言組成部分。
四川眉山,是蘇軾自小生活的地方,毗鄰佛教圣地峨眉山,是峨嵋佛教文化輻射的中心區(qū)域。早在蘇軾的青少年時(shí)代,他就表現(xiàn)出喜好佛道的趣向。初仕后,他在王大年的引導(dǎo)下,修習(xí)佛學(xué),遍閱佛書(shū)。中年以后,蘇軾在政治上屢受挫折,生活上和佛印和尚等人交往密切,又受到佛經(jīng)寓言影響。他創(chuàng)作了《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shí)日,問(wèn)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盤(pán)。”扣盤(pán)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為日也。日之與鐘、龠亦遠(yuǎn)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jiàn)而求之人也。”
此文描述了一個(gè)“生而眇者”向“有目者”了解太陽(yáng)是什么樣子的故事。故事結(jié)構(gòu)上取材于佛經(jīng)寓言故事《盲人摸象》,二文皆比喻看問(wèn)題總是以點(diǎn)代面、以偏概全,主觀臆斷;但《日喻》在情節(jié)構(gòu)建上卻更甚一籌:《盲人摸象》中,數(shù)位盲人各自?xún)H憑觸摸大象的一部分來(lái)認(rèn)知大象;而《日喻》則通過(guò)聽(tīng)覺(jué)、觸覺(jué)兩種錯(cuò)誤的方式來(lái)了解太陽(yáng),內(nèi)容更為豐富,層次感更強(qiáng)。
(二)受柳宗元諷刺寓言影響
唐代柳宗元的寓言對(duì)蘇軾寓言創(chuàng)作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蘇軾在其所作寓言《二魚(yú)說(shuō)》(即《河豚魚(yú)說(shuō)》、《烏賊魚(yú)說(shuō)》)序言中寫(xiě)道:“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ài)之,又嘗悼世之人,有妄怒而招悔,欲蓋而彌彰者。遞吳,得二事干海濱之人,亦似之。作《二魚(yú)說(shuō)》,非意乎續(xù)子厚者,亦聊以自警云。”蘇軾在《河豚魚(yú)說(shuō)》中諷刺那些“妄怒而招悔”的人,告誡人們遇到挫折困難不可怨天尤人,要分析原因,總結(jié)教訓(xùn);《烏賊魚(yú)說(shuō)》則提醒世人在政治斗爭(zhēng)中與其“自蔽以求全”,不如徹底“滅跡以杜疑”。此二說(shuō)中的諷諫意味濃重,反映了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人事、政局的種種弊端。《二魚(yú)說(shuō)》雖在思想、形式上與《三戒》相類(lèi),但和唐代柳宗元寓言及劉禹錫寓言詩(shī)中所顯示的戰(zhàn)斗性相比尚有不及,究其原因,是由蘇軾曠達(dá)樂(lè)天的人生態(tài)度決定的。
(三)受宋代理性精神的影響
在宋初,宋太祖問(wèn)宰相趙普:“天下何物最大?”趙即答曰:“道理最大。”伴隨著儒學(xué)的復(fù)古、理學(xué)派別的創(chuàng)立立、政治意識(shí)的增強(qiáng)、科舉策論的登臺(tái),理性的種子迅速地在思想意識(shí)空間生根發(fā)芽,全社會(huì)的思想文化形態(tài)很快呈現(xiàn)出空前的理性化傾向。理性精神牢固地占據(jù)了宋代的思想意識(shí)殿堂。
蘇軾在《寶繪堂記》中說(shuō):“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他認(rèn)為,留意于物,滯留于執(zhí)求物欲,貪得無(wú)厭,會(huì)招致禍患。寓意于物,寄托情意于物,不是停留于意欲占有此物,就能使人怡悅,而不會(huì)產(chǎn)生禍患。
《秦士好古》塑造了一個(gè)表面上托名好古、自詡風(fēng)雅的人物——秦士,其實(shí)質(zhì)只是追尋物質(zhì)上的古老,并沒(méi)有意識(shí)到真正的尊古其實(shí)是尋求古老事物背后的精神文化價(jià)值,最終為物所役、咎由自取。《小兒不畏虎》一文則揭示了無(wú)畏能戰(zhàn)勝?gòu)?qiáng)敵的道理。此類(lèi)寓言形成了睿智、深刻、耐人尋味的理性格調(diào)。
二、蘇軾寓言作品中突出的藝術(shù)特點(diǎn)
(一)寓言形象鮮明、獨(dú)特
1.人物形象塑造完整。蘇軾在《營(yíng)丘士》塑造了一個(gè)“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難而不中理”,不知變通,而鉆牛角尖的人。寓言中的營(yíng)丘士就大車(chē)上和駱駝的脖子上掛的鈴鐺之用途與艾子抬杠,步步追詰,顯示出其思維的固化,自取其辱。寓言中生活氣息濃郁,營(yíng)丘士既可厭也可笑的形象栩栩如生。
2.開(kāi)拓了獨(dú)立的人物形式——“艾子”。蘇軾寓言中有一批形象鮮明的人物,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艾子”。這種創(chuàng)作手法為后代創(chuàng)作帶來(lái)了深遠(yuǎn)影響,明代陸灼以艾子為主人公寫(xiě)了《艾子后語(yǔ)》。
(二)善用生動(dòng)的對(duì)話(huà)表達(dá)人物個(gè)性
在《螺蚌相語(yǔ)》一文中采用了對(duì)話(huà)的形式:螺“形如鸞之秀,如云之孤”,但內(nèi)多委曲;蚌雖“啟予口,見(jiàn)予心”,但腹內(nèi)藏有珠璣。通過(guò)螺蚌的對(duì)話(huà),贊美直言者無(wú)愧于心,諷刺那些徒有其表、華而不實(shí)的人。文章先揚(yáng)后抑,巧設(shè)情節(jié)逆轉(zhuǎn),將嘲諷之意從蚌之口緩緩說(shuō)出,使斥責(zé)更為有力。
再如《措大吃飯》: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他日得志,當(dāng)飽吃飯了便睡,睡了又吃飯。”一云:“我則異于是,當(dāng)吃了又吃,何暇得睡耶!”一般說(shuō)來(lái),言“志”應(yīng)是莊嚴(yán)、肅穆的大事,但在兩位“措大”口中,所謂“志”卻是“飽吃飯了便睡”和“吃了又吃”。寓言借這兩位窮酸秀才之口,描畫(huà)出了一副窮酸腐儒口讀詩(shī)書(shū),卻心如禽獸的可笑形象。
(三)汪洋恣肆的浪漫主義色彩
蘇軾早年讀《莊子》時(shí)曾經(jīng)慨嘆:“吾昔有見(jiàn)于中,口不能言;今見(jiàn)《莊子》,得我心矣”,莊子寓言中汪洋恣肆的想象力為蘇軾的寓言創(chuàng)作開(kāi)啟了一道靈感之門(mén)。蘇軾在《海屋添籌》寫(xiě)到: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wèn)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shí)與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shí),吾輒下一籌,爾來(lái)吾籌已滿(mǎn)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于昆侖山下,今已與昆侖齊矣!”以余觀之,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文中,三位老人借神話(huà)人物盤(pán)古、滄海桑田變換、蟠桃核堆高如昆侖等意象來(lái)吹噓自己年齡之高,想象意出塵外、新奇獨(dú)特,夸張至極。
(四)將自己作為人物形象融入情節(jié)。在《子瞻患赤眼》、《別石塔》等寓言作品中,蘇軾將自己作為文中的人物進(jìn)行說(shuō)理。《別石塔》作者用“石塔有縫,可容螻蟻”,悟出佛家的“普渡眾生”和儒家的“兼濟(jì)天下”殊途同歸,有異曲同工之妙。
(五)智慧的苦笑
1.自我解嘲。宋哲宗紹圣(公元1094-1098)年間,新舊黨爭(zhēng)再起,重新掌權(quán)的變法派大肆驅(qū)逐元佑黨人,清除異己,蘇軾遭到流放。《誅有尾》一文借短短七十六個(gè)字,穿越時(shí)空,描繪出蘇軾一生中巨大可怕的政治陰影。文中借“龍王有旨”:“應(yīng)水族有尾者斬”,反映了這一時(shí)期的政治斗爭(zhēng),抨擊當(dāng)時(shí)朝廷大興文字獄之事。小蝦蟆擔(dān)心自己因蝌蚪時(shí)有尾而被殺,正是蘇軾對(duì)李定等人在他的詩(shī)文中斷章取義、羅織罪名的影射,是蘇軾經(jīng)歷烏臺(tái)詩(shī)案后對(duì)文字獄發(fā)自?xún)?nèi)心的恐懼和自我解嘲。
2.曠達(dá)樂(lè)觀的人生態(tài)度。蘇軾一生仕途坎坷,但他天性樂(lè)觀,多次流放和佛道思想的催化促使形成了曠達(dá)詼諧的人生態(tài)度。他用超然達(dá)觀的態(tài)度笑對(duì)人生的困境,在困境中嬉笑怒罵、自得其樂(lè)。如《傍人門(mén)戶(hù)》,表面上說(shuō)不要“爭(zhēng)閑氣,”實(shí)際卻諷刺了那些不學(xué)無(wú)術(shù)卻愛(ài)在官場(chǎng)上爭(zhēng)名奪利。回看蘇軾一生,雖才華橫溢,卻在仕途上始終不得志,只能學(xué)“門(mén)神”在官場(chǎng)上不“爭(zhēng)閑氣”,他一笑泯然,這份超脫在騷人墨客中也是極為罕見(jiàn)的。這種詼諧幽默的手法對(duì)后世的寓言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
蘇軾一生仕途坎坷,其生活經(jīng)歷和佛道思想對(duì)他的創(chuàng)作都有積極影響,故雖經(jīng)歷“烏臺(tái)詩(shī)案”“元佑之禍”,他依然性格灑脫,寫(xiě)作風(fēng)格天馬行空,揮灑自如。蘇軾寓言的內(nèi)容豐富,他關(guān)注的對(duì)象從平民乞丐到貴族王孫,題材從日常生活到官場(chǎng)政治均有涉及,采用或委婉諷喻、或幽默調(diào)侃的方式表達(dá)深刻的寓意,每一篇都有獨(dú)特的藝術(shù)性。他的寓言對(duì)元、明、清的寓言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是寓言史上承前啟后的重要一環(huán)。
[1]孔繁禮點(diǎn)校.蘇軾文集[M].北京:中華書(shū)局,1999.
[2]朱靖華.蘇東坡寓言評(píng)注[M].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
[3]陳黎.“褒貶諷諭”“輔時(shí)及物”——淺析柳宗元寓言寫(xiě)作特點(diǎn)[J].佳木斯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2(2):48.
[4]林語(yǔ)堂.蘇東坡傳[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9.
[5]陳黎.禹錫寓言詩(shī)創(chuàng)作芻議[J].牡丹江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4:92.
[6]吳秋林.中國(guó)寓言史(上、下)[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1.
I206
A
1673-0046(2016)9-019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