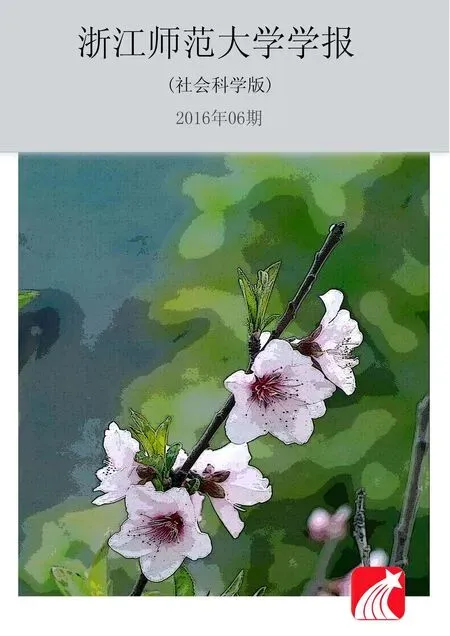進化論與嚴復的兒童觀
吳正陽
(首都師范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089)*
?
進化論與嚴復的兒童觀
吳正陽
(首都師范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089)*
在近代中國,嚴復給國人帶來了嶄新的兒童觀,為近代兒童觀的變革開啟了諸多新方向。嚴復兒童觀的哲學思想根基是進化論,同時也是他“三民”思想的具體展開,其內容包含兒童的基礎教育、家庭教養、生產養育、權利地位、意義價值等。嚴復進化論的兒童觀帶有鮮明的科學色彩,同時也創造了一種新的想象兒童的方式,將中國兒童帶到現代化的門檻前。
進化論;嚴復;兒童觀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日不落”帝國的槍炮驚醒了“天朝上國”的迷夢,也強行轟開了它緊鎖的大門。這是中國近代屈辱史的開端,但也不可否認,這是中國接受現代文明,踏上現代化進程的開端。在這其中,嚴復“不但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并且也是一位劃時代的人物”。[1]10誠如李澤厚所言:“嚴復代表了近代中國向西方資本主義尋找真理所走到的一個有關‘世界觀’的嶄新階段,他帶給中國人以一種新的世界觀,起了空前的廣泛影響和長遠作用……”[2]262實際上,在近代中國,嚴復也給國人帶來了一種嶄新的兒童觀,為近代兒童觀的變革開啟了諸多新方向,并且深深地影響了后來者。但在以往的研究中,這些一直被忽視,鮮有人加以論述。
在嚴復提供給國人的嶄新世界觀中,進化論思想無疑是其中最具影響力和感染力的一部分。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嚴復申明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首先成了不甘受帝國主義欺凌,渴求發展圖強爭取生存的中國人變革現實的重要思想武器”。[3]“更獨特的是,人們通過讀《天演論》,獲得了一種觀察一切事物和指導自己如何生活、行動和斗爭的觀點、方法和態度,《天演論》給人們帶來了一種對自然、生物、人類、社會以及個人等萬事萬物的總觀點總態度,亦即新的世界觀和人生態度……而這種觀點和態度,又是以所謂‘科學’為依據和基礎,更增強了信奉它的人們的自信心和沖破封建意識形態的力量。”[2]273-274而進化論思想也正是嚴復本人的哲學思想根基,“他的立論,自始至終都喜歡引用天演的原理”,[1]297他的兒童觀也是在進化論的根基上建構起來的。
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天演”面前,中國要自存、要富強,就要“變”(進化),但從哪些方面開始著手“變”,如何最終實現“變”,卻是更為關鍵的問題。值得一說的是,在嚴復這里,“適者生存”被作了微妙的改動,最終成了“使自身變得適應者獲得生存”。就“變”而言,不管是嚴復,還是之后的進化論推崇者如梁啟超等人,都意指有意識的、積極的變化,“他們相信自我轉變、自我修養、自強、自我改善、自力更生。他們因而設想,在進化的競爭中,人類有能力去轉變他們的‘共同自我’(corporate self)并使得那個自我存續下來”。[4]106-107由此,達爾文的進化論,經由嚴復的努力,也就從一種充滿威脅性的學說,轉而變成了一種“鼓舞人心的、大有希望的和提供拯救的”學說。[4]414
在《原強》中,嚴復提出要將“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三者視為變革、自強之本,[5]29這部分緣由正來自于進化論思想,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理解:
首先,從個體的自然生存競爭角度出發,“人欲圖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與是妨生者為斗,負者日退而勝者日昌,勝者非他,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6]196
其次,嚴復從斯賓塞那里接受“一群之成,其體用功能,無異生物之一體”這一社會有機體論,而“群之治亂、強弱,則視民品之隆污”。[6]209也就是說,社會“群體”的質量有賴于各個單位或各個細胞——“民”的質量,而“民”的“強弱存亡”就集中體現于“血氣體力之強”“聰明知慮之強”“德行仁義之強”。
再次,人作為自然界生物之一員,同樣受制于進化的進程。進化是一個長期的異常緩慢的過程,并非一朝一夕所能達成,而且與動植物相比,“民之性情、氣質變化難”。[6]209因此,要最終實現變革的效果,有必要從最緩慢、最艱難、最根本的方面做起,從民之性情、氣質漸漸變起。
總之,基于生物生存法則、社會有機體論及漸變論,嚴復將民智、民德、民力視為國家強弱貧富治亂的指向標,相應地,他所提倡的一切變革措施,也都旨在改善民眾的智德力。由此也奠定了與兒童相關的變革措施的目標指向,而這些與兒童相關的變革措施不僅表達了嚴復的一種潛在兒童觀,很大程度上也預示了近代兒童觀的變革。
一、廢八股:觸及兒童所念之書
嚴復深知中國所“最患者”為“愚”“貧”“弱”,而三者之中,又以“愈愚為最急”,因為使中國墮入貧弱之道但仍不自知的正是“愚”。因此,嚴復對不管古今中外之法,持以堅決的態度:“凡可以愈愚者,將竭力盡氣皸手繭足以求之”,而若有一道“致吾于愚”,則“雖出于父祖之親,君師之嚴,猶將棄之”。[5]148
嚴復首先將矛頭對準延續了上千年的科舉制度。“民智”乃“富強之原”,而八股的弊害恰恰就在于“錮智慧”“壞心術”“滋游手”,“使天下消磨歲月于無用之地,墮壞志節于冥昧之中”。[5]59在嚴復看來,八股取士不過是“圣人牢籠天下,平爭泯亂之至術”,[5]4因此,他大聲疾呼“欲開民智,非講西學不可,欲講實學,非另立選舉之法,別開用人之涂,而廢八股試帖策論諸制科不可”。[5]33
在主張廢八股、剖析八股弊害的過程中,嚴復自然地也就關注到兒童,關注到他們所念之書、所學之識,以及教育兒童的方法。因為在“八股取士”的傳統下,每個孩子自入學起,就要接受與之相配套的教育。在《原強》中嚴復指出:“且也六七齡童子入學,腦氣未堅,即教以窮玄極眇之文字,事資強記,何裨靈襟?其中所恃以開濬神明者,不外區區對偶已耳,所以審覈物理,辨析是非者,胥無有焉”。[5]32-33在《救亡決論》中,他又說:“垂髫童子,目未知菽粟之分,其入學也,必先課之以《學》《庸》《語》《孟》,開宗明義,明德新民,講之既不能通,誦之乃徒強記。如是數年之后,行將執簡操觚,學為經義。先生教之以擒挽之死法,弟子資之于剽竊以成章。一文之成,自問不知何語。迨夫觀風使至,群然挾兔冊,裹餅餌,逐隊唱名,俯首就案,不違功令,皆足求售,謬種流傳,羌無一是。”[5]56這也正如傳教士麥高溫所觀察到的,“中國人總是為成年人著想,兩千年來沒有哪位作家為孩子們寫過什么,沒有任何一個時期的藝術家為了帶給孩子們歡樂而拿起畫筆,去描繪孩子們的生活,也沒有一位學者提議編寫一套易學、有趣的教科書。”[7]
一個社會或一種文化對兒童進行教育的內容和方式,往往直接蘊含著或者說是昭示了這個社會、這一文化對兒童的理解、認識和態度。因此,嚴復對以往給兒童的教科書及教育方式的抨擊,實際上已經在醞釀著一種新的兒童觀。
正有鑒于此,嚴復后來對新設小學學堂的教科書,并不提倡學部統一頒定,建議自行編輯頒行外,“更取海內前后所處諸種而審定之”,對教科書的要求是只要不與教育宗旨相違背,對“學童道德腦力”無害,聽憑用者自擇。這可以說是后來兒童文學走入小學學堂,作為教育素材的先聲。而且嚴復一再強調,“童子性真未鑿”,給兒童讀的書很容易會使他產生先入為主的印象,這事關“國之隱憂”。[8]202將兒童與民族、國家聯系在一起,這也是近代兒童觀的一個顯著變化。
二、興小學教育:觸及兒童的基礎教育
嚴復將民之力智德視為國家政教改革、圖存富強之根本,那么,又該如何改善“種之寡弱”“種之暗昧”“種之惡劣”?“為今之計,唯急從教育上入手,庶幾逐漸更新”。[9]嚴復最終把希望全部寄托于教育上,在《天演論》中,就曾借赫胥黎之口說:“……故欲郅治之隆,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故又為之學校庠序焉。學校庠序之制善,而后智、仁、勇之民興;智、仁、勇之民興,而有以為群力群策之資,而后其國乃一富而不可貧,一強而不可弱也。”[6]160
前面所述“廢八股、興西學”只是嚴復學校教育方案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此外,他還曾提出學校教育的三級制,即分小學、中學、高等學堂,為培養師資,他又主張先設師范學堂于各省會,等等。在近代教育的變革中,這些都是富有創見的,這里僅就他的小學教育略談一二。
嚴復意識到當時教育首先要做的就是普及,由此他也提出相應的教育普及方案。他認為在一鄉一鎮中,有那么數十百家,就可以設立一個小學堂,用現成的祠堂,經費不用過高,師資用其最易得者,這樣哪怕是最貧窮的鄉鎮也能興辦。有了學堂之后,就要要求所有十歲以上的子弟入學,而在教學上,因為是普及,所以“程度不得不取其極低”,“以三年為期,教以淺近之書數,但求能寫白話家信,能略記耳目所見聞事”,嚴復期望“十年以往,于涂中任取十五六齡之年少,無一不略識字”。[8]169如果我們知道在傳教士坎貝爾·布朗士眼中,當時中國鄉村兒童的生活境遇,也許更能體會嚴復普及教育的意義,盡管在當時的語境下,普及教育仍難實現:“對大多數中國兒童來說,最大的苦難莫過于貧窮,很多孩子死于饑餓。很多人也許不相信,但他們一學會走路就要開始工作了。……他們化身‘小大人’……農村的孩子從小就要挑起生活的重擔,而在城里,孩子們會成為店鋪里的童工。正是因為生活困難,他們小小年紀就顯得飽經滄桑。”[10]171
對于兒童的教育,嚴復顯得十分慎重,他從斯賓塞那里得到的啟示是“非真哲家,不能為童稚之教育”,他認識到兒童的心靈,“萌達有定期”,而且因人而異,所以教育者所要做的就是“淪其天明,使用之以自求知;將以練其天稟,使用之以自求能”,[8]200學堂教育所要陶煉的是兒童的“母慧”(Mother wit)。[8]207另外,嚴復認為教育要使“學子精神筋力常存朝氣”,因為他注意到少壯之腦力較老年之人,更需要休息將養,那些在日后做出大事業,性格沉毅勇往,各方面能力突出的人,“其果非結于夙興夜寐之時,乃在少日優游,不過用心力之日”。[8]205-206這實際上也是在倡導給兒童一個寬松愉快的童年成長時光,對兒童的教育要特別契合他們的自然天性。
三、重家庭教育:觸及兒童的教養
除學校教育之外,嚴復也非常重視家庭教育。他看到中國不僅學校教育不興,而且家庭教育也很少實行,對于那些“窮檐之子”“編戶之氓”來說,他們是無教,而對于那些“民之俊秀者”來說,則是教而無當。[5]33
在《〈蒙養鏡〉序》中,嚴復再次強調一國一種的盛衰強弱,在競爭中的存亡,都與民有關,而“民之性質,為優勝,為劣敗,少成為之也”,[5]177而且很有可能會從家長那里遺傳得來。
盡管達爾文并沒有闡明氣質也會遺傳,但《天演論》中的某些說法似乎很容易使嚴復產生這樣的想法。“一人之身常有物焉,乃祖、父之所有而托生于其身。蓋自受生得形以來,遞嬗迤轉以至于今,未嘗死也”,[6]250這就是生物普遍具有的遺傳性。嚴復譯遺傳學為“種姓之說”,而他得到的科學知識是子孫是祖、父的分身,人的“聲容氣體”乃至“性情”,均非“偶然而然”,“或本諸父”,“或稟諸母”,或遠或近,都有源頭可溯,都承受自先人。當一個小孩出生后,他就帶有從先人那里遺傳而來的“性情”,只不過一開始還處于隱蔽的狀態,當他逐漸長大,隱蔽的“性情”就會逐漸顯露出來,“為明為暗,為剛為柔,將見之于言行”,都能如實被指出。而等到他自己結婚生孩,他又會與另一半的性情、聲容氣體雜糅,之后又遺傳給后代。[6]319
且不去談論嚴復在這里所理解的遺傳學是否完全科學,但他確實是在近代中國較早地嘗試去“科學”地認識兒童的人。20世紀初我國兒童學的逐漸興起,同嚴復最初引入的生物進化論不無關系。
既然“子弟之德,堂構之美,夫非偶然而至”,孩子長成什么樣,有什么樣的氣質與家長自身的品德修養密切相關,所以嚴復就特別重視家庭教育,尤其強調家長的“身自教之”。而有了“天演之說”的科學根據,嚴復大可譏刺那些“性習既成”卻又不自振作乃至自身品德敗壞的家長,他們寄望于子孫能夠“尚公、尚實、尚武”,“光明”“高潔”,能夠“于以合群進化”,“日進而與一世抗也”,從而帶給他們榮光,但這就如同“取奔蜂以化藿蠋,用越雞以伏鵠卵”,是違背進化論,而決不可能實現的。嚴復并非對未來無望,也非反對“深望于后之人”,他只是希望現時的家長能夠從自身“心德身儀”做起,唯此后代才有“大造”,才會日趨優勝。[5]177
四、保優勝人種:觸及兒童的生養
受進化論的啟發,嚴復繼而走上了“優生學”的道路。為了使人種優勝,嚴復又提出要控制人口。嚴復注意到中國歷來飽受“過庶之患”,中國作為一個宗法社會,其祖宗崇拜的傳統促使人們常以多子為福,而在家族主義及“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觀念影響下,婚姻、生育往往成為家族傳宗接代、綿延種族的需要,所以格外重婚嫁,重生子,最終導致人口過多。[11]1007但人口過多并不必然成為“患”,這同嚴復所受進化論的指示有關。
達爾文進化論的核心——自然選擇學說的理論基礎之一,就是生物都具有高度繁殖趨勢,生殖過剩常與生存空間的有限性形成尖銳矛盾,由此導致生存斗爭。在《天演論》中,“汰蕃”一篇對此就有詳細說明,而且說的正是人的狀況。這也就是嚴復后來所信奉的“人口消長的治亂循環論”,人口過多很可能就會面臨“亂”的局面——引發激烈的生存競爭,甚至是戰爭,直至人口在優勝劣汰中大幅度減少,重新達到平衡點。這也是嚴復所以為的“患”。
而中國既受著人口過多的患害,又“富教不施”,這是更大的隱患。“支那婦人……使一人生子四五人……則所生之子女,飲食粗弊,居住穢惡,教養失宜,生長于疾病愁苦之中,其身必弱,其智必昏。”嚴復擔憂的是等到這些孩子長大,勢必又“嗜欲而無遠慮,莫不亟亟于婚嫁”,如此一來,“謬種流傳,代復一代”,最終將導致種的退化乃至滅種。[8]87
在《天演論》中赫胥黎曾指出一些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為解決人口過多而擬采取的措施,其中一項即是同園夫治理草木一樣,“去不材而育其材”,使那些“罷癃、愚癎、殘疾、顛丑、盲聾、狂暴之子”不得結婚生子,使所繁衍的“必強佼、圣智、聰明、才杰之子孫”,這樣就不用擔心人口過多的隱患了。[6]142
嚴復雖然也是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但所幸他沒有走那么遠,也許也是赫胥黎幫助他打消了這種念頭。赫胥黎認為對動植物實施“擇種留良之術”的是人,但若是“以人擇人”,能勝任的實施者幾乎是不可能有的;而且“人種難分”,赫胥黎指出“聚百十兒童于此”讓天演家去挑選的話,也是幾乎不可能確定誰“為賢為智”,誰又“為不肖為愚”,誰該結婚生子,誰就該斷子絕孫,因為孩子性情品格雖說有遺傳的成分,但哪怕一個被視為“庸兒”“劣子”的孩子,通過后天的磨礪,人事的引導,仍可能“變動光明”,干出一番大事業。[6]150-151
況且在遺傳學上,又有“反種”,“牉合有宜不宜”等情況,若是兩個人結合恰到好處,則還可能“生子勝于二親”,所以嚴復只是感嘆“種胤之事,其理至為奧博難窮”,但此理又所關至巨,“非遍讀西國生學家書,身考其事數十年,不足以與其秘耳”。[6]211夾雜在進化論中的優生學讓嚴復倍感奧博,但這種學問卻是日后人們生養健康聰慧孩童的必備知識,是嚴復將其率先引入了中國。
針對人口過剩的問題,嚴復最終還是回到了提高民智的道途上來。嚴復注意到一個國家民眾的繁衍速度與教化程度常常成反比。這仍有生物學的“科學”依據,在自然界,“種下者多子而子夭,種貴者少子而子壽”,而所謂“種貴者”,即是其腦“重大繁密”,“腦進者”自然就會“成丁遲”,因為他們用腦更“奢”、更“費”,“用奢于此,則必嗇于彼”,如此一來,“生生之事廉矣”。[6]196-197
嚴復所要促成的就是“腦進”,這樣,不僅民眾生育會下降,就算生多了,也不足為患。因為“種貴者”不只是“少子”而已,而且還“愛子”“保子”,使得“子壽”。生物都有保育自己后代的本能,但“獨愛子之情,人為獨摯,其種最貴”,[6]176跟其他生物相比,人保育后代的時間也最長。斯賓塞曾提出保種公例二,其一便是“凡物欲種傳而盛者,必未成丁以前,所得利益,與其功能作反比例”。[6]225而赫胥黎,則進一步告示嚴復,正因為人保育后代時間最久,“久,故其用愛也尤深。繼乃推類擴充,緣所愛而及所不愛。是故慈幼者,仁之本也。”[6]176
而中國的現狀是什么呢?“不獨小民積蓄二三十千錢,即謀娶婦也。即閥閱之家,大抵嫁娶在十六七間。男不知所以為父,女未識所以為母,雖有兒女,猶禽犢耳!”嚴復自述每次在“都會街巷”中,“見數十百小兒,蹣跚蝶躞于車輪馬足間,輒為芒背”,并不是擔心他們會跌倒有危險,而是“念三十年后,國民為如何眾耳!”[11]987(魯迅在《隨感錄二十五》,周作人在《〈蒙氏教育法〉序》等文中都曾直接引述過嚴復的這段話,足見其影響深遠。而這種由小孩念及未來之國民的擔憂,也被他們所承繼,梁啟超、魯迅由嚴復的三民說,而進一步申發新民說、立人說,愈加發人深省。)
反觀歐洲“有教之民”,他們對結婚、生子則計慮深遠,“方當兵時,或猶在學校中,皆不娶。即學成之后,已治生矣,亦必積貲有余,可以雍容俯畜而教育二三子女俾成立者,而后求偶”。[11]987因此,除了提高對民眾的教化來減緩生育之外,嚴復也建議“必早婚變俗,男子三十,而后得妻”。[11]980中國早婚的現象非常嚴重,一方面緣于宗法,家長以嗣續為急,早早替子女擇婚完婚;另一方面,女子生存條件惡劣,很小時就被交換去當童養媳。早婚不僅造成如上述父母不盡教養的責任,也直接影響到下一代的體格。[11]987
與此同時,嚴復也特別重視女子教育。“一種之進化,其視遺傳性以為進退者,于男女均也”,女子教育事關婚配、遺傳和生計三件大事,“旋乾轉坤即是握動兒藍之手”,[12]又“蓋母健而后兒肥,培其先天而種乃進也”,[5]30女子正是未來國民的生養者和培養者,尤其需要強健的體格和優良的教育。
傳教士泰勒·何德蘭曾注意到當時中國的家庭“小生命的誕生往往會給家里帶來很多快樂,但快樂的多少取決于很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孩子的性別、他之前孩子的數量和性別,還有就是家庭的經濟狀況”;[10]19而傳教士坎貝爾·布朗士則觀察到當時的“童養媳”們通常要忍受巨大的苦難與不幸,“她們每天都要做苦力,沒有快樂的童年,也沒有父母和家人的疼愛,只有永遠做不完的工作”。[10]171這么看來,嚴復優生優育的想法對提高兒童的生存境遇有著不容小覷的意義,而他變革早婚風俗的建議也對延長兒童的童年期起到了客觀上的促進作用。
五、抨倫理綱常,尚自由平等:觸及兒童的權利、地位
面對中國內憂外患的局面,當嚴復等人力倡向西方學習,變革政教之時,一些守舊之士卻對此極力排擊,仍舊認為中國受外侮是因為“坐師不武,臣不力耳”,中國的衰弱,是因為“綱常名教”的敗壞。[8]115在他們看來,綱常名教“亙萬古而不變”,是“立國明民”的根本,只有“秩敘”不紊,紀綱不亡,治禮明禮,才能有所謂“國治、富強”,也才能“民德歸厚”。[8]116-117
中西“言治”的“必不可同”,嚴復認為緣于中西進化觀念的差異:
中之言曰:今不若古,世日退也。西之言曰:古不及今,世日進也。惟中之以世為日退,故事必循故,而常以愆妄為憂。惟西之以世為日進,故必變其已陳,而日以改良為慮。夫以后人之智慮,日夜求有以勝于古人,是非抉前古之藩籬無所拘攣,縱人人心力之所極者不能至也,則自由尚焉。自由者,各盡其天賦之能事,而自承其功過者也。雖然彼設等差而以隸相尊者,其自由必不全。故言自由,則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權。合自主之權,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謂之民主。天之立烝民,無生而貴者也……且以少數從多數者,泰西為治之通義也。乃吾國舊之說不然,必使林總之眾,勞筋力、出賦稅,俯首聽命于一二人之繩軛;而后是一二人者,乃得恣其無等之欲,以刻剝天下,屈至多以從其至少,是則舊者所渭禮、所謂秩序與紀綱也,則吾儕小人又安用此禮經為![8]117-118
也就是說,西方信仰進步,所以尚自由、平等、民主,變得富強;而中國從不思進步,不僅不尚自由、平等、民主,還處處以“禮”“秩序”“紀綱”壓制它們,所以日漸貧弱。要改變這種局面,除了樹立人們進步的信念外,在政教層面,還要“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對民眾加以引導。嚴復探求西方富強奧秘而得到的牢固信念是:“使西方社會有機體最終達到富強的能力是蘊藏于個人中的能力,這些能力可以說是通過駕御文明的利己來加強的,自由、平等、民主創造了使文明的利己得以實現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人的體、智、德的潛在能力將得到充分的展現”。[13]
盡管如史華茲所說,嚴復把自由、平等、民主變成一種促進“民智民德”、提高社會功效以及達到國家富強目的的手段,而非把自由、平等、民主作為個人權利和地位的體現,但這并非完全準確。嚴復從《天演論》中得到的最初啟示是“天之生物,本無貧賤、軒輊之心”“故以人意軒輊貴賤之者,其去道固已遠矣”,[6]248而人作為“天之生物”,“其受形雖有大小、強弱之不同,其賦性雖有愚智、巧拙之相絕,然天固未嘗限之以定分,使劃然為其一而不得企其余”。[6]166也就是說,在天演面前,萬物生而平等,人人生而平等。他又引西人之言“惟天生民,各具賦畀,得自由者乃為全受”,倡導“人人各得自由,國國各得自由”,指責“侵人自由者,斯為逆天理,賊人道”,[5]5實際上也是發出了人享有天賦自由、平等權利的呼聲。這同時也將兒童的自由、平等權利問題提上了議程,為下一個階段兒童的解放,贏取與成人平等的地位打下了最初的基礎。
中西自由、平等觀念的迥然相異,不僅體現于政教上,而且滲透在社會、家庭生活的各個方面。“自由既異,于是群異叢然以生……如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5]5在另一處,嚴復更是直接抨擊中國重三綱所帶來的流弊:“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眾,而貴自由。自由故貴信果。東之教立綱,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親。尊親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極,至于懷詐相欺,上下相遁,則忠孝之所存,轉不若貴信果者之多也。”[5]35
在中國的傳統倫理綱常中,有所謂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有所謂五倫,即“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些正是守舊派引以為豪的亙古不變的“禮”。在“父為子綱”“長幼有序”倫理規定下的傳統社會里,人們所信奉的必然是老者本位、長老至上,兒童幾乎無法擁有自己的獨立意志、實現自己的情感愿望。如傳教士坎貝爾·布朗士所觀察到的,“在中國的家庭里,父母對子女擁有絕對的權力,即使他們的子女成年了,也同樣如此”。[10]164尊長不能冒犯,卑幼只有服從的份兒,即使尊長錯了,卑幼也不能違拗,否則即視為“不孝”。而在以孝治天下的國度里,“不孝”如果不是意味著一項重大的罪惡,那也意味著對一個人的完全否定,意味著隨時可能被社會所拋棄。方衛平就認為,中國傳統社會中所形成的兒童文化,實際上是一種殘酷的“殺子”文化,是對兒童自然天性和生命活力的一種窒息、摧殘和扼殺,這也就造成了中國歷代兒童不幸的精神境遇和歷史命運。[14]
因此,嚴復基于進化信念,對“亙古不變”的“綱常名教”進行猛烈抨擊,力倡自由、平等、民主,無疑動搖了其根基,而在這其中,“父為子綱”“長幼有序”等傳統兒童觀也一并受到了沖擊,而這也為兒童擺脫一直被支配、被漠視的卑微地位贏得了新機。
六、信“后勝于今”:觸及兒童的意義、價值
嚴復在動搖“父為子綱”“長幼有序”等傳統兒童觀的同時,從進化論出發,也樹立起了一種新的信念,一種新的兒童觀雛形。嚴復深信人的可完善性、進步性,“自達爾文出,知人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進,來者方將”,[6]43“夫人類自其天秉而觀之,則自致智力,加之教化道齊,可日進于無疆之休,無疑義也”,[6]235“況彼后人,其所以自謀者,將出于今人萬萬也哉”。[6]442不僅人具有“且演且進”“日進于無疆”的進步性,“人類之事功”也同樣如此,與“篤古賤今之士”不同,嚴復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說道:“吾黨生于今日,所可知者,世道必進,后勝于今而已。”[6]237
嚴復的這種信念,隨之帶來的必然會是一種“重少輕老”的兒童觀。在《天演論》“矯性”一篇篇末,嚴復即注意到在不同的進化觀念下,中西民眾顯示出不同的倫理價值取向,西民“好然諾,貴信果,重少輕老,喜壯健無所屈服之風”。嚴復雖未直說中國為劣,歐洲為優,但在其深切的擔憂中,不難推測他內心是更傾向于認同西方的。[6]413
這“后勝于今”“重少輕老”的信念,也給予后來者以信心與力量。隨著“進化論的深入人心,其中所體現的人類應該有的‘以幼者為本位’的道德觀,不僅是對傳統舊道德‘以長者為本位’與‘父為子綱’兒童觀的直接反動,更為五四時期‘以兒童為本位’的新兒童觀的確立奠定了廣泛的社會與思想基礎”。[15]我們可以聽到后來進化論推崇者們的新聲:
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說》中熱情洋溢地贊賞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于歐洲,則國勝于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16]周作人在《兒童問題之初解》中則批判“東方國俗,尚古守舊,重老而輕少,乃致民志頹喪,無由上征”,人們沒有充分認識到“蓋兒童者,未來之國民,是所以承繼先業,即所以開發新化”,[17]而他日后則更是科學地認識到作為“完全的個人”的兒童,積極提倡、創建兒童學和兒童文學;陳獨秀創辦《新青年》(初名《青年雜志》),發起新文化運動,在發刊詞《敬告青年》中,希冀青年能夠“自覺其新鮮活潑之價值與責任”——“青年之于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18]李大釗則在《青春》中謳歌青春,又同樣地寄望于青春之青年,“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進前而勿顧后,背黑暗而向光明,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資以樂其無涯之生”[19];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則直接喊出了“本位應在幼者”“置重應在將來”的時代強音:“……所以后起的生命,總比以前的更有意義,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價值,更可寶貴;前者的生命,應該犧牲于他……”[20]
對于兒童、少年、青年的想象(實際上也是對于未來中國的想象),可以說是“晚清至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共同想象”,也是“杰出的世紀想象”,“從未見過(以后也不曾見過)一個時代那么多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對青年、少年甚至兒童表現出那么高的熱情”,“進化論以線性時間觀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少年觀、兒童觀……一舉扭轉了中國人一說兒童就習慣向后看的思維方式,引導人們將目光投向未來……創造了一種新的想象兒童的方式,將中國兒童帶到現代化的門檻前。”[21]或者如另一位學者Mary Ann Farquhar所言:“在傳統中國,兒童代表了一種家族的持續與傳統價值,而二十世紀早期的改革家們用進化論的思想重塑了一種兒童形象,他們代表民族而非家族,進步而非停滯不前。”[22]而這一切都首先得益于嚴復及其對進化論的杰出闡釋。
[1]周振甫.周振甫文集:第10卷(嚴復思想述評)[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
[2]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3]《進化論選集》編輯委員會.進化論選集(紀念達爾文逝世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選編)[C].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14.
[4]浦嘉珉.中國與達爾文[M].鐘永強,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
[5]嚴復.嚴復選集[M].周振甫,選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6]赫胥黎.天演論[M].嚴復,譯.馮君豪,注譯.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7]麥高溫.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M].朱濤,倪靜,譯.北京:中華書局,2006:67.
[8]王栻.嚴復集(第一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6.
[9]王栻.嚴復集(第五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6:1550.
[10]泰勒·何德蘭,坎貝爾·布朗士.孩提時代:兩個傳教士眼中的中國兒童生活[M].王鴻涓,譯.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11]王栻.嚴復集(第四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6.
[12]王栻.嚴復集(第二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6:313.
[13]史華茲.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M].葉鳳美,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40.
[14]方衛平.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發展史[M].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2007:42.
[15]蔣風,韓進.中國兒童文學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47-48.
[16]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2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13.
[17]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246.
[18]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新青年:第1卷[M]北京:中國書店,2011:1.
[19]沈永寶,蔡興水.進化論的影響力——達爾文在中國[C].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88.
[20]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67.
[21]吳其南.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的文化闡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20-22.
[22]MARY A 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a:From Lu Xun to Mao Zedong[M]. M.E.Sharpe, Armonk,New York,1999:1.
(責任編輯 傅新忠)
Evolutionary Theory and Yan Fu’s View on Children
WU Zhengyang
(SchoolofLiterature,Capital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089,China)
Yan Fu brought a brand new view on children and opened numerous new directions for reforms on the view on children in modern China. The found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Yan Fu’s view on children is evolutionary theory; meanwhile, Yan Fu’s view on children is also the demonstration of his Sanmin Thought, including children’s basic education, family education, birth and upbringing, rights and status as well as significance and values. Yan Fu’s view on children that benefits from the evolutionary theory not only has a bright color of science, but also has created a new way to imagine children, bringing Chinese children to the threshold of modernization.
evolutionary theory; Yan Fu; view on children
2016-09-12
吳正陽(1990-),男,浙江樂清人,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B256
A
1001-5035(2016)06-005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