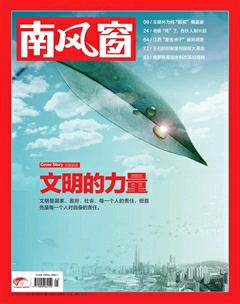菲律賓的另一個“聲音世界”
周雷
菲律賓作為一個特點明顯的天主教社會,當地人日常接觸的音樂、聲響混雜的傳教聲音結構,勢必會影響他們認知其他社會和國際問題。
2016年是菲律賓大選年,與中國有關的議題也在菲律賓輿論中升溫。為了解菲律賓民間的意見市場,2015年12月我在菲律賓考察了一周時間,主要關注傳統的媒體體制之外,菲律賓日常的民間信息交互和傳遞是在什么社會空間實現的。
在國際傳播中,受眾往往通過視覺獲得信息,即便電視新聞的聲音也往往是后期配上去的非原聲版,長此以往,會造成一種偏狹,形同坐井。我在日常調查的時候,更多關注聽覺,即使最終以寫作的方式分享發現,也想還原更多海外社會的聽覺原貌,用作對視覺的參照和補充。

車上的“泛新聞”環境
一到馬尼拉,從機場至馬尼拉大都會的馬卡蒂市區的8.5公里,因為嚴重的交通擁堵,走了近6個小時。一路上司機的車載音響和收音機開放,我于是在第一時間接觸到菲律賓某類出租車的聽覺日常。
當地司機很多用不起智能手機,所以沒有那么多微信式的聊天和刷屏可以做,也沒法使用導航系統,基本上就在車上干等,聽收音機里各種混合流行音樂、廣告和主持人插科打諢的節目。
馬尼拉的許多公共交通系統是“下沉式的”,也就是說,部分公路和路邊的建筑往往被公路橋、圍墻隔斷,車上基本上沒有“風景”可看。即使從下沉的公路“漂浮”上來,進入和地面商鋪、住宅區聯通的區域,也由于建筑過于密集和單調—往往都是超市、7/11便利店、Jollibee快餐連鎖、麥當勞和肯德基、Chowking (名為“超群”的中式快餐連鎖)之類的建筑,視覺因此被“封閉”。而噪音強烈的高污染排放、公共汽車轟響和車內廣告,成為聽覺的主要背景內容。
這些聽覺意義上的噪音氛圍,在傳播學上是有意義的:由于大量的中低收入者選擇“廂式對排坐”皮卡改裝的公車和大巴車作為日常通勤的方式,基本上每天要花3~4個小時在路上,這就形成了一種接受傳統新聞的“泛新聞”環境。不管是在車上看報紙、雜志,還是讀手機信息、聽車內廣播、看車內節目,基本上無法進行持續和清晰的內容記憶和思考。
一聲一階層:聲音上的“部落”
在馬尼拉轄下的馬卡蒂(Makati)、奎松(Guizon)、納馬彥(Namayan)等5個區域,我了解到當地的紙質媒體行銷主要通過街邊雜貨鋪或書報亭,貧民區域的街邊雜貨鋪通常只售賣《菲律賓問詢者》和《菲律賓星報》為主的10份報刊;家里的電視節目通常為3類:宗教類(各種講解圣經和大型彌撒的現場錄像)、新聞娛樂類(播放各類新聞、娛樂節目和電視劇)和購物類(各種電視購物節目)。
在馬卡蒂,我去了3所大型的宗教場所,包括Ayala商業廣場綠地的教堂、Velero路的基督教亞洲中心、圣安德魯使徒教堂。在這類宗教場所中,大量的時間是由宗教吟唱、合唱、懺悔、哭泣構成,部分環節使用PPT投影將內容呈現出來,現場的樂隊音樂使用非常普遍,幾乎是一個半場的宗教音樂會。
這些教堂音樂也至少分為兩種流派,一種是基督教的福音派,使用了大量不同風格的音樂,甚至可以改編一些流行音樂(在馬卡蒂的一座教堂,當地人甚至改編了英國搖滾樂隊Coldplay的歌曲Scientist,作為宗教音樂使用);另一種是羅馬天主教派,有固定的曲目,選曲非常嚴苛和相對保守。
從宗教人類學的角度來看,聲音與情緒乃至認知具有重要關聯;聲音通過在某些具體場合的集體行為放大,可以出現特殊的效果。菲律賓作為一個特點明顯的天主教社會,當地人日常接觸的音樂、聲響混雜的傳教聲音結構,勢必會影響他們認知其他社會和國際問題。
被媒體放大的現場聲效
在馬尼拉工作的中國記者和外交部派駐官員告訴我,當地人針對中國的南海示威和抗議雖然不罕見,但是在規模和持續性上,當地人對本地政府的腐敗和低效往往更有意見,同時,對美國霸權和軍事間諜的抗議也是當地人關心的熱點。可是,由于國際媒體的放大,中國的受眾往往會認為菲律賓存在一個整體的民族主義群體,他們對中國有一致的極端意見。
事實上,當四周出現警車,各種警報聲、喊叫聲、高音喇叭的演講、聚集地高聲播放的音樂混雜的時候,這往往是被媒體放大的現場聲效。而國際媒體很少從菲律賓日常世界的正常表達中去尋找平和、理智的聲音,例如在正常學術演講、公民論壇討論、咖啡館分享、街邊聊天中出現的真實情緒。
宗教模式對塑造日常抗議政治具有重要作用,菲律賓政治人物也清楚這一事實,并不斷把宗教和政治結合起來。2015年12月9日,菲律賓當地的報紙大版面報道阿基諾三世訪歐時尋求梵蒂岡教宗接見的新聞,而在當時,菲律賓政要在歐洲主要的政治事務是把南海問題國際化,包括向海牙法庭提交菲律賓仲裁案的最后陳述,以及尋求意大利在這一事情上的幫助。
當南海事務、羅馬教宗、海牙法庭、意大利外交幫助這些元素在媒體上融合,就形成了適合菲律賓宗教化社會問題傳播的基本要素,也可以在菲律賓進行跨群體、跨區域、跨社會空間的大范圍傳播。
第51屆國際圣體大會將于2016年1月24日~31日在菲律賓宿霧市舉行,主題為“基督在你們中,作了你們得光榮的希望”。這也是菲律賓開教500周年的紀念大會,這個宗教界的盛會必然也會被政客利用,成為討論和傳播現實政治事務的場所。

“多首國歌”背后的多元社會
馬尼拉的Ayala三角公園,圣誕期間用高分貝音響連續播放各種舞曲、流行音樂、商業廣告音樂、音樂劇音樂、電影剪輯音樂等,形成了一個跨階層、跨年齡的受眾現場,聽眾數百上千。
但是與中國的廣場舞和“國家在場”不同,馬尼拉的民眾不太使用國歌,或是那些表現家鄉、本土文化、族群文化的音樂來表達自己,而是不斷使用流行音樂來彰顯自己的都市身份。
菲律賓大學的民族音樂學學者何塞·布恩孔塞羅在接受筆者采訪時說,菲律賓人的國歌是法國式的進行曲—諷刺的是,這個反擊宗主國西班牙壓迫的音樂,在聲音上是抄襲西班牙《皇家進行曲》(National Royal March),一般不被民眾在表現民族主義情緒時使用,而是更多有儀式和政治功能;經常在抗議和游行中使用的音樂是《我的祖國》(Bayan Ko)。
另外一名菲律賓學者安東尼奧·希拉則認為,音樂在菲律賓的政治表現和日常反抗中起到比文字更重要的作用,某種程度上,菲律賓人反抗西班牙和美國殖民的情緒是借助高唱名為kundiman形式的傳統情歌表達的。在菲律賓,進行曲不一定是高昂激烈的,相反可以是悲傷和舒緩的,例如《邁向葬禮》(Marcha Funebre)。
希拉教授介紹,菲律賓某種程度上有多首音樂可以當作國歌使用,例如音樂家Nakpil的一首作品,里面的唱詞大意是:“向自由致敬,讓光榮和正義勇往直前,西班牙人遭人民唾棄,現在讓秩序凱旋。”
而在美國殖民時代,另一首歌也被當作國歌吟唱,那就是《獨立萬歲》(Viva La Independencia),作者是費爾南多·格列羅。如今在菲律賓,很多高中使用一種名為danza的音樂,當作“國歌”使用,它是根據菲律賓國父黎剎(Jose Rizal)作詞的一首曲目創作而成。
部分歌詞寫道:“在東方,歡樂之陽升起的地方,那是光芒之中的伊甸園,備受傲慢之徒蹂躪,那是我們的祖國,深愛的土地。”
當我結束在菲律賓大學的采訪時,音樂系的同學正使用菲律賓、爪哇、日本、中國的樂器準備一場校園音樂會,這也是多元文化融合的菲律賓聲音的日常。
無論是國歌的“眾唱紛紜”,還是幾個世紀以來不斷與海外融合,我們都可以感受到一個分化、多元、階層化、族群化、殖民化的菲律賓“聲音世界”,對很多人來說,這也是另一個“聲音世界”。而這種聲音具體到傳播學領域也同樣適用,這就決定了中國的對外傳播在菲律賓更要懂得“在什么地方唱什么歌”,而不是把菲律賓民眾當作一個概括和抽象的整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