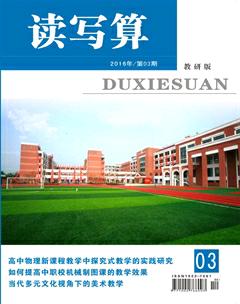沒有絕對的“管制”,正如沒有絕對的“自由”
李文文
摘 要:本文以赫爾巴特的管理、教學和訓育為邏輯起點,在闡明這三者之聯系的基礎上,結合盧梭的“自然教育”將二者進行了對比,提出“沒有絕對的管制,正如沒有絕對的自由”這一思想論斷。
關鍵詞:管理;教育性教學;自由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7661(2016)03-001-01
一、兒童管理——創造秩序,避免危害
兒童并非生來就有意志,卻處處表現出一種不服從的烈性。管理,“并非要在兒童心靈中達到任何目的,而僅僅是要創造一種秩序”。赫爾巴特把兒童管理這個教育措施劃分為威脅、監督、權威和愛。教育強制并不是用懲罰來施加威脅,而是要警告兒童他的不明智行為可能對自己或社會造成危害;監督不是要去監控兒童是否及時順從了這種警告,而是觀察兒童如何對待這些管理措施所指出的危險;權威不是讓兒童臣服于外在的權威,而是探討他們是否理解和適當把握這種權威的意義;教育之愛也并非秉持一個順從的孩子的形象,來要求兒童順從和認可自己的認識,而是對他們秉持一種無動機的好意,從而有可能產生一種自由的相互認可。
二、教育性教學——發展多方面興趣
如上所述,兒童的管理“僅僅是要創造一種秩序”,如此才能為教學的實現打下基礎。教學以“多方面興趣”為主要依據,因為在赫爾巴特看來,教學應該發展多方面興趣,才能達到教育的最終目的──培養德行。在教學過程中,學生有了興趣,教師所提供的事物便對他的心理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相反,學生缺乏興趣,教學必然空洞乏味,令人厭煩,甚至會影響教育目標的實現。然而,一個人的興趣必須是多方面的。只有多方面的興趣才是人們獲得廣泛而又完善的觀念的強大動力。所以,赫爾巴特既把多方面興趣看成是教學的基礎,同時又是教學的直接的目的。他將興趣的多方面性分為“認識”的興趣和“同情”的興趣。人通過經驗從自然中獲得“認識”,而通過交際獲得“同情”。在赫爾巴特看來,學習者深入到所要學習的內容之中,接著對所學習的內容加以思考,這種深入世界和自我思考的相互作用,就是教育性教學。
三、訓育——服務于性格培養
簡言之,“對青少年心靈產生直接影響,即有目的地進行的培養,就是訓育。”但訓育的目的,并不是管理和教學,而是使受教育者過渡到自主的行動之中。簡單來說,兒童管理是阻止兒童的不明智行為,為有秩序的經驗和教學過程創造空間,而教學則是對兒童多方面性的培養,訓育側重于對兒童意志的培養,使兒童在行動中自主塑造性格,或者說,訓育是服務于性格培養的。訓育對性格形成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兒童的情感和兒童的思想范圍。訓育對性格的間接影響,最重要的體現就是教學。“訓育對于性格形成的第一層關系是最重要的,乃是訓育賴以為教學開辟道路的第一步,教學將得以滲透到兒童的思想、興趣與欲望中去”。而訓育對性格的直接影響則表現為“對變動較少并以堅定的目的行動的主體進行訓育”。但三者并非無共同點,正如赫爾巴特所說,“它與兒童的管理有共同的特征;它是直接對兒童的心靈產生影響的;它與教學共同的地方在于它的目的是培養。”
四、沒有絕對的“管制”,正如沒有絕對的自由
一直以來,人們把赫爾巴特看作是“教師中心”的代表人物而加以批判,認為他主張的教育忽視兒童個性乃至壓制兒童,是一種“硬性教育”。的確,赫爾巴特在其教育理論中,非常重視教師的作用,但是這并不代表忽視兒童的個性發展。就教學而言,在其思想中,教學并非中心,他倡導的是經驗和交際,教學是它們的補充,通過以上分析可得,他其實非常尊重兒童的個性,并提倡主動學習。通過管理,為教學創造一種良好的秩序,及時指出危險,使兒童避免對自己和社會的危害;通過教學,發展兒童的多方面興趣,通過教師的感情流露來感染兒童;通過訓育對兒童的心靈產生影響,使兒童在行動中自主塑造性格。所以,說赫爾巴特的思想忽視了學生的積極性是不可取的,相反,在一定程度上為兒童的自主創新創造了良好的指引和條件。首先,教育者應充分地尊重兒童而不是單純把他們看成單純服從管理的對象;其次,教育者應當感受到人類能夠具備的一切美好與可愛的品質;再次,合適的語言、清晰的表達方式是教育者幫助兒童解除疑惑的關鍵;最后,作為教育者應對自己的教育態度形成一致性和穩定性,從而杜絕兒童對教育者、對教育的懷疑。由此看來,不管是管理、教學還是訓育,更多的是對教師的要求,而不是單方面強調教師的權威。同樣,在筆者看來,盧梭所培養的“自然教育”下的兒童,也并非是絕對“自由” 的。盧梭認為,對人的培養就像一株小樹苗,人們總是迫切地想讓它按自己想象中的樣子成長,而結果卻將其弄的歪歪扭扭。但盧梭所強調的“自然”,實質上是強調要避免各種給兒童帶來不良影響的可能。“我們人類不愿意受不完善的教養”,但若是將其完全暴露于自然之境,則無益而有害,就如同那株小樹苗的另一種命運,生長在未加任何保護措施的大路上,任由行人推搡,最后只能死去。在盧梭看來,這株小樹苗如同一個人發展的初期,人在此時期所受到的教育,便是“最初的教育”。盧梭極其強調母親在“最初的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因為母親在“最初的教育”階段為兒童排除危險障礙,就像為小樹苗圍起一圈柵欄一樣給兒童的靈魂周圍筑起一道圍墻。因此盧梭的自然教育中的“自然”,是有條件的,這種條件便是確保母親在“最初的教育”階段為兒童排除了一切危險障礙,然后使教育順應兒童的天性發展才是可能的和可取的。因此,不管是赫爾巴特的管理、教學和訓育所體現出來的“管制”,還是盧梭的“自然教育”所體現出來的“自由”,都并非是絕對的,但是教育家們為了兒童的教育所做的努力,卻如一面旗幟,指引著我們不斷致力于教育的發展和完善。
參考文獻:
[1] 赫爾巴特.普通教育學[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02
[2] 盧梭.愛彌兒[M].北京:商務印書社,1978.06
——關注自然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