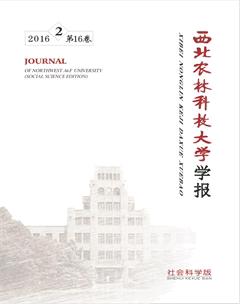中國土地制度改革市場化路徑選擇
摘要:以分析土地管理制度所處的耕地保護紅線、快速城鎮化和生態文明建設三個時代背景為邏輯起點,研究了在既有制度框架下市場化配置的三種策略:城鄉土地流動、耕地資源異地占補平衡和 “飛地工業模式”。在此基礎上,提出新一輪土地改革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改革路徑:城市土地一級開發的PPP模式,發揮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制度引擎作用,宅基地有限市場化配置和市場化思路推進征地制度改革。最后,提出政府在土地改革制度環境建設中的四個功能:科學規劃、搭建市場交易平臺、統籌協調利益關系和風險評估管控。
關鍵詞: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市場化;土地改革
中圖分類號:F32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6)02-0014-07
土地是財富之母,土地改革不是單純地重新配置土地資源,而是對社會資源進行調整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其一旦全面、縱深推進必將引起漣漪效益,帶動經濟社會全面變革[1]。縱觀我國歷史,幾乎所有重大社會變革都與土地制度改革相關,近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改運動更是如此,其與建立和鞏固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密切結合在一起,重塑了“國家鄉村社會”關系,改變了農村社會面貌和基層政權結構[2]。20世紀80年底初啟動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是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的重要轉折,直接奠定了我國現代農村基本經濟制度。歷史唯物主義觀啟示我們,任何制度都有其存在和發展的歷史環境和條件[3]。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時期,“新五化”與土地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土地改革被賦予了啟動經濟轉型升級,開啟新一輪改革制度紅利的歷史使命[4]。討論土地制度,應基于當前實踐,把握當前所面臨的核心矛盾,深刻理解土地與經濟改革的關系,把握歷史脈搏,把土地改革融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大潮中,服務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當前,土地領域主要矛盾是人地矛盾引發的土地資源短缺(有限資源在不同用途之間的優化配置問題)和農民在土地處置中話語權缺失[5]。因此,現階段我國土地改革必須在現有土地制度框架內,明確時代環境約束,遵循市場在土地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改革原則,優化土地資源的配置效率,并就相關權益進行確認、保護和完善,進而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大局。
一、當前我國土地管理制度背景
(一)耕地保護紅線
現行18億畝耕地紅線,是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提出:在土地問題上,我們絕不能犯不可改正的歷史性錯誤,一定要守住全國耕地18億畝這條紅線[6]。耕地紅線最終究源還是糧食安全問題,糧食安全概念是聯合國糧農組織1974年在《世界糧食安全國際約定》首次提出糧食安全是指保證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得到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夠食物。1996年11月,糧農組織對這一概念作了新的表述:只有當所有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夠在物質上和經濟上獲得足夠、安全和富有營養的糧食來滿足其積極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時,才可謂實現了糧食安全。 。糧農組織要求各國政府采取措施,保證世界谷物年末谷物庫存量不低于下一年消費量的17%~18%(安全系數)。從國家層面上來講,谷物安全系數低于17%為不安全,緊急狀態臨界值為14%[7]。同年,《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白皮書發布,提出立足國內資源、實現糧食基本自給的糧食戰略總綱。2008年,《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6-2020年)》發布實施,在國家層面對耕地紅線等土地管理政策進行了規劃確認。“18億畝紅線”是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的底線思維,習近平主席非常重視,指出保障糧食安全是永恒的課題,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松,解決13億人吃飯問題,要堅持立足國內[8]。在生產力不發達階段,法國重農學派以自然秩序為最高信條,視農業為財富的唯一來源和社會一切收入的基礎[9],隨著科技發展,農業生產效率和經濟產業總規模大幅提升,農業生產在國民經濟的比重逐漸下降,但是其重要性絲毫沒有減弱,是社會的基礎產業,“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這就要求把“18億畝紅線”戰略思維,在總體戰略布局中去謀劃思考,有效遠離或規避底線才能守住飯碗不端在別人手上的底線[10],才能更好地掌握戰略主動權。
(二)快速城鎮化階段
土地資源有多方面的需求,城市建設和糧食生產之間的競爭最為典型。我國城鎮人口比例由1995年的29.04%增加到2013年的53.7%,隨之而來的是全國城鎮建成區面積由1995年的5 603.6平方公里,增加到2013年47 855.3平方公里,18年間增加了8.5倍[11]。20世紀90年代,經濟戰略東移,東部沿海城市快速擴張,期間轉為城鎮建設用地的耕地面積占耕地減少總面積的45.96% [12];2000 年以后,隨著西部、中部和東北等區域開發政策實施,中西部城鎮也迅速擴張,期間轉為城鎮建設用地的耕地面積占耕地減少總面積的55.44%[12]。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相對于農村“散漫”建設用地,城鎮集中利用方式,對耕地減少有一定的緩解作用[13]。但城鎮一般布局在地勢平坦的糧食高產區,在城鎮化推進過程中,周邊大量優質耕地資源被占用基于這種現象,國土資源和農業部聯合發文《關于切實做好106個重點城市周邊永久基本農田劃定工作有關事項的通知》(國土資廳發〔2015〕14號),要求優先啟動106個重點城市周邊永久基本農田劃定工作,后續開展其他設區城市周邊永久基本農田的劃定工作。 。據統計,在1990-2010年20年間,全國建設用地增加主要分布在黃淮海平原、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四川盆地等地勢平坦、經濟發達的地區,由耕地轉為建設用地的規模為3.18×106公頃,占新增建設用地總規模的57.6%[12]。此外,我國城鎮化在達到70%之前,用地需求持續加快,已由20世紀90年代的約200萬畝/年,激增到本世紀頭10年的300萬畝/年[12],未來5~10年,城鎮化年均1.05%的增長速度,城鎮建設對土地的需求將更進一步增大[14],城鎮化與耕地保護的矛盾將進一步凸顯。
(三)生態文明建設提檔升級
土地的生態功能和生產功能、生活功能相互關聯且不可分割[15]。土地一般可直接發揮防風固沙、保持水土、凈化空氣、美化環境、維持生物多樣性等生態服務功能。隨著國家退耕還林(草)和其他生態保護工程的實施,生態用地在持續增加。據統計,1987-2010年,退耕還林(草)等生態建設用地增加導致耕地減少的面積占耕地減少總面積的34.54%,僅次于建設用地對耕地的占用比例[16]。但相較于土地空間利用屬性(生產功能)和食物生產屬性(生活功能)的價值取向,土地支撐自然生態系統的作用重視不足[17],導致生態系統在各地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土地是生態文明建設的空間載體,隨著城鎮霧霾等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我國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生態環境的恢復和建設日益急迫。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為了構建強化國家生態安全格局,遏制生態環境退化,以“生態紅線”的高度提出生態文明建設 [18],要求在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環境敏感區、脆弱區等區域劃定生態紅線。同時森林、草原、濕地、海洋等領域生態紅線也將隨之而來[19],其對土地資源利用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現有制度框架下市場化配置策略研究
基于當前時代背景,造就了我國現行土地制度的基本框架:以耕地保護為核心,以用途管制為手段,統籌土地利用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當中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土地利用規劃,我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自上而下的剛性規劃體系,通過國家、省、市、縣、鄉五級規劃體系,層層落實土地資源配置的空間和規模目標,明確了城鄉生產、生活和生態功能區范圍,具有空間分布確定性、規劃指標固定性和實施管理強制性三個特點。土地利用規劃是對未來區域經濟發展用地數量、用地結構、利用方式等方面的預測安排,面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確定,不可避免造成土地資源配置在區域、城鄉之間一定程度的扭曲和效率損失。為了彌補土地規劃剛性所帶來的效率損失,我國在土地管理整體制度框架內,形成了城鄉土地資源流動、耕地資源異地占補平衡、工業園區“飛地”模式等三種土地資源市場化的配置策略。
(一)城鄉土地資源流動
我國《憲法》和《土地管理法》都規定了城市國有土地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性質和用途,形成了城鄉二元土地結構。集體建設用地嚴格限制用途,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開發被嚴格控制,必須首先征收或征用為國有土地,以國有土地“市場化方式”來運作,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直接市場化配置方式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基本上無路可走。該套制度設計為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推進提供了基本保障[20]。加上1994年分稅制改革導致地方稅收比重下降和以GDP為核心的政府官員績效考核制度,助推了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進一步固化了城鄉土地二元結構。在多年的改革探索中,形成了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和地票交易制度兩種市場化策略來修正城鄉土地二元結構所導致的土地資源配置效率損失。
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是將擬整治復墾為耕地的農村建設用地和擬新建的城鎮建設用地等面積置換,其以項目區的方式來封閉操作,在保證耕地面積不減少的前提下,將生產效率低效的新增農村建設用地指標轉移到經濟產出效率高的城鎮范圍內,促進土地要素與勞動、資本結合,實現城鄉土地資源利用方式的優化配置[21]。增減掛鉤是被嚴格限制在縣域范圍內,因此可以說是小范圍、有限的市場化。2013年,國土資源部批準全國29個省份開展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安排指標90萬畝,標志著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在全國范圍內全面開展[22]。
重慶地票交易制度地票是指包括農村宅基地及其附屬設施用地、鄉鎮企業用地、農村公共設施和農村公益事業用地等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經過復墾并經土地管理部門嚴格驗收后產生的建設用地指標票據化的形式。。是重慶市作為統籌城鄉綜合改革試驗區的一個重要試驗內容,結合區域經濟發展和自然資源稟賦的空間非均衡性,根據比較優勢原則進行土地資源利用空間配置,有效實現了重慶遠離城市的經濟欠發達地區分享重慶都市區由經濟高度集聚而產生的經濟效益,從而實現了區域、城鄉之間的協調發展,是一項效率和公平兼顧的制度[23]。地票交易制度改革是發揮市場在城鄉土地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嘗試,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農村建設用地閑置、廢棄和城市建設用地緊張并存的矛盾,在耕地數量不減少、質量有保證的前提下,以市場化的方式發現農村閑置、廢棄建設用地的價值,使城鄉土地資源通過市場配置實現統籌利用、收益共享。地票交易制度相較于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有更大的空間配置范圍,不局限于縣域范圍內,其可在重慶整個市域范圍流動。同時,地票交易制度將城鄉建設用地指標增減掛鉤票據化,從更大的空間范圍內增加了城市建設用地指標的來源渠道。2010-2015年,重慶地票累計交易15.26萬畝,成交額307.59億元,均價20萬元/畝左右[24]。
(二)耕地異地占補平衡
《土地管理法》確立了占用耕地補償制度,要求非農建設必須經批準才能占用耕地,按照“占多少,補多少”原則,補充數量相等和質量相當的耕地。隨著經濟發展,可供開發的耕地后備資源日趨減少,越來越多的地區,尤其是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在本行政區內已無法落實耕地占補平衡義務。而部分區域耕地復墾潛力和后備資源又相對豐富,這樣就促成了耕地異地占補平衡市場化配置方式。國土資源部在2009年出臺《關于全面實行耕地先補后占有關問題的通知》中首次提到“有條件的地區可積極探索耕地占補平衡市場化運作方式”。耕地異地占補平衡有跨縣、跨市和跨省異地占補三個層次,除跨省占補平衡尚未開展外,跨縣域和市域的占補平衡已經開展多年。根據各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和土地資源現狀,各地探索模式也不盡相同。經濟相對發達地區,如江蘇、浙江、安徽都開展了耕地異地占補平衡指標調劑探索,其中安徽省建立了省級層面的耕地占補平衡指標交易平臺[25]。經過多年的實踐探索,我國已初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耕地占補平衡制度體系,不僅通過耕地占補指標的交易,籌措了大量耕地保護資金,實現了耕地保有量的整體平衡,同時也為快速城鎮化所需資金、勞動等生產要素高度聚集提供了建設空間[26]。
(三)“飛地工業”模式
根據科斯定理,在交易費用為零或者很小前提下,不管權利初始如何配置,當事人之間的自由交易都會促進資源配置的帕雷托改進。自上而下層層分解落實的土地利用規劃體系,不可能科學地顧及各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和自然資源稟賦。同時,建設用地指標作為我國政府協調地區平衡發展的重要手段,時常對經濟社會發展落后地區,給予建設用地指標配額上的傾斜。行政力量平衡區域之間建設用地指標,直接后果就是區域之間的苦樂不均,經濟發達地區指標不夠用,從而致使出現大量的非法用地;欠發達地區建設占用指標用不完而出現結轉現象[27]。當前東部發達地區建設用地指標嚴重稀缺, 土地成本劇烈上升, 而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卻有大量的建設用地指標沒有利用或者低效利用。在此背景下,發達地區由于發展空間有限,需要將一些產業層次相對較低的企業遷移出去,欠發達地區則為加快區域經濟發展,迫切需要產業項目。因此,“飛地工業”模式在上海、江蘇等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出現,并逐步擴散到中西部內陸地區。“飛地工業”是經濟相對發達區域輸出項目(附帶項目輸出的有資金、管理等生產要素),欠發達地區提供土地,以工業園區為紐帶和載體,雙方合作開發,共享“飛地工業”園區的稅收、GDP等。國內比較典型“飛地工業”園區有上海外高橋保稅區、啟東濱海工業園、湖南長沙汨羅(弼時)產業園。其中江蘇省應用最為廣泛,資源緊缺但經濟發達的蘇南地區和資源豐富但發展落后的蘇北地區,二者“一拍即合”,優勢互補,合作開發建設了33個“飛地工業”園區[28]。
三、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土地市場化改革路徑選擇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審議了《關于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標志著我國新時期的土地改革拉開大幕。無論是城市土地還是農村土地,在堅守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三條底線的基礎上,讓市場在城鄉土地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用市場化方式實現土地管理制度重構和程序再造,以提高土地資源配置效率,實現帕累托最優的改革路徑。
(一)城市土地一級開發的PPP模式
當前,在政府經營城市思路下,政府依靠對土地市場一級開發的壟斷,加上GDP政績觀驅使,一些地方政府通過廉價供地方式招商引資,助推了重復投資和產能擴張。同時,部分城市政府熱衷編制城市和產業新城規劃,規劃出來之后,就通過土地抵押貸款的方式,進行土地一級開發,隨后優先出讓住宅用地開發,消費者在政府規劃指引下,購買住宅,造就一派欣欣向榮景象。更為重要的是該階段是一個“自娛自樂”的階段,有著很強的自我循環動力,加深了這種趨勢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結果是新城產業園區能通過招商方式,成功實現產業發展,實現產城融合。但是,在經濟全球化分工背景下,一個城市經濟能否成功或持續穩健發展,很大程度上依靠自身資源稟賦,導致很多園區規劃往往不能完全按照政府的美好藍圖實現。比如比鄰的兩個城市A和B,A城市規劃汽車產業園區,B城市也規劃了汽車產業園區,兩個城市都將汽車產業規模規劃的很大,但整體市場份額有限,兩個產業園區不可能同時發展到規劃預期的規模,出現空城、鬼城現象。如果政府一直壟斷土地一級市場開發,不僅有可能造成土地價格扭曲,也可能嚴重誤導企業投資行為,不利于市場競爭。最終,土地升不了值,地方產業結構調整也不可能成功,與我國當前經濟結構升級方向背道而馳。因此,建議采用PPP模式對土地一級市場進行開發,實現城市土地市場化配置。政府可通過和專業園區管理經營公司簽訂合作協議,實現企業直接對開發區域進行前期規劃、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市政公用設施建設、土地整理、產業發展服務(招商引資服務)、物業管理、廠房建設租賃等“一條龍”服務,形成企業管理和主導的綜合園區、主體園區和產業港等生產聚集形式。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相較于政府,有著自負盈虧的經營壓力。企業可自由靈活(政府卻有各種限制)地整合全國乃至全球的產業專家,跳出政府各自為政和自我為中心的招商怪圈,針對特定區域具體情況,緊貼政策導向,通過產業價值鏈分析、資源匹配性分析、產業集群分析、產業類型綜合評估等技術措施,為區域量身定做戰略規劃方案,結合工業園區開發建設實踐,制定精準的產業發展策略,并依托強大的招商引資和產業培育能力推動落實。
(二)“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作為制度引擎,全面啟動土地制度市場化改革
土地制度本身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加上土地問題高度關聯性,導致了土地制度體系更顯重要、復雜。如2015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于授權國務院在北京市大興區等三十三個試點縣(市、區)行政區劃暫時調整實施有關法律規定的決定》,對土地征遷、宅基地、集體建設用地制度進行改革,需要對8部法律的24個條款進行修改[29]。任何制度變革,都會通過互補性關聯引發其他制度連鎖反應。對于當前城鄉統籌發展所面臨的諸多問題,我們不能再實施零散的改革,應抓住牽一發動全身的關鍵,積極推進一些基礎性制度改革,改變原有的制度均衡, 從而獲得制度變遷整體收益[30]。而這個關鍵,筆者認為就是農村集體建設土地入市,是新時期破除城鄉二元土地結構邁出的重要一步。因為當前集體建設用地涉及利益最多,矛盾最為集中。當農村集體進行建設用地入市取得實質性突破,可以取得以下幾個方面的政策效果:一是打破城鄉土地二元結構,實現城鄉土地資源的市場化流動,這是根本性突破;二是對基層政府土地財政依賴形成改革倒逼趨勢。在農村集體土地直接入市后,政府土地財政收益就會被大大削弱(不是沒有,通過設計相關稅費,在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中保障政府收益),倒逼地方政府調整城市經營發展模式,進而牽動全域整體性改革;三是通過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可以直接縮小征地范圍、減少征地矛盾;四是直接增加農民收入;五是釋放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用益物權特性,比如抵押、擔保權能,入市融資取得農村發展所需的資金。
(三)明確宅基地福利屬性的基礎上,實現有限市場化配置
現階段宅基地交易主要以 “流轉”的方式來操作,嚴格限制在本村集體內。我們可以設想,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直接入市,獲得土地增值收入,當宅基地被周邊大量經營性土地圍繞,這塊宅基地是否可以入市?如果不可以,受到利益驅使宅基地擁有者可能不顧土地利用規劃限制擅自交易,極有可能出現類“小產權房”或類“城中村”現象;如果可以,宅基地的福利屬性怎么保證。因此,筆者認為宅基地改革關鍵有兩個方面:一是如何保證宅基地基本的福利性質。當明確宅基地范圍后,參考城市控制性詳規,對宅基地建設進行規劃明確,比如其可以修兩層房子,只需一層即可保證該戶人家基本居住權,這時房地合一的產權證上注明該處宅基地上哪些房屋是用來保障基本居住權的,限制在市場上流通,或者在征得農民同意后集中居住,對于農民集中居住的那部分房屋禁止在市場上流通,以此保障宅基地的福利性質;二是如何實現宅基地有限市場化配置。當前大量小產權房不能轉為大產權的根本原因不是土地性質問題,如果是用地性質問題,可通過補交土地出讓金的方式改變土地性質。最根本的原因是小產權房建筑質量問題,因為合法合規的房屋在修建過程中有著嚴格的質量監管標準和過程,而這些是事后無法彌補,小產權房建設質量監管過程缺失,導致其不可能轉為大產權房。農民宅基地上修房屋,建設參照城市商品房施工許可和質量監管方式,在建筑質量有保證的前提下,宅基地上面所修房屋,在保障農民基本生存權后,無論是農民自己修建,還是村集體集中對多余宅基地修建,在規劃中明確,在相關稅費保證下,可以在市場上以買賣或者租賃的方式流通。這樣既能很好實現宅基地的福利屬性,又能充分發揮宅基地的其他權能,增加農民收入。
(四)市場化的補償方式,推動征地制度改革
如果農村經營性集體建設用地入市成功實現,城鄉土地市場就一體化,征地制度存在的基礎就將被大大削弱,其范圍必將縮小,只有涉及公共利益用地才應啟動征地程序。筆者建議公共利益征地也必須實行市場化的補償方式,具體方法可是雙方談判(政府和土地所有者)或第三方市場化評估的方式。沒有理由因為公共利益就損害那些被劃入公共利益范圍內土地所有者利益。比如,兩塊緊挨的土地,其中一塊是規劃道路要通過,而另外一塊可直接入市,如果直接入市的土地獲取了大量經濟利益,而因為公共利益(修路)而被征收的土地得到補償非常低,極有可能激發更大的征地矛盾。公共利益顧名思義,受益的是公共群體,大家都因為修這條路而受益,因此因公共利益受損方必須得到和直接入市大體相當的補償(但政府有強制征收權,這點和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自由買賣有本質區別,這里討論的僅是補償高低的問題),這個補償費用應由公共財政來承擔。
四、政府功能:建設好制度環境
制度是相互關聯和相互依賴的,一項新制度嵌入到穩定的現有制度體系中,整個制度體系的均衡性和穩定性就隨之改變,理想的制度設計和刻有歷史烙印的現存制度環境能否穩定“耦合”,是新制度成功的關鍵。只有相互支持的制度安排才是可維持和富有生命力的制度體系;否則完美的制度設計可能因“水土不服”,導致高度不穩定[31]。土地制度亦如此,當前土地制度改革單兵突進的改革不可能成功,必須改革配套措施跟進,相互支持配合。政府主體能動性主要體現在消除那些阻礙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既得利益藩籬,為市場發揮作用創造一個更好的制度環境,使改革能夠整體協調系統推進。
(一)科學規劃,并嚴格執行
土地利用規劃是發揮土地資源市場化配置方式的基礎,是用途管制、嚴守耕地紅線、生態紅線的根本手段。在允許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后,各農村集體組織和農民就成為土地一級市場的供應者,上市土地選擇、先后順序安排、用地類別等核心問題都會牽扯到利益多寡的問題,這些都會給土地利用規劃帶來全新的挑戰。建議在成熟規劃制度的基礎上,建立一套科學的規劃編制、規劃修訂以及規劃失誤后的補救機制。當前,面臨兩個較為突出的問題:執法不嚴和耕地質量控制不力。目前依靠遙感監測技術,可迅速甄別不符合規劃和政策的用地,但如果甄別后處罰措施跟不上,對規劃剛性將造成較大的損害。另一方面是耕地質量控制難度大,無論是增減掛鉤、異地占補平衡,還是地票等諸多制度創新,均涉及到耕地質量的這個本質問題,從數量上來講,相對比較好控制,在監管中,必須在耕地質量上多下功夫。
(二)搭建市場交易平臺,進行價格發現功能
建議地方政府在國有土地交易市場的基礎上,增加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交易的服務、管理功能,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交易平臺,實現國有建設用地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同一市場、統一管理”。市場交易平臺可以實現信息收集和發布,同時可建立法律顧問、政策咨詢、糾紛調解等配套機構。依靠公開統一的交易平臺,通過招標、拍賣、掛牌等市場交易方式,達到集體土地價格發現功能。
(三)統籌協調相關利益主體關系
土地改革核心問題是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問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須切實維護農民利益,在此基礎上通過集體權益分配體現集體經濟組織利益,并設計相關稅費兼顧國家利益。在本輪土地改革中,要理性務實面對產生的各方利益訴求,把蘊含在基層實踐的利益分配和化解矛盾的經驗做法,總結提煉上升為規范性制度固化。政府應搭建好利益分配和協調的整體框架,穩定的改革框架和分配預期能夠讓各利益相關方有穩定的預期,形成共識,取得最大公約數,對降低改革過程的交易費用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做好風險評估和管控
土地關聯的利益格局日趨復雜,深刻影響著各級政府利益和民眾的切身利益,敏感不確定因素增多,再精心的制度設計,改革也不可能實現百分之百的精準,總會出現各種各樣始料未及的問題。土地改革在小范圍試點中,要對利益相關方做充分的調研,尤其是農民,摸準他們的改革意愿和訴求,排查風險點,在改革方案設計中要建立風險排查、評估和處置機制,將風險和矛盾管控轉移,通過相關利益者的廣泛參與,穩妥決策、慎重實施,將土地改革風險降到最低限度,做到整體可控,不犯歷史性錯誤。著重評估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土地入市和征地制度改革對地方財政的影響,避免對現有政策體系造成較大沖擊,引發系統性、連鎖性風險。
參考文獻:
[1]佘君.建國初期土地改革與中國現代化的發展[J].黨史研究與教學,2002(5):3337.
[2]李里峰.經濟的“土改”與政治的“土改”——關于土地改革歷史意義的再思考[J].安徽史學,2008(2):6875.
[3]杜潤生.關于中闖的土地改革運動[J].中共黨史研究,1996(6):1522.
[4]巴曙松.土地改革是新一輪制度紅利的關鍵[J].經濟,2013(12):1920.
[5]臧知非.土地問題與歷史變革的深層邏輯[J].人民論壇,2011(10)上:2627.
[6]姜宏.耕地紅線的合理性探討[J].經濟研究導刊,2013(25):3637.
[7]焦建.中國糧食安全報告[J].財經,2013(25):17.
[8]習近平.手中有糧,心中不慌[EB/OL].[20131128].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28/c_118339303.htm.
[9]姚開建.經濟學說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23.
[10]李偉偉.農業的“底線思維”[J].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4(4):77.
[11]中國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4[Z].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4:453.
[12]劉紀遠,匡文慧,張增祥,等.20 世紀80 年代末以來中國土地利用變化的基本特征與空間格局[J].地理學報,2014(1):314.
[13]朱莉芬,黃季焜.城鎮化對耕地影響的研究[J].經濟研究,2007(2):137145.
[14]國務院.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EB/OL].[20140316].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16/c_119790653.htm.
[15]蔡運龍.認識環境變化謀劃持續發展——地理學的發展方向[J].中國科學院院刊,2011(4):390398.
[16]趙曉麗,張增祥,汪瀟,等.中國近30年耕地變化時空特征及其主要原因分析[J].農業工程學報,2014(2):111.
[17]龍花樓,劉永強,李婷婷,等.生態用地分類初步研究[J].生態環境學報,2015(1):17.
[18]朱前濤.耕地紅線與生態紅線概念比較[J].中國土地,2015(3):2426.
[19]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EB/OL].[20150602].http://www.scio.gov.cn/xw fbh/xwbfbh/yg/2/Document/1436286/1436286.htm.
[20]周其仁.縱論我國征地制度改革[EB/OL].[20040310].http://old.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3062.
[21]譚榮,曲福田.中國農地發展權之路: 治理結構改革代替產權結構改革[J].管理世界,2010(6):5664.
[22]國土部.增減掛鉤試點全國化[N].中國房地產報,20131102(05).
[23]白佳飛.探析重慶地票交易[J].中國房地產市場,2011(12):2425.
[24]黃奇帆.地票制度實驗與效果[N].學習時報,20150504(08).
[25]孫魯平.耕地占補平衡現狀及發展趨勢[N].中國國土資源報,20100716(08).
[26]張秋惠,薛劍,賈文濤.占補平衡怎樣“再平衡”——耕地占補平衡指標市場化交易機制研究[J].中國土地,2014(1):4345.
[27]陳江龍,曲福田,陳雯.農地非農化效率的空間差異及其對土地利用政策調整的啟示[J].管理世界,2004(8):3742.
[28]羅瓊, 金渡江.“飛地”之謎[N].南方周末,20130426(04).
[29]葉興慶.國研中心專家:2018年全面推進土改[EB/OL].[20150420].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04/20/c_127709409.htm.
[30]蔡昉.中國市場化改革三十年回顧中國農村改革三十年——制度經濟學的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08(6):99110.
[31]青木昌彥.什么是制度?我們如何理解制度[J].比較制度分析,2010(6):2838.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ree strategies (namely urban and rural land transferring, balance of cultivated land’s occupation and compens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 and enclave industrial model) during the market allocation under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rom the point of the red line of farmland protection, rapid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n, it puts forward a reform path on which market plays a decisive role during the new land reform, which are PPP mode of urban land development, bringing the collective profitoriented land entering the market into play, limited market allocation of homestead, reformation of land expropriation system pushing by market ideas. Lastly, it proposes four functions of the government during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land reform, which are scientific planning, setting up the market trading platform, coordinating interests and risk assessment and controlling.
Key words:land system reform; land market reform; land 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