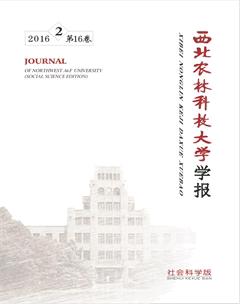農村養老方式的區域差異與觀念嬗變










摘要:伴隨中國經濟社會結構的轉型以及人口結構的變化,農村老人的養老觀念也在發生變化。通過對東、中、西和東北地區農村老人的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初步分析和探討了農村老人的養老方式及觀念變遷問題,并對其進行了區域比較。研究發現,“養兒防老”已變得難以為繼,多數老人在可承受范圍內進行自我養老,“土地養老”在部分農村地區較為盛行,但卻呈現出較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分地區來看,東部地區較為盛行自我養老,中部地區盛行家庭養老,西部和東北地區則盛行土地養老。究其原因,可從土地條件、經濟發展水平和文化傳統三個面向對其作出解釋。為順應當前中國農村養老方式和養老觀念的發展變化,從可能性、必要性、創新性和實踐性四個層面提出了農業養老的構想。
關鍵詞:農村養老;養老觀念;養老方式;農業養老;老人農業
中圖分類號:C913.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6)02-0093-10
改革開放以來,在工業化、城鎮化、人口老齡化的多重推動下,中國農村社會的人口結構和家庭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主要表現為農村老齡人口的增加以及代際分工模式的出現。根據2010年第6次人口普查數據統計,我國60歲及以上農村老年人口數量已接近1億。若按居住地計算,鄉村、鎮、城市的老齡化率分別為14.98%、12.01%、11.47%,鄉村地區要比城市地區高出3.51%[1]。另據民政部2013年公布的數據顯示,農村留守老人的數量已近5 000萬。伴隨城鎮化、工業化以及勞動力轉移速度的加快,農村老齡化趨勢還將進一步加劇。成年子女外出務工極大地改變了農村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并對傳統家庭養老方式帶來了挑戰。在此背景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是:目前農村老人的養老方式和養老觀念是否隨著經濟社會結構的變遷而發生變化,不同地區在養老方式和養老觀念上是否存在差異,如果存在差異,其原因是什么……
國內學者和政府部門對于農村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較為熟悉,相關研究成果積累也較多。但學界基于農村養老觀念視角的區域比較研究較少,且不夠深入,而政府部門則幾乎沒有關注到這種差異,從而導致涉及農村養老的各種政策、法律和制度的靈活應對性不足。據此,本文試通過對東、中、西和東北四大經濟區域60歲及以上農村老人的問卷調查與個案訪談資料,從時空觀的角度對農民養老的原生性供給——零散化的養老方式進行“深描”與“廣剖”。
一、調查情況與樣本介紹
本研究主要采用分層、典型抽樣的方法,以國家統計局認定的我國四大經濟區域范圍中選取江蘇、浙江、山東、安徽、河南、山西、湖南、四川、重慶、甘肅、陜西、內蒙古、黑龍江、遼寧13個省16個市44個鄉/鎮中的61個村為調查地點,由江南大學法學院農村與區域發展專業的研究生與社會工作專業的本科生利用2015年1-3月的寒假返鄉時間,對年齡在60歲及以上的農村老人展進行了問卷調查和半結構式訪談。本研究對于具體調研對象的抽取采用偶遇抽樣而非典型的概率抽樣,并以此調查資料為基礎,初步分析了農村老人參與農業生產的現狀、特征、動因及其養老經濟條件,同時立足于對現行農村經濟、鄉村倫理、社會關系、文化習俗等社會環境的分析,對農村養老觀念與方式進行區域比較,探討不同社會情境中的農村老人在養老偏好、養老方式、社會資本等方面的特征,以求對農村養老方式的區域差異進行深入解讀。問卷內容主要涉及個人基本情況、經濟供養、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以及養老方式等5個方面。其中,對于養老方式的界定主要是借鑒了穆光宗對于養老方式的認定標準:“在實際生活中,一種養老模式(制度)可能有多種的養老支持力來源,那么主要的支持力來源就決定了這種養老模式(制度)的特征”[2]。在問卷中設置了自我養老、家庭養老、土地養老和社會養老4種養老方式。其中,自我養老是指養老的主要的支持力來自于非農就業和非農儲蓄,如打零工等,從而與土地養老相區別;土地養老指養老的主要支持力來自于老人參與農業生產活動;家庭養老指養老的主要支持力來自于子女、配偶或者其他親屬;社會養老指養老的主要支持力來自于社會,包括居家養老、機構養老等。本次調查實際發放問卷300份,回收問卷267份,其中無效問卷7份,有效問卷260份,有效回收率為86.7%。
樣本的地區分布如表1所示,在東部和中部地區所獲得的樣本數量相對較多,但由于樣本在各具體地區的空間分布較為均衡,并不會影響樣本的代表性。
在本次調查中(見表2),男性占到一半以上;在文化程度方面,“小學及以下”的所占比重最高,達到70.8%,“高中及以上”學歷的僅占4.3%,這說明農村老人的受教育程度整體較低;在婚姻狀況方面,“沒有老伴”的占1/3;在年齡分布上,60~69歲年齡段的最多,80歲及以上的最少;從身體健康情況上看,表示“一般”和“較好”的比例合計占到八成以上;受訪農村老人的平均子女數為3個,最多子女數為10個;空巢老人的比例為37.3%,對于農村空巢老人,其子女回家探訪的頻率相對較高,外出子女半年內回家一次的占到49%,6~12個月的占19.2%,1年的占31.7%,超過1年的幾乎沒有。
二、農村老人的養老境遇與養老觀念
(一)四成以上的農村老人仍在從事農業生產,并將其作為重要的生活來源
調查結果顯示,77.9%的農村老人擁有土地,沒有土地的占22.1%,且均為土地被征收的失地農民。在擁有土地的農村老人中,38.7%的老人還在親力耕作,將土地交由子女或親屬耕種的占26.2%,把土地出租出去的占13.7%,其他占21.5%。通過進一步的深入訪談發現,目前農村老人參與農業生產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為了生計和養老需要;然后才是自我消費、休閑娛樂、補貼家用、習慣性行為、對土地有感情等。農村老人的經濟來源按所占比重見表3。六成以上的農村老人對于其基本生活來源表示“不擔心”。雖然子女供養是目前農村老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經濟來源,但參與農業生產仍是維持其生計和滿足養老所需的重要補充與保障。另外,本次調查顯示,仍有29.4%的農村老人目前正在幫子女帶孩子,78.8%的農村老人表示能從子女處獲得一定的贍養費,但這遠不能應付其日常開支。在訪談中許多老人都表示不愿意拖累子女,“趁自己身體還好還能勞動,就要多攢些錢,減輕子女的經濟負擔”“子女現在生活也不容易,能幫就多幫他們”。這無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學界的研究觀點,即:伴隨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離村從事非農活動,老年人獲得家庭成員照料的資源日漸萎縮,而且不得不更多地參與對孫子女的照料,以這種“付出”來“交換”自己高齡時子代的照料,代際互助中老年親代付出過多[3]。
(二)居住方式上以老兩口單住為主,生病照料與情感傾訴的對象主要是老伴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98.1%農村老人參加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75.4%農村老人享有政府發放的基礎養老金。雖然目前農村養老保障的水平相對較低,但對于提高農村老人的生活保障水平無疑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農村老人定期進行體檢的比例僅為23.5%,這可能與農村衛生醫療水平不高、看病不方便以及農村老人的醫療保健意識不高有關。在生病時的照料問題上,由子女照料和老伴照料二者所占比例相當(見圖1)。已有研究發現,伴隨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遷,農村老人在居住方式上的空巢化和隔代化趨勢不斷加劇[4],本次調查則進一步證實了這一觀點(見圖2)。農村老人與子女的日常溝通較好(見圖3),但在有心事時的主要傾訴對象還是老伴(見圖4)。從圖4可以看出,除老伴、兒子等家庭成員外,朋友與鄰居對農村老人的情感支持不容忽視,其作為一種傳統意義上的鄉村互助資源在農村養老方面的功能還有待進一步挖掘。
(三)休閑娛樂活動較為單調,急需開展多樣化的養老服務項目
由于目前農村文化娛樂設施較為缺乏,再加上代際分離及代際親情交流阻隔等問題,使得農村老人的情感生活匱乏,精神需求得不到滿足。從本次調查結果來看(見表4),目前農村老人的休閑娛樂活動較為單調,主要以看電視、串門聊天、打牌下棋為主,其他形式的文化娛樂較少,急切需要的養老服務項目主要集中在醫療保健、休閑娛樂、生活照料、身體鍛煉、心理護理及參與社會活動等方面。對于自己現在每天的精神狀態,37%的農村老人感覺很充實,認為自己的老年生活很幸福;31%的農村老人認為雖然自己現在衣食無憂,但無事可做,常感寂寞無聊;22%的農村老人覺得每天都很累,農活、家務做不完。目前具有互助性質的老年人協會等組織還屬于新興事物,僅在少部分地區存在,從而導致農村老人參與此類組織的比率較低,僅占6.9%。但這并不代表農村老人不愿意參加這樣的組織,通過進一步訪談發現,農村老人非常希望能夠通過加入這樣的組織來豐富他們的生活,滿足自身在養老方面的需求。
(四)老年生活滿意度總體較高,但主觀養老偏好與現實養老方式間存在一定差距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農村老人對于自己的老年生活表示“非常滿意”和“比較滿意”的合計占到57.8%,表示“一般”的占31.5%,而表示“較不滿意”和“非常不滿意”的僅占10.7%。對于子女在養老方面的義務問題,81%的農村老人認為女兒也有養老的義務。在主觀養老偏好方面(見圖5),家庭養老最受農村老人的推崇,其次為社會養老。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雖然家庭養老仍然是占主導的養老方式,但所占比重仍略低于理想中的狀態,自我養老和土地養老比重要高于主觀偏好。
由此可見,農村老人心目中的養老方式與現實生活中的養老方式間存在較大差異,在主觀上他們除推崇家庭養老外,對于社會養老抱有較高期待和需求,而自我養老和土地養老則屬于補充部分。但在現實生活中,由于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尚處于起步階段,村莊范圍內的社會養老服務建設還不完善,從而導致多數農村老人實際上仍主要依靠家庭和自己的勞作來為自己的晚安生活積聚資源,在生活中仍然與農業生產保持著密切關系。
三、農村養老觀念的嬗變
當前中國農村養老觀念在時代變遷中顯現出如下新特征:
(一)“養兒防老”變得難以為繼
尊老敬老素來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同時也是社會普遍遵從的道德規范之一。中國早在夏商周時期甚至更早的時候,就已經形成了尊老敬老的相關制度和風俗習慣,并隨后在儒家倫理思想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弘揚和強化[5],甚至將“孝行”列入中央政府選拔官吏的重要指標之中,漢武帝以后出現的“舉孝廉”便是明證,孝道觀念深入民心。受此影響,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家庭養老一直在傳統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相比之下,政府及地方對于鰥寡老人的社會贍養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則主要屬于救濟的范疇,發揮著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這種方式一直持續到新中國成立初期都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究其原因,這主要是鄉土社會的非流動性所致,“直接靠農業來謀生的人是粘在土地上的”[6],與非流動性相伴的是農民的農耕生計模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父母在,不遠游”的孝道觀念。然而,伴隨工業化、城鎮化以及人口老齡化的快速發展,鄉村社會逐漸轉型進入到“后鄉土社會”[7],其主要特征之一便是社會流動性增加,受此影響許多農村家庭依靠半工半耕的代際分工來實現家庭收入最大化,子女的持續外出在一定程度上對家庭養老支持力造成負面影響,傳統的家庭養老保障的功能趨向弱化,“養兒防老”觀念愈發變得難以為繼,并在個別地區甚至慢慢演變成“養老防兒”。
(二)強調在可承受范圍內進行自我養老
20世紀80年代初費孝通在對中國農村養老問題的研究中曾指出,西方國家是甲代撫育乙代、乙代撫育丙代的“接力模式”,子女沒有贍養父母的義務。而在中國則是甲代撫育乙代、乙代贍養甲代的“反饋模式”,贍養年老的父母是子女義不容辭的責任[8]。從社會交換的角度來看,在傳統的農耕社會,對于多子女的家庭而言,贍養老人是所有子女的共同義務,養老成本通過相互分擔而降低。與此同時,子女通過贍養老人不僅能夠實現對家庭財產、農業生產經驗的繼承,而且還能獲得地方社會的認可以及撫育孫輩的便利。因此,傳統的家庭養老具有一定的互惠性質[9]。然而,伴隨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和社會流動性的增加,農村多子女家庭逐漸消失,家庭日益趨于小型化和核心化,不僅增加了父母空巢的可能性,而且也弱化了代際贍養的家庭養老功能[10],從而導致農村養老在經歷了家庭保障和集體保障之后逐漸進入到家庭保障與多元保障相結合的時期[11]。本次調查也發現,隨著農村生育率的下降,家庭規模不斷縮小,從而導致兩重后果:一是子女養老負擔的加重,二是農村老人所能獲得的養老資源和養老支持的減少。對此,農村老人對子女多表現出體諒的態度,尤其是60~69歲年齡段的農村老人對子女贍養的期望相對較低,認為子女現在生活不容易,主張在有能力的范圍內進行自我養老。
(三)土地養老在部分農村地區較為盛行
在傳統農村社會中,家庭養老與土地養老是共生一體的,二者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土地作為親代傳承給子代的財產,子代自然有責任和義務去贍養自己的父母,因此,土地養老長期與家庭養老緊密結合在一起。但是在農村現代化變遷中,農業收入與非農收入、農村生活與城市生活之間的差距不斷被拉大,導致土地作為資產的傳承價值和作為職業的比較收益下降,減少了土地對于子代的吸引力。子女的持續外出使農村老人普遍認識到依靠子女養老已不符合實際,而真正靠得住的就是耕種土地,土地養老的功能在家庭養老弱化的背景下不斷得到強化。根據本次調查發現,在一般農業型的地區,土地養老已成為農村老人的主要養老方式,這一點尤其在東北、內蒙古等土地面積較多地區表現得較為突出。土地對于農村老人來言,不僅可以解決其基本的生存問題,而且還可以維持較低的家庭生活成本,解決老年人的休閑娛樂問題,并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老年人的尊嚴,確保其在家庭中的地位。
(四)農村養老觀念呈現出較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
根據國際上對于老年人的一般定義,將 60歲視作老年的開始。本次調查從生命周期的角度,分60~69歲、70~79歲和80歲及以上3個年齡階段對農村老人的養老偏好和現實養老方式進行分析。研究發現(見圖6),不論是主觀養老偏好還是現實養老方式,隨著年齡的增加,家庭養老的比重都在不斷增加,自我養老和土地養老的比重卻在不斷降低,而社會養老的比重則呈現出“中間高、兩頭低”的狀態。
但值得注意的仍然是主觀養老偏好與現實養老方式之間的差距問題,即:在主觀層面上,家庭養老與社會養老是農村老人最為認可的兩種養老方式,但在農村現實的養老圖景中,自我養老和土地養老卻是農村老人較為普遍的養老方式(見圖7)。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農村老人的養老觀念與他們的生命周期密切相關,在不同年齡階段表現出不同的養老偏好。年齡在60~69歲的農村老人一般還沒有完全退出勞動領域,自我養老和土地養老是主要養老方式,而對于年齡在70及以上的農村老人而言,由于身體的原因,參與農業勞動的比重在下降,家庭養老和自我養老是最為主要的養老方式。相關研究也證實,隨著年齡增大,老人對于家庭和政府社會保障的需求度上升[12]。事實上,絕大多數農村老人在年紀相對較輕且具有一定勞動能力的時候,基本都是依靠土地或打工進行“自養”,而其中土地養老是最為重要的養老方式。只有在他們喪失勞動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的時候,才考慮由家庭養老。因此,一個不可忽視的現實是,在打工潮對于家庭養老構成巨大沖擊的現實背景下,農村失能老人的養老問題如何解決,土地流轉雖然能使農村失能老人每年獲得少許收入,但并不足以解決其生存和養老問題。現行土地政策在制度改革上還存在較大的空間。
四、農村養老觀念的區域差異及其社會生態
本研究利用問卷調查數據,從宏觀上探討農村養老觀念的區域差異;并結合訪談資料,從經驗中提煉養老方式的具體形態,進而為推進農村養老方式的轉換提出可以操作化的、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
(一)農村養老觀念的區域比較
通過對農村養老觀念與養老方式進行區域比較研究,調查表明,當前中國農村養老觀念與養老方式的地區差異較為明顯。從主觀養老偏好的區域分布上來看(見表5),東部地區的農村老人贊同家庭養老和自我養老方式,中西部地區的農村老人贊同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方式,東北地區的農村老人則贊同社會養老和土地養老方式。可見,在主觀上農村老人對于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方式希冀較多。但現實情境中農村養老方式的區域分布卻與之有些差異(見表6),具體表現為:東部地區的農村養老主要以自我養老為主,家庭養老為輔,土地養老和社會養老的比重較低;中部、西部和東北三大地區的農村養老雖然都是以家庭養老模式為主,但還存在細微差異。其中,中部地區的農村以自我養老和社會養老為重要補充,依靠土地養老的比重較低;西部地區以土地養老和自我養老為重要補充,依靠社會養老的比重較低;東北地區的農村則是以土地養老為重要補充,然后是依靠自我養老和社會養老,二者比重相當。
(二)農村養老觀念區域差異的社會生態
如上文所述,農村養老觀念在國內不同的地方表現出一定的差異。那為何東部地區盛行自我養老,中部地區則推崇家庭養老,而土地養老則在西部和東北地區較為普遍?這些區域差異已不能籠統地用農業比較效益低來解釋。傳統觀點認為,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之所以流向城市就是因為農業生產比較效益低,從而導致農村空心化和農業勞動力老齡化。這一觀點能夠對農村養老觀念的縱向變遷作出宏觀性解釋,但無法對農村養老觀念的橫向區域差異作出中觀層面的分析,下文將主要從土地條件、經濟發展水平和文化傳統三個方面來分析農村養老觀念區域差異的社會生態原因。
1.土地經營條件。相關研究發現,一般情況下,如果農民有土地也有子女,他們的養老模式就是在享受社會養老保險的同時,通過家庭養老和土地保障進行養老[13]。然而,由于農業土地經營條件的差異,其對于農村養老的影響不能一概而論,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在不同地區表現不一。在本次所調查的樣本中,東、中、西、東北四個地區農村老人所經營的平均土地面積分別為1.51畝、3.72畝、8.03畝和10.24畝。結合進一步的深入訪談資料發現,由于地廣人稀,東北地區農村家庭所擁有的土地面積相對較多,比如:遼寧西南部農村人均耕地3畝左右如果以種植玉米為例,東北地區一般正常產量在500~600公斤左右,1年農業凈收入一般在每畝900元左右,一般農村老人擁有土地6畝以上,那么1年收入就是5 400元左右,那么農村老人依靠種地基本上可以滿足生存方面的需求。在西部地區,農村老人雖然擁有的土地面積并不算多,但由于青壯年勞動的流出,老人一般會接管親戚朋友的閑置的土地,再加上農閑時間從事養殖和打工一類副業的收入,晚年生活也獲得了相應保障。在東部地區,因土地收入比重下降、無土地與耕地集中趨勢、農民的土地保障情結變遷和年輕人脫離土地的傾向等方面原因,土地的保障功能不斷弱化[14]。中部地區則因家庭土地面積較小而限制了土地養老功能的發揮。應注意到,土地對于農村老人具有多重含義,在經濟上通過自給自足的農業耕作滿足其自身生活需要,貼補家用;在家庭內部通過從事農業勞動減輕子女的養老負擔和保持老人的經濟獨立,平衡家庭內部資源,維護老人的權威和尊嚴;在精神上成為娛樂休閑的重要方式,由于農村老人對于土地的特殊情感,農業勞作實際上已經成為其生活中的一種習慣、一種調劑、一種寄托。
2.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作為宏觀環境因素,區域整體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了一個地區的就業機會和就業環境。不同于一般的農業型地區,東部沿海農村由于鄉鎮企業較為發達,鄰近就業機會較多,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發展也較為完善,使得許多身體條件較好的農村老人仍堅持在附近的工廠里做工,在尚可憑借個人勞動來積蓄養老資源的經濟條件下,自我養老在東部地區得到大力推崇,且有部分經濟條件較好的農村老人還反過來為其子女提供必要的支持。相比之下,西部和東北地區的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就業機會較少,年輕子女紛紛外出務工經商,農村老人一般較為體恤子女的生活壓力,在土地面積尚能維持老年生活的情況下多選擇繼續從事農業生產。而像本次所調查的河南、山西、安徽、湖南等中部地區都屬于農村勞動力流出大省,在這些地方普遍盛行的是“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即通過子代進城務工經商和父代留村務農來實現家庭收益的最大化,但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鄰近就業和土地養老幾乎都不可能,半耕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農村家庭的生活負擔,但少量的土地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農村老人的養老問題,所以,農村老人仍需要子代在養老方面提供支持。
3.區域文化傳統。本次調查發現,中部地區農村多子女家庭所占比重高達94.1%,高于東部地區的91.1%、西部地區的83.6%和東北地區的88.9%。這種多子女的家庭結構勢必會對農村老人的養老愿景產生一定影響,因為多子女家庭可以均攤養老成本。但這也并不足以解釋家庭養老模式為何在中部農村地區最為普遍,因為多子女的家庭結構同樣存在于國內的其他地區,且多子女家庭在養老問題上容易產生互相推諉的現象。究其原因,除了土地經營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等因素外,另一重要因素便是文化因素,“重男輕女”“傳宗接代”“多子多福”“養兒防老”等傳統觀念在中部農村地區仍然根深蒂固[15],農村的孝道觀念與尊老敬老的氛圍也較為深厚,這無疑為家庭養老在中部農村地區的興盛提供了有利的輿論保障。而在東北農村地區,由于村莊形成的時間較晚,文化傳統和宗法關系較弱,家庭養老的文化傳統相對較弱。在東部地區,商品經濟發達,農村老人多秉承著“活到老、干到老”的生活理念,只要身體條件允許仍繼續到周邊企業中打工或為子女幫工,對于子女養老的期待并不太高。但從本質上來看,“養兒防老”在全國范圍內已呈弱化趨勢,且在個別地區甚至慢慢演變成為“養老防兒”,但由于中部農村地區在土地面積和經濟水平的雙重約束下,養老暫無其他出路,所以導致家庭養老仍占主導地位。
總的來說,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以及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深,中國社會中傳統的“家文化”基礎不斷受到削弱,導致中國長期建立在多子女基礎上的家庭養老模式無法延續[16],農村養老觀念已逐漸從“養兒防老”向“自我養老”“土地養老”“社會養老”等方面轉變,且各地區農村老人對于養老資源有著不同的需求,即使在同一地區,由于收入水平的分層也導致了農村養老的分化[17]。
五、一個政策性圖景的討論:農業養老的提出
農村養老觀念的變遷不僅是對家庭結構和代際關系變動的反映,更是對經濟社會環境發展變化的體現,同時也暗示著農村養老方式的可能發展走向。因此,準確把握農村養老觀念的發展走向,探索順應這一轉變過程的有效實現方式將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農業養老有無可能
長期以來,學界對于“自我養老”與“土地養老”的概念使用存在一定交叉,二者都包含了農村老人通過農業勞作而為自身提供養老資源的情況,提出“農業養老”的概念,具體涵蓋“以地養老”與“以農養老”兩個方面,前者主要涉及土地承包權與經營權的處置問題,包括將土地流轉收取租金和以土地換社保等情況,后者則更為精確地指代與農業生產有關的養老方式。提出“農業養老”這個概念主要是希望能夠將養老與農民所從事的職業連接起來,把農民、養老、農業這些原本被分割的問題重新聯系到一起,用另外一個概念去思考它們之間的體系性問題,比如:從事農業生產是否能為農民積累一定的養老資源;再比如,農民作為生產者能否決定和選擇自己的養老方式,等等。根據國際發展經驗,隨著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發展完善,農業生產中的諸多環節都可以通過專業部門的服務來實現社會化生產,農業機械化的普及和推廣為實現“以農養老”提供了可能。同時,以土地流轉為支撐,盤活農村土地、房屋、林權等資源,實現“以地養老”也并非完全沒有可能,而且可以較好地解決農村的養老困境。
(二)農業養老有無必要
農業養老方式早就存在,卻為何鮮有學者單獨把它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主要原因在于國家和社會對于農業養老的關注不夠,一直將其視作是家庭養老的一部分。農耕文明的一大特點就是自給自足,農業耕作以家庭為單位展開,四世同堂是其至高理想,在此情境中,農業與家庭渾然一體,農業養老與家庭養老密不可分,農業耕作為養老提供經濟支持,宗法關系及傳統道德則為家庭養老提供輿論保障。家庭收入的單一化隱沒了農業養老的特殊性,社會的不流動消解了農業養老的獨立性,而實際上傳統農村社會的家庭養老水平并不高,多數老年人還是主要通過參與農業生產活動來積蓄資源以換取子代較好的供養。但進入現代社會,隨著城鎮化、工業化進程的推進,社會流動加速,一方面,家庭養老作為一種典型的私力救濟,對子女的健康、收入、孝道觀念、道德等方面要求較高,其不確定性愈加突出;另一方面,農業生產的比較效益降低,農業生產不再是家庭唯一的收入來源,尤其是當子代外出務工經商的收入遠遠超過務農收入之后,農業幾乎成為了農村老人的專屬職業,代際生活的區隔進一步突顯了農業生產對于農村老人的重要意義,同時也預示農業養老和家庭養老開始從合一走向分離。與傳統家庭養老方式相比,農業養老的制約因素較少,是一種更加穩定的保障,它支撐著農村老人維系低消費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從而實現老有所依[18]。對此,我們十分有必要重新審視農業生產以及土地對于農村老人晚年生活的價值,將農村老人的“農業養老”能力納入決策分析,科學定位農業養老的地位和作用,構建農業養老的政策支持體系,從而為家庭養老向社會養老的順利過渡提供保障。
(三)農業養老如何創新
發展完善農業養老意義重大而豐富,那么基于現存的制度條件如何對農業養老方式進行突破和創新?通過調查與走訪發現,農業養老對于農村老人而言,經濟效益不是那么被看重,重要的是通過農業勞作維持長期形成的生活習慣,確保經濟上的獨立,捍衛自己的尊嚴。在這個意義上,農業除經濟功能外的社會保障、文化傳承、娛樂休閑等功能無形中被加以突出和放大。因此,發展完善農業養老應緊扣國家政策文件精神,通過開發農村二三產業增收空間,延長農業產業鏈,提高農業附加值,拓寬農村外部增收渠道。第一,可以嘗試引入農業的多功能元素,結合地方的資源稟賦與戰略規劃,積極開發農業多種功能,挖掘鄉村生態休閑、旅游觀光、文化教育等價值,將完善“以農養老”與發展休閑農業結合起來。第二,探索土地托管、經營權入股等形式,與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相結合,提升小規模農戶的生產效率。第三,還應鼓勵發展“公司+合作社+農戶”模式,增加農村老人的就業機會和社會福利,通過農業的“接二連三”實現產業整合,進而達到增進農民晚年福利的目的。
(四)農業養老的階段性如何超越
如果考慮到絕大多數農村老人的養老圖景,其養老方式可能主要由三塊構成:一是農業養老,二是家庭養老,三是社會養老。在農村養老保障體系尚不完善和家庭養老功能不斷弱化的情況下,第一塊農業養老的作用不容忽視。只要有土地,一個身體尚好的老年人多少都會種點地、養點雞,加上每月的養老金,養老問題不大。然而,現行的農業養老方式只能夠解決那些年紀不大、尚有勞動能力的農村老人的養老問題,而年齡較大的失能老年人則會因為無法從事農業耕作而失去這種依靠。隨著時間的推移,曾經依靠農業勞動養老的老人將不可避免地面對無力勞作的困局,那么此后的養老方式也必然會發生轉換,需要農業養老的創新、家庭養老的接續以及社會養老的完善。對于農業養老而言,重點是在穩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推進土地流轉政策的調整,探索“以地養老”的實現形式,充分開發和利用土地資源,為農村養老提供有力支撐。對家庭養老而言,需要在整個社會范圍內弘揚孝道觀念,樹立尊老敬老的社會風尚和道德氛圍,同時,培育和挖掘各種社會支持網絡,減少老人因子女外出而產生的孤單和無助感。對于社會養老而言,由于目前在農村地區實施的“新農保”和其他社會救助制度的整體保障水平較低[19],且在籌資方式、管理機構設置及與城市養老保險制度銜接方面仍然存在諸多問題[20],受繳費能力的限制,農村老人的基本養老保險等級尚不能在短期內得到較大幅度的提升[21],子女供養、農業生產仍是其生計的主要來源[22]。對此,當務之急需要探索多樣化的社區養老、居家養老和助老服務模式,輔助發揮家庭養老的功能。
參考文獻:
[1]沈毅.土地養老緩解農民壓力[EB/OL].[20141006].http://www.cssn.cn/sf/bwsf_tpxw/201410/t20141006_1351853.shtml.
[2]穆光宗.家庭養老面臨的挑戰及社會對策問題[M]//中國老年學學會.中國的養老之路.北京:中國勞動出版社,1998:54.
[3]王躍生.城鄉養老中的家庭代際關系研究——以2010年七省區調查數據為基礎[J].開放時代,2012(2):102121.
[4]孫鵑娟.勞動力遷移過程中的農村留守老人照料問題研究[J].人口學刊,2006(4):1418.
[5]杜振吉,郭魯兵.儒家的社會公德觀[J].孔子研究,2007(6):415.
[6]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J].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7.
[7]陸益龍.后鄉土中國的基本問題及其出路[J].社會科學研究,2015(1):116123.
[8]費孝通.家庭結構變動中的老年贍養問題[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3) : 615.
[9]余飛.家庭養老的困境與出路——兼論孝與不孝的理性[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5):124130.
[10]周長洪,劉頌,毛京沭,等.農村50歲以上獨生子女父母與子女經濟互動及養老預期——基于對全國5縣調查[J].人口學刊,2011(5):5763.
[11]張仕平,劉麗華.建國以來農村老年保障的歷史沿革、特點及成因[J].人口學刊,2000(5):35.
[12]王世斌,申群喜,余風.農村養老中的代際關系分析——基于廣東省25個村的調查[J].社會主義研究,2009(3):8488.
[13]柳清瑞,穆懷中.中國有無土地和有無子女兩序列農民養老模式及水平分析[J].人口與經濟,2014(4):109117.
[14]梁鴻.蘇南農村家庭土地保障作用研究[J].中國人口科學,2000(5):38.
[15]魏利香,鐘漲寶.農村養老性別偏好影響因素分析[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15(2):121126.
[16]風笑天.從“依賴養老”到“獨立養老”——獨生子女家庭養老觀念的重要轉變[J].河北學刊,2006(3):8387.
[17]劉春梅,李錄堂.農村養老資源供給模式優化及運行[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15(1):814.
[18]王海娟.莫讓農民老無所依[EB/OL].[20150316].http://snzg.cn/article/2015/0316/article_40695.html.
[19]穆懷中,沈毅,樊林昕,等.農村養老保險適度水平及對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分層貢獻研究[J].人口研究,2013(3):5670.
[20]彭希哲,宋韜.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研究綜述[J].人口學刊,2002(5):4347.
[21]黨國英.統籌城鄉土地規劃 提高農民養老水平[EB/OL].[20140209].http://theory.rmlt.com.cn/2014/1209/356653.shtml.
[22]Suyan Shen, Fang Li, John Kipkorir Tanui.Quality of Life and Old Age Social Welfare System for the Rural Elderly in China[J].Ageing International,2012,37(3):285299.
Abstract: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 and demographic change, the endowment ideas of rural elders were changing. Through a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s of rural elders from eastern, central,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of China, this paper preliminary analyzed the change of rural elders’ endowment mode and endowment ideas, and comprised regional differences. This study found that “raising children for old age” had become unsustainable, more rural elders emphasized on self endowment in the affordable range, land endowment was prevalent in some areas, but showing a more obvious stage characteristics. Regionally, self endowment is more prevalent in the eastern region, family endowment is prevalent in central region, and land endowment is prevalent in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The reasons can be explain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land condi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cultural tradition.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current endowment mode and endowment ideas of Chinese rural elders, this paper proposed agriculture endowment from four aspects of possibility, necessity,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rural endowment; endowment ideas; endowment mode; agriculture endowment; aging agri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