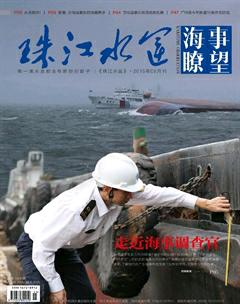水上“福爾摩斯”
胡素青

海事調查官是個特殊的崗位,不是誰都能做得。他需要是個全才。“海上事故的原因錯綜復雜,調查人員需要具備航海、輪機知識,船體結構,公司管理,船員心理,調查技術等多方面的知識。”珠海海事局執法督察處處長、高級海事調查官、部海事局涉外調查機動組三名正式成員之一的許巖松這樣告訴記者。
他需要思維嚴謹。“事故調查過程中涉及對對證據的分析、對事故原因的分析、還有對責任的認定,這些都對調查人員的思維能力提出要求。”許巖松表示。
他還需要有探索精神。“事故原因往往隱藏于事物表象之下,需要不斷去挖掘去思考,才能找出事故背后的真正原因。”身經百戰的許巖松深有體會。
還有關鍵的一點,他需要公平公正。“若不公平公正,其調查結論必然經不起時間的檢驗。”許巖松認為,這對一名事故調查人員來說,是“硬傷”。
總之,選擇這份職業,就要將自己百煉成鋼,像福爾摩斯一樣具備洞悉一切的本領。
屬于“調劑志愿”
事實上,這份職業并非令人趨之若鶩。
許巖松告訴記者,綜合比較各項海事業務,事故調查其實是個苦差事。這種苦,不光是對外在困難條件的克服,心理上還要承受更多壓力。“不但體力上辛苦、精神上更辛苦。”許巖松深有感觸。
體力上自不必說,一旦事故發生,事故調查官必須第一時間趕赴現場。水上事故的現場情況,大家可想而知。而無論環境多么惡劣,海事調查官也不能退縮,必須立即進行緊張的現場調查工作;調查后還要立即對證據進行認真分析,然后要快速完成幾十頁的事故報告。
到這里,事情遠遠沒有結束,或者說這才是精神折磨的開始。因為調查報告完成后,還要經受當事人、法院等各方面對報告的質疑和挑戰,期間還要妥善解決當事人的糾紛,要防止事故各方因情緒失控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做到高級海事調查官,幾乎都會經歷幾宗投訴。因為水上事故一旦發生,事故責任賠償動輒幾千萬。而事故調查涉及責任認定,難免有不服被處罰一方前來信訪,或者向更高一級法院上訴,要求重新審議調查結果,重新判明責任。據廣東海事局高級海事調查官方同林介紹,有些事故責任方競能因此糾纏幾年還不罷休,讓海事調查官不堪其擾。
許巖松也承認,海事調查官的最大難處就是“心累”。就拿PSC來說,檢查官上船檢查主要靠個人,想業務提高就檢查細致些,想混就專挑一些容易的檢查,但不管細致與否,檢查完一艘船就是一艘船,事情有個結束,事后也不用反復再想。海事調查就不一樣,一宗事故有時能處理若干年。讓人只想仰天長嘆:“事故調查何時休?”
因此,很多人不愿從事海事調查。
這也就導致很多人對事故調查官有些偏見。一個普遍的說法是,“水平高的人都不想干,想干的入水平大多又欠缺”。雖然有失偏頗,也真實反映出這個崗位的尷尬處境。
許巖松對此不太贊同,但是無法否認一個現狀:很多調查人員是因工作安排,到了這個崗位,本身意愿并不強烈。或者被第二志愿調劑過來,水平也就參差不齊。
但不可否認,水上事故調查過程中,在不斷涌現出一批批杰出的代表。不管他們因何走向這個崗位,最終卻盡心盡力地完整自身的使命。廣東海事局如是,全國海事系統亦如是。
中外福爾摩斯對比
在培養水上“福爾摩斯”的過程中,因為國情和制度上的差異,各國海事調查的水準某種程度上也是有差別的。
許巖松也承認,我國的事故調查工作起步較晚,在理論和技術上與發達國家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這一點與海事調查職能的變遷息息相關。據了解,在82年《海安法》出臺之前,我國水上事故調查的作用主要是解決因海上事故引發的民事糾紛,港監部門承擔了目前海事法院的工作。在《海安法》出臺之后,各地成立了海事法院,海事調查的職責明確為“查明原因,判明責任”,海事調查的重點也從解決民事糾紛逐漸轉為查明事故原因方面。此時,海事部門依然承擔著許多事故調解工作,一些海事人員包括調查人員在思想上并沒有轉變,依舊以解決民事糾紛為重點,滿足于責任的認定,導致查找事故真正原因的動力不足,長期以來制約了海事調查的發展,海事調查在理論及技術上落后于發達國家。
直到90年代初,出臺了《海上交通事故調查條例》,規定了事故調查的程序及要求,我國的事故調查水平才從此發生質的飛躍。1999年“大舜”號事故發生后,調查人員更是從人、船、環境、救助等多方面查找事故發生的真正原因,最終促使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安全制度,如老舊船管理規定,客滾船管理規定等,同時在其推動下建立健全了我國的搜救體系,組建了國家及各地海上搜救中心,成立了飛行服務隊,大大提高了我國水上搜尋救助能力。這一點海事調查官功不可沒。
發展到現在,差距仍然無法消彌,從理念、組織機構到調查技術,我們的海事調查官與國外“福爾摩斯”相比始終差了一點距離。
其中,理念上的差距表現在,發達國家調查理念為獨立調查、安全調查,其調查不受任何組織和個人的干擾,而其調查也僅以防止類似發生為目標,并不作出責任判定的結果,屬于安全調查的范疇。我國更多是為了服從履約的需要,對事故有一個交代。這一點,香港水域與國際接軌度更高。據方同林透露,類似的兩宗海上事故,分別在香港水域和廣東水域發生,因為調查角度的不同,最終事故判決的責任雙方可能是相反的。這與調查對錯沒有關系,純屬理念上的差異。
機構上的差異也很明顯。據許巖松介紹,國外事故調查官是獨立機構,有專業的調查團隊。比如英國的MAIB、美國的NTSB和澳大利亞的ATSB,這些機構唯一的業務便是海事調查工作,不但專業,而且更容易結成團隊作戰。而國內受體制所限,海事調查人員基本是“兼職”。就像古時代的屯田法,士兵“平時務農,戰時打仗”。有事故發生時,他們是“福爾摩斯”,調查結束后還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在等著他們。這是國內海事系統的一個普遍現象,像安全檢查官、PSC等,都面臨同樣的問題。而且,一崗一人,一個單位(部局、直屬局、分支局、海事處等)海事調查崗位也就一人,“發生事故時,難于形成專業的團隊開展調查工作”,這也是許巖松比較擔心的問題。
調查技術的差距也不容忽視。許多國家,如英國MAIB的海事調查人員幾乎是全是船長、輪機長,進入該機構后還得經過兩年的實習過程,這兩年要熟練掌握調查詢問,現場勘查、安全評估、證據分析、報告編寫、媒體應對等技術,真真兒是一個長期的“福爾摩斯培訓營”。單從海事調查人員的培訓來看,我國可以取長補短,這個真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