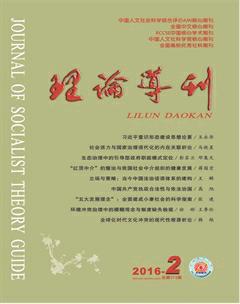關于大學生法律信仰教育問題的思考
范光杰
摘要:法律信仰問題既是法治國家建設的精神條件,也是大學生法治教育的核心。澄清法律信仰是否可能、法律信仰何以可能,是法律信仰教育的前提和基礎。大學生法律信仰教育要實現從重外在制度到重內在制度的轉化,路徑上要從培養大學生法律情感入手;要實現從重義務到重權利的轉化,路徑上要從培養大學生法律生活方式入手;要以法律意識為切入口,培育大學生的法律信仰。
關鍵詞:大學生;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教育;良法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6)02-0094-04
法律信仰是人們信仰體系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當前我國正處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依法治國的關鍵時期,大學生作為時代青年的先進代表,他們的法律信仰狀況如何,直接關系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成敗。
一、規則與信仰:法律能否被信仰?
談法律信仰教育問題,首先要厘清法律能否被信仰這一前提。法律信仰問題在我國法學理論上存在很大爭議。1971年,美國法制史學家和比較法學家哈羅德·伯爾曼在《法律與宗教》中提出:“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將形同虛設。”[1]40多年來,伯爾曼關于法律信仰的這句箴言式的表述成為了研究者必須的引文,甚至是研究的起點,在法學理論界引起了熱議。爭議的焦點涉及法律信仰這一命題的真偽,即法律能否作為信仰的對象,法律是否具有被信仰的要素。這是我們研究大學生法律信仰問題的前提,這樣才可能進而研討大學生法律信仰教育問題。對此我們是持肯定態度的。
在西方法律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一直存在二元化思維方式,即存在一個自然法和實在法的對立統一問題。自然法是永恒的、不變的,實在法是具體的、流變的,甚至西語里用不同的詞匯來表達它們之間的差別。比如拉丁語的Jus和Lex,前者不僅表示法,更為重要的是它具有正義、公平、權利等抽象的含義,后者指稱國王、元老院等機構頒布的具體的規則。自然法高于實在法,實在法應該體現和表達自然法也是西方重要的法觀念。在這種文化基因中就包含了對實際存在的、世俗的東西的警惕、貶抑、批判,哪怕是世俗的最高權力及其出自于最高權力的規則。對超實體、超自然的東西特別信服、崇拜,對于法,他們信仰規則后面的理念、價值,正如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對法的定義:“人和神的事務的概念,正義與非正義之學。”[2]西方社會經歷過宗教絕對統治的中世紀,對上帝的信仰和對上帝之法的信仰是一致的。上帝法、自然法、實在法依然存在二元化,統一于最高的上帝之法。法律與宗教在西方中世紀有一個否定之否定的回復,規則融合于信仰之中,借信仰的力量規則獲得了普遍性、神圣性。世人通過對上帝的信仰,得到神的啟示和顯現,認識到部分自然法或永恒法,制定出在俗人世界適用的世俗法,不通過信仰或者沒有上帝投射下來的“影像”,人類甚至連永恒法的“殘片”都無法認識,更不能制定出自己的法律。而且世俗的法律只有符合自然法、永恒法才是有生命力的,實在法在下,永恒法、上帝之法在上,世俗法律是由俗人制定出來的,它可以追求公正但永遠不能達到永恒法的公正,它只能隨著時間的變化而加以適當修正。凡是能接近永恒法律的世俗法律一定能長久存在,否則就會自取滅亡。[3]
西方近代化過程中,人性戰勝了神性,啟蒙運動使得理性精神極度張揚,他們用正義、平等、自由、人權等法的現代價值對宗教信仰進行“去魅”,自然法的理論得到了極大的傳播和支持,但是,自然法的基礎理論同樣具有超驗的品格,是先驗的,是不用質疑的公理或不言自明的真理。因此,在上帝隱退以后,對法的理性的挖掘,使西方價值體系中的信仰要素得以轉換和延續, “人們對宗教經典《圣經》的信仰也轉化為人們對世俗法律的信仰。”在自然法大師們的經典著作里,我們可能很難得到法律的具體規則、具體知識,但是我們能夠真切地感受到他們對正義、自由、平等、人權等超驗價值近乎宗教般的狂熱追求。人類的理性戰勝了宗教,但是并沒有完全背叛信仰、摒棄信仰。
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問題的關鍵所在,法律等同于規則,規則中不包含信仰的因素,不能夠成為信仰的對象。這使得在中國語境下規則與信仰的建構相當困難,法律信仰教育的前提就是規則體系與信仰體系的內在轉化和高度融合。在規則中完全清除了價值的因素,法律就是法律,規則就是規則,法律被空心化,它的生命力就枯竭了。在中國式語境下,當我們用法律去修飾、限定信仰的時候,去討論法律信仰問題的時候,由于缺乏西方語境下的那種法律與法的二元化的歷史文化和思維方式,舍棄了法律的價值、法律的精神,法律就剩下規則的殼。沒有規則,就沒有秩序。沒有秩序,人就沒有類生活。沒有對公平、正義的追求,規則就只剩下強力,單純強力甚至暴力的規則難以長久維持秩序。法律信仰問題不單是對規則的信服、崇拜,法律信仰更為深層次的意味在于對規則所應體現和反映的崇高價值,諸如正義、平等、自由、權利等的強烈渴望和追求,以揚棄人性中的粗陋、自利和殘暴。在這一層面上,規則和信仰應該是統一的,法律信仰是可能的。這一前提存在,法律信仰教育的問題也才是可能的。
二、良法與良民:法律信仰的兩個條件
法律信仰教育問題,還要弄清楚法律何以被信仰的問題。法律信仰問題包含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個是信仰的主體,一個是信仰的對象,或者簡言之,即良民與良法的問題。這個問題要回答的是什么樣的法律才能作為法律信仰的對象,什么樣的主體才能構建法律信仰。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提出了法治的兩層含義,也是法治的兩個條件或標準,“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4]從這兩個標準來看,法治不能只講服從規則治理,這只是法治的形式方面,它主要強調法律的權威性,簡言之就是法律至上;法治的內涵還包括其實質方面,即人們應該服從善法之治、良法之治。法律信仰的問題應該是信仰主體與信仰對象的高度統一。
從法律信仰的對象方面來說,人們何以對法律表現出極度的尊崇、敬仰,乃是法律本身反映了主體的利益、意志和愿望,法律體現了尊重生命、尊重權利,符合人性、符合正義,崇尚自由、崇尚公平等社會主體追求的良好價值,簡言之即“良法”。西方社會在近代化的過程中,一方面能夠成功地對宗教信仰進行“去魅”和解構,另一方面啟蒙思想家,特別是自然法學派的思想家們用正義、平等、自由和人權等建構起了一個新的神圣的法律帝國,否則,當上帝被解構,神性被“去魅”,信仰體系就會發生斷裂、崩塌,人們就會迷失方向,其行為就會無所適從,心靈就會空虛。西方社會能夠成功從宗教信仰轉換到對法律的信仰,離不開思想家們對法律精神和價值的建構,在他們的著述中我們難以發現非常精細準確的法律規則,但是他們極力倡導法治精神,傳承自然法傳統,把正義、平等、自由和人權等推崇到極高的地位,超然于具體規則之上,而具體的法律規則要體現出、服從于這些精神價值。這些原則和精神構成我們制定良法的精神向導。如今,在改革開放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宏觀背景下,我國法制建設雖然取得了很多成績和進步,但是還很不完善,尤其當下各種矛盾處在多發期,問題比較多、比較復雜,利益調整的格局比較難以駕馭,我們的法律規則還不能完全適應。但我們要清楚一點,作為規則的法律雖是不斷發展的,變動不居的,難以把握的,但作為信仰層面上的法律精神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卻是穩定的,所以只有體現公平正義,符合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法律,才是良法。
從法律信仰的主體方面來說,即便有了良法,法律信仰也不可能自發形成。只有法律信仰的主體自身的素養得到很大的提高,才能與良法之治相匹配,既有良法,又有良民,這樣社會才會崇尚法治,社會才會信仰法律。“只有良法而沒有良民,不可能有法律信仰;同樣,只有良民而無良法,也不會有法律信仰。”[5]如果說良法是法律信仰的“硬件系統”,那么,良民就是法律信仰的“軟件系統”,是心理和行為的內在統一。法律,就一般意義而言,是外在于人們的行為的,這是法律與道德、宗教相區別的顯著特征。人的行為是社會的產物,是受社會環境的影響和社會關系的制約的,與動物的活動有著根本的區別,是通過社會化的方式習得的,而不是本能和自然的稟賦。馬克思指出:“人的活動和享受,無論就其內容或就其存在方式來說,都是社會的,是社會的活動和享受。”[6]而且人的行為也是在一定思想、意識、意志支配之下的有目的的活動,表明人們的行為必定存在一定的主觀方面、內在方面,人的行為本身是主客觀方面的統一。作為規則層面的法律可能更加關注行為的客觀方面、外在方面,作為信仰層面的法律則觸及行為的主觀方面,信仰是主體對信仰對象極度的信服、敬仰、崇拜,在主觀、心理層面處于積極肯定的狀態,在客觀、行為方面表現出對法律的尊重、服從和捍衛。
法律信仰教育問題當然的職責就是塑造良民。作為法律信仰的主體,良民是法治建設的社會基礎,既是法治社會建設力量,也是法治建設成果的重要體現。法治社會不僅要有公平合理的良法,還要培育具有良好素養的公民。法治社會良民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形成,要啟蒙、培育公民對法律的認同感、信服感,體認法律所包含的精神價值,在行為上才能表現為強烈的自覺。作為規則層面的良法,可以通過制定、修改、補充、廢止等方式不斷改進完善,但是作為法律信仰主體層面的良民,則要通過系統教育加以培養,法律信仰教育的目標就是培養良民。
綜上,良法可以被信仰,法律信仰可通過系統地教育培養良民得以實現,即大學生法律信仰問題可通過教育加以解決。
三、理念與路徑:法律信仰教育的觀念與方法轉變
當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針對性、實效性難以令人滿意,許多研究者對大學生法律信仰問題表現出極度的憂慮,對大學生的法律信仰重構缺乏信心,研究大學生法律信仰問題的成因和對策的文章很多,讀來仍然使人茫然,我們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教育的理念和實踐的路徑。在教育實踐層面上,要注重回答法律信仰如何成為現實的問題。
首先,法律信仰教育理念要實現從重外在制度到重內在制度的轉化,路徑上要從培養大學生法律情感入手。盧梭曾言:“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們的內心里。”[7]在人類行為的規則體系中,總是存在正式的規則和非正式的規則、外在規則和內在規則,人類的行為不可能完全由正式的規則或者從外面強加的規則來控制和調整,“內在制度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內化為國民信仰的過程中,承擔著外在制度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內在制度的作用,類似于道德規范的作用。人們的社會實踐,不僅僅要遵守強制性的外在制度規范,更應該具有道德自律。這種自律,是內在制度的范疇。內在制度中的社會習慣、習俗、內在規則,以看不見的約束促使人們遵守這些行為規范,以求得社會群體的廣泛認同。”[8]中國傳統文化非常重視道德的作用,但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這些反而被相當多的學者和教育工作者視為法治建設和法治教育的不利因素和阻滯因素,對西方法治模式卻從理念到規則頂禮膜拜。實際上,對我們本土資源缺乏自信,缺乏挖掘,缺乏研究,就更談不上在大學生的法律信仰教育中對之加以應用。我們一些思想政治理論老師不懂得培養大學生法律情感的重要性,不懂得法律與人們日常生活形成的內在規則的聯系,在有限的課堂時間里總想教授給學生更完整更系統的法律規則,并期望這些規則能夠得到遵守,卻不知外在規則越是強硬,內心的抵觸也越強烈。規則無非是一些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應該做的一套行為模式,它的本性是從外在約束人們的行為,是與自我相對的,如果單憑強制力規范人們的行為,人們對它就沒有好感,就更談不上對它的內在信仰了。要培養大學生法律信仰,就要從培養他們對法律的好感開始。要結合實際地增進他們對法律的情感,就要對他們已經具有的習俗、習慣、道德和其他規則進行分析,哪些與我們的法律是一致的,哪些是與法律相沖突的,讓他們自己同外在的法律規則進行比較、斗爭、選擇。不要期望給大學生簡單植入一套規則,也不要期望這些規則對他們有什么影響和作用。從內到外要比從外到內的教育路徑更容易被大學生所接受。我們過去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進路就是典型的從外到內,從外面灌輸,忽略大學生的實際感受,導致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實效性普遍缺乏,你講你的,他做他的,內心抵觸,好的不好的都拒絕,到最后大學生的行為表現出非常明顯的機會主義傾向。因此,法律信仰的教育要轉變觀念,堅持從內到外,內外結合,注重培養大學生對法律的情感認同。
其次,法律信仰教育理念要實現從重義務到重權利的轉化,路徑上要從培養大學生法律生活方式入手。法律,作為人們信仰的對象,應當包含值得追求的積極的正面的價值,法理學中涉及到諸如正義、自由、平等、秩序、效率等都是這些價值的表現,但是更為根本更為廣泛的概念是權利。古代的法制以秩序和效率為價值目標,以義務為本位,現代法治精神以權利為核心,洛克曾說,“法律按其真正含義而言與其說是限制還不如說是指導一個自由而又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當權益。”[9]我國傳統文化缺乏民主法治精神,封建專制統治壓抑人性,貶抑權利,法律被當作“馭民”之器,只要老百姓遵守義務,做順民,不以下犯上,就能最大限度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一旦違反義務抗拒義務,就是違法,就會招致非常苛厲的處罰。這是我國傳統文化中老百姓厭訟、怕官心理的重要根源。法律從根本上是與自己的權利、利益無關的一種異己的力量,法律與自己有著強烈的疏離感、距離感。這種法律工具主義思想影響非常深遠,在我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相當長時期里,我們對法律的理解就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階級統治的工具,是鎮反專政的工具。對法律泛政治化的理論和實踐,使法律與權利發生分裂,使權利和義務發生分裂。法律只是作為一種工具對人們的行為發生作用,對普通公民來說,法律只是一種責任或者義務,與自己的權利和利益關聯不大,不是一種生活方式、社會態度。加上改革開放以后,一些基本的社會領域產生了大量不遵守規則的現象,甚至可以說底線屢屢遭到突破,人與人之間產生了嚴重的信任危機,人們更加不愿相信法律,而因循社會漸漸形成的潛規則,遇事“找路子”“托關系”,倚仗權力解決問題,甚至期望獲得不當或不法利益。權錢交易、衍生腐敗,有權有勢的人不相信法律,不愿相信法律,甚至把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間,作為自己撈取好處的工具;弱勢的人群沒有遇到事情的時候疏遠法律,害怕法律,盡量避開法律,更談不上信仰法律。遇到事情的時候效仿別人找關系、找門路,盡管有時候成本很高,也只有咬碎牙往肚子里咽。法律工具主義思想的泛濫衍生出兩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有權有勢的人弄權弄法,崇尚權力、輕侮法律;另一方面普通老百姓規避法律,逃離法律。法律教育的重要責任就是要培養守法的良民,法律信仰教育就是要培養良民信守法律的素養,如果施教者把法律理解為一種工具,一種單純的義務,在教育過程中只是注重教授一些冷冰冰的規則,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大學生們就不能從法律教育中體會到生活世界的意義和價值,他們的生活世界就沒有法律,甚至會形成法律無用論,轉而把目光投射到更為現實的東西,如金錢、權力、地位等等。因此,法律信仰教育理念要從義務層面轉變到權利層面,權利意識是建立法律信仰的基礎和動因。權利的意識與法律的精神是一致的,與良法是一致的,與守法精神是一致的,與現代性生活方式是一致的。要使大學生充分體味和踐行尊嚴、權利的生活意義,一方面要意識到自己的尊嚴和權利,感悟到法律對于權利的保護和救濟,具有沖破一切阻礙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由于權利的平等性,要實現自己的權利,就要承認別人的權利,要得到別人的尊重,就要尊重別人。從權利的層面引申出義務、責任,使之成為他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要過有權利、有自由、有尊嚴的生活,就不能侵犯和阻擋別人過這樣生活的權利和自由。如此,大學生對法律的親近感就會增強,接受度就會提高。
第三,要以培養大學生法律意識為切入口,培育其法律信仰。切忌觀念保守、方法老套,隔靴搔癢,枯燥乏味,應該觸及學生的精神世界,打動學生,觸及學生的信仰層面,激勵學生的奮斗激情和欲望。大學生體會法律的精神,法律意識在大學生的心里才能不斷地疊加、增強,才能漸次使其做到學法、守法、尚法、信法,才能不被一些社會亂象所迷惑和影響。沒有信仰,就會隨波逐流,甚至不相信真情、不相信真相、不相信真理,關于法律的一些支離破碎的知識不足以幫助他們在行為中作出正確的選擇。馬加爵事件、藥家鑫事件等發生在大學生中的嚴重犯罪行為,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法律知識的缺乏,難道他們不知道殺人是犯罪嗎?不能建立起法律信仰,人的良心、理性和正義感就不能被喚醒,對好的事物就缺乏渴望和追求的激情,對壞的事物就缺乏抵御和抗拒的能力,甚至為了自己的私欲鋌而走險、以身試法。反之,有了法律信仰,就不會因為法律的缺陷和漏洞而投機取巧謀求不當利益,甚至為了法律的尊嚴和實現社會正義,甘愿犧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這種守法、護法的精神是法律信仰的外在展現。
結語
法律信仰是法治國家的精神基礎。大學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也是推進依法治國進程的重要力量,科學地引導和培養當代大學生的法律信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們認為,思想政治理論教育依然是培養大學生法律信仰的主渠道,是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重要職責。但是教育的理念和方法一定要與時俱進,要有創新,方能適應新時期大學生法律信仰教育的需要,才能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效性,依法治國的“中國夢”才能實現。
參考文獻:
[1][美]哈羅德·伯爾曼. 法律與宗教[M]. 梁治平,譯. 北京:三聯書店,1991∶76、69、28.
[2]張文顯. 法理學[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
[3][美]卡爾·弗里德里希.超驗正義——憲政的宗教之維[M]. 周勇,王麗芝,譯. 北京:三聯書店,1997∶9.
[4][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 吳壽彭,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276、275.
[5]謝暉.法律信仰的理念與基礎[M]. 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18.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1-122.
[7]盧梭.社會契約論[M]. 何兆武,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12.
[8]陳新漢. 警惕核心價值體系“邊緣化危機”[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53-54.
[9][英]洛克. 政府論(下篇)[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35-36.
【責任編輯:張亞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