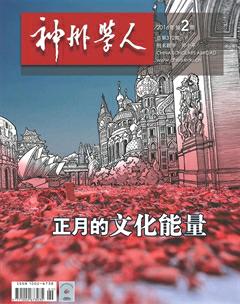“荷”你在一起
吳錦華
春節是中華民族最隆重的傳統節日,也是中國留學生最重視的節日。留學生借各自之特長為荷蘭添加了不少前所未有的“年味兒”。下面這4個春節小故事,講述了留學生如何借助英文、廚藝、民樂、書法、太極等“十八般武藝”傳播中國文化,尤其是春節傳統文化。故事里有順其自然的文化交流,也有不期而遇的文化沖突;有傳道授業解惑的師生關系,也有萍水相逢的高山流水。在荷蘭的星空下,更多的荷蘭人因為中國留學生而知道并了解年夜飯的意義,欣賞中國傳統民樂的魅力,見識中國書法寫就的春聯之飄逸,以及太極中剛柔并濟的博大涵韻。在荷的留學生們用實際行動詮釋著新春佳節的核心意義:和(荷)你在一起,因尊重而溫暖彼此,因交流而欣賞你我。英文·廚藝近些年荷蘭媒體對中國春節的報道角度有著明顯的變化,眼光從在中國的春節慶典轉向荷蘭的春節歡慶活動,從熱鬧的群體慶祝轉向溫馨的家庭聚會,從街道轉向餐桌。《萊頓日報》(Leidsch Dagblad)便是其中一例。該報2012年報道中國的春運,以及環衛工人的工作量因爆竹的大量燃放而倍增;2013年報道席琳·迪翁在央視春晚唱中文歌曲;2014年則開始關注荷蘭本地的春節慶祝活動。報道以圖為主,拍下財神酒樓請來的洪英武術學校的舞獅表演。財神酒樓臨近萊頓有名的五月花廣場,又在萊頓主街上。從照片上看,參與舞獅的是幾位人高馬大的荷蘭小伙,不少荷蘭人舉著手機在拍照。2015年,記者Annebelle de Bruijn特意學了一些中文,在荷蘭最大的中文門戶網站荷樂網發布帖子,尋找愿意接受英文采訪的中國留學生。不久,她便受邀在大年三十那天的下午(與中國同步過年)走進留學生陳春紅的家里,深入體驗海外學子如何慶祝佳節。春紅的先生廚藝了得,利索地端出了10多道春節傳統菜肴。春紅用流利的英文一一給Annebelle介紹:比如餃子,與“交子”諧音,象征新年與舊年相交的時刻;魚,與“余”諧音,吉慶有余,等等。對尚未系統學過中文的Annebelle來說,這特別新奇且有意思。之后,Annebelle在文章中描述萊頓博士樓(萊頓大學中國留學生的最大聚集地)門窗貼的大紅的“福”字,講述中國傳統菜肴的象征意義。文章開篇寫道,“對大部分荷蘭人來說,他們對中國春節的印象多是舞獅、煙花和五彩斑斕的服裝。但是,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春節意味著家庭的大聚會,家人和朋友的相聚,一起品嘗許多許多美味佳肴。”民樂紅薯樂團(SweetPotato)是由瓦赫寧根大學暨研究中心(Wageningen Universiteit en Research Centrum)和阿納姆阿爾特茲音樂學院(Arnhem ArtEZ Conservatorium)的留學生攜手組成的,致力于將中國傳統民樂帶給荷蘭民眾。王舒航為主唱,林慧之吹笛子,葉揚帆吹笛子和演奏葫蘆絲,楊帆和鄧彥澤彈古箏,閔錢希曦演奏琵琶,劉雨晴拉二胡,李歆表演鋼琴。紅薯樂團讓荷蘭人近距離地接觸了中國傳統民樂。2014年春節前夕,紅薯樂團在瓦赫寧根市中心舉辦音樂會,吸引了近80名荷蘭觀眾前來欣賞中國傳統民樂。2015年春節前,紅薯樂團攜手荷蘭民族樂團一起奉獻了一場新年音樂會,并在瓦赫寧根大學舉辦午餐音樂會,受到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們的熱烈歡迎。每次的新春音樂會,紅薯樂團都會事先為觀眾精心設計一本小冊子,用英文或荷蘭文介紹樂團成員的生平、樂器、曲目及歌詞的內容。表演結束后,留有充裕的時間給想進一步了解民樂的觀眾提問交流,并近距離接觸了解中國的樂器。問起荷蘭觀眾對民樂的接受程度時,團長王舒航回答說:“是觀眾的熱情支持讓我們自然地走到了現在。初次欣賞演出的荷蘭觀眾往往驚訝、贊嘆我們的音樂,有些人只是覺得好聽,但聽不太懂,因為和西方音樂完全不一樣;有些人卻可以很直觀地理解中國音樂的線條和畫面感;也有的幾次三番來聽我們的音樂會,請我們參加他們的活動,甚至邀請我們去家里做客。中國觀眾大多數在我們的音樂中找到了故鄉的溫暖,為此不少觀眾開車幾個小時從荷蘭各地趕來聽我們的音樂會。現場音樂和錄音、錄像是很不同的,我們正是希望用現場感的音樂帶動人與人、文化與文化的交流。音樂無國界的魅力讓我們交到許多好友,收獲很多快樂。”書法2012年春節期間,夏小雙和於迎春買來紅紙,潑墨寫春聯和福字,在學生公寓房門上粘貼,還作為禮物送給中國留學生和荷蘭朋友。萊頓大學漢學院的大門,也第一次貼上了學生親筆書寫的春聯,至今貼了3年有余,一直留在那里。曾在萊頓大學就讀的夏小雙在課余時間兼職當書法老師,他的學生中有土生土長的荷蘭人,也有不少到荷蘭留學的學生。這些學生對中國文化尤其是書法很感興趣,定期來研習書法這一奧妙的藝術。小雙用英文授課,從基本的執筆開始,筆畫之橫豎撇捺,各種筆畫的形態,如何運筆,等等。耐心、細致、具體、易懂,是學生給他的評價。盡管因研習時間短而出現行筆不流暢、寫不直、間架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學生們的研習熱情和興趣依然很高。小雙在荷蘭有一位很好的書法朋友——荷蘭老先生魏雅瑟(Arthur Witteveen)。魏老先生原是海牙國際法院第一秘書,退休后便到萊頓大學漢學院攻讀碩士學位。兩人的相識從簡單的中文對話開始。小雙丟了相機套,郁悶地坐在漢學院一樓的衣物柜旁。正巧雅瑟過來取東西,小雙怕妨礙他,便讓開了。雅瑟用中文說沒關系,于是乎兩人開始說起話來。當聊到彼此的共同愛好——書法時,一段長久的中荷友誼就開始了。中午時分,漢學院大樓的庭院那兒,便會看到小雙和雅瑟,一人吃著米飯和炒菜,一人吃著三明治和水果,聊著書法。雅瑟喜歡黃庭堅的行書,小雙愛黃庭堅的草書,二人相談甚歡。小雙對雅瑟的書法評價是:“他的漢字會得也不很多,可是中國書法卻寫得很好,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這么多年來一直堅持寫書法,對書法極為熱愛。跟中國人比,他的書法功力都算是很好的,在外國人當中就更是出色了。”太極上文剛提到的於迎春,到萊頓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前是一位高校老師。他待人溫文爾雅,卻沒想到有一天自己會成為荷蘭朋友口中的那個“嚴肅的”“好像在生氣的”中國人。2011年10月12日的《萊頓校報》(Mare)頭版發了1張迎春在陰天身著黑衣打太極的照片,配發在以《為微波爐而戰》為標題的長文中。標題雖有嘩眾取寵之嫌,卻也使人管中窺豹,猜測出文中將展開的“中荷文化之戰”。荷蘭人午餐多為冷餐,一個簡單的三明治加一杯酸奶(比如讓不少中國學生以為是變質酸奶的Karnemelk)就是一頓午飯。在工作間歇,荷蘭人常常直接從水龍頭接出一杯冷水就喝。這對習慣了熱飯和熱水的中國學生來說不啻于一個考驗。若在學院餐廳買冷餐,基本消費在5歐元左右;若自己買菜做飯,一頓飯成本大概在2歐元左右,然而很難在學校里找到微波爐。迎春的微波爐之戰,初戰受挫。當他打電話跟學生中心的工作人員溝通時,也許措辭不太客氣——當胃要去“加熱”冷菜時,身體消耗了太多的能量,冷菜和冷飲對健康有害。學生中心的工作人員并不認同他的養生觀念。迎春只能安慰自己,在讀碩士前并沒有很多時間享受做菜的快樂,留學后只能機緣巧合地在裊裊輕煙中撫慰自己的中國胃。在接受校報記者采訪時,他和室友小雙很實誠地說了自己的想法:當荷蘭大學忙著將教育出口產業做大時,當他們瞄準國際留學生尤其是中國留學生這一龐大消費群體時,或許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來自歐盟國家的學生在荷蘭攻讀碩士學位,學費為每年1700多歐元,而非歐盟國家的國際學生學費則是每年14000歐元左右,將近10倍的差距。沒有微波爐只是一件小事。當大學的便利措施都只有荷蘭文說明,甚至一些重要的活動(比如著名漢學家高羅佩生平展)也只有配荷蘭文介紹時,更多的缺憾和失落便產生了。迎春很敢說,記者也很愿意記錄。文章的最后,迎春說,荷蘭人很喜歡說話,但在實際行動中缺少了那么一點對別人的關心和考慮。中國人相對安靜些,但會體貼人。荷蘭人不像中國人那么拼,很少考慮未來和夢想。荷蘭人愛喝酒,而中國人(比如迎春自己),喜歡太極和茶。“中荷文化之戰”還在上演著,但這期校報出版后,學生中心和漢學院的辦公樓多了一臺微波爐。每天中午來熱飯的,不只是中國學生,還有其他國家的國際學生。各學院的自動販賣機那兒,屏幕上多了一個選項,叫做“熱水”,不收錢。不僅如此,迎春也多了幾位來學太極的徒弟,荷蘭小伙Fedde De Vries便是其中一位。迎春和博士生郝清剛,在春節期間受邀到海牙表演太極,一著黑,一著白,一招一式讓在場的人印象深刻。迎春的太極弟子,也小露了身手。Fedde后來到美國求學,轉而成為了中國文化在美國的傳播者。(作者系荷蘭萊頓大學區域研究所在讀博士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