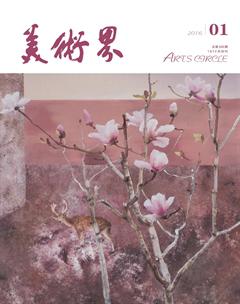試論古典中國畫現代性轉換的開端
潘少梅 杜振東
【摘要】本文研究了20世紀初多位中國畫家的畫作及思想認識,闡述了中國畫融入現代性的改革歷史。
【關鍵詞】古典中國畫;現代性;中西結合;素描;以線造型
古典中國畫帶有根本性的變化發生在20世紀初,這是它古典時期的結束與現代時期的開端。20世紀初的中國畫“改良之爭”,是不同風格流派構建自身藝術體系的草創階段。這場世紀之初的中國畫論爭中最大的焦點:一是革新的一方思考傳統中國畫自身如何進入現代,即如何尋找與新時代結合的途徑:二是守護的一方如何看待傳統中國畫的價值,中國畫的現代性使命是革新與守護的雙方共同完成的。
參照以往相關研究分析,20世紀的中國畫“改良之爭”,我們可以看到各種不同標準的流派劃分,但大體都是按照守護與顛覆的思路劃分,如張少俠、李小山在《中國現代繪畫史》中分為“開拓派”與“延續派”,與這種分類傾向相對的是郎紹君對于百年中國畫的三種類型劃分:“傳統型”“泛傳統型”和“非傳統型”,其中“泛傳統型”是指古典中國畫的變異形態,其代表人物主張中西融合的徐悲鴻以及“二高一陳”:非傳統型是指介于中國畫與非中國畫之間的邊緣形態,如林風眠的彩墨風景以及后來沿著這條路繼續向前探索的趙無極、朱德群等人。與前兩種分類角度皆不相同的是薛永年的分類方法,他把20世紀初中國畫壇分成“三種類型”“兩派別”:“三種類型”分別為“引西潤中”的“水墨寫實型”;“融合中西”的“彩墨抒情型”;“借古開今”的“水墨寫意型”。第一種類型以徐悲鴻、高劍父等為代表;第二種類型以林風眠為代表;第三種類型以陳師曾、黃賓虹為代表。第一、第二種類型又稱之為“革新派”或“融合派”。陣營的劃分有利于厘清論爭中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但一切劃分都只能是某種趨向上的模糊劃分,試圖做到既客觀又嚴整的劃分都是不現實的,在中國畫的革新問題上,不存在絕對的顛覆派,也不存在絕對的守護派。為了敘述的需要,參照以上學者的分類思路,本文根據“改良之爭”中不同的藝術策略,分為革新與守護的雙方,革新中又分為在“傳統與現實之間的探詢”以及在“形式與情感之間的調和”兩種不同的藝術傾向。守護的一方由于陳師曾等人發起的對文人畫價值的再思考而使搖搖欲墜的傳統價值沒有被完全解構。革新的一方采用的是“中西融合”的策略,“中西融合論”由于康有為、陳獨秀、梁啟超、蔡元培等社會改革者強調而得到了眾多畫家的思考與實踐。采用寫實法在“傳統與現實之間探詢”的代表人物徐悲鴻無疑是對中國現代美術的發展進程影響最大的,徐悲鴻的寫實人物畫以及其“兼工帶寫”或稱為“半工半寫”的花鳥畫語言在造型上不走極端,在意筆的不確定性和工筆拘于形似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由于兼顧到物態的寫實性與文人意趣以及欣賞者普遍接受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改良帶來的文化壓力。采用西方現代藝術中的“情緒表現”創作理念的林風眠則刷新了水墨畫的視覺樣式。由于每個論爭者在性格、經歷與審美旨趣上皆不相同,所以不管是守護傳統價值的一方還是追求現代性的一方,其內部都有不同程度的分歧,在對現代性的追求中也包含著或多或少的傳統情結,而本文之所以把守護傳統的一方也置于“中國畫的現代性轉換”一章加以論述,是因為守護傳統價值的一方并不排除一定的變革意識。
康有為主張“以院體為畫正法”“合中西而為畫學新紀元”。梁啟超在為北京美術學校作的“美術與科學”講演中極力推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繪畫,認為繪畫是對自然的復現:“因為美術家能否成功,全在‘觀察自然,怎樣才能看得出自然之美,最要緊的是觀察‘自然之真。能觀察自然之真,不惟美術出來,連科學也出來了。所以美術可以算得科學的金鑰匙。”梁啟超明確指出,應該以純客觀的態度描寫出事物的特性,觀察取代傳統的心悟,強調以透視學、解剖學和色彩學為科學手段的寫實精神。
康有為的“今歐美之畫與六朝唐宋之法同”中尊崇唐宋思想也成了科學寫實派中的理論起點,這種融合傾向以徐悲鴻和高劍父為代表的嶺南派為代表,但他們從唐宋的切入點是不同的,前者主張“引西潤中”式的改良,將西歐學院派寫實主義與中國傳統線描相結合,側重西方寫實性語言與傳統寫意語言的結合。我們以徐悲鴻中國畫改良之后的作品特點來分析他的中國畫語言變革:首先,徐悲鴻作畫用的還是中國畫的材料工具;其次,徐悲鴻始終保持了文人畫詩、書、畫、印一體的傳統風格,堅持在畫中題跋,在徐悲鴻的中國畫作品中都可見題跋,保持了詩、書、畫、印一體的傳統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保持了文入畫的基本特征;最后,徐悲鴻堅持中國畫的用線,在融入一些西方寫實因素的同時始終堅持使用傳統的“以線造型”描繪對象。對于徐悲鴻中國畫的成就,更多的觀點是他注重造型而不是以筆墨為標準的,但我們不能因此忽略了徐悲鴻中國畫的筆墨韻味,若單純以其寫實能力來評價徐悲鴻,無疑是抹殺了徐悲鴻對傳統中國畫繼承的自覺性,徐悲鴻的人物畫中多數仍用勾染、白描等傳統方法,并把西方素描中的光影、比例、透視、解剖等因素融入其中,如《九方皋》《愚公移山》《李印泉像》等都體現了他的這種嘗試。西方寫實觀念和素描手法的引進引發了中國畫藝術語言上的探索變革,使中國畫和現實之間的關系發生轉變。素描提供了一種方法論,提高了中國畫的造型能力,改變了傳統中國畫用色的程式化和裝飾性,增強了中國畫的表現力。雖然寫實觀在徐悲鴻之前已經出現,但只有到了徐悲鴻的大力倡導以及實踐之后,才使傳統人物畫在表現題材、表現方式、藝術觀念上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觀。
主張融合的嶺南畫派采用的是近代寫實畫風與日本藝術趣味相結合的藝術策略。高奇峰和陳樹人等以“怒吼的醒獅”為題材所作的中國畫,結合了形象的象征寓意與政治宣傳功能,將中國畫的現代化與大眾化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他們看重的是藝術在革命宣傳中的重要作用。高劍父的新國畫改革運用的武器是日本的藝術趣味加西方的寫實技法,但同時保留一些傳統中國畫的情趣,而支持其融合論觀點的人也大多從西方的科學原理中為其找到合理性與合法性。楊樸之在《繪學雜志》上發表的《繪事外評》一文中提出:“生物學家,以異種相配,則所生優于原生。繪事亦何不然。今若合中西畫法,而貫通之,則西畫可具中畫之奧秘,必愈得其精神。”實際上,高劍父等人的這種結合潛藏著無法調和的矛盾:一方面,高劍父等人認為“國畫獨到的妙處,確值得奉為圭臬的”:另一方面,他以飛機、坦克等象征革命的物象為題材,如高劍父的《東戰場的烈焰》,把傳統山水畫的高山流水變成了一片滿目瘡痍的廢墟,確實離傳統中國畫的意境追求相去甚遠,是一種“界于中西畫之間的‘非驢非馬式的別格”,因此也難以逃脫自我夭折的命運。對于嶺南畫派的“中日融合”策略,其策略意識比其策略本身更值得研究,它的意義更多的是一種參照與警醒。嶺南派對現實、對民生的關注,將中國畫的現代化與大眾化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并使中國畫壇上分化為“為藝術而藝術”和“為社會而藝術”的兩種創作路向,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畫的大眾化進程。高劍父所一直堅持的這種“與國家民族不發生關系的,不啻與國家社會民族絕緣”的藝術是無法適應國家民族需要的觀點,也正是20世紀傳統派畫家們主動追求的目標。最終也成為20世紀末中國畫發展路徑的共識性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