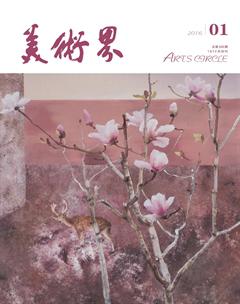淺談“漁父”精神在吳鎮繪畫中的應用
張咪
【摘要】中國美術史上有文獻記載漁父形象的繪畫出現在魏晉南北朝之際,在此之后,傳世的畫作中便留有漁父形象,至元代時,漁父形象在山水畫中最為盛行。吳鎮將漁父這一形象賦予了更多的時代意義和思想內涵,聯系時代背景和作者生平,通過對畫面內容進行對比和分析,并采用詩畫相互參證的方法,研究吳鎮筆下的漁父精神以及這一形象在他創作中的應用。
【關鍵詞】吳鎮;漁父;墨竹;山水畫;道禪哲學
一、何為“漁父”精神
漁父,是中國古代哲學和藝術中的一個古老話題。楚辭和《莊子》中都有《漁夫》篇。楚辭《漁夫》中屈原潔身自好,所謂“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不愿與世俗同流合污;而漁父則認為,君子不帶凝滯之物,應該與世推移,任運而行。《莊子》雜篇中的《漁父》,通過孔子與漁夫的對話,諷刺儒家欲以仁義來教化天下的積極用世觀,而漁父則是莊學的化身,提倡順化一切。這兩段對話中的漁夫形象,都突出任運自然的思想。
漁父這一形象頻繁地出現在傳統的中國畫和古老的中國哲學當中,他所代表的絕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漁翁這么簡單,山水畫中的漁父形象,往往暗示著一種隱居的世外高人形象,而這種隱士的形象又遠遠有別于隱居山林中的隱士,“漁父”相較居士而言,面臨更多自然界的挑戰,不消極避世而是積極面世、深諳其中的勇士精神。張志和的不來不去、樂在風波的精神,具有明顯的禪者風范,與隱者態度明顯有別,一為艱危中的性靈超越,一為逃遁中的心性自適。
二、吳鎮的經歷及漁父情節的內在關聯
吳鎮作為“元四家”之一,其繪畫和作品對于后世的影響不言而喻,吳鎮是南宋末年將相之后,身份顯赫,卻遭遇改朝換代,元代朝廷對漢文人的打壓,“九儒十丐”的說法足以表明當時的讀書人受到極其巨大打擊,懷才不遇的吳鎮心中的無限苦悶可想而知。
吳鎮將自己化身成漁夫的形象,游離在自己心中唯美的山水之間,縱情山水,忘記坎坷不安的人生經歷,依然積極面世。再大的禁錮也不能囚禁一個人的思想,文人畫總是能在最壓抑的社會氛圍中,爆發出持久而又驚人的力量。強大的精神支柱才是生命最大的支撐,而漁父的生活常常伴著兇險,沒有山林中的寧靜,漁父生活在“江湖”之中,“江湖”在中國是險惡的代名詞,江湖中濁浪排空,充滿著格殺和掠奪、充滿著功利和占有。《洞庭漁隱圖》中的題詩:“洞庭湖上晚風生,風攬湖心一葉橫。蘭棹穩,草衣輕,只釣鱸魚不釣名。”作者生活在險惡的江湖,卻不沽名釣譽,生活在風浪險惡中,卻不求名利雙收,只求能夠“漁的魚心滿意足,樵得樵眼笑眉舒,一個罷了釣竿,一個收了斤斧,林泉下偶然相遇,是兩個不識字的漁樵士大夫,他兩個笑笑加加的談今論古。”
三、“漁父”精神在吳鎮畫面中的再現
在宋元文化大背景的影響之下,文人畫的發展已成為大勢所趨,“畫者,文之極也”體現出文人畫的本源是人抒發自身情感的一種高雅的渠道,而非嘩眾取寵地討好他人服務別人。
這樣的思想至今仍是我們解讀吳鎮的角度,吳鎮的漁父藝術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漁隱”藝術,但深入地剖析這哲人思想之后,得知“隱”只是表面,于無藏處藏才是他的追求。這其中隱含著道禪哲學的思想影響痕跡。當人的精神受到壓迫和痛苦,而現實中卻無法解答這一切的時候,人開始去尋找另外一種獲得幸福和快樂的方式,表達自己,釋放自己,這與中國古代哲學觀點中的道家學說中道法自然、無為而治契合,以理明情,讓自己的心靈從現實中的痛苦中解脫出來,才能尋找真正的快樂。不茍合,不卑微,不反抗,欣然接受現實,面對挑戰,總是用同一種溫和而積極的態度面世。同當時道家學派的藝術精神為一體,安于現實生活,游于藝,求于藝。“生命充實不可以已”的精神狀態來自他的以虛靜為體之心,此時的生命,乃是“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吳鎮的一生中留下了很多傳世的優秀作品,生平好道禪和易學,繪畫作品中多有體現一種哲思的精神內涵。吳鎮的《漁父圖》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上題有兩首詞:“西風瀟瀟下木葉,江上青山愁萬疊。長年悠優樂竿線,蓑笠幾番風雨歇。漁童鼓枻望西東,放歌蕩漾蘆花風。玉壺聲長曲未終,舉頭明月磨青銅,夜深船尾魚撥刺,云散天空煙水闊。”此外,吳鎮還有大量以漁父為題材的作品,如漁樂、漁隱、漁家之類,雖未直接以漁父類命名,但都可歸為漁父一類作品。吳鎮的《漁父圖》相關作品,沒有漁歌唱晚的祥和,沒有可以依賴的寧靜港灣,也很少有風平浪靜的畫面,總是濁浪排空,總在西方蕭瑟處,多是暮色蒼茫,夜色沉沉時,以一葉之微,橫江海之上,“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之勢躍然紙上。這種在江湖險惡中泰然自若的心態,并非人人可得。
在吳鎮的《秋江漁隱圖》《漁父圖》《洞庭漁隱圖》等作品中,呈現出各種動態下漁者的形象,或仰望蒼穹,或披著蓑衣戴著斗笠,沒有描繪漁者的神態,卻在煙波浩渺的山水中若有所思。究竟是憂傷還是豪情滿懷,漂泊的人總有一種無法安定的情緒,可漁父卻對這種生活樂此不疲。吳鎮早年間的《漁父圖軸》現藏于故宮博物院,采用高遠的構圖,高山遠水中神情泰然自若的漁父,與意境唯美的山水渾然一體,吳鎮在一葉隨風飄萬里的江湖中畫他的世界。其《漁父詞》有云:“風攬長江浪攬風,魚龍混雜一川中。藏深浦,系長松。直待云收月在空。”沒有對風波的回避,只有超然的性靈。“醉倚漁舟獨釣鰲,等閑入海即乘潮,從浪擺,任風飄。”
四、吳鎮漁父精神在墨竹中的應用
吳鎮的畫風對后來明清山水畫乃至后世都有著巨大的影響。同時,吳鎮的草書,筆法古樸道勁,筆墨酣暢淋漓。吳鎮的書法多存在于繪畫題跋中,如《漁父圖》《墨竹圖譜》。
元代隱士書法中,吳鎮在草書上追晉唐的風格,繼承懷素一脈書風,頗有瀟散古樸的氣息,并且作為“元四家”,吳鎮還將繪畫技法以及詩歌融入到草書作品中。吳鎮身上具有儒、道、釋三種深刻的哲學思想,舉世皆醉唯我獨醒清高的氣節,在亡國之際選擇歸隱,不問朝政。晚年崇尚佛教禪宗思想,空靈與超脫的淺淡意識在其繪畫和書法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從繪畫手法上分析,吳鎮的繪畫技法積眾家之長,借鑒多種手法,追求筆墨意境,并形成獨特的風格。吳鎮將此種繪畫的技法和意境融于他的書法之中,其草書淺淡、孤高、單薄和隨性。骨法用筆、變化豐富都體現在他的書法當中;從他的成長環境不難分析,這種難得的文學修養始于其年少博學,作品大多是自題自畫。
元代,可以說是漁父圖最盛行的時代,不管是身在朝廷的官員還是遠離朝政行走江湖的俠客,抑或是職業的畫家對漁父這一形象都情有獨鐘,漁父題材的繪畫一時間成為世人稱道的高尚精神世界的代表,同時也反映出當時的畫家和文人們對社會秩序不公平的失意和控訴,以及對自由的向往和心靈得到解脫的愿望。時至今日,漁父的題材仍然是世人追隨的抒情形象。藝術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藝術反映時代和社會有兩種途徑,一種是肯定的順承,另一種是反思和對抗。“漁父”精神就是人的內心和社會現實的對抗,是文人們企圖用另一種方式去控訴社會的制度,既能明哲保身又能告訴后世的人,他們心中的無限苦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