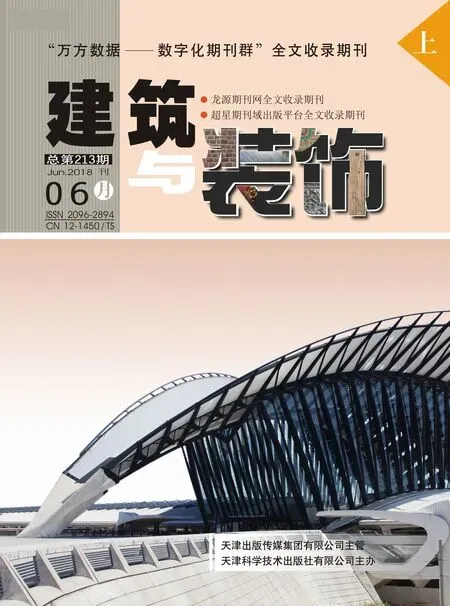淺談建筑外墻保溫滲漏防水處理技術(shù)及施工質(zhì)量管理問題
徐杰
江蘇南通三建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江蘇 南通 226000
前言
在建筑施工過程中外墻保溫能有效起到節(jié)能效果,在材料選擇和施工過程中要保證外墻保溫的施工質(zhì)量,避免在使用過程中出現(xiàn)開裂和滲漏現(xiàn)象。
1 外墻滲漏原因分析
住宅項目外墻有多處泄漏原因,包括設(shè)計錯誤,材料選擇不當,非標準施工技術(shù),不準確的詳細實踐,交付后的不正確裝飾以及自然環(huán)境條件的影響。這些包括以下內(nèi)容:
(1)外墻雨滴管的設(shè)計和維護;(2)外壁預(yù)留孔的密封不良;
(3)鋁合金或塑鋼窗的生產(chǎn)和安裝不規(guī)范;
(4)外墻瓷磚外層清理不完全,砂漿不滿,墻壁與瓷磚之間形成水或水;
(5)外墻開裂;
(6)房屋二期改建時,不加區(qū)別地施工和改建會導致墻體開裂;
(7)房屋頂面的溫度開裂;
(8)地基沉降不均勻造成墻體開裂;
(9)外墻保溫系統(tǒng)滲漏。
2 保溫系統(tǒng)的節(jié)點防水處理
建筑物保溫系統(tǒng)的防水性能對建筑物的保溫節(jié)能效果影響很大,甚至影響建筑物的功能和耐久性。外壁最容易出現(xiàn)裂縫和泄漏的部位主要在接縫處。節(jié)點的設(shè)計與絕緣系統(tǒng)直接相關(guān)。保溫系統(tǒng)節(jié)點的防水設(shè)計是達到防水和防裂目標的有效解決方案。絕緣系統(tǒng)節(jié)點的防水設(shè)計主要由配件完成。所有細節(jié)節(jié)點都使用相應(yīng)的附件進行防水處理。例如,底座支架具有防水,防火,抗機械應(yīng)力,耐侵蝕等功能;有效抵抗機械應(yīng)力;滴水線具有防止系統(tǒng)底部污染和形成連接的功能;門窗的連接可以提高系統(tǒng)的密封性和防水性[1]。
2.1 門窗處理
(1)設(shè)計:門窗通過一系列門窗連接到絕緣層,以起到密封,防裂和防水的作用;內(nèi)門檻比外門檻高2厘米以作為止水裝置;設(shè)置外門檻以提高窗臺的整體防水性能;外檻應(yīng)向外≥20%以避免傾倒水;盡可能減少雨水向外墻的流動,如屋檐和陽臺可用于減少流向墻體的雨量或在高層住宅樓頂層使用挑釁,引發(fā)下方滴水線的設(shè)置,并在每個窗口使用完成的滴水線。
(2)結(jié)構(gòu):在門窗框架和外部保溫系統(tǒng)表層砂漿之間形成的縫隙應(yīng)有5至12毫米寬的縫隙,并填充泡沫聚乙烯圓棒(縫隙寬度的1.5倍)。然后使用預(yù)壓密封膠帶進行密封處理;外墻外保溫砂漿必須用45°角的耐堿玻璃纖維網(wǎng)布在門窗角處進行處理,以防止窗角傾斜。
3 房屋建筑工程防滲漏技術(shù)
3.1 房屋建筑工程出現(xiàn)滲漏水問題的主要形式
(1)屋面和樓面的滲漏水
房屋建筑工程的屋面在日常使用場合中會出現(xiàn)大量積水現(xiàn)象,造成這種問題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工程材料未能達到設(shè)計、質(zhì)量的要求,造成平層表面起砂、起皮、酥松,保護層覆蓋不均、黏結(jié)性低,保護層和防水層之間缺少隔離層,砌鋪不嚴、不平,搭接順序、卷材鋪貼未嚴格依照規(guī)定進行操作,保溫厚度、排水管、泄水孔、蓄水屋面與設(shè)計要求差距較大等都會造成屋面滲漏水。樓面的滲漏水,是由于防水材料不合格、管線損壞、房屋裝修過程中破壞了防水層、房屋有裂縫等原因造成的。
(2)門窗滲漏水
不少房屋建筑工程的門窗采用鋁合金塑料或異型鋼材進行制作,若材料與墻體材料間的性能差距較大,會由于溫度原因造成形變,在兩者接觸的位置出現(xiàn)細縫,造成漏水;另外,若雨篷、窗套、陽臺、挑檐、落水管等構(gòu)件滴水線不標準甚至根本未進行設(shè)置,都會造成水沿外墻流動,相應(yīng)的排水坡度不足、落水口堵塞、防水高度不足等都會出現(xiàn)滲漏水問題。
3.2 房屋建筑工程滲漏水的主要原因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在房屋建筑工程當中,無論哪個系統(tǒng)的滲漏水原因都是由于以下3種情況造成的問題:
(1)防水設(shè)計存在問題。防水設(shè)計存在問題造成房屋建筑工程存在滲漏水的問題幾乎達到三分之一的比例,防水設(shè)計方面的問題主要是由于設(shè)計人員的專業(yè)技術(shù)水平或經(jīng)驗不足造成。
(2)材料方面存在問題。以上分析中出現(xiàn)的選材不當、材料質(zhì)量不符合設(shè)計施工要求或施工過程中早強水泥使用較多、混凝土收縮量較大等,都會造成房屋建筑工程存在滲漏水現(xiàn)象。
(3)施工技術(shù)方面存在問題。在房屋建筑工程施工過程中,由于防水層厚度不合格、涂刷不均勻,或?qū)⒓毷炷痢⑺嗌皾{等材料直接涂抹在防水卷材上,破壞了房屋建筑工程防水層,部分管道接頭不牢固,收縮量增加,埋管不當?shù)榷紩斐煞课萁ㄖこ痰臐B漏水問題。
3.3 房屋建筑工程防滲漏技術(shù)措施
(1)加大房屋建筑工程材料進場驗收工作力度
房屋建筑工程中砌墻抹灰時用的砂子含泥量要確保低于5%,并嚴格控制沙子顆粒大小,所有材料控制在2%的偏差以內(nèi)。在進行外墻涂抹的過程中,要注意將灰砂漿防水劑、抗裂劑一起應(yīng)用,才能有效提升抹灰的抗?jié)B漏能力。砌墻的多孔磚、空心磚、加氣混凝土砌塊材料等,在使用前要對其尺寸、質(zhì)量進行檢查,在現(xiàn)場注意落實好見證取樣的送檢制度,針對需要進行檢查的材料,要根據(jù)規(guī)范標準進行抽樣,并選擇具備相應(yīng)資質(zhì)的監(jiān)督檢驗機構(gòu)進行測試,確保合格后才能用于房屋建筑工程。對于抹灰、砌墻過程中使用的水泥要盡量選擇防滲漏性能好的,拒絕使用粉煤水泥、礦渣水泥、硅酸鹽水泥等收縮性大的水泥類型。要嚴格管控房屋建筑工程材料驗收,有效防止房屋建筑工程滲漏水現(xiàn)象的發(fā)生。
(2)做好墻體砌筑施工,保證抹灰質(zhì)量
房屋建筑工程中,為防止整個墻體的縫隙,應(yīng)控制填充墻縫隙,對框架梁柱與砌體間的夾縫要用砂漿進行鑲嵌,并保證鑲嵌密實。當墻體砌筑到距樓板或梁附近20cm左右時,要停止施工,將剩余部分的墻體在一周后使用立磚或側(cè)磚斜砌擠緊,盡量用磚、板、梁、柱頂緊,縫隙處采用砂漿填實。墻體砌筑過程中,要避免使用干磚,減少磚對砂漿中水分的吸收,避免砂漿不飽滿的可能性。外墻抹灰應(yīng)分層進行,砂漿中適當加入聚丙烯以增加抹灰層抗裂能力,抹灰前對基層進行清理并澆水濕潤,甩槎時要將槎端抹實壓平,定漿后用尺板貼好,墻體再次抹灰過程中,要灑水濕潤,并刷素水泥漿,待其被墻體吸收后再抹灰,為防止砌體、梁柱間產(chǎn)生裂縫,要在抹灰層內(nèi)掛滿鋼絲網(wǎng)進行防裂。
4 結(jié)束語
綜上所述,在當前建筑施工過程中要做好外墻的保溫工作,減少能源的消耗,針對重點的門窗、墻體在施工過程中對質(zhì)量進行有效的控制,提高建筑的施工水平。
[1] 葉琳昌,葉筠.建筑物滲漏水原因與防治措施[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2016:7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