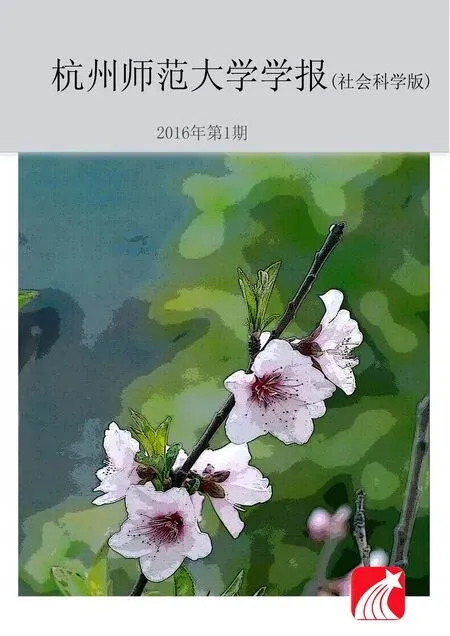清末訴訟法改革爭議之探討——以《訴訟法駁議部居》為考察中心
洪佳期
(華東政法大學 法律學院, 上海 201620)
?
清末訴訟法改革爭議之探討——以《訴訟法駁議部居》為考察中心
洪佳期
(華東政法大學 法律學院, 上海 201620)
摘要:清政府在內憂外患之下諭令變法修律,1906年完成《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朝廷諭令地方封疆大吏進行討論,其后一年多時間內各省督撫將軍紛紛上奏闡明,疑其窒礙。時人趙彬將此意見編纂成《訴訟法駁議部居》,逐條羅列律文,其后附上官員的相關駁議意見。草案條文263條,駁議條文達到85條,理由各異,亦不盡然是“墨守成規”,畢竟法律的移植如同“南橘北枳”,要考慮所移植的本土之質,立法相對容易,但其實施成效并非一紙所能完成。
關鍵詞:晚清;西法東漸;訴訟法草案;《訴訟法駁議部居》
清政府在內憂外患之下諭令變法修律,歷經僅十年時間,致使傳統法律體系發生解體,從體例、術語、內容到理念、精神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清末立法中對程序立法有足夠重視,從審判機構的改革、法律人才的培養、司法人員的考選等方面入手,此外,從法律規范層面完善訴訟法的建設,把民刑訴訟法從刑法典中分離出來,繼而又把民事訴訟法從民刑訴訟法中分離出來。但在修訂訴訟法伊始,質疑、爭論紛至沓來,改革之艱有目共睹。1906年完成《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朝廷諭令地方封疆大吏進行討論,其后一年多時間內各省督撫將軍紛紛上奏闡明,疑其窒礙,一時輿論沸沸,時人趙彬將此意見編纂成冊《訴訟法駁議部居》,在逐條羅列律文之后附上官員的相關意見。本文擬以此為文本,結合當時奏議、資料等,對這一歷史事件盡量還原、分析和探討,以期對西方訴訟觀念進入近代中國的路徑、沖突、應對及結果等有一個較為清晰的了解,從而能對清末法律變革及其成效這一宏大敘事的考察提供某種視角。
一、朝廷奏議訴訟法的制定與嘗試
在清廷頒布修律諭令之前,西方法律觀念的傳播及法律制度的引入是其關鍵,訴訟法觀念及其制度的“西法東漸”概莫能外。①對于西方訴訟法觀念如何在近代中國傳播并生根發芽,可參見拙文《西方訴訟觀念在近代中國(1840—1911年)的傳播路徑初探》,收入《中國邊疆法律治理的歷史經驗》(中國法律史年會2014年學術年會論文集),法律出版社,2014年。隨著危機日深,朝堂上一些較為清醒的官員紛紛上奏要求變法,開始借鑒和改革之路。1898年2月10日伍廷芳上書《奏請變通成法折》,提出變法主張。1901年4、5月間張之洞與劉坤一聯合上奏“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奏響變法序曲。1902年內外交困的清政府頒布變法詔令,自上而下進行法律改革。
首次向朝廷提出改革民刑訴訟的是御史劉彭年在1905年的《禁止刑訊有無窒礙再加詳慎折》。在奏折中,劉彭年認為刑訊為東西各國竊笑,但東西各國裁判所原本民事刑事分設,外國人不用刑訊,是其有裁判訴訟各法,凡是犯人未獲之前,有警察包探偵查案情,犯人到案以后,則有辯護人、陪審員以聽之,自預審至公判,則旁證于眾人,不取供于犯人,而證據確鑿,罪名立定。但當時中國卻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民事刑事不分,聽訟之法未備,若是驟然禁止刑訊,可能會導致衙門案件積壓,有礙于矜恤庶獄之法。因此劉彭年認為問刑之法不能一概而視,應酌核情節以示區分,所有戶婚、田產、錢債等不準刑訊,至于人命、賊盜及情節較重之案則不免除刑訊,要禁止刑訊則應以裁判訴訟法完備為前提。最后,劉彭年得出的結論是外國不用刑訊在于有裁判訴訟各法,而我國禁止刑訊,亦須等到裁判訴訟各法俱備后方可實行。[1](P.5357)
沈家本、伍廷芳等聯名上奏予以駁斥,除了認為刑訊的廢止乃收回領事裁判權這一修律宗旨所決定,刑訊的廢止與法律是否完備無關,而且西方各國無論法律是否完備,無論刑事民事大小案件,均不用刑訊。他們對于劉御史“編纂訴訟法典”的奏議表示贊同,但認為這要等刑律編纂以后才可進行,考慮當時亟需訴訟律,則擬編輯簡明訴訟章程。因劉彭年的奏折,是否先修訂訴訟法被提上議程,而沈家本雖不盡贊同劉彭年之議,但仍首選制訂訴訟法,亦是出于多方面的考量。對傳統法律的缺陷洞若觀火,欲改變舊律,“尤以刑法為切要,而欲變刑法,須先從程序入手”,“查諸律中,以刑事訴訟尤為切要,西人有言曰:‘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訴訟律不備,即良民亦罹其害。’蓋刑律為體,而刑訴為用,二者相為維系,固不容偏廢也。”[2](P.469)這是清末以沈家本為代表的法律人士的法律理性使然。而領事裁判權的存在,收回治外法權成為重要考量因素,至少是朝廷內外一致的緣由所在,清廷需要重新建立一套與“各國律例”完全一致的法律體系和訴訟審判制度,特別是需要消除西方列強侵奪我國法權每每以民刑不分和審判制度不良的借口。而且,中國傳統法律并無獨立的訴訟法典,不涉及實體利益,可以減少修律的阻力。基于以上諸多因素的考慮,晚清法律改革以訴訟法的制訂為切入點。
為了立法上有參考,在修訂法律館組織人員大量翻譯西方國家的訴訟法典和著作的同時,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沈家本、伍廷芳專折奏請派員赴日考察。在這個奏折中,沈家本他們特別提到考察的必要性,尤其是訴訟審判之法,“必親赴其法衙獄舍,細心考察,方能究其底蘊”,將來新律完成,亦能實際操作。之后確定董康、王守恂、麥秩嚴為赴日考察人員。任務之一即是分赴各裁判所,研究鞫審事宜,按日報告,以備采擇。但因王守恂調任巡警部大臣而延遲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四月方成行。沈家本已率領修訂法律館人員起草訴訟法草案,經過近一年的時間,在赴日考察之前,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十二日(1906年4月5日),修訂法律館已編纂完成《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認為《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由伍廷芳主筆或在其主導之下制定,汲取英美訴訟法制的影響而非仿效德日法制的產物,參見何志輝《外來法與近代中國訴訟法制轉型》,中國法制出版社,2013年,第108—109頁。,并闡述編纂訴訟法的理由。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初二日(1906年4月25日)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上奏《進呈訴訟法擬請先行試辦折》,對草案進行解釋與說明,奏請光緒帝先頒試行。光緒帝接到奏折后認為茲事體大,為審慎起見,沒有即刻批準頒行,草案與要求地方軍政大員復議的諭旨一并發至各省將軍、督撫和都統等地方大員,*“上諭:法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等奏,刑事民事訴訟各法擬請先行試辦一折,法律關系重要,該大臣所纂各條,究竟于現在民情風俗能否通行,著該將軍、督撫、都統等,體察情形,悉心研究,其中有無捍格之處,即行縷析條分,據實具奏。欽此。”令地方軍政大員就草案進行討論。此后的一年多時間里,封疆大吏們陸續就本草案上折復奏,闡述自己的觀點與意見。以地方將軍、督撫和都統等大員組成的保守派與沈家本、伍廷芳為代表的改革派之間關于本草案的爭議主要集中在刑訊、逮捕、刑事裁判、判案后查封產物、律師、陪審等六個方面。
對此草案,封疆大吏的陸續上折復奏,闡明觀點,結果“各督撫多疑其窒礙,遂寢”(《清史稿·刑法志一》)。此后直至宣統二年(1911年)清廷才完成《刑事訴訟律草案》和《民事訴訟律草案》的制定,但未及審議頒行。訴訟法的頒行在清末來說皆可謂“出師未捷身先死”。然而盡管如此,圍繞這部《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發生的爭執和討論,在近代中國訴訟法轉型的大背景下,仍具有其研究的價值,即使關注其中細節,仍有問題值得去探究,如以沈家本、伍廷芳為首的修律大臣何以選擇訴訟法為修律之先,而且還在赴日考察大臣未成行之前即已完成草案的編訂;雙方對草案的爭議背后是否存在利益之爭?亦或純粹法典內容之爭?根據資料顯示,表示反對的省份有:熱河都統、廣西巡撫、直隸總督、山西巡撫、杭州將軍、閩浙總督、新疆巡撫、浙江巡撫、湖南巡撫、湖廣總督等。以地域分布來看,甚廣;以發表意見多少來看,以湖廣總督張之洞意見為最多,次之為陜甘總督升允,前者對其中的52條,后者對其中的35條提出自己的看法,浙江巡撫張曾敭則對其中的10條提出不同意見。[3]下文即以草案結構與《訴訟法駁議部居》匯編之意見為考察,對督撫、將軍等對訴訟法條文的不同意見進行分析、對比和探討。
二、訴訟法草案的駁議——以《訴訟法駁議部居》為考察文本
《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草案條文可參見懷效鋒主編《清末法制變革史料》(上卷,憲法行政法訴訟法編),李俊等點校,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436—454頁。的結構如下,
第一章總綱(第一條至第二十條),下分四節:
第一節刑事、民事之別(第一條至第三條)
第二節訴訟時限(第四條至第七條)
第三節公堂(第八條至第十五條)
第四節各類懲罰(第十六條至第二十條)
第二章刑事規則(第二十一條至第八十八條),下分七節:
第一節捕逮(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八條)
第二節拘票、搜查票及傳票(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七條)
第三節關提(第三十八條至第四十三條)
第四節拘留及取保(第四十四條至第四十九條)
第五節審訊(第五十條至第七十二條)
第六節裁判(第七十三條至第七十九條)
第七節執行各刑與開釋(第八十條至第八十八條)
第三章民事規則(第八十九條至第一百九十八條),下分十一節:
第一節傳票(第八十九條至第九十四條)
第三節訟件之值逾五百元者(第一百零一條至第一百零九條)
第四節審訊(第一百一十條至第一百二十條)
第五節拘提圖匿被告(第一百二十一條至第一百二十七條)
第六節判案后查封產物(第一百二十八條至第一百三十七條)
第七節判案后監禁被告(第一百三十八條至第一百四十六條)
第八節查封后在逃被告產物(第一百四十七條至第一百六十一條)
第九節減成償債及破產物(第一百六十二條至第一百八十四條)
(1)化學成分和力學性能 UNS N08367材料是通過氬氧脫碳法(AOD)或真空脫碳爐(VOD)精練技術對雜質元素進行了嚴格的凈化處理,從而提高了材料的耐蝕性能。其化學成分和力學性能如表1、表2所示。
第十節和解(第一百八十五條至第一百九十一條)
第十一節各票及訟費附訟費表(第一百九十二條至第一百九十八條)
第四章刑事民事通用規則(第一百九十九條至第二百五十條),下分四節:
第一節律師(第一百九十九條至第二百零七條)
第二節陪審員(第二百零八條至第二百三十四條)
第三節證人(第二百三十五條至第二百四十三條)
第四節上控(第二百四十四條至第二百五十條)
第五章中外交涉案件(第二百五十一條至第二百六十條),不分節,共十個條文。
第六章附頒行例(第一條至第三條)。
以上可見,《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是將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置于一個法律文本,繼第一章“總綱”之后,設兩章“刑事規則”與“民事規則”,再設“刑事民事通用規則”。最后再附兩章“中外交涉案件”與“附頒行例”。
第一章“總綱”首先明確“刑事民事之分”,定義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規定公堂規則,以及各類懲罰。與傳統法律相比,最大不同莫過于允許原被告和訴訟當事人“站立陳述,不得逼令跪供”(第十四條),而且不允許用“杖責、掌責及他項刑具或語言威嚇”(第十七條)。
第二章“刑事規則”共68條,是按照刑事訴訟階段將其內容分為捕逮、拘票、搜查票及傳票、關提、拘留及取保、審訊、裁判、執行各刑及開釋等7節。第一節“捕逮”,8個條文,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四條以及第二十六條規定逮捕的特殊情況,即逮捕不使用拘票的情況。這幾個條款是仿照西方國家逮捕現行犯之規則。第二十七條規定:“除以上所載各條外,非奉有適當公堂簽發之拘票,概不準徑入房院,或在道路擅行捕拿。”第二節“拘票、搜查票及傳票”主要規定了拘票、搜查票和傳票的適用范圍和適用方式。第三節“關提”的內容主要是關提的條件、程序以及被關提人的程序性權利和權利救濟。第四節“拘留和取保”,規定行使拘留權的主體和拘留期限,不適用拘留的情況以及拘留的處所。以上四節內容,其核心是除緊急情況對現行犯采取措施外,必須按照規定辦理審查手續,申領拘票、搜查票或傳票后才能進行。顯而易見,該草案引入西方國家普遍實行的司法審查原則或令狀主義,即對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搜查或限制人身自由措施必須事先經過司法審查,而后才能實施。第五節“審訊”規定了承審官須遵照的審訊規則。第六節“裁判”規定裁判官在裁判前應細心研究7項事,即“兩造各證人之名譽若何,所供是否可信;兩造所呈之證據;每造前后各供,有無自相牴牾之處;權衡兩造供詞之重輕;權衡兩造情節之虛實;所呈證據是否足定被告之罪;證據已足,是否為法律所準”。第七十四條、七十五條、七十六條內容,不僅確立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是排除合理懷疑,同時還規定罪刑法定原則。第七節“執行各刑及開釋”,詳細規定各種刑罰的執行辦法以及與開釋相關的條款,其中第八十六條做出了“疑罪從無”的原則性規定,“凡證據難憑,或律無正條,或原告所控各節間有疑竇者,應即將被告取保釋放,令其日后自行檢束”。第八十七條“凡本刑期滿,或遇赦,或被告經公堂判為無罪者,日后不得再因本案拘傳審訊”的規定,則可視為“一事不再罰”的原則。顯然,該章“刑事規則”沿襲了英美法系的刑訴原則。
第三章“民事規則”共110條,分11節。第一節“傳票”主要規定傳票的適用范圍和使用方法。第二、三節規定了“訟件之值未逾五百元”和“訟件之值逾五百元”案件所各自適用的審前程序。第四節“審訊”,規定了民事審訊的程序規則,如第一百十一條規定“凡審訊,原告、被告及各證人均不得拘留”。第五節“拘提圖匿被告”,規定拘提被告的條件、法律后果以及拘提不當時被告的救濟方式。第六節“判案后查封產物”規定查封產物的條件、范圍,違例查封或查封不當的救濟手段以及查封產物的拍賣。第七節“判案后監禁被告”,包括監禁的條件、期限、釋放條件等內容,同時規定了對被監禁人的保護條款。第八節“查封在逃被告產物”,分別規定了原告請求查封被告產物之條件、公堂之權限、查封之法律后果。第九節“減成償債及破產物”,規定了減成償債的條件、程序及法律后果,破產的條件、處理程序及法律后果,破產中各種違法行為的處罰。第一百八十四條為兜底條款,規定:“凡破產事宜,如本節有未賅載者,仍依商事破產律辦理。”第十節“和解”,主要內容有和解的條件、處理方式以及法律后果。第十一節“各票及訟費(附訟費表)”,規定各項單票的事宜及訴訟費,規定“訟費表須懸于公堂墻壁或門外,務使眾人易見”,“除表內載明各費外,概不準另索他費,另不準額外浮收,違則從嚴懲處”,以防止公堂亂收訴訟費。
第四章“刑事民事通用規則”共52條,分4節,第一節“律師”,主要規定律師的權利、職業資格、職責以及處罰等。第二節“陪審員”,引入英美法系的小陪審團制度。規定設立陪審制度的意義和陪審員的責任,“凡陪審員,有助公堂秉公行法,于刑事使無屈抑,于民事使審判公直之責任”。還規定陪審的范圍,陪審員的選任、任職資格、權利和義務、回避、陪審評議、決定規則以及陪審員的紀律等。第三節“證人”,規定證人的作證義務和責任、證人的限制條件。對傳統的“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進行修正,第二百四十二條規定:“凡職官、命婦,均可由公堂知會到堂供證,但公堂須另置座位,以禮相待。若系三品以上大員為證人者,即由公堂遣員就詢。”第二百四十三條規定:“凡證人供證,須以目睹或自知之實情,不得以傳聞無稽之詞,妄行陳述。”第四節“上控”,包括上訴的條件及所要履行的手續,上控期間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第二百五十條規定:“高等公堂復審后,平反或更改原判者,原審公堂之承審官,除查有貪賄、曲庇或溺職等弊確據,照例懲治外,余俱不得申飭議處。”借鑒英美法系的有關法官責任規定,摒棄傳統律典的不合理規定。在這四節中主要是對前三節的意見居多。
《訴訟法駁議部居》的編纂結構則是根據上述訴訟法草案的篇章結構,逐一羅列法律條款,附上相關人物對該內容的意見。不僅能一目了然,而且可以比較不同官員對同一條款的各自意見。以下就《訴訟法駁議部居》所記錄的官員對訴訟法條文的意見做一簡表,然后進行相關分析。

官員(時任職位)簡介贊成條款及其理由反對或有疑義條款及其理由瑞興:杭州將軍1904年—1910年擔任杭州將軍,1905年兼署浙江巡撫。第一章“總綱”“明允精當,大致井然”;第四章“刑事民事通用規則”中“證人”和“上控”“平允可行”;第五章“中外交涉案件”“立法簡易,無懈可擊”。第二章刑事規則“宣誓”條,認為“恐啟民之詐”,與中國不通。第四章“刑事民事通用規則”中“律師”、“陪審員”,恐啟杠訟之風及多牽制之弊。對于目前民智未開之時,實行則“殊多捍格”,應先試行于通商公堂。松壽:閩浙總督(?—1911),歷任陜西督糧道、山東按察使、江寧布政使、江西巡撫、江蘇巡撫、工部右侍郎兼正藍旗蒙古都統、熱河都統、兵部尚書、工部尚書、察哈爾都統、閩浙總督等。認為草案全編五章二百六十條整體而言,“條理井然”,“國家收回法權,用意極為周密,自可逐一推行”。但尚有數條“參以閩省風俗,似宜變通緩議者”,相應條款有:第十二條、十七條、二十四條、一百九十九、二百一十、二百四十二條。聯魁:新疆巡撫(1849—?),滿洲鑲紅旗人。歷任兵部候補員外郎、海軍衙門章京、會典館纂修、兵部郎中、甘肅甘涼道等,1905—1910年擔任新疆巡撫。就訴訟法本身而言,“應予遵守”。但“新省處極邊,民情風俗遠殊內地”,應“審慎而后行”。具體條款:第五十條,第四章第一節“律師”認為若以刑幕之人充任,難免訟棍之流藉端漁利,第四章第二節“陪審員”較難選合適之才。升允:陜甘總督(1858-1931),蒙古鑲藍旗人。歷任山西按察使、布政使,陜西布政使、巡撫,江西巡撫,察哈爾都統,陜甘總督等職。第十五、十九、二十四、二十五、三十三、四十六、五十一、五十四、五十九、六十六、六十八、七十六、七十八、七十九、九十三、九十六、一百六、一百八、一百十、一百二十八、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七、一百三十九、一百四十五、一筆四十九、一百六十、一百六十九、一百七十一、一百八十七、一百九十五、一百九十九、二百十二、二百十三、二百十五、二百十九條。張之洞:鄂總督(1837—1909),直隸南皮人。歷任教習、侍讀、侍講、內閣學士、山西巡撫、兩廣總督、湖廣總督、軍機大臣等。第一、二、三、四、十四、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三十三、三十七、四十七、五十、五十一、七十六、七十八、八十六、九十、九十一、九十六、九十八、一百一、一百四、一百三十、一百三十八、一百三十九、一百四十五、一百四十九、一百五十五、一百六十三、一百六十七、一百七十三、一百八十一、一百九十、一百九十一、一百九十五、一百九十八、一百九十九、二百五、二百七、二百八、二百九、二百十三、二百十五、二百十七、二百二十二、二百二十五、二百二十八、二百三十三、二百五十七、二百五十八條、“附頒行例”第二條。張曾敭:浙巡撫(1852—1920),1905年任浙江巡撫,1907年因秋瑾一案,遭輿論譴責,調任江蘇巡撫,又改山西巡撫。后稱病歸籍。第129、130條查封財產,“體恤周全,用意良厚”。第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四十五、五十一、七十九條、第四章第一第二節“緊要地又難實行”、二百四十九條。岑春煊:湘巡撫(1861—1933),廣西西林人。清末重臣,與袁世凱史稱“南岑北袁”。第二十四、二十五、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九、一百三十條(應酌刪,以省枝節,避免造成隱匿財產)、一百三十九、一百八十六、一百八十七、一百九十條。
從《訴訟法駁議部居》所輯的督撫將軍等大臣意見來看,草案共263條,對其中85條提出或應刪除或應暫緩實行或修改的意見,占32%,而其中有5人對第二十四條,3人對第二十五、五十一、七十六、七十九、一百三十、一百九十九等6條,2人對第十七、二十六、五十、七十八、九十六、一百三十九、一百四十五、一百四十九、一百八十七、一百九十、一百九十五、二百十三、二百四十五等13條,共同表示其不贊成意見,當然,理由并不盡相同。無論從其不贊成意見的比例還是內容上看,這些督撫并非一概反對訴訟法草案,其實大多是無意見的,而且對其篇章體例,杭州將軍瑞興評價總綱“明允精當,大致井然”,閩浙總督松壽評價訴訟法草案全編五章二百六十條是“條理井然”,“國家收回法權,用意極為周密,自可逐一推行”,只是“其中尚有數條參以閩省風俗,似宜變通緩議者”。[3](P.1)因篇幅所限,僅就其上述涉及較多的某些條款及督撫所提意見,予以剖析。
以爭議的具體內容來看,主要集中于刑訊(第十六、十七條)、逮捕(第二十四、二十五條)、審訊(第五十、五十一、五十四、五十九、六十六條)、刑事裁判執行(第七十六、七十八、七十九條)、判案后查封產物(第一百二十八、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七條)、律師(第一百九十九、二百五、二百七條)、陪審(第二百十、二百十二、二百十三、二百十七條)等方面。理由各異,有的認為草案與中法本原有乖違,與國情不合,致使“壞名教之防,啟男女平等之風,悖圣賢修齊之教”,引起內亂。有的僅就條文是否切實可行予以討論,大多是結合自己所任職當地情況條分縷析或提出建議。如新疆巡撫聯魁對“總則”提出自己看法,認為“新省地處極邊,民情風俗遠殊內地”,建議對于“命盜案暫行變通辦理”,應“審慎而后行”。當然,即使是同一條款,官員的意見也會大相徑庭,如第一百二十九、一百三十條的“查封產物”,浙江巡撫張曾敭認為該條文“體恤周全,用意良厚”,但在岑春煊、張之洞、升允看來,應予刪除,甚至因“中西習俗不同”,國家法令原以“厚風俗正人心”,“此法萬不可行也”。[3](P.1)
以官員共同提出意見最多的條款來論,當屬第二章第一節“捕逮”的第二十四條:“如有殷實之人指控道路之人犯罪,巡捕不持拘票即將被指之人捕送公堂審訊。”這一條款,除了聯魁和瑞興沒有發表意見外,其余五位官員皆表示其反對意見。閩浙總督松壽認為中國情形與外洋不同,“閩省下游往往有大鄉欺小鄉,強房凌小房之事”,尤其書吏的欺凌鄉民,“此法以出,恐益肆其欺凌,一經指控即行捕送公堂,迨至紕出實情,原得釋放而被控之人已不堪其擾累矣”。[3](P.9)陜甘總督升允認為“甘省紳士最好交結官長,借此武斷鄉曲欺壓平民,其在不肖,州縣奉之如神明,視之如益友而稍有識斷者,尚能節制裁抑,不使大權旁落。今若準殷實之人指控道路之人,不持拘票即捕送審訊,恐劣衿挾一己之私,妄控誣奸蔓訟不休,即至事后剖白其冤,而無辜之被害已不堪間矣”。浙江巡撫張曾敭也以“浙省民情好訟,誣告甚多”,臺衢溫等府民風“尤為強悍”,而且“現時巡警人民其程度尚未能及東西各國”,新法的施行無法成效,反而對民造成傷害。湘巡撫岑春煊和鄂總督張之洞對本條及第二十五條(“如在道路犯違警罪,或情節較輕之罪,且犯罪者似系殷實之人,即不得將該犯捕拿。只須問明姓名、住址、事業,請公堂發票,傳令聽審”)皆提出反對意見,認為外表難以看出殷實之人,容易以偽亂真,而且巡捕程度優劣不可概論,又不似“外國法令周密,警察靈通”,從而致滋流弊,即使富戶亦未必盡屬良善,“為富不仁之徒”也可能“挾誣陷之舉魚肉鄉愚”。這里,已可看出兩個經常會被提起的理由,一是當地習俗或民風之彪悍或地處僻陋之隅,難以適用該法;二是現實中國社會無法有如外國法律之周全或制度完備或法務人員素質之高,反而易為劣幕俗紳所控,滋生流弊。這很大程度上是為事實,但問題在于:法律移植的前提是否必須先改善移植之地質或俟條件皆具?還是移植之后再改善其環境或條件以使適應之?改革之初此論似為必然。
除此第二十四、二十五條外,反對意見相對較為集中的主要有第五十一條的“無論刑事民事案件,原告及兩造證人,須矢誓后方可作證”及誣告處于罰金,第七十六條的“凡裁判均須遵照定律。若律無正條,不論何項行為,不得判為有罪”,第一百三十條的“凡下列各物,不在查封備抵之列”,以及第一百九十九條的“凡律師,俱準在各公堂為人辯案”。這些條款,與傳統中國的法律條文或法律精神是相悖或沖突的。如第五十一條的規定,浙江巡撫張曾敭就認為應分罪之輕重,不能僅以罰金了事,而且“矢誓”乃“法設羅馬宗教之習慣”,中國的“矯誣之徒”豈會忌憚“矢誓”。[3](P.17)對于第七十六條,更是在傳統的“法制有限,情變無窮”思想、“悉心比附、期無枉縱”的制度之下,難以接受如此“律無正條不得為罪”的條文。[3](PP.21-22)而對于律師制度的設置,主要擔心律師的專業素養和品行非一日所養成,卻被訟師所奸謀得呈,原被告雙方延聘律師,易“啟終兇之禍而樹公堂之敵”,兩造貧富易造成“富者雖曲而必勝”之弊。[3](PP.52-53)同樣,第一章第二節第十七條的規定:“凡審訊一切案件,概不準用杖責、掌責及他項刑具或語言威嚇或逼令原告被告及各證人,偏袒供證,致令混淆事實”,與傳統法律的內容精神皆大相徑庭。閩浙總督松壽提出反對:“原以小民無知犯法,當存哀矜折獄之義,上年奏準通行凡笞杖改為罰金,已分飭各屬照辦,然偏小州縣風氣未明,每遇斷罰之案,有情愿身受笞辱不愿呈繳罰金者,狡黠之徒反詆牧令貪賄,信口污蔑,辦理已多棘手。閩省民情強悍,下游一帶械斗頻仍,強盜會匪不時出沒,一經獲案,明知身犯重罪,不肯吐認實供,若非稍加刑責,該犯必任意狡展,決獄永無定期,查前奉矜恤獄囚折內,原由除犯罪應死,證據已確而不肯認者,準其刑訊明文。今再察情形,凡提訊重罪人犯,似未可盡廢刑章者也。”[3](P.6)
以官員個人發表意見來論,以張之洞與升允的意見為甚,升允對其中的35條發表其不同意見,涉及面較廣。而張之洞更是對二百六十余條中“捍格難行”的52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所纂的訴訟法章程二百六十條大多采用西法,“與中法本原似有乖違,與中國情形不合”,不僅“壞名教之防,啟男女平等之風,悖圣賢修齊之教”等,也“難挽法權轉滋獄訟”。張之洞固然認為“編纂法律,有體有用,先體后用”,西方各國是先有刑法、民法,然后有刑事、民事訴訟法,有訴訟之法,尤須確定裁判官的權限分明,而后才能推行訴訟法。但其觀點并不僅僅局限于禮教、法權、實體與程序之爭,他對草案的具體內容進行條分縷析。如對于刑事訴訟法的概念等提出看法,認為應先分析刑事、民事,將現行律例厘然分開;又如陪審員問題,張之洞并沒有一概否定該制度的設置,而是對其中11條,即陪審員的資格、人數、職責、罰則等提出異議,雖說某些意見是因對西方陪審制的不了解所致,但更多是對于陪審制的具體運作與實效提出質疑,如訴訟法章程中的第二百十三條、第二百十五條、第二百二十條、第二百三十條、第二百三十三條等,自有其合理之議*因篇幅和主題所限,對該問題的剖析以及張之洞在近代法律轉型中的作用等有待以后另文探討。。
除《訴訟法駁議部居》所輯的駁議外,還有其他官員發表看法,如袁世凱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十月二十五日上奏《遵旨復陳新纂刑事民事訴訟各法折》[4](PP.386-388),將刑事民事訴訟法內有捍格之處羅列10條,有的“原文罅漏,尚待聲明”,如第八、七十六條;有的則認為有損承審官威信或無必要明言而建議刪除,如第十五、十七條;有的則是概念不明確,如第二十四、二十五條的“殷實之人”的“殷實二字,范圍太廣”;認為“捍格不行,則法為虛設”,民法未頒,第一百三十條內容實無根據。而對于“陪審”一節則建議刪除,原因在于實行陪審制有三弊,建議以檢察制度代之。其他督撫也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見,當時《京華報》報道說:“各督撫之章奏皆系逐條駁詰,無一贊成者。”*“張安帥奏駁訴訟法”,《京華報》第43冊,光緒三十三年二月初二。如在《撫部院曹奏題旨議覆刑民訴訟各法折》中,肯定應學習西方之法,但強調國情不同,不可完全舍舊從新,否則難以“一人之昭昭矯眾人之昏昏”。《桂撫林奏新纂刑事民事訴訟各法廣西尚難遵行折》就其中的13條提出異議,包括第四條、第十七條、第二十五條、第五十一條、第七十六條、第七十八條、第九十一條、第九十六條、第一百三十條、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一百八十一條、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二百十三條。這些地方將軍、督撫和都統等對草案內容發生諸多爭議,致使訴訟法草案的命運堪憂。
三、訴訟法草案的后續命運及余論
正因為以張之洞為代表的封疆大吏們紛紛提出反對意見,使得本草案及時頒布試行已成為不可能之事,清廷遂令法部就該草案再行核議。法部遲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九月才奏呈《奏議刑事民事訴訟律俟法律草案定議再行妥擬折》,提出了對本草案的處理意見。該折全文如下: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二日,臣部議復訴訟法擬請旨展限八個月,以便詳核妥議一折,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正復議間,復據湖北奏陳,并將折單咨送前來。除山東一省至今尚未議復,未便久候外,臣等匯閱各省復議,或以為輿情未洽,或以為人才未備,或以為關鍵多疏,或以為窒礙難行,均系體察各該地方實在情形,確有所見。而升任湖廣總督臣張之洞復奏內稱,本法過沿西制,與中國禮教似有乖違,且未盡合法理,誠恐法權難挽,獄訟轉滋。其中摘駁各條,探原抉弊,最為切中。臣等當即督飭司員更番核議,再四酌商。該法當更始,討論不厭求詳,道貴因時,推行必期盡利。若必觀摩歐美,而中外殊尚,難免削足適履之譏,若仍循襲故常,而風會所趨,徒貽膠柱鼓瑟之誚。既經修律大臣按照中外法律酌擬訴訟辦法,而中國各省情形不同,即不得不體察時宜,斟酌法理,為預備試行地步,以期本末兼貫。謹就原纂各條,按照各省復議,逐加參考。其中或雖經各省指駁,而事理或可變通試行者;或俗尚不同,驟難仿效,應擬緩辦及刪除者;或法理本無不合,而詮次繁復,字句未盡詳明;或本法應有而原纂未備,節目殊多疏漏。即使由臣等愚見所及,遽為修改,勢必拘牽西律,終無當于中國禮教之大防。且法律者,主法也,民刑訴訟者,輔法也。輔法于主法,必附麗而行,然后有所依據。若主法未定指歸,輔法終虞枘鑿。此次法律草案,既經欽奉諭旨交修律大臣及臣部訂議,則訴訟法一事,擬請旨俟草案定議后,仍由修律大臣會同臣部,按照各省復議暨升任湖廣督臣復奏各節,折衷訂議,再行奏明辦理,次第施行。既無凌縱之虞,亦鮮糅雜之弊,庶幾尊法權而垂久遠矣。得旨。如所議行。①清會議政務處檔231號,轉引自徐立志著《沈家本等訂民刑訴訟法草案考》,載楊一凡總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甲編第七卷,《清代法制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652頁。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二日,臣部議復訴訟法擬請旨展限八個月,以便詳核妥議一折,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正復議間,復據湖北奏陳,并將折單咨送前來。除山東一省至今尚未議復,未便久候外,臣等匯閱各省復議,或以為輿情未洽,或以為人才未備,或以為關鍵多疏,或以為窒礙難行,均系體察各該地方實在情形,確有所見。而升任湖廣總督臣張之洞復奏內稱,本法過沿西制,與中國禮教似有乖違,且未盡合法理,誠恐法權難挽,獄訟轉滋。其中摘駁各條,探原抉弊,最為切中。臣等當即督飭司員更番核議,再四酌商。該法當更始,討論不厭求詳,道貴因時,推行必期盡利。若必觀摩歐美,而中外殊尚,難免削足適履之譏,若仍循襲故常,而風會所趨,徒貽膠柱鼓瑟之誚。既經修律大臣按照中外法律酌擬訴訟辦法,而中國各省情形不同,即不得不體察時宜,斟酌法理,為預備試行地步,以期本末兼貫。謹就原纂各條,按照各省復議,逐加參考。其中或雖經各省指駁,而事理或可變通試行者;或俗尚不同,驟難仿效,應擬緩辦及刪除者;或法理本無不合,而詮次繁復,字句未盡詳明;或本法應有而原纂未備,節目殊多疏漏。即使由臣等愚見所及,遽為修改,勢必拘牽西律,終無當于中國禮教之大防。且法律者,主法也,民刑訴訟者,輔法也。輔法于主法,必附麗而行,然后有所依據。若主法未定指歸,輔法終虞枘鑿。此次法律草案,既經欽奉諭旨交修律大臣及臣部訂議,則訴訟法一事,擬請旨俟草案定議后,仍由修律大臣會同臣部,按照各省復議暨升任湖廣督臣復奏各節,折衷訂議,再行奏明辦理,次第施行。既無凌縱之虞,亦鮮糅雜之弊,庶幾尊法權而垂久遠矣。得旨。如所議行。①
作為一部過渡性的立法,《大清訴訟法草案》是修訂法律館開館以來起草的第一部近代意義上法律草案,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訴訟法典,其具體內容引進西方訴訟理念和訴訟制度,開啟了中國訴訟法近現代化之門。但在訴訟法改革肇始發生的爭議、草案的出臺及地方督撫的駁議、草案的“胎亡”皆反映出中國傳統法律在轉型過程中的艱難,從另一側面體現出西方訴訟觀念和制度在近代中國的傳入和移植所面對的困境。不過,呈現的問題也許不止如此,駁議的意見并非盡然是“墨守成規”,畢竟法律的移植如同“南橘北枳”,要考慮所移植的本土之質,立法相對容易,但其實施成效并非一紙所能完成。如前所述,1905年奏準通行凡是笞杖改為罰金,但州縣之民,每遇斷罰之案,仍有愿身受笞辱之刑,而無錢付罰金。《塔景亭案牘》第九卷就記載了相關案件的當事人“堅稱情愿受笞,求免罰金”。[5](P.240)即便如此,立法改革是第一步,實施艱難,仍然前行。天時地利人和之下的“水到渠成”固然完美,但時代的命運和歷史的齒輪自有其道。以近代中國訴訟法發展的全景來看,《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的“曇花一現”,徒有“過渡”之結局,但亦是法律近代轉型的必然歷程,其帶來的爭議在客觀上促進法理的辨明和觀念的更新,繼而推進新訴訟法的修訂與出臺。
參考文獻:
[1]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G].北京:中華書局,1958.
[2]吳宏耀,郭恒.附錄一:沈家本等奏《刑事訴訟律草案》告成裝冊呈覽折[M]//1911年刑事訴訟律(草案)——立法理由、判決例及解釋例.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
[3]趙彬.訴訟法駁議部居[G].北京:北新書局,1908.
[4]懷效鋒.清末法制變革史料:上卷[G].李俊,等點校.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
[5]許文濬.塔景亭案牘[G].俞江點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責任編輯:吳芳)
A Discussion on the Dispute of Litigation Law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Based on Procedural Law in the Department Refutation”
HONG Jia-qi
(Law School,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In the background and era of domestic trouble and foreign invasion, the Qing government decreed law reform. After completing the “Great Qing Draft Criminal and Civil Procedural Law” in 1906, the court ordered governors in local or border provinces to hold a discussion. More than a year thereafter, provincial governors and generals have submitted their reports, which brought about great obstruction to the government. Zhao Bin codified all of their advice intoProceduralLawintheDepartmentRefutationwith statutes listed one by one, followed by relevant refutation comments. There were 263 draft articles and 85 refutation provisions with different justifications, not all of which were fettered by old conventions. In fact, the transplanting of law, as goes the Chinese saying “oranges change with the environment”, should take the local context into consideration. It is easy to carry out legislation; however, its implementation is destined to be more than a paper of words.
Key words:Late Qing Dynasty;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aw to China; procedural law draft;ProceduralLawintheDepartmentRefutation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6.01.003
中圖分類號:D9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2338(2016)01-0016-08
作者簡介:洪佳期(1972-),女,安徽歙縣人,法學博士,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主要從事明清司法、近代法史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一般項目“法律文明史”(11&2D081)的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5-11-17
主題研討清末民初中國的學術和思想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