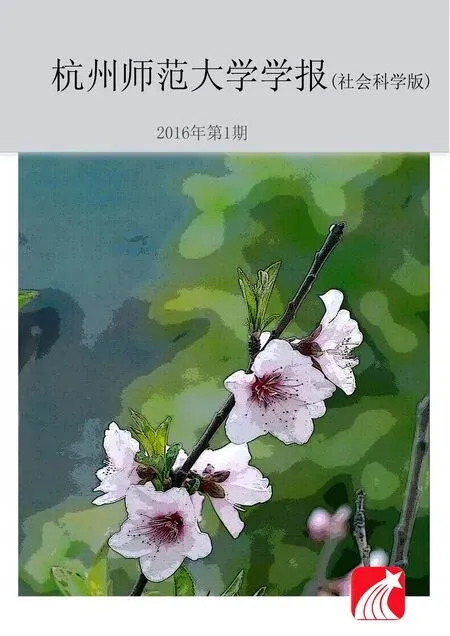宋代湖州城的“界”與“坊”
來亞文,鐘 翀
(上海師范大學 人文與傳播學院, 上海 200234)
?
城市學研究
宋代湖州城的“界”與“坊”
來亞文,鐘翀
(上海師范大學 人文與傳播學院, 上海 200234)
摘要:宋代湖州城中“界”與“坊”的格局、空間實態與歷史變遷研究具有典型意義。《永樂大典》輯本《嘉泰吳興志》卷二《坊巷·州治》全文實為清人錯輯明初《吳興續志》之文,在此資料批判的基礎上,可以確認南宋后期城中的“坊”的實際形態,應為街口樹有牌坊的街巷;同時,在復原獲得宋代湖州羅城平面形態的基礎上,由明、清回溯復原宋代湖州城“界”的分布與區劃,可以確認湖州城的“界”并非“坊”的別稱,實即城中之“里”,是附郭鄉的賦役征發基本單位和“廂”的警巡消防基層區劃。
關鍵詞:宋代;湖州城;界;坊;城市歷史形態學
引言
在中國城市史的研究中,城市的管理一直以來都是學界備受關注的課題,在唐至宋元這一城市變革的時代,其內部的構造變化則更加顯著,涉及到城市內部的管理區劃,即廂、坊等方面的興廢變遷,是我國中古城市史研究中的核心問題之一,對此學界已有相關成果,但在個案積累上尚顯不足,尤其對地方中心府州級城市的深入研究則更為缺乏,且往往局限于片面的文獻解讀,對一些基本問題尚未形成普遍的認識。因此開展地方城市典型個案的中長時段演變研究是極有必要的。
位于太湖南岸的湖州城便是一個可以清晰展現宋代城市管理區劃的典型范本。在史料方面,今存《嘉泰吳興志》二十卷系《永樂大典》輯本(下文簡稱《嘉泰志》),此志成書于南宋嘉泰元年(1201),作者談鑰“本舊志,參正史,補遺糾誤”[1](P.4679),書中引用了許多宋代已佚方志,如北宋時的《吳興統記》(成書于景德元年,1004年)、《祥符吳興圖經》(成書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等[2](PP.346,347),均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北宋前期的城市風貌。此外,從明代早期的《永樂大典·湖州府》(下文簡稱《大典》)[3],而到晚清的同治《湖州府志》與光緒時期附郭烏程、歸安二縣的縣志,自15世紀至19世紀,每百年均有至少2種方志可供參考,為今人了解湖州城的歷史形態提供了比較系統的參考文獻。通過詳查歷代史志及參閱方志圖、近代城市實測圖可以發現,湖州城中觀尺度下的街道網絡至少在近千年來變化甚微,這使得我們運用城市歷史形態學方法考證復原和研究宋代湖州城的城市行政區劃(即廂、坊、界等)的空間平面形態成為了可能。
一、明清時期湖州城中“界”的轄區
隨著學界對宋代城市研究的不斷加深,城市中“界”的區劃逐漸受到關注,這一城市管理區劃在宋代湖州城中有顯著的體現。《嘉泰志》載:“坊名鄉地久廢,官司鄉貫止以界稱,今為界十七,分屬四廂。”*按《大典》輯本《嘉泰吳興志》為清人自《永樂大典》中輯出,今查《永樂大典》原文“坊名鄉地”作“坊名鄉也”。并記錄了各界的大致范圍。值得注意的是,湖州的“界”直至清末仍在城市管理中發揮重要作用。至晚成圖于明永樂間(1403-1424)的湖州府城圖(下文簡稱《永樂圖》,見圖1)[3](PP.6-7,《湖字韻·湖州府》)中標出了湖州城中的全部界名,崇禎《烏程縣志》所附《城郭圖》(圖2)中亦標明時屬
烏程縣轄8界及其所轄各鋪之名;此外,明清各方志均對界和鋪作了詳略不同的記載,而這17個界名也始終未有改變。通過對比《嘉泰志》和明代方志圖中標記的界鋪位置以及清代方志對界鋪的詳細記載可以發現,《嘉泰志》中記載的“界”的轄區具有很強的穩定性,這使得通過復原湖州城明清時期的城中界區來觀察宋元城市管理區劃概貌成為可能。

圖1 《永樂大典》附《湖州府城圖》

圖2 崇禎《烏程縣志》附《城郭圖》注:圖2中文字經過清晰處理。
《嘉泰志》卷二《坊巷》對“界”的轄區作了簡要描述,是今可見最早記錄湖州城界區范圍的文獻描述,可為由今及古地展開復原提供關鍵的文獻支持(見表1)。

表1 《大典》輯本《嘉泰吳興志》所載界的區劃
注:兩平橋為子城護城河南段跨河橋,因子城護城河古已湮廢無跡,經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三《津梁》考證,該橋在羊巷口,即圖3上羊巷、下羊巷相接處。狀元坊原為苕陰坊,因賈安宅更是名,即圖3小西街,故鵝行界北至小西街口。
明清時期湖州城的“鋪”是“界”的下轄單位,鋪主要以巡警、消防為務,一般由城市居民服役。元末之后,湖州城內的各“界”分屬附郭烏程、歸安二縣,而不再由專門的城市管理機構(如廂官、錄事司等)管理,各鋪以街巷為基本構成單位,均有明確的管轄范圍。經詳查湖州歷代方志,只有光緒時期《歸安縣志》和《烏程縣志》的記錄可為復原明清界區提供重要線索,其信息見表2、表3。
光緒《烏程縣志》對烏程縣轄部分界鋪的界線有更為直觀的記錄(文中所述線路參照圖3):
城內與歸安分治,迎禧門內西南為本縣所轄倉場界之縣后鋪,鋪東北接歸安濟川界,又南過獵場橋,東穿安定書院巷,南為縣轄中書界之清華鋪,北亦歸安濟川界,又由巷東口折而南,經愛山臺至府治子城坤隅,其西仍為清華鋪,東接歸安崇節界,又繞府治前,東出羊巷,抵河頭,西、南為縣轄南門界之經堂鋪、魚行鋪,東北接歸安崇新界,又溯河中流,迤至儀鳳橋,西北為縣轄南門界之小市鋪、平康鋪,西市界之橋北鋪,東南對岸接歸安歸安界、魚樓界,又由儀鳳橋南直街中分至所前巷口,西為縣轄鵝行界之橋南鋪,東接歸安魚樓界,又穿所前巷,東抵河頭貴涇橋,折而南,其南與西為縣轄南市界之三井鋪,北亦歸安魚樓界,東接歸安中界,又截河而南,水道至展家橋,出南小河,其西與南為縣轄南市界之渡東鋪,其東與北接歸安迎春界、中界,城內烏程所轄地由西北而迤東南,即歸安便民倉,亦屬烏程南市界地。[4](卷1《疆域》)

表2 歸安縣所轄界、鋪
注:表中記錄詳見光緒《歸安縣志》卷七《街巷》。“書墻弄”應即“獅象弄”方言近音;“太平勝境”即子城北太平巷,“太平勝境”在光緒二十六年《湖州郡城坊巷全圖》(日本東北大學藏)可確認。

表3 烏程縣所轄界、鋪
光緒時期的城內街巷名絕大多數均在民國25年的《吳興縣城區坊巷全圖》中標出,因此根據光緒《歸安縣志》記載,可以準確復原清代歸安縣所轄9界17鋪,且復原后呈現的烏程、歸安二縣縣界與《吳興縣城區坊巷全圖》所示縣界基本一致,對比《嘉泰志》對這9個界的大致范圍記載也均吻合,足見湖州城中界區之穩定。但烏程縣所轄界鋪的文獻資料相比之下要缺乏得多,雖然如此,《永樂圖》、崇禎《烏程縣志》所附的《城郭圖》及明清方志對于地物的描述等資料仍可作為復原剩余8個界的重要補充線索。
從崇禎《城郭圖》(圖1)來看,西市界及其所轄橋北、縣橋二鋪均在寶帶河(又稱西河)東岸,這與《嘉泰志》“市門至眺谷橋、縣橋”的記載完全吻合,可知西市界與倉場界的分界處為寶帶河,東則以儀鳳橋北之觀風巷為界,又據康熙《烏程縣志》載:“社學,一在西市界儒學南相對”、“湖協鎮督府,在縣橋鋪”[5](卷2《社學》、卷6《本朝備兵》),其址民國時為縣公安局,在圖3喬梓巷西;光緒《烏程縣志》載“新倉在經堂鋪文昌閣之北”[4](即圖3中新倉巷西側),可知西市界之縣橋鋪與南門界之經堂鋪以學前攤為界(如圖3);又前文引光緒《烏程縣志》文有“經愛山臺至府治子城坤隅,其西仍為清華鋪”,坤隅即西南隅,那么可知南門界之經堂鋪與中書界之清華鋪的分界處為榆樹街(見圖3);又前文已述及鵝行界之橋南鋪與歸安縣魚樓界以南街為界,《崇禎圖》中橋南鋪與石鼎界以旱瀆為界,這也與《嘉泰志》關于石鼎界為“旱瀆橋至祥符寺”的描述一致;又“便民倉即大倉,在定安門內西岸南倉鋪”,“歸安便民倉在定安門內東岸渡東鋪”[4](卷2《公署》),《永樂圖》將南市界標記在余不溪(入定安門之河)與其西側的南大街之間,這亦與《嘉泰志》關于南市界“橫塘至西岸史家巷”的記載一致,故南市界與鵝行界應以南大街為界;又“育嬰堂在縣治南百步眺谷鋪”[4](卷2《公署》)(即圖3育嬰堂弄),則烏程界之眺谷鋪與縣前鋪界分基本可知。綜合上述,明清湖州府城內的界鋪轄區平面分布可基本得以復原(如圖3)。

圖3 明、清兩代湖州府城界鋪詳圖
注:底圖為民國25年(1936)《吳興縣城區坊巷全圖》,比例尺為5000分之1,吳興縣政府清丈處測量,見劉宏偉主編《湖州古舊地圖集》,中華書局2009年,第231頁。是圖繪制時湖州城大部分城墻均未拆除,古城形態變化甚微。原圖地物街巷文字根據需要,有所刪減。圖中縣轄界的表示舉例:中書界①②,意為中書界包括圖中①(清華鋪)和②(泮宮鋪)所轄區。
需要說明的是,表2中魚樓界包括“門北兜”和“新開河”,“門北兜”應即“聞波兜”之方言近音,“新開河”即新開河路,這與光緒《烏程縣志》“又穿所前巷,東抵河頭貴涇橋,折而南,其南與西為縣轄南市界之三井鋪,北亦歸安魚樓界”相矛盾(見圖3)。相比之下,光緒《歸安縣志》記載更為明確,今從之。
二、宋代湖州的羅城
(一)元代湖州城的拆毀與重建
古代湖州城是典型的圍郭都市,南宋歸安人倪思*倪思(1147-1220),歸安人,乾道二年(1166)進士,官至禮部尚書。稱湖州“城外居民室宇不過數十家”[6](P.88),甚至在1900年的《湖州郡城坊巷全圖》中,仍可見城內四隅田園隙地甚多,可知宋代湖州城區范圍僅限于羅城之內,因此對宋代湖州的羅城展開考證復原是研究其廂、界、坊等問題的必要前提。
唐代以來的湖州在筑城史上可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始于唐初,終于元初,《嘉泰志》載:
羅城東西一十里,南北一十四里,《統記》云:“一十九里三十步,折二十四里。”唐武德四年越郡王孝恭所筑。景福二年,刺史李師悅重加版幹之功,見舊《圖經》。《統記》云:“有記見存。”紹興三十一年知州事陳之茂修,有記在墨妙亭。城上舊有白露舍,太平興國三年奉敕同子城皆拆毀。[1](P.4686)
文中稱湖州羅城為越郡王李孝恭始筑于唐初武德四年(621)*按李孝恭武德四年至五年皆在荊湘征討蕭銑,六年始至江東討伐輔公祏,武德七年(624),“公祏窮蹙,棄丹陽東走,孝恭命騎將追之,至武康,擒公祏及其偽仆射西門君儀等數十人,致于麾下,江南悉平。”(參見《舊唐書·宗室·列傳第十》,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349頁)故《嘉泰志》始筑城于武德四年的記載或有訛誤。,其后雖經修繕,但其平面形態并未改變,太平興國三年(978)也僅拆除羅城上的白露舍及子城城墻,宋人倪思言湖州“自唐末五代以來,不經兵火”,“今尚有唐末五代時屋宇”[6](卷七《霅川城守己見》、卷五《霅川》,PP.67,88),足見唐宋湖州城形態之穩定。
唐宋羅城在元初時被拆毀,具體時間不見史志。《大典》載:“羅城,舊志所載周二十四里,元初削平之。”[3](卷2277,湖字韻,《湖州府》,P.59)按元軍于至元十三年(1276)降宋廷,取湖州,同年九月丁未,“命有司墮沿淮城壘”[7](卷9《世祖六》,P.185),與湖州相臨的嘉興城便于該年拆毀,故可知湖州應亦在同時拆城。元末張士誠命其左丞潘元(原)明取湖州,其事詳載于張周天佑四年(1357)三月三日的《吳興臨湖門記》《吳興郡城迎禧門記略》及元至正十九年(1359)五月的《左丞潘公政績碑》中。
如饒介*饒介(1300-1367),時任張氏淮南行省參知政事。《吳興臨湖門記》云:“是年十一月十九日□烏程□□存忠董工□□,明年二月十七日門成。”[4](卷二《城池》)饒介《吳興郡城迎禧門記略》亦云:“天佑三年冬十一月十九日筑城,明年春二月城成。”[8](卷二《城池》引《苕紀》,P.54)*按《湖錄》載,《苕記》于明萬歷癸丑(四十一年,1613年)成書,作者張睿卿。宇文公諒*宇文公諒,生卒年不詳,吳興人,至順四年(1333)進士。《左丞潘公政績碑》則提及:
公于是年夏四月十有九日統兵入城,清蕩苗頑,宣布德澤,既安其民人,即經構其城郭,乃以是年十有一月之八日審機相度,有事版筑,都事吳陵、張瑛、掾史孟熙從公宣力,樹旗定方,萬夫畢集,甫四視朔土,功告完成。[9](卷十六,PP.664-666)
從上文可知,潘元(原)明于1356年十一月八日規劃新城,并發動萬人,于十九日動工,次年二月(十七日)完工,前后僅耗時90天,工程是趁冬季緊急開展的,并且“城甫畢工而寇卒至”[9],可見新城的修筑是以戰爭防守需要為首務的。
(二)新舊羅城的形態變化
元末湖州羅城的修筑以工程效率及軍事防守為主要目的,因此唐宋時期24里大城的規模便不再適用于戰爭年代,如宋人所言:“筑城之法,以小為貴,小則守城之人用力為易,若所筑大闊,兵力不及,反誤百姓,利害非輕。”[10](P.183)潘元(原)明便顧及于此,“以舊城寬而不固,難守,乃筑小之,周圍一十三里一百三十八步。”[11](卷三《城池》,P.86)
縮小之后的羅城形態即為圖3所示,其在宋城基礎上縮建之處亦有據可考。《大典》引明初《吳興續志》載:
至正十六年,張士誠據湖州,守鎮官潘元明重筑,較舊基約而小之。東門退入半里許,西門退入一里許,南北稍入數丈,周圍一十三里零一百三十八步二尺,水陸共八門,上建城樓,改鑿壕塹,非復舊處。[3](P.59)
這段記載似乎以一篇名為《湖州府沿革志碑》的碑文為依據*光緒《烏程縣志》稱該碑見載于成化《湖州府志》,為洪武十一年知府談士奇立,按該碑文不見今本成化《湖州府志》,但光緒《烏程縣志》稱“如碑所言,則東西共減一里半”,這與《大典》引《吳興續志》“東門退入半里許,西門退入一里許”說法相同。,并將縮減部分精確到東、西二門的退縮里數*萬歷《湖州府志》卷一載:“以東西二門退入數百步”;光緒《烏程縣志》卷二:“東退入半里,西縮入一里,南北稍入數丈,四面各縮于舊。”,對于羅城此時縮建的問題,清人提出疑惑:
今府城東西止四里,南北止六里,較李孝恭所筑東西減六里,南北減八里,如碑所言,則東西共減一里半,南北共減不及半里,其數懸殊,豈孝恭里數乃夸詞非實數耶……存疑俟考。[4](卷二《城池》)
這是湖州新、舊兩城形態比較的一個明顯問題,今可見最早記載宋城周長的《吳興統記》(1004年成書)云:“一十九里三十步,折二十四里”,《嘉泰志》稱“東西一十里,南北一十四里”。筆者認為,所謂“東西一十里,南北一十四里”非指羅城長與寬的長度,而應當理解為東、西兩面羅城長10里,南、北兩面長14里,這樣一來,兩者之和恰好是羅城的周長。所謂羅城的東、西、南、北,在方志中亦有類似表達,如萬歷《湖州府志》載:府城“東、北隅系歸安境,西、南隅系烏程境”[12](P.26),各隅包含數界,這與宋代城內的東、西、南、北四廂范圍一致(湖州城內宋代四廂的問題詳后文)。故“東西”、“南北”當如是解。“十九里三十步”,應為《吳興統記》所記北宋以前的早期數據,“折二十四里”應即折合為北宋《吳興統記》編纂之際的長度單位后所得的數據。
新舊二城的形態變化在其他文獻中亦可找到佐證,乾隆《湖州府志》載:
自元末潘原明縮而小之,止十三里有奇,其并省處在西門外直抵大溪,入清塘一路尖地,則清塘、清源二門以外棄為田野者多矣。[13](卷二《城池》)
乾隆《烏程縣志》引《苕記》載:
潘原明并省處在西門外直抵大溪,入清塘一路尖地。三面倚大溪,惟西多陸,守者尤須加意。[8](P.52)
關于西面縮建的記載在《嘉泰志》中亦有印證:
(苕溪)至城下,一自清源門入經漕瀆,至江子匯為霅水;一自清源門外徑趨釣魚灣,沿壕經迎禧門,又經奉勝門,合霅水以入太湖。[1](卷五《溪》,P.4709)
可見宋代羅城的清源門及清塘門(即迎禧門)是緊臨苕溪的。清源門至定安門的城墻段亦沿大溪,其地在今杭長橋中路之側,今尚可見該處有高出平地1到3米、長近1000余米的隆起土坡,這應是宋代湖州城的西段城墻遺址。
羅城的東段城墻應變化不甚大,《嘉泰志》載:“東壕又為二重,曰外壕,曰里壕。”而在日本明治十七年(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繪制的《兩江楚浙五省行路圖》第三號《浙江省湖州府局地圖》*圖系美國國會圖書館藏1884年刊本,由上海師范大學陳濤博士告知,謹致謝意。中,明顯可見城東有兩條并行的護城河(圖4),可知羅城東段仍大致保持宋城形態。除退入半里的東門之外,文獻中可見的變化在城東放生池處。《大典》載:“忠烈廟,即顏魯公廟,在駱駝橋東放生池上,元至正十七年筑城,隔于城外,總管陳眜移建于廣化橋北。”*按該文為《大典》引明初《吳興續志》。[3](P.248)放生池在東街里(古忠烈坊)之東,《永樂圖》中繪于城外。又《嘉泰志》載:“城門舊有九所,放生池側有閶門……顏公放生池東南城上有遺跡尚存。”[1](卷二《城池》,P.4686)這應是東側城墻有據可考的唯一縮建之處(唐宋羅城示意圖見圖6)。

圖4 《浙江省湖州府局地圖》局部
三、宋代湖州城“坊”與“界”的考證復原
(一)《大典》輯本《嘉泰吳興志》之《坊巷·州治》篇考辨
《嘉泰志》卷二《坊巷·州治》(下文簡稱《坊巷》)中收錄了宋代湖州城中新舊坊名共計65個,這些坊具體是何種形態,學界說法不一。有學者認為這些坊即街巷[14](P.347),也有學者予以反駁,認為只是坊額建筑。[15](P.119)然而,《大典》輯本《嘉泰志》中的這段文字記載卻存在一個被普遍忽視的基本問題,這一問題不解釋清楚,則難以輕下定論。
在目前所見的《大典》輯本《嘉泰志》之《坊巷》篇中,出現三處十分可疑的時間記載:
嘉定癸未,太守宋濟既新銷暑,葺清風,于是邦人相率各于其居請表坊名,務稱守意……
叢桂坊,舊名仁政坊……今江陰太守孟奎先諸兄擢丙辰第,咸淳乙丑,少監孟圻、運干孟至,機帥孟垕一榜同登……禮宜柱表,改用今名。[1](P.4689)
以上兩條記載分別出現了嘉定癸未(十六年,1223年)、丙辰(應為寶祐丙辰,1256年)、咸淳乙丑(元年,1265年)這3個年份,而《嘉泰吳興志》成書于嘉泰元年(1201),何以會記載其后數十年間之事?這一“矛盾”亦曾被人注意,陳振所著的《宋史》中提及該問題,但并未作出解釋[16](P.561,注釋1);包偉民則認為“嘉定癸未”應為“嘉泰癸亥”(1203),但未對寶祐與咸淳作出解釋,因此將湖州增設坊額的時間改為嘉泰三年,這是值得商榷的。[15](P.118,注釋9)
筆者認為,這段文字并非《嘉泰志》原文,而是后人所作。《嘉泰志》原書已佚,今本為《永樂大典》中輯出的殘本。民國三年(1914),南潯嘉業堂劉承干據鈔本校刻,收入《吳興先哲遺書》,其跋曰:
《嘉泰吳興志》二十卷,宋談鑰元時撰,明嘉靖時,徐長谷撰《吳興掌故集》,猶及見之,后不傳。開四庫館時,館臣從《大典》輯出,未及編纂進呈,外間傳鈔,有分二十卷者,有分十五卷者,亦有不分卷者,今所存原目,仍分為二十卷。[2](P.350)
因此《大典》輯本《嘉泰志》并非原始文獻,清乾隆間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錄時極易出錯,其后雖經劉承干校勘,但仍未完善。今《大典》之“湖州府”尚存8卷,曾有學者利用《大典》及《吳興備志》中的《嘉泰志》佚文與輯本《嘉泰志》進行校勘,發現輯本“錯漏百出”,“文字脫訛比比皆是”[17],《坊巷》一篇,應亦是其中的一處明顯錯誤。

《坊巷》篇對坊的具體記載,可以有力證明這段史料的年代:“叢桂坊,舊名仁政坊,在隆興橋直至郭尚書廟華表對峙。”《永樂圖》中隆興橋東的街巷上標有“□桂坊”,該街道直通臨湖門側,即圖3中的府學前街,那么可知文中記載的郭尚書廟址便在后來的府學前街東端。而元代以前,該廟在駱駝橋北,“元至正十二年毀于兵火,皇朝命列祀典,知府楚岳改建于臨湖門西北。”[3](PP.247-248)因此臨湖門側的郭尚書廟為明初始建。這便有力證明了《坊巷》篇成文于明初,其所展現的當是明初重建之坊的狀貌。清人之所以在輯錄中出錯,應是誤讀了《大典》中的:“《吳興志》、《舊圖經》、《統記》,坊十有六,多名存而無表識”這一句,故誤將“《吳興志》”以下作《嘉泰志》之文,而從“《舊圖經》”處開始輯錄。結合上文分析來看,宋《嘉泰志》原文中所載古坊數量應仍為16個。
雖然如此,但《大典》的記載,是以舊志為據,注以時事,而并非完全創新。其中巷名更是直接摘抄南宋淳熙間成書的《吳興志舊編》,故如前文提及的養濟坊巷、白塔巷、曹家巷、西營巷,元末筑城均隔于城外,而《坊巷》仍錄其名;坊的記載亦與之相似,如明初“觀文、擁旌、余慶三坊,俱筑于城外,已廢”[3](P.65),但《坊巷》亦予以收錄。這均是《坊巷》篇據舊志所作的表現。《大典》之《坊巷》全文以《吳興續志》開頭,那么這段文字實際上應該仍是明初《吳興續志》之文,宋《嘉泰志》的《坊巷》篇原文隨著該書的散佚已經不存在了。
除上述之外,在《坊巷》的解讀上亦須特別注意。該文共收錄65個新舊坊名,其中前半部分載:
和樂坊、平康坊、仁政坊、烏氏坊、程氏坊、苕陽坊、桃李坊,以上四坊屬烏程界;車騎坊、章后坊、德本坊,以上七坊屬歸安;白華坊、吳歈坊,以上二坊未詳所在。右《舊圖經》有其名而無其識。*引文省略原文夾注。
文中稱“以上四坊”,而其前所記卻有七坊,又稱“以上七坊”,其前卻只有三坊,這該作何解?通過比較可以發現,其中平康坊,成化《湖州府志》稱“舊名樂眾,在市街瓦子巷口”[11](P.98),而樂眾坊之名亦見載于《坊巷》;又仁政坊,咸淳間更名叢桂,但新舊兩名亦均見載,因此可判斷上文所引應為明初《吳興續志》摘錄的“《舊圖經》”所載殘文*按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考證,《舊圖經》約修于紹興后。據《大典》輯本《嘉泰志·宮觀》載“祥應宮”條稱:“《舊圖經》、《續圖經》皆作‘今廢’”,則二經應大約同時,《續圖經》成書于紹興中,則《舊圖經》應亦在此前后,那么《舊圖經》所載北宋坊名應為摘錄北宋某志之文。,文中“章后坊”下注曰:“《舊經》云:‘天寧寺在章后坊’,天寧今曰光孝。”按天寧寺之名用于后唐長興二年(931)至北宋崇寧二年(1103)間,文中仍稱“天寧”,則應在崇寧二年之前,故上述應為北宋時坊名,且僅存其名。
此外,《坊巷》中明確寫出了各界所歸屬的4個廂的區劃,需要說明的是,宋代湖州的廂在元代并未廢除,而只是“以郭內四廂之地置錄事司”。[11](P.13)以烏程縣為例,元末張士誠據湖州,廢錄事司,“以二廂復入縣轄”[18](P.241),可見廂的建制是一直存在的。明代文獻中未見廢廂的記載,而可見類似“廂”的“隅”,《大典》載:元代歸安縣“以在城東、北隅分置九界”[3](P.76),萬歷《湖州府志》亦明載“東、北隅系歸安境,西、南隅系烏程境”,“東隅四界”、“北隅五界”、“西隅四界”、“南隅四界”[12](卷一),《坊巷》中所載四廂名為“左一廂”、“左二廂”、“右一廂”、“右二廂”,而《元史·地理志》載:“湖州路,舊設東、西、南、北四廂”[7](P.1492),成化《湖州府志》亦載:張士誠時“罷錄事司,以西、南廂屬烏程,東、北廂屬歸安。”[11](P.13)可見“廂”的建制在明代依然保存,只是改換了名稱而已,因此《坊巷》對湖州城的“廂”的記載,雖非宋代之文,但可基本反映宋代的原狀。
綜上所述,《大典》輯本《嘉泰志》中的《坊巷·州治》篇為錯輯明初洪武《吳興續志》之文,其中關于坊的記載雜糅了以下三種來源的史料:前兩種為摘錄北宋舊志、或南宋方志所引北宋舊志的殘文,還有一種可能為據元代某方志所載的南宋晚期坊名為綱,注以明初重立后之狀而成之文本。這應是研究宋代湖州城坊的基本認識。
(二)明初重建之坊的復原
《大典》輯本《嘉泰志》中所記之坊雖是明初之物,但其年代距元末戰亂毀壞時甚近,仍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南宋后期的坊的情形。且南宋淳祐七年(1247)的《仁濟廟加封敕牒碑》文末有“浮玉王震同男泳刊”句[9](P.615),其中“浮玉”即為其居所在的浮玉坊;又元至元甲申年(1284)時的《湖州報恩光孝禪寺置田山記》[9](PP.627-629)記錄了多數賣田及舍田之人的籍貫,其中除大多數以界相稱者之外,尚有“府城東溪坊”之稱,東溪坊同前浮玉坊均見載于《坊巷》,可見明初重立之坊在宋元時期已用于城市居民住址稱謂中,確為南宋后期的坊。因此,嘉定癸未(1223)郡民樹立的新舊51個坊名便應皆在明初重立的新坊之內,因此對明初重立之坊展開復原,便可略見南宋舊坊的狀況。《坊巷》記載及注釋匯總如表4。
根據上表可復原明初重建之宋坊的概貌,見圖5。

表4 《坊巷·州治》主要內容
注釋:表中出現的“全捷營”與“雄節營”均為南宋軍營名,“全捷營”在《大典》輯本《嘉泰志》作“令捷轡”,據《大典》原文改,為輯錄時訛誤。南宋亦有“馬軍營”,宋亡后至民國而其巷仍用其名。該軍營名與此相同,為明代巷名,非指南宋時地物。

圖5 明初重建宋坊復原圖
注:明初烏程、歸安二縣所轄界不同于其后,南門界屬歸安,濟川、魚樓二界屬烏程,故兩縣縣界如本圖。
在《永樂圖》中,坊名均被標記在道路中間,結合《坊巷》的文字描述可知,明初重建的宋坊,其空間實體便是街巷和沿街的官署祠廟及民居。其中如通往北門的大街,長約千米,名為太和坊,且該名一直沿用至民國時期;通往臨湖門的大街長約500米,名為東溪坊,即前文所引元初《湖州報恩光孝禪寺置田山記》中賣舍田人所居之處。
《大典》中亦有稱某地物在某坊內者,如“三皇廟在湖州府壽昌坊鴻禧寺東”[3](P.246),可見南宋后期“邦人相率各于其居請表坊名”時所建的坊,是在街巷路口樹立起牌坊,且整條街巷也因之而名。從圖5中樹立坊的街巷來看,多為城市主干道路,支離小巷則多因官署、寺廟、名人宅邸而建坊,如富民坊有都稅務;賢福坊與飛英寺相對;聽履坊有沈尚書宅等,因此“坊中有坊”的現象,實即對干道內分離支巷的坊的描述,“以坊統巷”與之同理,如光緒《烏程縣志》稱:“兩平橋,在府治東南彩鳳坊羊巷口”那樣(見圖3),仍舊采用這種“以坊統巷”的地點描述方式,實則“坊”為干道,“巷”為支路而已。坊與巷的關系在于,街口立坊額者為坊,無坊額者為巷,且多有舊巷立坊后,雅俗二名通用者,如樂眾坊,舊名平康坊,俗稱瓦子巷;集賢坊俗稱盛家巷;忠賢坊,俗稱顏魯公堂巷等等,在方志描述坊的位置時,往往用人們熟知巷名來指示坊之所在,因此便容易讓人誤認為其所記載的坊僅為坊額建筑,而實際上,陳振的見解應更為妥當,即南宋晚期湖州的坊其實是街巷的雅稱。
(三)飛英塔銘文所見宋代湖州城的“界”
陳振認為宋代“一部分大中城市開始實行廂統界,界轄坊(巷)的‘廂界坊(巷)制’”[14](P.347),這種觀點的主要根據之一便是《大典》輯本《嘉泰志》的《坊巷》篇,而據本文考證可知,這段文字實出自明初《吳興續志》,因此基于這一史料得出的論斷是需要重作討論的。
前文所引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的《湖州報恩光孝禪寺置田山記》中出現了元初界名記載,如“郡城迎春界趙承奉”、“郡城報恩界任安人”、“郡城崇新界□□□平安界陳□□”、“郡城□樓界”、“郡城西□界”、“郡城飛英界陳六七”、“郡城倉場界許□”等等*其中“平安界”應為“歸安界”;“□樓界”即“魚樓界”;“西□界”即“西市界”。,均明確了元初湖州城中已存在“界”的區劃。除此之外,至今保存完整的宋代飛英塔內層石塔刻有銘文28條,計1461字,記載了南宋紹興年間湖州居民舍錢糧重建石塔時所寫的祈愿寄語,其中多記錄了施主的籍貫住址,這為了解宋代湖州城的界提供了至關重要的依據,摘錄其文如下*飛英塔銘文分布在石塔各層,今仍清晰可見,資料的獲取亦得到湖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嵇發根、民政局地名辦公室劉宏偉以及湖州飛英塔工作人員的幫助,謹致謝意。:
州郭南門界居住,奉佛女弟子□氏三五娘,法名善德,謹施凈財一百二十貫文足……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四月八日□氏謹愿。
湖州歸安縣仁風鄉南門界居住,女弟子任氏十四娘,法名智通……追薦亡夫周三四太醫往升凈土,求乞懺悔,紹興二十五年十月日題。
湖州烏程縣霅水鄉府郭倉場界居住,女弟子沈氏大娘,法名善慈,施錢一百二十貫文足。
歸安縣仁風鄉府郭崇節界居住,清信奉佛弟子吳寧,宿有善根。
湖州烏程縣霅水鄉府郭鵝行界居住,弟子張拱在日,謹施凈財一百貫文,助緣造塔。
州郭崇新界,弟子顧擇弟顧詵與家眷等,施財六十貫文足……仍保家眷安寧者。
湖州歸安縣仁風鄉南門界,女弟子宋氏五娘,法名善廣,舍錢三十貫文足,鐫造佛像三十尊,保安身位,集福消災者。[19](PP.9-12)

圖6 南宋前期湖州城市行政區劃示意圖
這數條銘文刻于南宋紹興二十四(1154)、二十五年(1155)或其前后,均確鑿地證實了湖州城早在南宋初便已存在了“界”的區劃,且被慣用于居民住址描述中。湖州于兩宋之際免遭宣和、建炎兵火,可以相信這一區劃是十分穩定的,且作為界名由來的一些地物——如倉場界內的西倉、崇節界內的崇節營等,均為北宋初期之物,界也極可能在北宋時便已形成。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湖州城的界為鄉所轄,這與臨城嘉興的狀況如出一轍*宋代嘉興城內分屬五個鄉,下轄十二界,亦設有南、北、西三廂,坊(巷)歸界轄。[20],從上文看,位于城西和城南的倉場界、鵝行界均屬烏程縣霅水鄉所轄,城北的崇節界及子城南的南門界屬歸安縣仁風鄉所轄(見圖6),此外《大典》輯本《嘉泰志》引北宋李宗諤《吳興圖經》(1010年修)稱飛英寺“在白鶴鄉”,則城東北隅在北宋初屬白鶴鄉所轄。由此看來,宋代湖州城的行政區劃并非如學界一般認為的宋代通行的“廂坊制”,而與嘉興同樣呈現“鄉界”與“廂界”的二重結構。注:據1957年湖州市人民政府民政科繪制《湖州市區圖》改繪,圖見劉宏偉主編《湖州古舊地圖集》第458-459頁。圖中廂轄區舉例:“①②③④北廂”是指北廂包括了①(飛英界)、②(報恩界)、③(崇節界)、④(南門界)四界的轄區。
與飛英塔銘文年代相近的《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1148)記載了兩位湖州籍進士:(第四甲)“第二十三人,王康年,湖州烏程縣霅水鄉倉場里”;(第五甲)“第十九人,莫沖,湖州歸安縣仁風鄉迎春里”。[21](P.351,354)其中隸屬于霅水鄉的“倉場里”和仁風鄉的“迎春里”與湖州城中的“倉場界”和“迎春界”同名,據《大典》本《嘉泰志》載:“《舊圖經》載鄉距縣里數,如霅水鄉在縣西一十五里,今縣治即系霅水。”[1](P.4691)而烏程縣治在倉場界內,且湖州之里無名“倉場”者,則上文之“倉場里”應即霅水鄉在城的倉場界;又成書于元代的《夷白齋稿》載湖州武康下渚里人沈母事跡:“至元間父昌徙城迎春里”[22](卷三十四《沈母傳》),可見“迎春里”亦在城,實即迎春界別稱。這些均可表明宋元湖州城的“界”均被時人視為鄉屬在城之“里”,在行政管理中應承擔與“里”相似的職能。明代則明確記載“界各設里長”[12](P.27),亦可為證。“界”應當既是土地房產登記、賦役征發的基層組織,也是治安消防的基本分區(圖6)。*如圖6可知,清人稱“宋時城寬,石鼎界至龍溪口,迎春界亦包東關鋪在城內。”其說可信。見同治《湖州府志》卷四《鋪界》。
有學者根據《嘉泰志》所載“坊名鄉也久廢,官司鄉貫止以界稱”(實為明初之語)句,認為南宋湖州的17個界是北宋16個古坊增設后的別稱*陳振《略論宋代城市行政制度的演變——從廂坊制到隅坊(巷)制、廂界坊(巷)制》;魯西奇《唐宋城市的廂》(《文史》,2013年第3期);包偉民《宋代城市史研究》第二章《管理制度》(中華書局,2014年),均持此論。,僅從文本上來看,筆者認為,清人從《大典》中輯錄《嘉泰志》時,將“坊名鄉也”抄作“坊名鄉地”,亦可能是因為不解其意而擅斷為之。由前文來看,湖州城市居民的籍貫在宋代常有某鄉、某界或某坊的表達,但到了明代,在城之鄉已不見諸史志,坊表也因元末至正十六年(1356)的兵火而幾乎盡廢,至明洪武十一年(1378)始重設,期間20余年街巷無表可識,洪武十一年時知府重立坊表尚需“考諸志書”。[3](P.65)故官府及民間對于籍貫的稱謂便只剩下“界”,因此“坊名、鄉也久廢,官司、鄉貫止以界稱”句,其意更應側重于表達明初湖州城市居民的籍貫問題,而并不一定可以證明宋代湖州城的“界”是由早期的“坊”改設而來。
且由前文可知,原本《嘉泰志》與北宋《吳興統記》、南宋《舊圖經》所載者均為16個古坊,而《坊巷》引《舊圖經》等所載的北宋古坊,坊名見載者便已有20個,且尚有遺失坊名者*如《嘉泰志》引《舊經》文稱:(小景德才院)“在歸安縣南苕溪坊”,“苕溪坊”之名不見《坊巷》記載,應為《舊圖經》所載殘文中漏記之坊,則北宋的古坊數量便已多于21個。,這與今本《嘉泰志》中16個古坊名的記載并不相符,可知所謂“坊十有六,多名存而無表識”句,應只是北宋早期的數量,可能最早由《吳興統記》(1004年成書)記載,并為南宋《舊圖經》《嘉泰志》傳抄,可見宋代湖州城中的坊的數量是逐漸增多的,并在嘉定十六年普遍新建,其前后性質應當相似。
余論
南宋地方城市中的坊多為樹立牌坊之街巷,這在其他城市中皆有體現,最為典型的便是《平江圖》所展現的南宋紹定間平江府城(今蘇州)中的坊,其他如《淳熙嚴州圖經》所附《建德府內外城圖》、《嘉定赤城志》所附《黃巖縣治》、《仙居縣治》圖等,均將坊繪于街口,可明確表明這一事實。此類坊在南宋大量涌現或許并不能簡單地用坊墻倒塌而使得街巷無標可識來解釋,僅從湖州的狀況來看,始建于唐初的羅城的不規則形態以及城內復雜且長期穩定的城市肌理似乎沒有受到當時都城里坊制度的顯著影響。宋代地方城市中的坊,更為突出的或許是其分劃街區、標識巷陌的實用功能以及標榜文治、教化風俗的文化功能。明初湖州重建的南宋舊坊起初仍欲恢復舊用,但到成化之后,這些坊便在方志記載中被視作單純的牌坊建筑了,由官方規劃的文雅的城市街道名終究多為市井慣用的通俗巷名所取代,坊的地理指代功能的弱化,或是明清旌表牌坊普遍樹立的一個主要原因。
宋代湖州城的“界”介于廂、鄉和坊巷之間,從行政隸屬上看,它既為縣轄財政管理和賦役征發的單位,又是廂官行使其監管城市、巡警消防等職能的分區,應與一些城市中的“坊”區具有相似功能。湖州的鄰城嘉興于南宋時亦設有3廂、5鄉、12界,且明確呈現附郭縣領鄉,鄉轄界,界統坊巷的結構,元廢廂,又改為錄事司—鄉—界—坊巷的結構。[20]此外南宋臨安府城*見《乾道臨安志》卷二《坊市·界分》、《淳祐臨安志》卷七《界分》、《咸淳臨安志》卷一九《疆域志四·廂界》。、北宋元祐時期的鄧州武勝軍、崇寧間的襄州[23]等城,亦存在“界”,足見此類城市行政區劃在宋代地方城市中的常見。至于附郭鄉,似乎與城郊鄉有所區別,如嘉興出土北宋政和三年(1113)修街磚銘文有“大宋國秀州嘉興縣郭五鄉居住會”字,似設有在城五鄉管理城內居民的聯合機構。但是宋代地方的鄉之在城者是否與城郊相似,在至和之后僅為用于土地登記、確定稅則的地域單位[24],抑或是兼具行政管理職能的城市行政區劃,目前仍難斷言,尚有待于日后個案的深入探究來予以解答。
參考文獻:
[1]談鑰.嘉泰吳興志[M]//宋元方志叢刊: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2]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M].北京:中華書局,1962.
[3]解縉,等.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七十五[M].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4]周學濬.烏程縣志[M].潘玉璿,等修.清光緒七年(1881)刻本,上海師范大學圖書館藏.
[5]沈從龍,等.烏程縣志[M].高必騰修.清康熙二十年(1679)刻本,國家圖書館藏膠片.
[6]倪思.經鋤堂雜志[M].長沙:岳麓書社,2001.
[7]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
[8]杭世駿.(乾隆)烏程縣志[M].羅愫修.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9]陸心源.吳興金石記[G]//歷代碑志叢書:第19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10]黃干.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三十七[M]//宋集珍本叢刊:第67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
[11]張淵.(成化)湖州府志[M]//上海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第88冊.勞鉞修.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
[12]唐樞,等.(萬歷)湖州府志[M].栗祁修.明萬歷六年(1578)刻本影印本.上海:古籍書店,1963.
[13]李堂.(乾隆)湖州府志[M].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刻本,上海圖書館藏.
[14]陳振.略論宋代城市行政制度的演變——從廂坊制到隅坊(巷)制、廂界坊(巷)制[M]∥漆俠先生紀念文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
[15]包偉民.宋代城市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2014.
[16]陳振.宋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7]黃燕生.《永樂大典》征引方志考述[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6,(3).
[18]徐守綱,等.(崇禎)烏程縣志[M]//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第9冊.劉浕春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
[19]朱仰高.湖州雜識[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20]來亞文.宋元與明清時期嘉興城中的“坊”[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5,(3).
[21]紀昀,等.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4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
[22]陳基.夷白齋稿[M]//四部叢刊三編·集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23]魯西奇.買地券所見宋元時期的城鄉區劃與組織[J].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3,(1).
[24]夏維中.宋代鄉村基層組織衍變的基本趨勢——與《宋代鄉里兩級制度質疑》一文商榷[J].歷史研究,2003,(4).
(責任編輯:吳芳)
“Jie” and “Fang” of Huzhou City in Song Dynasty
LAI Ya-wen, ZHONG Ch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The research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of “Jie”(界) and “Fang”(坊) of Huzhou City in Song Dynas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urban geography.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full text ofFangXiangZhouZhi(《坊巷·州治》), the second volume ofJiaTaiWuXingZhi(《嘉泰吳興志》) which copied from Yongle Canon(《永樂大典》), was actually a wrong copy from the text ofWuXingXuZhi(《吳興續志》) by the scholar in Qing Dynasty. On the basis of this material criticism, the true shape of “Fang” in the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reconstructed, which proved to be the street with “Paifang”(牌坊) on the street corner. Meanwhile, based o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lane form of broad walls in Huzhou City in Song Dynasty, we backdate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boundary” of Huzhou City District in Song Dynasty, and arrived at the conclusion that “Jie” in Huzhou City was not the nickname of “Fang”, it was “Li”(里) in the city, which was the basic unit of “Xiang”(鄉) for tax levy within the city walls and the primary division of “Xiang”(廂) for police patrol and fire control.
Key words:Song Dynasty; Huzhou City; “Jie”; “Fang”; historical urban-morphology study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6.01.015
中圖分類號:K901.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2338(2016)01-0109-14
作者簡介:來亞文(1990-),男,河南息縣人,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歷史人文地理研究;鐘翀(1971-),男,浙江浦江人,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主要從事歷史地理學等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研究基金項目“基于早期近代城市地圖的我國城郭都市空間結構復原及比較形態學研究”(41271154)的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5-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