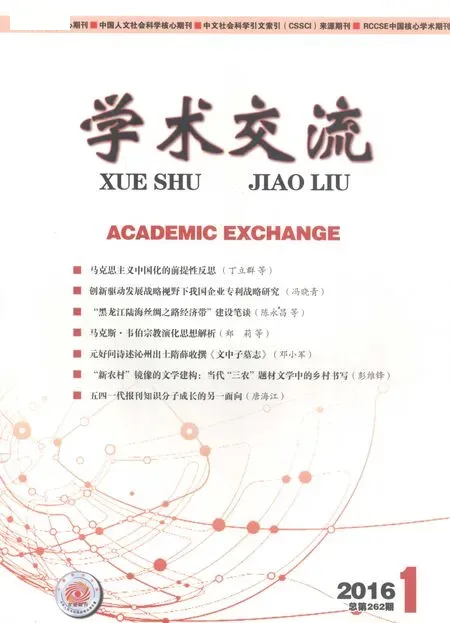公共際遇的現實與命運
2016-02-27 01:57:21杜娟
學術交流 2016年1期
關鍵詞:現實
?
公共際遇的現實與命運
楊偉偉在《哲學研究》2015年第11期撰文指出,20世紀60年代東歐馬克思主義與蘇聯馬克思主義的分歧,其實質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與批判的馬克思主義的沖突,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與“回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運動的對立,其現實表象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思潮與官方意識形態的斗爭。由此,這種分歧并不局限在東歐與蘇聯兩者之間,而是深人到蘇東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這種深入只能由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總體性進行闡釋,并且深入的主題和內容必須設置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危機中。這次分歧本應成為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一次公共際遇,然而歷史并沒有對它作出客觀的、科學的評判,從而致使馬克思主義喪失了一次重大發展的歷史機遇。試想,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后,世界學者普遍做到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切反思,如果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自己(既包括它的官方意識形態機構,也包括它的民間學者,哪怕只有一方)能夠從斗爭中獲得啟示、借鑒,馬克思主義是否就能夠決然走出“危機”,社會主義事業是否就能夠無間斷地開疆拓土,這是擺在馬克思主義者面前的歷史“難題”。困難不在于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真正困難的是我們是否把馬克思主義視作一種事業、一種實踐而不僅僅是理論。正如馬克思所言:“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
(杜娟摘)
猜你喜歡
小獼猴學習畫刊(2024年6期)2024-07-09 00:00:00
中國新聞周刊(2024年18期)2024-06-07 22:40:49
文苑(2020年11期)2021-01-04 01:53:20
人大建設(2019年12期)2019-05-21 02:55:32
語文世界(初中版)(2016年6期)2016-06-29 22:44:39
現代計算機(2016年12期)2016-02-28 18:35:29
發明與創新(2015年25期)2015-02-27 10:39:23
中國衛生(2014年12期)2014-11-12 13:12:38
杭州科技(2014年4期)2014-02-27 15:26:58
新東方英語(2014年1期)2014-01-07 20: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