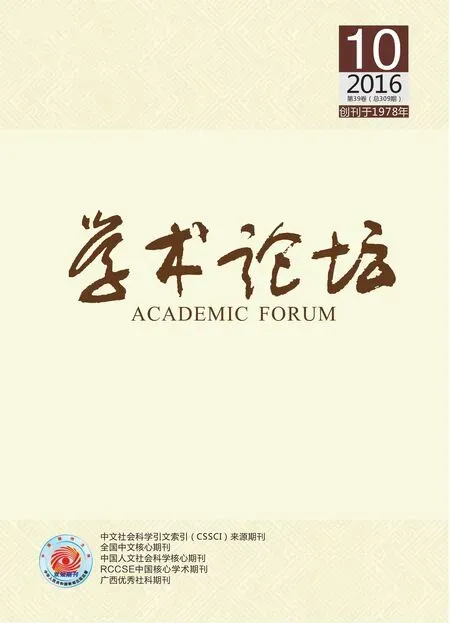大數據時代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思維變革
付安玲,張耀燦
大數據時代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思維變革
付安玲,張耀燦
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是一項長期、復雜的系統工程,應根據時代變化與時俱進。大數據作為互聯網時代的鮮明特征,已成為各國占領教育信息化發展的制高點。大數據在教育資源、受眾范圍、傳播效果和數字平臺等方面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帶來巨大契機,同時也帶來嚴峻挑戰。運用大數據思維,將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與大數據技術有效結合,促進整體性、多樣性、動態性、開放性和復雜性的思維變革,對于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提升主流話語權和維護意識形態安全等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大數據;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大數據思維;思維變革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時指出:“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是以馬克思主義進入我國為起點的,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逐步發展起來的。”[1]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需要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與時俱進。當今世界,大數據帶來的信息風暴使人們的生活、工作和思維產生深刻變革,“數據就是未來流通的貨幣”,是“產生信息、知識、智慧的基礎”,是“數字化生存時代的新型戰略資源”[2](P3-4),“大數據”的“大事實”已然成為社會判斷的重要依據和鮮明的時代特征。面對社會發展、科學進步和教育信息化的要求,2010年我國頒布了《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信息技術對教育發展具有革命性影響”,2012年頒布的《教育信息化十年發展規劃(2010—2020年)》稱“以教育信息化破解制約我國教育發展的難題,促進教育的創新與變革”,2016年教育部關于印發《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規劃》的通知,指出要“落實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和國務院有關‘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智慧城市等重大戰略對人才培養等工作的部署”[3],都為大數據時代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信息化提供了重要遵循。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應及時研究、提出并運用新思想、新理念、新辦法,否則理論就會蒼白無力,就會“肌無力”,馬克思主義就無法更好地指導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促進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信息化,這一重大戰略任務在互聯網時代與大數據緊密相關,將大數據融入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全過程,無疑是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掌握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堅守主流意識形態陣地和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四贏”策略。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必須抓住國家實施的大數據戰略機遇,充分挖掘大數據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潛在價值,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思維變革,從而進一步堅定人們的馬克思主義理想信念,維護我國意識形態安全。
一、認清大數據的科學內涵
“大數據”(Big Data)一詞最早由美國的未來學家托夫勒提及和使用。他在《第三次浪潮》一書中,提出大數據將在第三次浪潮中“譜寫華彩樂章”,預言“大數據”時代即將到來。最早正式提出“大數據”概念的是全球知名咨詢公司麥肯錫公司(MGI),在一份名為《大數據:創新、競爭和生產力的下一
個新領域》的研究報告中,MGI指出,在當今世界分析大數據是支撐新的生產力增長的基礎[4]。真正把大數據推向公眾視野的是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ViktorMayer-Sch?nberger)和肯尼思·庫克耶(Kenneth Cukier)合著的《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一書。在書中,舍恩伯格認為,大數據能夠“通過對海量數據進行分析,獲得巨大的產品和服務”[5](P4)。隨著“大數據”在各行各業的廣泛應用,大數據帶來的變革與日俱增、影響日益深遠。抓住大數據戰略機遇,促進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思維變革,對于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信息化,增強馬克思主義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權,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大數據,并非簡單意義上理解的大量數據。對于“大數據”概念的界定,學界莫衷一是。權威IT研究機構Gartner認為,大數據是在一個或多個維度上超出傳統信息技術處理能力的極端信息管理和處理問題[6](P142);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認為,大數據是“由科學儀器、傳感設備、互聯網交易、電子郵件、音頻視頻軟件、網絡點擊流等多種數據源生成的大規模、多元化、復雜、長期的分布式數據集”[7]。MGI對大數據的定義為:大數據是指大小超出了傳統數據庫軟件工具的抓取、存儲、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數據群[8](P5)。按照摩爾定律(Moore's Law),全球數據每年增長50%,每2年翻一番,并呈現出多源、異構、碎片化、低價值密度、實時性等復雜特征。因此,人們更多地基于大數據本身的特點,采用 “4V”或 “5V”的定義。“4V”是指大規模(Volume)、多類型(Variety)、高速度(Velocity)和低價值密度 (Value);IBM認為,大數據需要精確性(Veracity),構成“5V”特征[9]。大規模(Volume)是指大數據的體量巨大。根據互聯網數據中心(IDC)的“數字宇宙”的報告,預計到2020年,全球數據使用量將達到35.2ZB①1KB=1024B 1MB=1024KB 1GB=1024MB 1TB=1024GB 1PB=1024TB 1EB=1024PB 1ZB=1024EB 1YB=1024ZB.。截至目前,人類生產的所有印刷材料的數據量是200PB,而歷史上全人類說過所有話的數據量大約是5EB[10](P48)。當前,典型個人計算機硬盤的容量為TB量級,而一些大企業的數據量已經接近EB量級。多類型(Variety)是指數據來源多樣、類型繁多、結構復雜、多元多變。總體上分為三類,即結構化數據(以文本形式存在的便于存儲的數據等)、非結構化數據(網絡中的文字、表格、圖像、音頻等綜合數據)和半結構化數據(超文本文檔,如HTML網頁等)[11](P12)。高速度(Velocity)是大數據區別于傳統數據挖掘的最顯著特征。起源于處理網頁數據的開源Hadoop系統可容納100億條數據,如果對這些數據進行條件排列查詢,平均需要600秒以上。而經過數據結構優化的UniHadoop系統,數據分析的速度更快,同樣100億條數據的條件排列工作,只需要7秒就能完成。低價值密度(Value)是指大數據中有用數據占數據總量的比例偏低。價值密度的高低與數據總量的大小成反比。以視頻為例,一部1小時的視頻,在連續不間斷的監控中,有用數據可能僅有1~2秒。如何通過強大的機器算法更迅速地完成數據的價值“提純”成為目前大數據時代的難題。由此可見,大數據首先是指不斷呈現爆炸式增長的海量數據,常規的獲取手段和處理技術已經無法完成對數據的集成、存儲和分析;其次,大數據的低密度價值特點決定,不是所有的數據都有價值,要學會分析、整合有用的數據,打開大數據的“潘多拉之盒”,掌握規律、發現價值,才可以獲得大發展和對問題的高效解決。
在某種意義上,大數據已經成為一種新的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方法,世界的本質就是數據的集合、數據的分析與處理。特別是隨著發掘數據價值、征服數據海洋的“動力”之稱的“云計算”技術的出現,網絡社交、電子商務和信息通信等將進入以“PB(1024TB)”為單位的數據信息新時代,大數據的分析、預測和研判更具潛在價值。“大數據對于人類社會的意義在于,其具有創造新的方法、明確新的戰略框架和構建新的社會秩序的可能性。”[12]毋庸置疑,大數據作為網絡時代的鮮明特征,已滲透到國家、社會、企業甚至個人生活的各個領域,并帶來巨大的發展機遇。大數據作為一種新的技術和戰略,將促使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進入一個全新時代。
二、大數據時代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發展的戰略機遇與嚴峻挑戰
(一)大數據時代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發展的戰略機遇
“面對社會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日趨活躍、主流和非主流同時并存、社會思潮紛紜激蕩的新形勢”[13],要促進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與時俱進,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必須將大數據融入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全過程,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數字化和信息化。抓住這個戰略機遇,不僅面臨理論難題,而且面臨實
踐難題。只有進行科學理性地分析,找到二者的戰略契合點,才能發揮大數據本身優勢,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思維變革。
首先,大數據搭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數字平臺。大數據的開放性和共享性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搭建了數字平臺。一方面,互聯網、“云計算”等信息技術提供的便捷共享手段,使隨處可見的電腦、智能手機、攝像頭及其他信息采集設備和存儲設備將海量數據置于網絡公共空間,為開放教育資源和分享教育信息提供了數字平臺。另一方面,大數據技術搭建的數字平臺具有虛擬性的特點,使人人可以隱藏自身的真實身份,反而消除了在現實世界中的戒備心理,更容易袒露內心的真實想法。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者來說,可以借助大數據技術分析和研判受教育者的真實思想,并較為準確地把握他們的思想動態,有助于增強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針對性。此外,大數據的可視化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傳播的數字平臺更具形象性和直觀性。大數據的可視化是指將數據以視覺形式呈現出來,如圖像、圖表或地圖等,可視化數據方式可以充分展示數據的模式和趨勢等,幫助人們更形象直觀地了解數據的意義,揭示事物發展變化的趨向。數據的可視化既可以是靜態的,也可以是交互的。像傳統的圖表、地圖等是靜態的可視化數據,而Flash動畫、GIF動畫等則是動態的可視化數據。比如,美國按年齡段進行的人口百分比統計,就是采用動態方式呈現單一數據的典范。Pew Research將美國各個年齡段的人口比例制成GIF動畫,直觀展示了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各個年齡段人口百分比的動態變化。這種可視化的數據可以將內容復雜的故事和數據信息做成一個簡單的Package。這樣的“微內容”適合在社交網絡上傳播、在微信朋友圈中分享以及在網絡博客上嵌入,擴大了信息傳播的范圍,實現了傳播的廣覆蓋,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提供了直觀形象的數字平臺。
其次,大數據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信息資源。小數據時代,受到數據信息處理的技術水平限制,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資源有限。大數據時代,教育資源可以依托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技術存儲于“云空間”。無論文本、視頻、音頻、Flash動畫等,只要輸入關鍵詞,就能快速高效查找。而對于圖片資源則可以采用“意象化感悟”法快速找到。即根據教育需要形成所需要的具象,以關鍵詞命名具象形成意象,然后在搜索欄中輸入關鍵詞,就可以快速鎖定需要的圖片資源范圍,進行優選。大數據為豐富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資源提供了技術支撐。第一,大數據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資源的數據來源更加多樣化。大數據的多樣性和包容性強,可以調動一切學習主體的積極性,參與開發無限的教育資源。目前的微課、慕課、翻轉課堂等都是有效嘗試,不僅形式多樣,而且極大豐富了教育的資源。第二,大數據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資源更具全局性。比爾·弗蘭克斯指出:“當你在處理大數據時,你并不僅僅是拿到了一堆數據而已,大數據正在以復雜的格式,從不同的數據源高速地朝你奔涌而來。”[14](P5)大數據通過網絡終端源源不斷地生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提供了全方位、原生態、全程化的數據源,這些數據承載了受教育者真實可靠的學習理念和學習行為方式等,是一種全新、全局性的數據源。第三,大數據提高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資源利用率。大數據時代,對受教育者學習信息的收集不僅僅局限于“點擊率”“下載量”等。隨著“云計算”和物聯網的發展,每個唯一的IP標識都可以將信息時刻與互聯網緊密相連。所有傳輸而來的數據都可能成為整個馬克思主義教育資源系統的組成部分,通過對海量信息的相關性分析,預知教育狀況,及時調整輸出,從而更好地利用教育資源,使其價值最大化。
再次,大數據拓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受眾范圍。大數據時代,移動終端隨時隨地將海量數據源源不斷地上傳,大數據的規模和范圍空前擴大。大數據之“大”,不僅僅在于“規模之大”,更在于價值之大。通過對海量數據的整合與分析,挖掘和發現新的價值,從而帶來大知識和大發展。大數據以難以量化的規模覆蓋了人們生活的全部領域,人們通過各種數字終端設備將海量的語音通話、圖像傳輸、視頻點播、文字輸入、GPS定位等數據信息,源源不斷地匯集到大型的網絡社區和信息中心,匯聚成大規模的數據群。眾多的網絡時評、商業促銷、科技創新、“心靈雞湯”等通過兩微一端(微信、微博、手機客戶端)等方式廣泛傳播開來,使每個人都成為信息的傳播者和接受者,不僅拓寬了人們接受數字信息的渠道,也拓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受眾范圍。此外,大數據提供的數據是全方位的,能夠兼顧到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各個層次。大數據改變了傳統教育的“你講我聽”的單一接收方式和整齊劃一的教育內容,使教育內容的傳播渠道更廣、內容更豐富、形式更多樣。通過匯總海量數據,分析各個層次受眾的接受能力、習慣和偏好,按分類向受眾推送相應形式的內容,從而兼顧各類受眾,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受眾更廣。
最后,大數據增強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
傳播效果。大數據時代,“兩微一端”等數據平臺的普及,在融合與提升傳統傳播方式的優點基礎上,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低成本、廣覆蓋、快傳播,教育宣傳效果明顯。首先,大數據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精準傳播。通過大數據分析,按照不同標準把受教育者分成不同的群體或個體,實施精準教育。比如按年齡將受教育者分成青少年、中年和老年等幾個層次,或者按照身份不同將其分成學生、工人、農民、公務員、教師等不同類型。根據不同受教育者的特點進行分層或分類傳播,能提高傳播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其次,大數據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傳播的大眾化。大數據時代,信息傳播的渠道更加多元、信息量更大,從傳統的科層式結構過渡到扁平網絡化結構,自媒體終端上的每個人都成為信息傳播的節點,信息傳播更加精細化,傳播門檻降低,受教育者作為信息的接受者,也可以作為信息的制作者和傳播者參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全過程,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傳播更加高效、快捷、平民化,有利于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第三,大數據提高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傳播的時效性。大數據的及時性使信息傳播具有巨大的速度優勢,各種數據信息通過四通八達的信息高速公路隨時隨地傳遞給受教育者,使他們可以通過及時的、泛在的學習獲取知識、聆聽教誨,克服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覆蓋面小、形式單一、時效性低等弱點。第四,大數據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雙向傳播。大數據的交互性特點,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傳播實現了雙向互動。一方面,受教育者根據自己的個性化需求選擇相關的教育信息和服務,通過自媒體終端等傳遞需求信息給教育者;另一方面,教育者借助網絡平臺收集和分析受教育者的個性化需求,比如,通過分析被搜索關鍵詞的熱度、相關關鍵詞及搜索人群的屬性等,采取針對性的傳播策略,有的放矢地對不同的受教育者進行教育,從而避免信息不對稱帶來的教育偏差,易于使受教育者形成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正確認知,在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上“入腦入心”,增強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傳播效果。
(二)大數據時代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發展的嚴峻挑戰
應當看到,除了上述戰略機遇外,大數據也給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帶來了嚴峻挑戰,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整體環境遭遇深刻變遷。一是擠壓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空間。大數據時代海量信息通過各種自媒體終端實時不斷涌現,滲透到人們生活、學習和工作的各個角落,使網絡信息極度多元。歷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普世價值”、民主社會主義等社會思潮充斥網絡空間,各種思潮之間的博弈愈演愈烈,價值觀和文化滲透交織、真假難辨。這些消極落后甚至反動的信息肆意流傳,不僅影響甚至顛覆了人們的主流價值觀,更是使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從而在學科中“失語”、教材中“失蹤”和論壇上“失聲”,嚴重擠壓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空間。二是挑戰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權威。大數據時代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資源從傳統的黨政宣教部門、輿論傳媒機構和高層理論學者向網絡傳媒大亨、網絡意見領袖和網絡自媒體終端轉移,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海量數據混亂雜陳的遭遇中“迷茫”甚至“失語”,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受到挑戰。加之西方發達國家憑借大數據技術優勢,通過網絡大肆傳播西方文化,潛移默化地進行價值觀滲透,甚至抹黑中國,使廣大青年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扭曲,理想信念動搖,民族認同感淡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被誤解、被扭曲、被玷污中,其權威遭遇嚴重挑戰。三是顛覆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傳統方法。大數據的交互性使信息的獲取和發布更加便捷,信息發布人人可為。網民的平等意識增強,數字平臺提供的雙向互動、平等對話的橫向無中心交流模式,賦予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開放性和平等性。人們不再僅僅被動接受單向的理論“灌輸”,不再無意識地追隨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者的權威闡釋,教師權威削弱,從而使自上而下的單向“灌輸式”教育方法被顛覆,不能適應新的變化,而開放式、自主式、互動式、立體式的教育方法成為主流。
三、大數據促進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思維變革的路徑選擇
“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教育需要根據現實變化而變化。大數據時代移動互聯網、“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科技在改變了人們思維方式的同時,搜索引擎、電子書包、社交網站、慕課、私播課、智慧教室、云課桌等也深刻改變了知識傳播和教育共享的方式,從而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生態環境發生了深刻變遷。對此,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不僅要有“清醒的理論自覺”“堅定的政治信念”,更要有“科學的思維方法”。
按照舍恩伯格的說法:“所謂大數據思維,是指一種意識,認為公開的數據一旦處理得當就能為千百萬人急需解決的問題提供答案。”[5](P167)從本質上
講,大數據思維是一種復雜的數據化的整體思維,“它通過‘更多’(全體優于部分)、‘更雜’(雜多優于單一)、‘更好’(相關優于因果)等思維理念,使思維方式從還原性思維走向了整體性思維,實現了思維方式的變革”[15]。大數據的“5V”特征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提出了整體性、多樣性、動態性、開放性、平等性、相關性和交互性等新思維要求,這些思維通過智能終端、云計算、物聯網等傳播而體現。“就像望遠鏡能夠讓我們感受宇宙,顯微鏡能夠讓我們觀測生物”[5](P9)一樣,大數據思維使人類可以打破哲學社會科學曾經難以數據化的困境,像自然科學一般實現定量研究,使人類行為和人類社會的數據化測度成為可能,促進了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有機統一,從而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思維變革成為現實。
(一)大數據促進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整體性思維變革
大數據以其全局性、多樣性、及時性和相關性等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提供整體性思維。一是利用大數據實現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全局性把握。大數據思維方式以全局性為前提,以事物的相關性為思維切入點,在多樣性事物的相關性中及時把握事物的存在狀態和發展方向。大數據以教育數據信息的全貌為研究對象時,能夠較為全面和準確地反映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整體情況和發展趨勢,實現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全局把控。二是利用大數據增強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各要素之間的關聯性。傳統的教育在把握各個要素之間的關系時采用抽樣調查的方法,關注的是因果關系,而大數據卻以整體數據為研究對象,注重數據之間的關聯性。因而有利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進行深入考量,把握各個核心概念及相關關系,從而體現整體性。三是利用大數據促進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協同性。隨著大數據信息處理技術的不斷升級,馬克思主義教育理念的秉承、學習場景的變幻、教育情境的設計、教育數據的采集、挖掘、分析、處理等,在“云計算”、物聯網和大數據的技術支撐下都成為可能。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如果注重了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并分析了教育信息化的發展和演進軌跡,便能實現整體性思維變革。
(二)大數據促進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多樣性思維變革
一是利用大數據優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選擇性。在信息激增、知識爆炸的大數據時代,受教育者面對海量的信息往往無從選擇,增加了學習的盲目性。利用大數據技術可以充分挖掘和深入分析教育實踐活動中產生的半結構化和非結構化數據,包括文本、圖片、視頻、音頻等,將其轉化為結構化的多維數據或關聯數據,然后利用快捷、高智能化的數據信息處理軟件(如SPSS、NCR等)進行高效處理,發掘教育數據背后潛藏的關聯性、規律性的信息,提高教育數據信息的附加值。根據這些教育數據所反映的需求信息,結合教育目標相關數據鏈,對不同層次、不同群體甚至不同個體的對象進行針對性挖掘,在眾多的教育方案中找到各自的“最佳方案”。二是利用大數據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針對性。大數據技術的運用,可以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針對多樣化的受眾群體或個人精準發力。以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由于條件限制往往千篇一律、大水漫灌、針對性差。借助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可以根據受眾的特點和需要推送相關學習數據信息,量身定制學習方案,提高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的針對性。三是利用大數據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個性化。舍恩伯格等認為,大數據帶來的改變之一就是“我們可以實現迎合學生個體需求的,而不是為一組類似的學生定制的個性化學習”[5](P104)。大數據使“因材施教”得以更好地實現,大數據主要通過反饋、個性化和概率預判促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個性化教育。利用大數據技術支持,通過全程化和立體式記錄和跟蹤,從而掌握受教育者的學習特點、學習進度、學習需求和學習風格等,為他們量身打造個性化的學習方案,并隨時調整教育的內容、方法等,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針對性,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多樣性的思維變革成為可能。
(三)大數據促進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動態性思維變革
一是利用大數據增強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預見性。大數據分析的關鍵就是即時性和可預見性,可預見性是對數據進行實時分析和挖掘的核心價值所在,比如“預測股市走向”“預測疫情變化”“預測消費動向”等。大數據技術對已有的信息進行價值挖掘,建立預測數據模型去預測未來,用以輔助決策。運用可預見性,可以提前預知教育的過程甚至結果,及時發現問題,及時糾正和改進教育方案,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全程科學化和數字化。大數據的及時性和可預見性特點,促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實現動態性思維變革。二是利用大數據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全過程的動態監控。基于即時性和相關性基礎上的動態性特點,綜合運用
多種技術和方法,對教育大數據進行處理和分析,“通過數據建模,發現學習者學習結果與學習內容、學習資源和教學行為等變量的相關關系,來預測學習者未來的學習趨勢”[16]。甚至可以針對不同受教育者之間的差異,制作成動態化數據,讓受教育者作為自我教育的參照,直觀地了解自己在學習中的行為、習慣、時間等方面與他人的不同,通過動態比較和分析,較為客觀和全面地評價教育的結果。三是利用大數據把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發展趨勢。大數據技術的可視化將數據信息更加直觀、動態和藝術化地表現出來,使數據更具說服力、感染力和震撼力,如“4分鐘看完世界5500年版圖演變”就是大數據可視化的動態呈現,能提高學習效率,教育效果明顯。大數據技術的可視化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動態性思維轉變成為可能。大數據可以根據受教育者的點擊、轉載、評論、分享等數據信息來量化教育的走向和趨勢。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動態性特點,使教育更具科學性和針對性。四是憑借大數據促進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發展的持續性。包含各種APP學習軟件的“電子書包”使隨時隨地的動態學習成為可能。大數據根據受教育者的學習情況形成學習行為動態數據,將大量實時變化的數據通過電子書包的分析軟件對不同的數據信息進行實時處理,在掌握受教育者思維變化規律的基礎上,為個性化、多元化的后續學習提供技術支持。
(四)大數據促進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開放性思維變革
一是樹立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大數據分享理念。大數據時代互聯網的核心理念是分享,“百度分享知識,微博分享信息,微信分享友情,阿里巴巴分享購物”[17]。數據分享為網民提供學習、娛樂的數據平臺,比如社交網站、QQ空間、朋友圈等;為企業盈利提供數據空間,比如京東、亞馬遜等。人們在免費獲取知識信息,接受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同時,可以隨時隨地將知識共享出去,“贈人玫瑰,手有余香”。鼓勵專門的技術隊伍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者,成為大數據時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分享學習的排頭兵,促進分享學習更加專業化、制度化、數字化。二是利用大數據促進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泛在性。大數據的開放性使得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資源呈現全球化、智能化、大眾化、可視化、動態化、泛在化等特點。數據的開放性引起的“數字海嘯”悄然改變了傳統的教學方式,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課堂,電子書包、云課堂、云課桌、慕課等數字平臺為泛在學習提供了技術保障,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泛在性成為可能。特別是全息技術的情境化藝術化教學、私人訂制的個性化方案、娛樂游戲化的隨堂測驗、智能化動態化的互評機制等使泛在學習更具趣味性,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打破時空界限,更具開放性和包容性。2014年9月,為滿足學生個性化、及時性、交互性學習的需求,清華大學利用慕課平臺“學堂在線”,推出首門思政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將網絡學堂作為豐富教學資源、深化師生互動的重要載體,吸引了上萬名校內學生和校外人士在線選修,并作為高校思政課信息化教學的經驗加以推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泛在學習的典范。三是利用大數據增強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競爭力。大數據時代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面臨的國際化、全球化的競爭加劇。充分挖掘和分析各種在線教育平臺積累的海量結構化(測試成績、統計數據等)和非結構化數據(文本、圖表、音像、超文本、超媒體等),促進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開放性思維變革,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在競爭激烈的生態環境中,保持開放性和活力、增強競爭力并脫穎而出的必要途徑。
(五)大數據促進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復雜性思維變革
首先,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本身是一個復雜的動態變化系統。一方面,受教育者在大數據時代的線上線下活動,都可以通過復雜的數據計算來傳輸和展示,而且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認知、認同、情感、體驗等都需要依賴復雜的計算來掌握。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不再是傳統教育的簡單“灌輸”模式,而是一個多樣性、動態化、開放性的復雜系統。受教育主體更加多元化和復雜化,利用大數據技術分析各個群體甚至個體的思想特點、學習習慣、接受規律和發展要求,真正做到“入腦入心”,這就需要調動各種教育主體的積極性,最大限度地開發各種顯性和隱性教育資源,使各部門突破“信息孤島”和“數字藩籬”,加強協同合作,這本身就是一項艱難復雜的系統工作。其次,利用大數據促進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評價的多樣化和復雜化。教育評價將從“經驗主義”、單一維度走向“數據主義”、多元維度。一是教育評價的方式更科學。大數據支撐的教育評價不再是經驗式的,而是可以通過大量數據的科學“歸納”,從而反映出教育活動是否符合客觀規律。二是教育評價的依據更多元。可以對學生進行多元評價,比如參照學生的出勤率、互動率、作業正確率等各方面表現,而非傳統意義上僅僅借助于學科考試成績和教師主觀感受來評價。
教育評價的途徑不再是傳統意義上通過經驗而獲取,而是依靠大量數據的歸納與整理,在此基礎上找出規律,為實現教育的評價與優化之間的良性循環提供依據和參考,從而避免傳統評價方式的“證據片面性”。三是教育評價的過程更科學。教育評價跳出了結果評價的窠臼,實現過程性和動態性評價。綜合運用信息科學、社會學、計算機科學、心理學等理論和方法,對教育大數據進行科學地處理和分析,去評估學習行為,揭示教育規律,為學習者提供人為的適應性反饋。第三,以復雜性思維積極應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面臨的挑戰。一方面,是應對我國教育大數據技術短板的挑戰。包括教育數據處理和分析技術,教育數據采集技術和問題解決分析技術,以及教育數據兼容性的挑戰等。另一方面,是應對我國教育大數據人才缺乏的短板挑戰。MGI曾預測美國到2018年需要深度數據分析人才44萬~49萬,缺口14萬~19萬人;需要既熟悉本單位需求又了解大數據技術與應用的管理者150萬,這方面的人才缺口更大[18]。中國是人才大國,但能理解與應用大數據的創新人才特別是教育領域的數據型人才更是稀缺。包括進行大數據分析的資深分析型教育人才,精通如何申請、使用大數據分析的教育管理者和分析家以及實現大數據的技術支持專門人才。應當看到,我國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面臨國際國內的復雜形勢,其中教育大數據技術及人才的短板,是目前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面臨的復雜難題。只有具備高水平的專門人才和數據分析處理技術,才能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中,運用大數據復雜思維提高數據采集和問題的分析解決能力,增強復雜多樣數據之間的兼容性,應對復雜挑戰,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資源的開放共享。
大數據時代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思維變革,是一項極其復雜而繁重的任務,要加強頂層設計,統籌各方面力量協同推進。從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決策者、實施者、管理者到一線教師和受教育者,都將面臨教育理念、教育內容、教育技術、教育方法和教育評價等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大數據時代,誰掌握了教育大數據,實現了教育的大數據思維變革,誰就掌握了教育的未來。大數據并不神秘,大數據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思維變革,將會促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在除舊迎新中積極探索華麗的數字化轉型。而只有遵循教育規律,充分挖掘教育數據背后的價值信息,才能使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更加趨向于本真。正如上海思來氏信息咨詢有限公司創始人張韞所說,“大數據時代的到來,讓社會科學領域的發展和研究從宏觀群體逐漸走向微觀個體,讓追蹤每一個人的數據成為可能,從而讓研究每一個個體成為可能。對于教育研究者來說,我們將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發現真正的學生”[19],而這正是教育的進步。
[1]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05-19.
[2]陳潭等.大數據時代的國家治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3]教育部關于印發《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規劃》的通知,[EB/OL].http://www.ict.edu.cn/law s/new/n20160617_3-4574.shtm l,2016-06-07.
[4]M cKinsey Global Institute.Big Data: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Competition,and Productivity[EB/OL]. http://www.m ckinsey.com/insights/business_technology/ big_data_the_next_frontier_for_innovation,2011-03-10.
[5]V.M.舍恩伯格,K.庫克耶.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M].盛楊燕,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6]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國產業的歷史性機遇[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14.
[7]王超.大數據時代我國意識形態安全探析[J].學術論壇,2015(1).
[8]郭曉科.大數據[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
[9]付安玲,張耀燦.大數據助力網絡意識形態治理及提升路徑[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6(5).
[10]朱小翠.輿論的隱喻引導與組織認同[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
[11]李海生.知識管理技術與應用[M].北京:北京郵電大學出版社,2012.
[12]付玉輝.大數據傳播:技術、文化和治理[J].中國傳媒科技,2013(3).
[13]習近平.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04-26.
[14]比爾·弗蘭克斯.駕馭大數據[M].黃海,車皓陽,等,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13.
[15]黃欣榮.大數據時代的哲學變革[N].光明日報,2014-12-03.
[16]徐鵬,等.大數據視角分析學習變革[J].遠程教育,2013(6).
[17]曹峰.借助互聯網思維 創新宣傳思想工作[J].紅旗文稿,2016(1).
[18]鄔賀銓.大數據時代的機遇與挑戰[J].求是,2013(4).
[19]易鑫.教育如何玩轉大數據[N].中國教育報,2014-03-24.
[責任編輯:陳梅云]
付安玲,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北京 102488;張耀燦,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 武漢 430079
A8
A
1004-4434(2016)10-0169-07
2016年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基于信息空間的國家主權理論研究”(16AKS006);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體關系研究”(13AKS011);山東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計劃(思想政治教育專項)一般資助項目“新時期高校思政課教師意識形態話語權的挑戰與應對研究”(J15YB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