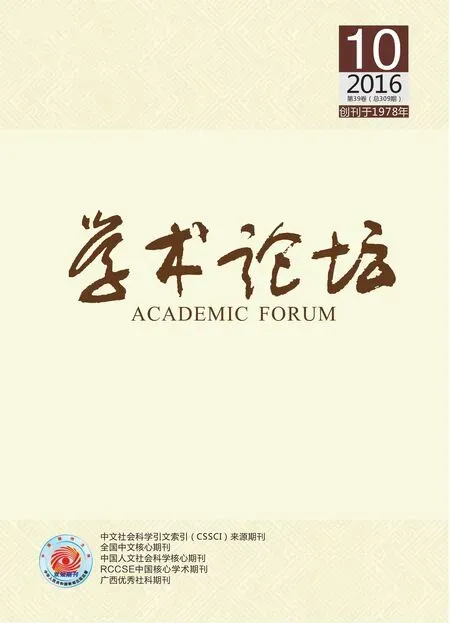高等教育治理的探新與圖治
左崇良
高等教育治理的探新與圖治
左崇良
由于歷史、文化和制度方面的原因,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的發(fā)展深陷多重困境。高等教育治理的探新,需要借鑒國內外的治理理論,在全面細致的剖析之后對其進行取舍,并將之應用于高等教育的宏觀治理和微觀治理。高等教育的革新圖治,需要重建高校與政府之間的權責邊界,通過學術規(guī)范的制度建設和學術道德的文化建設等舉措來保障和維護學術權力。
高等教育治理;學術權力;學術道德;學術規(guī)范
高等教育治理是21世紀的一個關鍵政策問題,是各國高等教育的共同追求。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使得政府總在想方設法推動各種法律政策及其影響,不斷加強高校的外部質量保證。與此同時,高校在力爭自主權和維護法人地位方面也在努力作出新的嘗試。
一、高等教育發(fā)展過程中的矛盾沖突
在現代社會中,高等教育呈現出很大的復雜性,內部出現分化,外部聯系增加,高等教育內部不同利益集團的沖突,以及這些集團和外部集團的斗爭,都在持續(xù)加強。在高等教育的外部關系中,政府、市場、社會與高校四者之間存在明顯的權力博弈;在高等教育的內部關系中,學校與學校、學校與院系、學術與行政、師生與大學管理者之間也有矛盾沖突。
(一)政府對高校的過度干預
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國政府開始加強對高校的干預。在新管理主義的影響下,政府制定出許多評估政策,按照績效來分配公共經費,監(jiān)控高校經費的使用,等等。長此以往,政府的管理模式與程序逐漸滲透進入高校管理之中,使高校的管理與政府的管理趨同。哈羅德·珀金 (Harold J·Perkin)有言:“當大學最自由時它最缺乏資源,當它擁有最多資源時它則最不自由。”[1](P24)這句話辯證地說明了大學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困境。在我國,高等教育原本就有很強的官本位文化,當下政府干預的加強使得高校難以真正做到自主發(fā)展。
我國高校不同于西方大學,權力結構的演化屬于一種強制性制度變遷,政府在高等教育治理體系中處于核心地位。政府對高等教育的過度干預,不可避免地會造成高等教育的官僚化和高校管理的行政化,從而扼殺學術的活力。國家確定的“副部級”大學及其待遇,以及其他各種按照行政級別所進行的資源分配,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對高校的行政約束。我國高校辦學自主權之所以反復落入“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怪圈中,原因在于“放”和“收”的都是行政權力。我國高等教育的學術體制被納入了一個非學術的權力體制之中,而這個權力體制的強大程度遠超過學術體制本身,其內在的解構力量極為有限。因此,不只是學術,就連職稱評定制度、學術獎懲制度、科研基金發(fā)放制度等,都存在嚴重的非學術化傾向。
我國高校長期在一種高度集權的行政體制中運行,必然形成以行政約束為主導的運作機制,使高校隸屬于行政機構或演變?yōu)樾姓M織,由此引發(fā)一個嚴重后果:層次過多,機構臃腫,嚴重地影響到高校的辦事效率與工作質量。
(二)高校行政權力對學術權力的約束
在復雜的外部環(huán)境中,高校內部管理正在經歷從傳統(tǒng)的學院精神向經濟理性轉化,管理超越了學術而成為高校應對激烈競爭的動力源泉。十幾年來,我國高校規(guī)模的快速擴張,使得高校變得更加擴散、不透明、無凝聚力。在高校內部權力結構中,行政權力的強大與學術權力的虛弱形成了鮮明對照。
我國高校的行政權力還在繼續(xù)膨脹,而學術權力不斷受到侵蝕,這樣就出現了主體倒錯。高校是人才培養(yǎng)的場所,高校的主體本應是教師和學生,行政人員是為教學科研服務的。現在的情況是行政人員成了學校的第一主體,教學科研人員則處于弱勢和附屬地位。高等教育的資源通常是按照權力位格分配,因此,許多高校領導的最大目標就是升格,想方設法提高學校排名。為了滿足高校排名所需的各項指標,學校調整發(fā)展方向,進行各項測評。這需要大量增加行政人員,行政人員為了應對評審,分配給教師各種任務,要求教師參加大量會議和填寫表格。在這種安排中,行政人員數量增加并擴權,從而進一步助長了衙門作風。我國高校職能部門占有過多的學校資源,擁有過大的權力,它們更多的是在為領導工作,對領導負責,而將基層學術組織視作下屬機構,將教師視作被領導者。
從制度的層面來看,我國高校從未真正建立起學術權力,學術權力嚴重依賴于行政權力。同時,這種狀況也普遍地存在于高校內部的委員會和評議組織中。例如,職稱評定機構、課題評審委員會等,這些都反映了我國高校行政權力對學術權力的制約。在行政化的環(huán)境中,國內高校難以產生真正推動社會發(fā)展的學術思想,難以培養(yǎng)出具有創(chuàng)新思想和批判精神的人才,自然難以躋身于世界一流大學之列。
(三)高等教育的學術失范
高等教育的學術失范分為兩個層面:一為技術層面,即作假、抄襲、賄賂、功利炒作等表層現象;另一為精神層面,即深層次的道德失范。在外部已被格式化的社會中,我國高校學術的自主性與自律性程度低下,學術共同體內部缺少規(guī)范甚至難以建立自身規(guī)范。
通過國際比較我們發(fā)現,國內大學教授的商業(yè)行為與國外的最大不同就是,國內教授多是腳踏兩只船,既是教授又當“老板”,而且多是依賴學校的資源,研究生則成為教授的打工者。無疑,教授兼“老板”的雙重身份會導致學術商品化,這不僅使得昔日圣潔莊重的學府,演變成各種以營利為目的的“學店”,導致大學校園彌漫浮躁的學術氛圍,從而引發(fā)學術失范,而且使一些教授漸漸失去了專業(yè)研究的興趣和能力,同時也失去其早年建立起來的社會道德感和批判精神。專業(yè)研究能力的缺失,將會誘發(fā)高校教師萌生學術權威地位是否合法的情緒體驗,產生“學術動機不良”和“偽學術”,高尚的學術研究發(fā)生了蛻變。
學術活動的過度商業(yè)化和學術失范,不利于高等教育的持續(xù)發(fā)展,不利于學術生態(tài)圈的建設,這一點我們必須警覺。如果大學失去了守望社會的職能,不能給人類以終極關懷,甚至異化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另類機構,也就失去其獨立存在的價值。高等教育的學術失范,引起了我國教育決策者的關注。出于對“學術失范”的一種無奈的補救,近年來學術界開始強調“學術規(guī)范”,可收效甚微。這是因為,這種“學術規(guī)范”只是注重外在的形式化規(guī)范,如標點符號、引文注釋、摘要的“細則要求”,而內在的實質性規(guī)范難以建立。
(四)高等教育的學術腐敗
學術腐敗是我國高等教育最受社會關注的問題之一。由于官學一體的制度安排,我國高校學術生態(tài)圈中還出現了價值倒錯。一些校長到任后秉持上行下效的教育行政慣性力量,只對上級行政部門負責,這表明校長蛻化為官僚。一些教師放棄自己的學術追求,將其主要行為轉為官場的逢迎。一些頗具學術潛力的教師,為擺脫清貧和受冷落的狀況,為了以后能享受某級待遇,開始調整思路而躋身官場,他們把大量精力耗費在官場的吹拍中,這是當今大學的悲哀。學者官員化,非其所愿地寄生在一種既無壓力又無動力的異質環(huán)境中;官員學術化,一些毫無學術根基的高校管理人員利用自己的職權謀取學術地位,控制著學術資源,學術科研變味走調,高等教育的本質出現異化。
學術腐敗現象在我國泛濫成災,有體制和文化方面的原因,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學術界官本位盛行,學術評價被當權者控制,很難有正常的學術批評。權與錢在高等教育領域的聯姻是產生學術腐敗的根源。由于歷史和文化的原因,我國高等教
育長期運行于一種受“政治化”與“經濟化”框范的秩序之中,在價值取向上搖擺不定,時而追求“教育政治化”,時而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高等教育的發(fā)展缺乏相對獨立的學術運行邏輯和學術價值追求。高等教育領域,“為學術”的非學術活動猖獗,學術被錢權污染,“學術泡沫”越吹越大。
二、高等教育治理的理論探新
高等教育治理是一個復雜而模糊的對象,要想使該領域的研究更加全面而系統(tǒng),就得對高等教育的發(fā)展困境作出認真而嚴肅的反思,對國內外的治理理論進行深入探析。
(一)黑格爾的國家干預理論
古典學術自由觀認為,學術自由作為一項絕對權利,排斥任何形式的社會干預。這種觀點旨在強調學術自由權的正當性,但其本身是有缺陷的。黑格爾的國家干預理論認為,學術自由是一項絕對權利,這是啟蒙時代的觀念,在近現代社會,要求公權力退出大學既無必要也不可能。
黑格爾的國家干預理論,對中國問題有它的適切性,他的學術自由和法治憲政的思想切中了中國問題的要害。高校自主辦學是保護學術自由的重要機制,在此機制下,大學可在與學術自由相關的范圍內行使相應的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宏觀上高等教育的法治對高校自主權的落實也有保障和規(guī)范作用。
(二)利益相關者理論
利益相關者理論是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一種治理理論,是西方經濟學家在研究公司治理時提出的一種理論主張。之后,利益相關者理論被廣泛應用于研究社會組織的權力與責任等。利益相關者理論認為:利益主體的多元化意味著利益的分化,利益主體的訴求不同,各種利益易產生沖突,決策時需要注重多元參與,加強協(xié)調和妥協(xié)。
高等教育治理改革可以借鑒利益相關者理論,重視利益相關者的共同治理,加強外部利益相關者對高校的監(jiān)督,強化內部利益相關者的權力制約和平衡。治理意義上的“利益”,包含了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的內容。對組織而言,利益是組織運行必不可少的各種物質、精神條件和環(huán)境的總稱,是組織賴以存續(xù)和發(fā)展的根本;對于個人而言,它是個體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上的各種需求。利益主體的行為目標和組織的運行動力就是對自身利益的不懈追求。
(三)法人治理理論
大學治理的前提是大學法人實體的存在,法人治理理論為高等教育的微觀治理及其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法人是法律中的概念,是指與自然人相對應的民事主體,是法律關系中的主體。法人是法律所賦予的人格,其本質特征有二:一是它的團體性,二是它的獨立人格性。用最精煉、最概括的語言給法人下一個定義:法人,即團體人格。
法人制度是近現代民法史上一項極為重要的法律制度。“法人制度的出現純粹是經濟發(fā)展的需求導致法律技術進步的結果,是一種經濟生活的客觀現實與法律技術運用相結合的產物”[2]。法人概念的出現,體現了立法者的價值取向。在現代法治國家,除了作為“自然人”的人外,法律還認可某些社會組織的法律人格。同樣,高校法人地位的確立,可在制度上保障高校自主權的獲得。
(四)“合作網絡”治理理論
網絡治理理論是一種嶄新的治理理論,是社會法學的最新成果,其科學的區(qū)分和網絡的建構適合對高等教育的復雜系統(tǒng)進行精細的研究。“合作網絡”治理理論不僅推出了高等教育“合作治理”的觀點,而且提出了高等教育“良好治理”制度框架。
網絡治理理論的核心觀點是:“治理是政府與社會力量通過面對面的合作方式而組成的網絡管理系統(tǒng)。”[3](P232)公共治理是一個多主體組成的合作網絡,存在著政府部門、私營部門、第三部門、公民個人等參與者,治理的目標是共治和共贏。高等教育領域各主體之間存在權力依賴性和合作伙伴關系。高等教育治理實質上是一種合作管理,一種以公共利益為目標的社會合作過程。
三、高等教育的革新圖治
我國高等教育已初步具備治理的社會基礎,多元權力主體并存的社會關系網絡基本形成,民主、協(xié)商和合作價值日益凸顯。因此,可在高等教育政策的框架范圍內探索高等教育治理的可行途徑。
(一)高校與政府之間的權責邊界
高校自主與教育行政是一對相互關聯的范疇。教育行政為高校自主辦學提供法律、資金等全方位的保障,通過政策法規(guī)這一制度中介作用于高校。政府對高校具有管理的職能,但政府不能因此而任意干涉高校的行政和學術事務,高校也不必為迎合政府而對之言聽計從,而應依法行政。高校與政府
的這種關系,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東西方概莫能外。當前,國內高校要爭創(chuàng)雙一流大學,就必須要有更高的學術追求,追求卓越的學術理想與競爭態(tài)勢,并通過章程建構相對獨立的自治機制,國家和政府為其創(chuàng)設宏觀上的制度環(huán)境,提供法律制度上的保證,克服行政權力的約束與直接干預。
高校與政府的邊界重建,基于以下兩個基本原則:其一,學術自由不能沒有限制,政府以公權力來限定學術自由的范圍;其二,公權力對學術自由的干預不能無邊界擴展,應為學術活動保有一塊不受侵犯的自由領地。我國《高等教育法》賦予高校以辦學自主權,可公辦高校依舊面臨著過多的行政干預。因此,如何劃分政府與高校之間的權責關系,以促成兩者之間的合作,就成為高等教育宏觀治理結構層面所要解決的問題。為確保學術組織的純正性,必須參照我國的相關法律架構,由立法機構制定“大學法”或“高校組織法”,規(guī)定高校的目標,解決好高校辦學與發(fā)展的權利與責任問題,規(guī)定高校作為法人機構的各種權利、管理機構的設置及行政職位的構成等。在此基礎上,各高校進一步制定具體化的細則。
基于高校學術組織特性的準確認識,對高等教育系統(tǒng)的權力要素進行精細分解和準確定位。教育行政機關依法享有規(guī)劃和指導高等教育的權力,履行監(jiān)控和協(xié)調高等教育的職責;高校依法享有辦學自主權,自主權以學術自主為核心,并以服務于學術發(fā)展為目標導向,高校負有建設學術組織的使命與責任。高校擁有管理其內部事務的自主權,但同時必須有明確和透明的責任制,向政府、教師、學生和整個社會負責。因此,以共同利益、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為基礎的合作伙伴關系應成為改革高等教育的主要方式,高校與政府結成伙伴關系與聯盟。
(二)學術權力的保障與維護
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要旨,是通過一整套完備的制度來保障學術權力,建立良性互動的大學治理結構。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不可避免會出現沖突,學術權力的維護須有一種邊界意識,因為兩者的沖突不僅以邊界存在為前提條件,而且沖突本身有助于建立和維護沖突群體的身份邊界。學術權力并非外部賦予的,而是學術自身的內在要求。學術權力作為一種判斷真理的權力,在中世紀大學就已產生。相對而言,大學的行政權力是后生的,是依附于學術權力而產生的。但在中國,現代大學是從西方引進的,權力的演化途徑與西方大學相反:先有行政權力,后有學術權力,而且行政權力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學術權力來自于行政賦權是我國高等教育權力結構的顯性特征。在大學組織中,學術權力的取向是自由,行政權力的取向是秩序,正是自由與秩序的沖突導致了學術與行政兩者關系的緊張。
學術權力的維護,不僅依賴于法律保障,還依賴于大學的制度革新。從法理上講,學術權力是以憲法保護的學術自由為法律依據的,故學術權力的行使必須堅持學術獨立和學術自由的原則。學術權力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源于學科專業(yè)能力,而不是源于官位和組織。在劍橋,有一種書籍被稱為“永恒之書”——數百年來劍橋積累下來的繁瑣的校規(guī),清晰地界定著劍橋人的一舉一動,不可改變。校長治校、教授治學,是現代大學的共同特征。可在我國公辦高校,校長很難改變董事會成員的選擇程序。學術委員會和教授會,是高校的學術組織,具有決策權力,通過良好的制度設計,可發(fā)揮學術權力在治校中的作用。在中國高等教育,如能建立起有影響力的校際學術組織,能更好地維護學術權力。
以制度化的方式來維護學術權力,構建符合學術組織特性的高校管理制度。合作、共治、平衡構成現代大學治理的價值選擇。人們對高校領導與管理有一個基本預期,那就是權力分享。高校的學術領導是許多人的責任,校長與其他成員之間如何進行溝通和互動,如何評價自己和他人的效率,如何確立目標,這是權力分享的關鍵所在。教師和學生是高等院校的主力軍,高校的決策者應把教師和學生及其需要作為關心的重點,將他們視為高校改革的主要參加者。教師與學生作為學術自由的主體,在享有自由權利的同時,必須履行一定的社會責任。高校及其師生應當:(1)享有作為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的學術自由和自主權,同時對社會盡職盡責。(2)在各項工作中堅持嚴格的倫理準則和嚴謹的科學態(tài)度,保持和發(fā)揮自己的重要作用。
(三)學術規(guī)范的制度建設
高等教育的學術出現嚴重失范之時,就有必要把那些不明文的規(guī)則進行闡明,使之制度化,并輔以一定的懲罰措施來維護其權威性。通常情況下,在學術活動中,大量的學術規(guī)范是不明文的,用哈耶克的話來說是“未闡明的規(guī)則”。國人對大學寄予了極大的期望,但大學的現狀與人們的期望之間存在著深深的鴻溝,學術的失范和腐敗令人痛恨。學者不是圣人,他們并沒有天然的道德優(yōu)勢,如果缺乏制度約束,他們一樣可能戲說學術,如果有程序公正且嚴密的評審制度監(jiān)督,或許可以建立行之有效的學術規(guī)范。
學術失范的治理需要基于學者的專業(yè)能力來重建學術規(guī)范。學術規(guī)范源于學者的專業(yè)能力,是教授身份獲得同行認可和社會認可的坐標。馬克斯·韋伯指出,一個學者要想贏得社會的認同感,“無論就其表面和本質而言,個人只有通過最徹底的專業(yè)化,才有可能具備信心在知識領域取得一些完美的成就”[4](P23)。在專業(yè)能力之外,知名教授還具有超強的公共能力,從某種意義來講,教授社會權威的支撐點,不僅要看他們是否是專業(yè)規(guī)范的立法者,還要看他們能否跨越其專業(yè)領域,在專業(yè)與公共之間找到一個融合的關聯點,直接或間接地成為公共規(guī)范的立法者和護法者,解釋生活、申訴正義、弘揚民主,從而履行教授的社會責任。
公平正義的學術制度有助于建構大學的學術秩序,并促進教育質量的提高。教育家夸美紐斯說:“學校的長處全在于制度,它包括學校發(fā)生的一切事。因為制度才是一切的靈魂。通過它,一切產生、生長和發(fā)展,并達到完美的程度。”[5](P18)夸美紐斯高度評價了現代學校制度,同樣,大學制度也具有無與倫比的優(yōu)越性。大學制度的發(fā)展經歷了三部曲:大學自治被奉為理想的大學制度;政府等外部權力的相繼介入;重建大學與政府、社會的邊界。1998年我國《高等教育法》已將大學章程定位為高校成立的法律依據之一,為高校治理變革奠定了基礎條件。大學章程本身就是一種學術組織的規(guī)范,規(guī)范著高校及內部組織的權責、教師和管理人員的義務和權利,其中學術組織的建設是其重要內容,學術規(guī)范的制度建設必不可少。在我國當前,現代大學制度的核心內容,既要完善以大學法人化為標志的外在制度,又要培育以學術自由精神為核心的內在制度。
(四)學術道德的文化建設
高等教育的學術失范和學術腐敗,不能完全依靠制度建設,還有賴于學者的自律,或者說訴諸于道德。學術道德有三個層次,即學術的自主、誠實與獻身精神。學術的自主反映的是學術的自由和民主的環(huán)境,民主的精神與學術自由的精神是共生的。馮友蘭認為,民主有兩個原則:一為少數服從多數,一為多數容忍少數[6](P243)。多數容忍少數是民主的較高境界,也是民主的精髓之所在。學者所追求的學術創(chuàng)新,往往是一些與常識不相稱的“異端邪說”。新的真理會使人感到不舒服,尤其對當局者來說更是如此。在民主社會,學術自由是大學的永恒追求。正如潘光旦在《自由之路》中所言,“從教育的立場看,唯有一個真正的民主的政治環(huán)境,始能孕育真正自由或通達的教育”[7](P160)。
大學校長的人格魅力有助于學術道德的文化建設。“魅力”一詞,最早源于古希臘,意思是神圣天賦的力量。馬克斯·韋伯把這個詞運用到管理學和社會學等領域,將其理解為領導者個人影響力的一種非凡狀態(tài),是一種超凡的權力。按照韋伯的解釋,社會生活存在三種合法權力,即法定權力、傳統(tǒng)權力、超凡權力。前兩種權力屬于法律和傳統(tǒng)授予的硬權力,超凡權力屬于非權力因素的軟權力,卻集中表現了領導者是否具備激發(fā)部屬動機的能力。大學校長的為官之道,在于其與師生的情感溝通。校長集行政、學術及經濟權力于一身,其是否愿意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是否具備學理同情心,這是高校學術文化建設的關鍵所在。我國高等教育史上,民國大學校長在開創(chuàng)大學之時,就準確地把握住了高等教育的主旨。他們具有教育家的品質,責任大于權力,敢于與世俗作斗爭,為維護大學的宗旨、個性和學術榮譽能挺身而出。
大學教授的精神氣質,是學術道德文化的重要組成。今日教授的精神氣質和專業(yè)水準較之過去的教授,在社會權威、信任度等方面的正面得分明顯偏低,這是導致教授身份危機的內在原因。一些教師把主要精力放在校外活動中,忽略了教學,不關注學生的需要,忘記了自己的職責。因此,學術道德的文化建設,必須重塑教授的精神氣質。教授的精神氣質,表現為教授的行為特征:視學問為自己安身立命的唯一支撐;教授的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教授身上極強的人文精神,等等。
[1]伯頓·克拉克,等.高等教育新論——多學科研究[M].王承緒,等,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2]馬俊駒.法人制度的基本理論和立法問題之探討(上)[J].法學評論,2004(4).
[3]Donald F.Kettl.Sharing Power:Public Governance and Private Markets[M].W 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3.
[4]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M].馮克利,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
[5]夸美紐斯.夸美紐斯教育論著選[M].任寶祥,等,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6]馮友蘭.三松堂小品[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7]楊東平.大學精神[M].沈陽:遼海出版社,1999.
[責任編輯:陳梅云]
左崇良,江西師范大學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員,江西 南昌 330022
G64
A
1004-4434(2016)10-0176-05
江西省教育科學“十三五”規(guī)劃2016年度重點課題“基于校企合作雙主體辦學的省域高等教育治理體系構建研究”(16ZD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