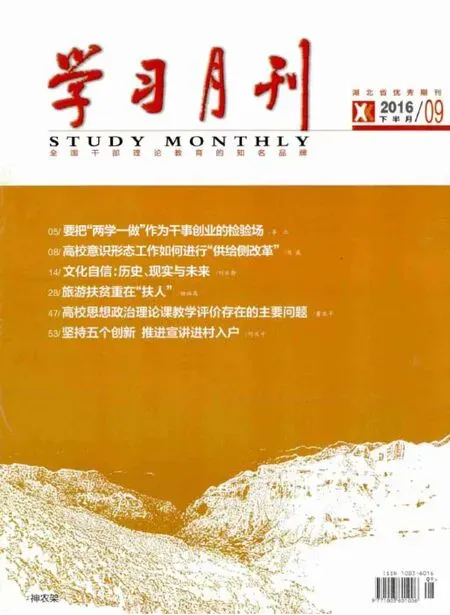《荷馬史詩》與《詩經》中的女性審美觀比較
產生于同一時期的東西方兩部史詩——《詩經》和《荷馬史詩》分別展現了中華民族和古希臘民族兩個不同民族的生活圖景。相隔萬水千山的兩個民族在社會歷史發展的同一階段,即使相互間沒有直接的互動與影響,其文學創作也出現了某些相近的圖式。
兩部史詩都有不少詩篇直接贊美女性的美貌,但是在審美的角度及深度方面兩部史詩又有差異。荷馬史詩創造了豐富的女性美形象,其中有天界的女神,凡間的民女;社會上層的女王、公主,下層的女工、女奴;家庭的母親、女兒;依據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社會分工,史詩展現了她們不同風格的美。這與《詩經》中統一強調的女性“內在精神美”、“品德美”是不同的。
《荷馬史詩》突出建構的是女性的“外在形體美”。《荷馬史詩》首要突出表現的是豐潤的母性美,以佩涅洛佩為代表。在《奧德賽》中,她的美是神賜的,智慧女神雅典娜用神脂為其清洗面容,使其更為嬌嫩豐潤,肌膚像象牙一樣白皙潤澤。“豐潤”一詞大多數被用在佩涅洛佩身上,其他女性則多用“美貌的”、“閃亮的”、“高貴的”等修飾。
為什么西方人如此鐘愛“豐潤”?這是因為在荷馬時代,戰爭頻繁,傷亡慘重,人口成活率極其低下,于是生育就成了頭等大事。在史詩中,特洛伊國王普利阿莫斯就因為生育了六十二個兒女而名揚天下。可見,人們將生育能力旺盛視為一種榮譽。而“豐潤”恰恰就蘊含著這種強大的生育能力,故而,“豐潤”便是對女性的最高的贊美,是女性美的最高表征。而《詩經》中的母親皆以慈祥、辛勞的形象出現,幾乎沒有以外表的“豐潤”形象出現的。
其次,《荷馬史詩》中還出現了以秀美為特征的少女美。奧德修斯用木馬計攻占了特洛伊后因傷害了海神波塞冬的兒子獨目巨人而被海神詛咒滯留在外鄉。經歷了海上漂泊十年后奧德修斯在雅典娜的指引下遇到了阿爾基諾奧斯的公主瑙西卡婭,奧德修斯見到她時這樣說到:“我從未親眼見過如此俊美的世人,或男或女,我一看見你不由得心驚異。我去過得洛斯,在阿波羅祭壇旁見到一顆棕櫚的如此美麗的新生幼枝,我一看見那棕櫚,心中驚愕不已,從未有過如此美麗的樹木生長于大地。史詩中描寫出了少女的挺拔秀美、窈窕多姿,表現出少女特有的勃勃青春氣息。
當然,荷馬史詩神話色彩濃郁,其中各路女神所展現的女神美也不失為外在美的一種表現。如在《奧德賽》中是這樣描寫仙女卡呂普索的:“那神女身著一件寬大的白色長袍,輕柔優美,腰間系一條無比精美的黃金飾帶,用巾布把頭部從頭頂包扎。”在這里史詩并沒有直接細致的描寫女神的五官及形體美,而是以華麗的服飾和裝扮來烘托女神的高貴氣質,展現了她們的雍容華貴,綽約多姿的風采。
《詩經》著意構建的則是女性的“內在精神美”。詩經中并不缺乏贊美女性“外在形體美”的詩篇,但更多的是贊美女性的“內在精神美”。如《詩經·衛風·碩人》: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
領如蝤蠐,齒如瓠犀。
螓首蛾眉,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這是衛人贊美衛莊公夫人莊姜的詩。詩中贊美莊姜手指纖細、皮膚白皙、蛾眉細長、梨渦含笑。一個秀美多情的女性形象躍然紙上。不過如此美麗多姿的美女并不是僅僅停留在她們的外在形體上,外在美是作為內在精神美輔助出現的,倘若衛莊公夫人莊姜沒有美好德行,就不會得到衛國人民如此愛戴和贊美。
再如《詩經·邶風·靜女》中的: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
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
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這是一首青年男女約會的詩。詩人用“靜女其姝”“靜女其孌”來描繪女子,通過姑娘的善良表露出她的美麗、漂亮,這是一種由內而外的美麗,表達出古代男子的審美追求,重視女子的內在品質——善良。
再如《詩經·鄭風·有女同車》中: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將翱將翔,佩玉瓊琚。
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
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這是一首貴族男女的戀歌。從詩中可以看出男方看中的姜家大姑娘,不但容貌美麗,更使他難忘的是品德好、內心美。
以上三首詩充分的說明了詩經時代東方男性審美不僅關注女子的外在形貌美,更強調女性內在的品德美、智慧美,這是和《荷馬史詩》截然不同的審美取向表現。
造成東西方這種審美差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由當時的政治背景決定的。荷馬時期是西歐世界的大拆分大組合,戰爭是主旋律。整個社會系統都要求為戰爭服務,女性也不例外,她們不僅被要求容貌美麗,而且要生育能力強。而《詩經》產生之初是西周大一統時期,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統治階級從內部改革出發,對人民的思想進行控制,要求女子德才兼備。其次,是地理環境上的。古希臘坐落在地中海的東部,陸地都是小塊分布,且多貧瘠山陵,人民都發展海外貿易,深受海洋文明的影響,他們享受現實的愉悅,欣賞女性外貌形體的直觀自然美。而詩經時代的中華民族先民們住在富饒的黃河流域,氣候溫和、土壤肥沃等優越的自然環境給人們發展農業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小農自然經濟條件下,他們形成了安土重遷、安于現狀的意識,個人更關注社會體系的建構以及家庭內部的規范,對女性“德”的要求也就應運而生。再次,與《詩經》相比,荷馬史詩中的女性不受任何明顯的倫理道德規范的制約,他們的審美是直觀理性的,美就是美,不摻雜任何雜質。而詩經中的男子評判女子時首先關注的是她的性格、脾性、品德等感性因素,然后才是相貌,而這里的相貌又不單單是美麗的容貌,更強調的是女子出入要端莊穩重持禮,不能輕浮隨便。
總之,通過對《荷馬史詩》與《詩經》的女性審美標準的比較,我們發現,不管是關注“外在形體美”,還是醉心于“內在精神美”,都不能判定哪個民族審美旨趣的優劣好壞,只是由于不同的地域環境、歷史條件、民族心理等因素的歷史作用所致。這種差異性突顯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價值觀念下,所培育出的不同的女性審美意趣。也正是因為這種差異性,才有了東西審美文化的多姿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