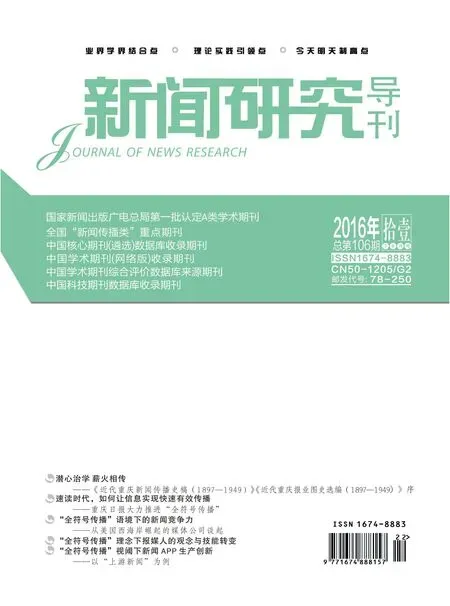淺論“微”時代的參與式文化對節日儀式景觀的消解
孫丹陽
(中國人民大學 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北京 100000)
淺論“微”時代的參與式文化對節日儀式景觀的消解
孫丹陽
(中國人民大學 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北京 100000)
在“微”時代的參與式文化不斷勃興的今天,傳統的節日儀式景觀逐漸被消解。本文將不同的節日從參與程度上分成了三類,并從內部原因與外部原因兩個方面對消解的原因展開分析,認為雖然參與式文化對于節日儀式景觀有部分的消解,但善于運用媒體規律、制造話題、引導輿論仍然有可能重建一種新的“微”時代節日秩序。
“微”時代;參與式文化;節日儀式;景觀
“微”時代的到來以微媒體的誕生為表征與標志。微媒體是以微博、微信等新興平臺為傳播媒介代表,以移動終端為傳播載體的媒介。微媒體以精準短小的微內容為傳播對象,在傳播上以移動化、社交化、跨平臺、流動、瞬時性、扁平化的微傳播為基本特征,傳播對象面向小范圍的微社群用戶(微圈子)。[1]“微”時代有兩個被廣泛使用的平臺,一個是微博,另一個是微信。“微”時代有多重內涵,“微”時代是文化傳播、人際交往、社會心理、生活方式等多種復雜語義的信息傳播時代。
參與式文化是一種以全體網民為主體,以積極主動地創作媒介文本、傳播媒介內容、加強網絡交往為主要形式創造出來的一種自由、平等、公開、包容、共享的新型媒介文化樣式。在參與式文化不斷勃興的今天,越來越多的節日成為網絡的狂歡,傳統的節日儀式景觀以各種“炫耀”、段子及泛娛樂手段遭到了異化,參與式文化從多方面對節日儀式景觀產生了消解。
一、“微”時代的節日儀式景觀分類
從參與的程度上來分,可以將節日儀式景觀進行媒介化的分類,它們分別是媒介主導類、受眾主導類與受眾媒介共融類節日儀式景觀。
筆者將第一類稱為媒介主導的節日儀式景觀,如中國植樹節、保護母親河日、世界水日、世界無煙日、世界知識產權日等。這種景觀當中,主要是由網絡上的主流媒體和官方平臺所指引言論,并定時提醒節日的到來在第一類的節日儀式景觀中,受眾的參與程度是最低的,其表現行為僅僅局限為跟帖和跟發評論,或者是不屑一顧。
第二類稱為受眾主導型,情人節、七夕節、母親節、光棍節、520表白日等。這種景觀中,受眾的參與程度是最高的,這些節日也都是人們喜聞樂見的。網絡上這些節日的參與的歡騰呈逐年遞增趨勢,所呈現的景觀可以說是蔚為大觀。
第三類稱為媒介受眾共融型,如春節、婦女節、勞動節、端午節、中秋節等。在這類節日當中,主流媒體與草根用戶的參與程度是相當的,介于前兩者之間。本文所研究的節日儀式景觀主要是在參與式文化的影響下所呈現的第二與第三類媒介節日儀式景觀,從不同角度研究參與式文化對節日儀式景觀的新建與消解。
二、參與式文化對節日儀式景觀消解的原因
(一)內部原因
1.參與文化使得受眾易于融入群體成為“烏合之眾”。如果說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擔憂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替代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笑以及為什么不思考,那么網絡上的受眾更像是赫胥黎所擔憂的那樣,成為了這種無意識的群體之中的一員。但凡是有節日在網絡上的狂歡景象,受眾在看到了自己所在的群體的展演后,也要加入其中,這時候只要是“加入”就好,而“思考”就成了可以跳過的步驟。
2.參與機制作用下強烈的情緒和情感的感染機制作用。狂歡的形成除了來源于觀點的自由表達以及無差別的身份認同,還來自強烈的情緒以及情感。情緒感染是指:“一種下意識地(或不自覺地)獲得與他人抑制情緒的傾向。”[2]其機制可能有模仿-回饋機制、認知機制、直接誘導機制。在感染機制的作用下,個體會被一時的沖動所主宰,卷入非理性的狂亂當中。
在微博、微信的平臺上,參與式互動行為的加強使得這種機制更容易開啟,在節日儀式這個帶有強烈情感訴求的景觀當中,這種情緒與情感的感染作用有加強的可能。
(二)外部原因
1.經濟方面:國家經濟體系——“假日經濟”。節假日生發一種衍生物“假日經濟”時,節假日的意義已經變成了國家利用法定節假日來刺激消費的一種隱性手段,如果經濟的利益占據了制高點,那么文化的重要性必定要為其讓位。在這樣的“假日經濟”的大氣候環境下,消費主義實際上已經廣泛存在于文化乃至各個領域,而不僅僅是我們今天所要探討的節日儀式的文化一方面。
2.文化方面:作為傳統文化發展的整體瓶頸與困境——內憂外患。傳統節日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在中國的節日譜系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最近幾年的時間里,傳統節日自身的發展也出現了很多的問題。一方面,西方文化理念不能充分地內化為公眾的心理情感;另一方面,傳統文化的價值和規范又呈現出缺位的狀態,由此衍生出來的是受眾內心的一種對文化的漂泊感,難以建立起對傳統節日文化的身份上的認同。當這種景觀發生在網絡上,這種匿名性也融入組織性的平臺的時候,受眾的身份就更難建立了。
3.生活節奏方面:節日只是假日——休閑需求增加。社會壓力大,休閑時間少,已經是多數中國人所面臨的生存現狀與問題。西方生活方式對于“勤勞勇敢的中國人”的生活理念的沖擊,以及公眾自身對于國家社會個人關系、工作與生活關系的重新認識,喚醒了長期以來被壓抑的休閑需求。然而節假日的來臨,好像是一種出口,對平日積攢的壓力以及疲勞的一種宣泄口,節日往往就只是“假日”,人們在休閑的時間段上,是很少考慮到節日儀式對于我們的其他歷史意義的,很多人認為“節日就是用來狂歡的”,這種對文化與歷史的忽略已經成為社會的常態,反倒是擔憂文化與歷史的人成為“異類”。
4.社會語境方面:中國的轉型特殊時期。發展中的中國是一個國家與個人關系逐漸疏離的情景。以春節聯歡晚會為例,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是一個經濟不斷發展、各種文化不斷沖進國門的時期,春節作為中國人最重要的傳統節日,是凝結中國人的絕佳時機,因此在意識形態觀念的滲透下,春節聯歡晚會誕生了。隨著國家的發展,各方面不安定的因素逐漸趨于平穩,逐漸過渡到了平穩發展的發展中國家。此刻的中國并不急于利用一個儀式來聯結不同主體以提高凝聚力,這時的春節聯歡晚會在受眾心目中的地位就沒有最初那般神圣。春晚之于現今的中國人,娛樂的意義要大于儀式的意義。所以,從社會語境上講,發展中的中國對儀式的需求在降低,人們更多的是關注娛樂以及生活的必需。
轉型期的中國利益多元,矛盾突出,社會壓力空前,人們在微博上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是把微博當作“社會減壓閥”。人們在轉型過渡中感到焦躁不安,社會壓力空前,現實社會中,人們積攢了不少壓力和情緒。微時代的微博與微信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社會減壓閥”。
三、如何利用參與式文化重塑節日儀式景觀
首先,可利用新媒體信息傳播的優勢,對節日的相關背景知識進行宣傳和普及,著重突出其歷史含義,突出與當代的傳承性和對當下的啟示性。對于沉浸在后現代“斷裂”文化中的人們來說,發現自己的文化根源,進行歷史坐標的定位是彌足珍貴的。其次,還應當對本民族特有形象系統進行統一和固定,利用新媒體視覺、聲像傳播的優勢,在網民特別是青少年群體中推廣,將視覺形象與較為抽象的民族、家國、人文傳統觀念相對應,使民族文化形象鮮明。最后,通過重復性的長時間的強化培養并建立一個新樣式的網絡節日儀式秩序與節日儀式的新邏輯。
儀式作為一種文化形式,發生變遷是非常正常的現象。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發生了變化的全新空間的突出表現在于所有的參與主體得到了個人廣闊的展示空間和表達權利,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受眾的情感。但是網絡傳播中的各種限制使得節日儀式景觀中的歷史感在弱化,網絡媒介的非中介性,使得信息擴散迅速而活躍,同時,快速的傳播剝奪了人們停下腳步來思考的機會。所以想要在長時間培養建立這樣一個新的網絡節日儀式。
要通過輿論引導機制鼓勵人們在節日到來的時候走出網絡,多一些人與人之間的真實互動,到真實的場景中去感受節日的氛圍。其次,要注意放慢自己的腳步,在無聊的指尖滑動屏幕的過程中,思維是不夠活躍的,由于字數的限制,人們的感受也成了只言片語。如果這種節日儀式的景觀必然有新媒體的參與,那么傳統媒體的責任就更大了。一個節日,尤其是傳統節日的背后有著怎樣的歷史,世界各地有哪些風俗習慣等,都需要傳統媒體或新媒體具有傳播歷史文化的觀念與意識,為構建一個更加理智的節日儀式景觀作出應有的貢獻。
[1] 杜建華.“微”時代:表現、特征及傳統媒體的著力點——以紙媒體為例[J].新聞大學,2015(02):60-67.
[2] 張奇勇,盧家楣.情緒感染的概念與發生機制[J].心理科學進展,2013(09):1596-1604.
G206
A
1674-8883(2016)22-007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