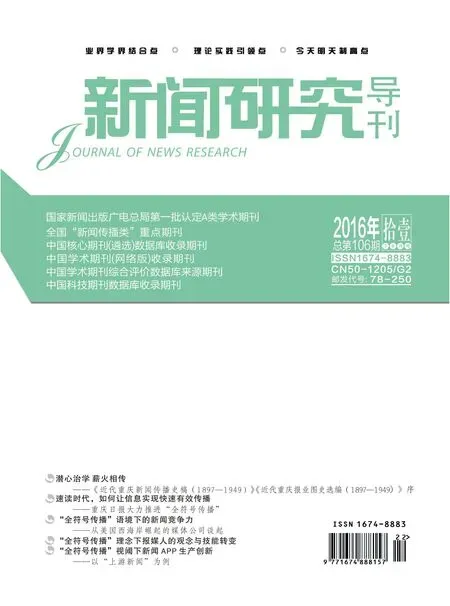大學生群體在微信和微博上自我呈現的差異研究
孫 行
(四川大學 文學與新聞學院,四川 成都 610000)
大學生群體在微信和微博上自我呈現的差異研究
孫 行
(四川大學 文學與新聞學院,四川 成都 610000)
網絡平臺的發展給予了大眾更豐富的傳播空間和更廣闊的展示舞臺,自我呈現也隨之更加復雜多樣。本次研究以大學生群體為對象,主要探討這一群體在兩大社交平臺——微信和微博上自我呈現的差異。分析了這些差異出現的原因,并由此對大學生群體社交網絡自我呈現的心理機制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自我呈現;微信;微博
自我呈現是個體社會生存和社會交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他人了解個體的重要途徑,自我呈現的內容和效果都對個體的形象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網絡社交的出現則賦予了個體更大的呈現舞臺與更復雜的呈現方式和心理。
自我呈現(presentation of self)又被稱為自我表現、印象管理。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中,美國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對該理論作了較為系統的闡釋:“個體或群體在與他人互動時如何運用各種方法和技巧,產生和維持符合自己或他人期望的理想形象。”
近年來,網絡社會快速發展,網絡空間不斷擴大,改變了個體或群體“表演”的舞臺,也影響了個體或群體自我呈現的行為和心理。
學者在探討網絡社會和現實社會中自我呈現的關系時,得出的結論是“網絡的虛擬并非是絕對的虛擬,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真實”。[1]《網絡空間自我呈現過程中的工具利用——以QQ空間為例》研究中也發現:“與在現實生活中相似,網絡空間中人們的自我呈現行為也會在一定程度上走向模仿。”[2]正如陳曉婧所認為的那樣,“現實社會中的個體特征及人際關系已越來越多地映射到網絡,真實社會與虛擬網絡相互交織”。[3]
同時,學者們還提出,“網絡使得自我呈現前臺擴大,后臺壓縮。”戈夫曼“戲劇論”中提出前臺和后臺的概念,認為“表演要想成功,就需要協調好前臺和后臺的關系。”而如今,各種網絡社交平臺興起,大家都爭相將自己生活的點滴呈現給別人。人們“自愿放棄在后臺的放松,而選擇了時刻進行表演。后臺的空間在不斷縮小,致使前后臺的界限相當模糊”。[4]
為了解大學生群體在微信和微博這兩大社交平臺的自我呈現情況,筆者在專業的問卷調查網站問卷星(www.sojump.com)上進行了問卷調查,共收回有效調查問卷325份。
一、主要差異表現
通過對問卷調查的整理分析,可以得出大學生群體在微信和微博上自我呈現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兩者都以熟人好友為主,微博中陌生網友更多。在微信好友中,位列第一的是“同學、熟人”,“陌生網友”極少;微博粉絲中占比最大的雖然也是“同學、熟人”,但“陌生網友”位列第二。
朋友圈的內容以生活為主,微博上的內容更加多元。大學生在朋友圈發布的主要內容中,“分享生活”和“表達心情”在所有選項中分別排第一和第二,被選率分別是76%和66.77%;微博中各項內容則分布得十分均勻——“分享生活”“表達心情”“共享信息”和“轉帖”的被選率都在50%以上。
大學生在發布微博時更加果斷。22.15%的用戶在發布朋友圈時從不猶豫,37.85%的用戶在更新微博時從不猶豫,而38.15%的大學生也承認自己在發布微博時更加果斷;50.77%的大學生用戶在發布朋友圈時從不會設置分組可見,而微博中這一比例達到了75.38%。因此,大學生在朋友圈中自我呈現時會有更多的考慮,在微博上則更加果斷、隨性。
情緒表達的差異。對于現實生活中不敢或不愿表達的內容,大學生會選擇在微博上呈現或干脆不對任何人表達。由此可見,在部分大學生看來,微博與現實生活的界限和區分更加明晰,更有可能成為現實生活之外的另一個自我呈現舞臺。
二、原因分析
自我呈現是復雜多樣的,大學生群體在微信和微博上自我呈現的差異也因此略顯散亂,產生這些差異的原因也是復雜多樣的。本文僅嘗試從兩個網絡平臺本身特性的差異和用戶的心理這兩個方面來做一些分析。
(一)微信和微博特性的差異
微信和微博雖然都是用戶自我呈現的重要網絡平臺,但兩者在功能設計、主導訴求、功能價值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筆者認為,這些區別主要源于兩者本身特性的不同。
微博以信息的廣泛和共享著稱,主打全民傳播,注重的是信息的發散狀流動。這是微博的開創性,也是它的價值所在。
微信則是介于微博和QQ之間的一個傳播媒介。它在原有QQ的基礎上加入了“微信公眾號”這一功能,使之也具有了信息傳播的價值。但總體來看,微信注重的還是點對點的流動,是小范圍內的信息傳播。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微博偏向于媒體化,是一個非常開放的交流平臺,觀看的是大千世界;而微信偏向于社交化,是一個閉環傳播,觀看的是周邊生活。
根據卡茲的“使用與滿足”理論,網絡用戶傳媒接觸行為的發生條件之一就是媒介印象,根據媒介印象,人們選擇特定的媒介或內容開始具體的接觸行為。因此,大學生的媒介印象與兩大平臺的觸媒特性相匹配,使得大學生群體在兩個平臺上的自我呈現自然就會有諸多差異。
本次研究中大學生在自我呈現對象和內容上的兩大差異就源于此。
從自我呈現的對象來看,微博中熟人好友的比例明顯小于微信,而陌生好友的占比要遠遠超過微信。順著平臺特性的引導,大學生群體在微信上呈現的內容以日常生活為主。我們在朋友圈關注朋友們生活的點滴,也向朋友們展示自己生活中的所見、所感、所想。這是雙方不用言明就能達成的默契;微博則不同,它賦予普通大眾更多的知情權和表達權,使每個人都成為“記者”,因此微博上“共享信息”和“轉帖”的內容都遠超過朋友圈。
然而,筆者在本次調查中發現,微博雖然向來以媒體化傳播著稱,但用戶在平臺上的自我呈現卻與其并不十分一致。“共享信息”和“轉帖”這樣的公共信息傳播固然占比很大,但“分享生活”和“表達心情”這些內容所占的比例與之不相上下。這是微博在進行用戶引導時走入的誤區——社交網絡已經進入相對成熟的發展階段,不同的社交媒體開始分工,社交網絡的用戶也被分化,但微博的定位似乎并不是那么準確和堅定。
(二)社交心理因素的影響
自我呈現處于傳播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的交叉點,個體的心理狀態和傾向對于自我呈現的作用不容小覷。筆者試圖從心理學的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分析。
已有的研究結果表明,用戶使用網絡社交的動機主要包括兩種:自我展示和獲取歸屬感。人們進行自我呈現就是希望得到別人的關注和認同,提高自己的受歡迎程度。為了得到他人的肯定,個體就會盡量在自我呈現時展示一個符合社會評價和社會期待的“客我”形象,也就是戈夫曼所提出的“印象管理”(也稱“戲劇論”)。
大學生群體之所以在網絡自我呈現時出現猶豫不決、設置分組可見、避免負面情緒等情況,就是基于“印象管理”的考慮。
當某件事或某個情緒出現的時候,大家會有自我展示和獲取歸屬感的動機,想要把自己的生活分享給大家。但從組織語言到選擇圖片,再到最后按下“發送”鍵,有一部分人會略顯猶豫和糾結。而這一過程就是個體在有意或無意地進行“印象管理”——這件事是否符合我給大家的已有印象?語言是否準確、有趣?圖片是否足夠引人注意?等等,這些都可能是個體網絡自我呈現前猶豫的事情。
雖然從一般思維來看,朋友圈的關懷等社會支持能有效抵御傷痛,但實際情況并不與之相符。
“熟人社交”的親密度處在陌生人和親密朋友之間,個體對它的信任度也處于這兩者之間。正如一位網友所說的那樣,當把自己的失落表現出來時,要么“朋友一掃而過,沒有給予任何回應,更挫敗”,要么“朋友給予回應,給你來一碗雞湯,實際上也幫不了你什么”。因此,對于生活中的挫敗,大多數用戶還是會尋求親密朋友的幫助和支持,或者寧愿將其展示給生活中沒有交集的陌生網友。
因此,網絡用戶,特別是大學生群體,總是能清晰地意識到平臺環境的差異,扮演好不同的社會角色,管理好自己的社交網絡形象。“熟人社交”并沒有帶來更真實的自我呈現,相反,出于“印象管理”的需要,為了維護自己的個人形象,個體在微信朋友圈中呈現的是精心選擇、慎重考慮后的自我。
[1] 沙艷.網絡空間與現實社會中自我呈現的差異性——以J大學新浪微博達人為例[D].吉林大學,2014.
[2] 謝榕.網絡空間自我呈現過程中的工具利用——以QQ空間為例[J].江西青年職業學院學報,2010,20(3):21-23.
[3] 陳曉婧.新網絡社交時代的自我呈現[J].淮陰師范學院學報,2012(2):243-247.
[4] 羅丹妮,羅麗.微博中的自我呈現:讀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J].黑河學刊,2014(2):56-58.
G206.3
A
1674-8883(2016)22-008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