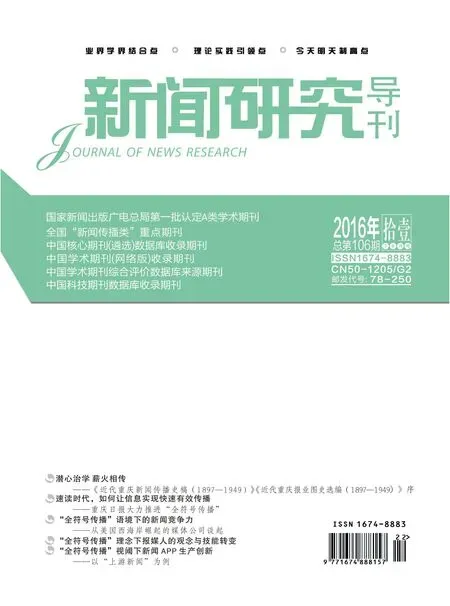擬態環境:現實與反思
許 雪
(北京師范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875)
擬態環境:現實與反思
許 雪
(北京師范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875)
擬態環境理論是大眾傳播時代的經典理論之一。基于網絡時代和新媒體樣態的現實,本文對擬態環境的新特點進行了探析,并進一步反思了擬態環境理論的未來發展趨向。
擬態環境;建構機制;網絡時代;發展趨向
當今互聯網時代,新媒體樣態層出不窮,以計算機和手機終端為代表的數字化新媒體的發展勢頭已超越傳統主流媒體。數字化的擬態方式雖然并未對文本、圖像本身帶來質的改變,但這一技術卻深刻地影響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動準則,給擬態環境帶來許多新的可能的同時也給擬態環境理論帶來了新的挑戰。
一、擬態環境新特點
(一)就受眾而言
第一,受眾地位得到提升。網絡技術的升級帶來了自媒體的發展,在自媒體時代里,信息渠道更加多樣化、便捷化。也因此,大眾媒體的權威性受到了挑戰,其部分權力需讓渡給受眾。受眾在傳播中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人們既是信息的生產者、傳播者,又是信息的接收者。但是,我們應認識到這一提升是有限度的,自媒體并未完全擺脫擬態環境。伴隨著受眾地位上升的是傳播的低門檻化和碎片化,大量的自媒體信息表現出數量龐雜、篩選困難等特點,常會帶來事實失真或受眾一知半解的情況;導致受眾不易形成完整的、正確的認知,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擬態環境的多層次性和影響的復雜性。
第二,民眾話語權開放。文章開始已談到,李普曼提出此理論的一個大前提便是——公眾無法獨立地對世界形成理性的認識。換句話說,李普曼的“擬態環境”從本質上來講是被理性的媒介精英所操縱而構建的信息環境。一方面,李普曼的預設本身是對公眾理性的過分否定;另一方面,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自由民主的觀念深入人心,連接民眾與社會的信息渠道得到了極大開拓,民眾有能力且有機會參與到公共空間的討論和建設中來。正如學者劉懷丕指出,“在現今時代,李普曼所謂的被社會精英操縱的結構化的‘擬態環境’已轉變為公眾積極參與構建的非結構化的‘擬態環境’。”[1]
第三,受眾分眾化明顯。當下正處于信息變革時代,新舊媒體形式并存,不同年齡段群體的信息渠道偏好不同:新媒體的主要受眾以年輕群體為主,而老一輩人由于長期形成的使用習慣則更傾向于傳統媒體形式。此外,新媒體內部提供了豐富化、多樣化、專業化的平臺選擇,受眾基于階層、喜好、經驗等方面的不同,亦會發生分眾化,難以像傳統媒體時代一樣形成統一的整體,統一的“擬態環境”亦難以建立起來。
第四,受眾碎片化的閱讀習慣。互聯網上信息的零散性與海量性,以及移動終端閱讀方式的普及,使大眾的閱讀習慣朝碎片化、淺層化的方向發展,與網絡上海量的、混亂的信息流相迎合。
(二)就傳播者主體而言,社會控制力弱化
在大眾媒體時代,由于傳播者隊伍單一、傳播基調統一、內容較少等特點,大眾媒體能夠嚴格地控制新聞信息的生產與傳播,既發揮“把關人”作用,又負責進行“議程設置”,進而影響受眾的意見。而在網絡新媒體的模式下,“把關人”功能被大大弱化,構建了“弱把關”的擬態環境。之所以如此,主要有幾個方面的可能:一是網絡專業媒體為了追求信息發布和反饋的速度而降低了把關的力度,甚至放棄把關;二是傳播主體的多元化和信息發布的自由化給網絡把關帶來了困難;三是受眾呈現分眾化,受眾難以聚集于傳統媒體那樣的公共信息平臺,由此導致了媒體社會控制權力的弱化;四是微博等社交媒體平臺改變了輿論自上而下的生產方式,從話題發酵到裂變傳播等各方面都對傳統媒體的輿論引導和監控帶來挑戰。
二、發展趨向
基于媒介環境的以上幾大新特點,學界對于擬態環境理論,以及其中“擬態環境的環境化”在網絡時代的發展趨向進行了激烈討論。經過梳理可知,學界觀點主要分為兩大方向:有的學者持有積極的觀點,認為新擬態環境將在整體上更加展現真實世界,諸如殷俊、楊麗萍基于“播客”的研究(2009)和張嬌對新媒體生態的討論(2014)等;但大多數學者持消極(或觀望)態度,認為新擬態環境將趨于復雜,加速擬態環境的環境化,很可能帶來媒介與大眾的異化,諸如學者劉懷丕(2010)、孔景志(2010)、秦一喬(2012)、倪洋(2016)、劉娜(2016)等等。
(一)擬態環境趨于透明和真實
學者們對于這一趨向的認同,主要著眼于媒體控制作用的弱化和受眾的主體性的增強,“擬態環境”呈現出雙方互動、多方影響的格局。更重要的一點是,他們肯定了受眾在信息社會中逐漸提升的媒介素養與理性的認知—表達的能力。人人都可表達,各種意見都能表達,且多元意見表達的空間增大,從而能夠促使擬態環境走向動態平衡的真實。
(二)擬態環境的非結構化:復雜、不確定、多維度
傳統媒體時代的擬態環境經過媒體統一的篩選和加工,具有內在的統一性。而在新媒體時代下,信息渠道多元、公眾傳播主體性及分眾性的增強,加之媒體的把關功能的減弱,進而帶來信息海量而泥沙俱下、意見多元而邏輯混亂、傳受者模糊難分、認知流于淺層且同質化嚴重等問題,擬態環境的多維度性、多層次性和不確定性也凸顯出來。
(三)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的加速:媒介與人的異化
之所以持有消極態度,是因為這部分學者認為,信息時代只是給人們提供更多信息和渠道的選擇的可能,并不會必然地增強人們對信息的辨別力和選擇力;反而,受眾被信息的洪流淹沒、被碎片信息裹挾會帶來選擇力的削弱。因此,人們更加依賴于如門戶網站、社交媒體等媒介,更加傾向于依照主觀的預設去接受媒體構建的擬態環境,并將其融入現實環境中,“將虛擬表現為真實,把想象表現為存在的一種狂歡式的媒介消費”,從而帶來媒介的異化。同時,在網絡時代下,人們極易沉浸于虛擬的環境之中,逃避現實活動。這使得網絡擬態環境的影響無限放大,最終來反對、甚至奴役人本身,這樣的情形便是人的異化。
[1] 劉懷丕.重建擬態環境理論[J].傳媒論苑,2010(2):110.
[2] 李普曼(美).公眾輿論[M].閻克文,江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6.
[3] 湯普森(英).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M].高铦,等,譯.北京:譯林出版社,2012:20.
G206
A
1674-8883(2016)22-0111-01
許雪(1995—),女,山東青島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