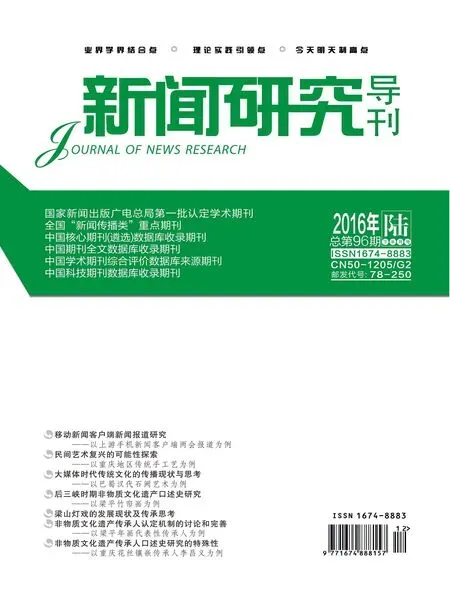淺析《彎曲的脊梁》中傳播學理論的運用
張 慧
(西北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7)
淺析《彎曲的脊梁》中傳播學理論的運用
張慧
(西北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陜西 西安710127)
美國傳播學者蘭德爾·彼特沃克所著的《彎曲的脊梁》(Bending Spines)描述了納粹德國與民主德國時期的宣傳活動,解析了這兩個集權主義國家體制下的宣傳架構和勸服技巧。本文旨在分析書中所運用的傳播學的相關理論,依次從內容梳理、理論運用(從傳播的儀式觀、沉默的螺旋—謹慎的螺旋理論、議程設置理論以及規訓與懲罰等方面來具體論述)和思考與追問來進行論述。
《彎曲的脊梁》;傳播的儀式觀;沉默的螺旋
美國傳播學者蘭德爾·彼特沃克所著的《彎曲的脊梁》(Bending Spines)描述了納粹德國與民主德國時期的宣傳活動。作者通過對比處于不同歷史時期的兩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科學、宗教等方面,著力從宣傳與勸服的角度,進一步分析納粹主義和馬列主義在德國失敗的原因。
一、理論運用淺析
(一)傳播的儀式觀
美國學者詹姆斯·凱瑞在《作為文化的傳播》中提出了兩種傳播觀,分別是傳播的“傳遞觀”和傳播的“儀式觀”。他指出,傳播的儀式觀并非直指訊息在空中的擴散,而是指在時間上對一個社會的維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為,而是指共享信仰的表征。在儀式觀中“傳播”一詞的原型是一種以團體或共同的身份把人們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禮。
這樣看來,不管是納粹德國,還是民主德國,都在對國民的宣傳和勸服過程中,運用了傳播的“儀式觀”作為理論基礎。
(二)沉默的螺旋—謹慎的螺旋
德國大眾傳媒學家和政治學家伊麗莎白·諾埃爾-諾伊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提出了著名的“沉默的螺旋”理論。諾伊曼提出這個理論的背景就源于她在納粹德國的生活經歷,所以這個理論就是完全為納粹德國這樣的極權主義社會所量身定做的。極權主義社會的最大特點就是權力集中于一人或一個集團,社會上只有一種聲音,不存在其他的對抗性意見。而這個結果的實現就借助了諾伊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論”。納粹德國和民主德國為了消除少數人的聲音做出了種種努力,包括無所不在的1984式的監視,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的360°無死角的宣傳與勸服。表面上看,少數人的觀念在公共話語體系中慢慢消亡了,但實際上,“沉默的螺旋”只是一種表象。
因此,美國學者第默爾·庫蘭對諾伊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論進行了修正,他提出更合適的表達,應該是“謹慎的螺旋”,即人們通常會隱藏他們的真實觀點,進行自我審查,只是公開提出與其私人信念相沖突的觀點,以規避不必要的風險,甚至還會帶來很多好處。
不管是“沉默的螺旋”,還是“謹慎的螺旋”,這些理論提供的解釋都體現出處于高壓環境之下人們內心的掙扎。實際上,歷史證明,高強度的極權主義社會是不會長久持續下去的,人們日積月累的怨氣和無處釋放的壓力總會經歷一個量變導致質變的必然過程。不斷被迫彎曲下去的脊梁要么被折斷(謹慎的螺旋理論表明至少有那么一批人的脊梁并沒有被折斷),要么就會在瀕臨崩潰之際開始反彈,當大多數人都開始反彈時,這時的極權主義政權就岌岌可危了。納粹德國最終因軍事力量的崩潰,而失去了民眾的支持;民主德國則因蕭條的經濟和蘇聯軍事力量的撤出,而最終瓦解。雖然在這兩個國家的失敗中,民眾的反抗似乎是微乎其微的,但是這并不代表他們的力量不重要,只是這兩個國家還沒有等到民眾力量的崛起而已。
(三)議程設置
議程設置理論同樣可以運用到納粹德國和民主德國的極權統治中,概括地說,首先獨裁黨會對媒體的議程進行建構,然后媒體重點報道的議題又會形成公眾議程,而這些報道又會在受眾當中引起信息鋪墊效果,從而影響他們對于現實的評估,但是更多時候這種議程設置所起到的功能卻是微乎其微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斯大林格勒戰役中納粹的戰敗,納粹黨控制下的媒體被授意不得報道真實的戰敗消息。因此,就需要轉移公眾的注意力,設置其他的議程,讓他們去關注、去討論,但是這樣一來導致的后果就是人們的好奇心和猜疑心越來越重,媒體和獨裁黨的公信力也隨之越來越低(很難相信,極權主義社會的政府也是需要有公信力、需要得到人們的認可的,但這是事實),不穩定的因素在慢慢發酵。最后納粹擋不住俄羅斯人的廣播電波,人們通過俄羅斯廣播中的遇難者名單得知了真相,獨裁者感到很尷尬,人們則只能咒罵媒體無良無德。在這場鬧劇中,受傷最深的卻成了夾縫中的媒體。
二、思考與追問
(一)大眾角色
在宣傳的過程中,納粹德國把大眾看作是頭腦簡單的木偶人,因而他們強調重復的力量,口號要簡單響亮,多次重復就會有效果,這對比到傳播學的理論中,就像是研究傳播效果時的“皮下注射論”和“魔彈論”。但是民主德國的領導人卻不這么想,他們認為大眾是有能力行動的,在他們看來,宣傳的效果就像傳播的效果一樣,是有限的。因此,他們需要從邏輯的層面上加強對公眾思想的控制,不斷地寫報告、發文件,企圖用這些文字來統治有一定理解能力的大眾。
(二)夾縫中的新聞工作者
在極權主義社會下的媒體是可悲的,卻也是值得同情的。經他們的筆寫出的文字,雖然原則上講也應該由他們承擔最終的責任,但是他們又有什么錯呢?錯的不是媒體,而是他們所在的時代,所處的國家。難道他們不值得同情嗎?不是所有的社會條件都能夠產生出一個救世主般的正義英雄,也不是所有的歷史背景下都能譜寫人們所期待的——船頭的瞭望者改變世界,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傳奇。但不努力就沒有資格哭泣,媒體的社會責任感不應只是掛在嘴邊的空話,而是應該深埋于心的處事原則,也許我們能做的很少,但希望說不定就萌芽于我們做了的那一點,脊梁可以暫時彎曲,但媒體人的獨立人格和氣節卻不可以低下去。
(三)楚門的世界
納粹德國控制下的媒體整天播放著虛假的新聞片,在那些畫面當中一切都是欣欣向榮的,直到法西斯的力量最終崩潰,很多人才像《楚門的世界》那部電影中的主人公一樣走出了那個封閉的“假世界”,感受到了真實世界的陽光溫度。民主德國的行徑更是可恥,不僅把豎起的柏林墻美化成反法西斯主義的保護墻,而且他們還對墻內的人們進行思想的恐嚇,妖魔化墻外的世界,給他們套上思想的枷鎖,讓他們的靈魂成為肉體的監獄。
G206
A
1674-8883(2016)12-008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