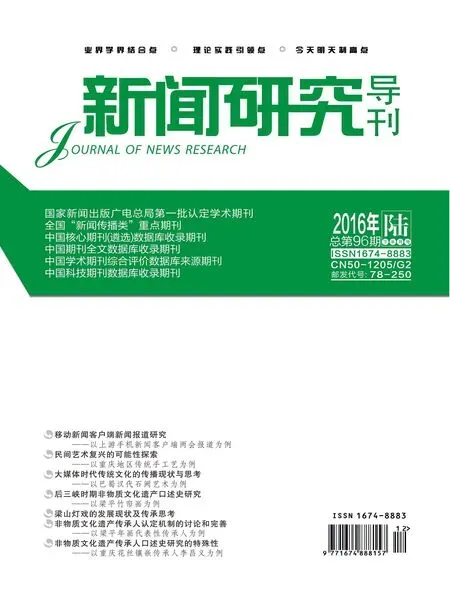報界梟雄張季鸞
陸美京
(吉林大學,吉林 長春 130000)
報界梟雄張季鸞
陸美京
(吉林大學,吉林 長春130000)
張季鸞是《大公報》的靈魂人物,而《大公報》又是民國時期的輿論重鎮。在那個充滿政治力量變革、新生事物與思想不斷更新、軍閥割據、異國敵寇入侵的大時代里,他始終保持自己鮮明的個性與立場、獨立的精神與信念,帶著強烈的民族使命感,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了深刻的足跡。《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一身粗質布衣,卻一生以筆言論救國,贏得了國共兩黨人的敬重。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他用筆桿勝過槍桿,深深影響著國人前進的方向。
《大公報》;張季鸞;報業經歷;“小罵大幫忙”
張季鸞祖籍陜西榆林,出身于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其父一直對其灌輸封建地主思想。據張季鸞回憶:“我的人生觀很迂淺的,簡言之,可稱為報恩主義,就是報親恩,報國恩,報一切恩。”以至于后來,他的“報一切恩”思想深深地影響著他的言行與筆鋒。由于家鄉的環境,從少年時代起,張季鸞就萌發了愛國之情和憂民之心,他十幾歲開始寫文章,受陳兆璜賞識,招入道屬。1902年,張季鸞到劉光蕡“煙霞草堂”進行學習。劉光蕡是一位關學大師,注重史地與國學。后來張季鸞留心經世學問,立言在天下,歷辦各報評,獲得成功。1905年,他官費留學日本東京經緯學堂后不久,升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政治經濟學,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說與經濟理論從此打開了他的眼界。當時,孫中山革命派的《民報》與梁啟超改良派的《新民從報》展開論戰持續兩年之久。在這個關頭,陜西留日學生出版了反對清朝統治的雜志《夏聲》,這本雜志屬于革命派,堅持武裝起義,深深吸引了張季鸞投稿并加以言論。由于張季鸞才華出眾,很快被推選為《夏聲》的編輯,這是他新聞工作的起點。從此,他走上了言論報國、新聞救國的道路。但是,此時的他一直是超黨派人士,始終沒有加入任何革命團體同盟會。
1910年,張季鸞赴上海幫助于右任創辦《民立報》,這是一份革命色彩濃厚的報刊。隨后1912年,張季鸞又從南京報道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事件,并且拍專電給上海,這是民國成立后第一條新聞專電。在于右任的推薦下,他擔任南京臨時政府秘書。待孫中山辭職,張季鸞短暫的政界生涯結束,與于右任在上海創辦民立圖書公司。1913年,張季鸞和曹成甫在北京創辦《民立報》,同時他兼任上海《民立報》駐北京通信記者,開始與袁世凱斗爭。張季鸞在上海《民立報》發表袁世凱非法簽訂《善后借款合同》,掀起大波,成為二次革命導火線。袁世凱因此怒封北京《民立報》,張季鸞被迫入獄三個月之久。1915年,張季鸞在上海創辦《民信日報》,抨擊袁世凱,后來任政學會機關報《中華新報》總編輯。1918年,因為《中華新報》及北京其他一些報紙聯合揭露段祺瑞內閣非法簽訂“滿蒙五路中日借款合同”,張季鸞再次被捕入獄,出獄后在1919年任上海《中華新報》總編輯,后經營不善停刊。
然而,真正塑造張季鸞的是《大公報》,張季鸞可以說是《大公報》的靈魂。新記公司《大公報》于1926年9月1日正式復刊,由吳鼎昌出資,張季鸞任總編輯,胡政之為經理,三足鼎立,共同經營,并且制訂了規章制度。第一,資金由吳鼎昌一人籌措,絕不募款。第二,三個人在三年內不得擔任任何有俸給的公職。第三,吳鼎昌任社長,張季鸞任總編輯及副總經理,胡任經理及副總編輯。第四,三個人共組社評委員會,少數服從多數,意見各不相同,則服從張季鸞總編輯。第五,張季鸞、胡政之勞力入股。根據當時的社會形態,政治勢力群雄爭霸,《大公報》只有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場,才能站穩腳跟。因此,張季鸞提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字方針,相輔相成,辯證統一。“不黨”指的是純以公民的立場發表意見,不代表、不庇護任何黨派;“不賣”指不接受帶有一切政治性質的金錢補助,也就是不接受政治方面的人入股入資;“不私”指的是報紙不能私用,必須面向全國開放,成為群眾之喉舌,這也是《大公報》中“大公”的很好體現;最后“不盲”指的是不盲從、不盲信、不盲動、不盲爭的理念,《大公報》也確實打破了傳統通訊社待家守夜的陋習,建立了全國性的站點記者,包括特派員、通訊員的新聞采寫。
但也有種說法表示,張季鸞的“四不方針”具有很大的欺騙性,讓所有人誤認為《大公報》是一家超黨派的“客觀公正”報紙。發表這種觀點的人也許揪住了張季鸞與蔣介石私交甚好。事實上,《大公報》社評采取不署名制,張季鸞對自己的文章不珍惜、不留底稿也不收集,能確認出自他手里的社評為數不多。張季鸞起初就是立言“反蘇,反共,也罵蔣”的原則,發表眾多社評。關于觸及國民黨的現行政策,張季鸞為了維護國民黨的統治,對國民黨進行批評,具有“恨鐵不成鋼”“小罵大幫忙”的意思。這其中也是因為張季鸞與蔣介石私交甚好,文人氣質彼此欣賞。蔣介石的現行政策符合張季鸞的政治理想,兩人不謀而合。《大公報》夸耀的“文人論政”是在國民黨許可的限度,歸根結底是為蔣介石的統治幫忙的。張季鸞最終成為蔣介石的謀士與“諍友”。蔣介石懂得讓《大公報》保持“獨立”的外表,又使自己收到“小罵大幫忙”的實利。九一八事變以后,蔣介石要于右任打電話給張季鸞,支持不抵抗政策,張季鸞決定宣傳“緩抗”,為此《大公報》館被投了炸彈。1934年,蔣介石在南京勵志社大宴群僚,首席主客是張季鸞,張季鸞儼然成了蔣介石的顧問。“士為知己者用”的封建思想在張季鸞腦海中根深蒂固,其人生信條之一也是“報一切恩”。蔣介石對他有知遇之恩,抗日戰爭爆發以后,張季鸞更加擁護蔣介石,到了個人迷信的程度。他曾說:“國家局面無論多么困難,我一見到蔣先生就覺得有辦法。”
周恩來評價張季鸞:“他在推動中國資產階級報紙,特別是報紙評論的發展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因此,稱他為中國資產階級的一代報人并不過分,他應在中國新聞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 編輯委員會.新聞界人物(一)[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105-137.
[2] 王芝琛.百年滄桑[M].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6:98-126.
[3] 文昊.民國的報業巨頭[M].北京:中國文史版社,2013:45-76.
G219.29
A
1674-8883(2016)12-007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