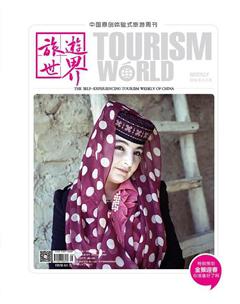春節,我們的文化胎記
蕭放
唐朝一句詩:“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每年20 億人次的春節人流涌動成為當代中國一大民俗景觀。人們雖經歷了買票、奔波、擠車、嘈雜等種種“磨難”,返鄉熱情卻絲毫不減。
說春節是特殊的文化現象,是因為它不像普通的生活方式,可以簡單替換或改變。春節負載著厚重的歷史積淀和情感聚合。舊時北京人過年時要吃荸薺,荸薺諧音“必齊”,說的就是新年團聚之意,因此,即使沒有回來的親人,也要給他擺一副碗筷。
從一個角度看,人是群居的社會動物,除了一般的生理滿足外,還尋求文化與心靈的歸屬。在信奉基督耶穌的西方社會,人們以圣誕作為最盛大最神圣的節日,他們在圣誕這一天的儀式中獲得精神愉悅。
而中國人的春節與西方的圣誕有著同樣的文化功用,只是春節人文倫理色彩更厚重,人們要奉祀祖先,親人要聚會歡樂,人們的精神在親情的浸潤交融之中得以升華。
春節是由古代的豐收祭祀活動演變來的。上古以作物成熟為時間標志,隨著歷法的進步,年成為四季輪回的周期。過年就處在新舊年交接的節點上。新舊時間更替的過程,在古代人的心目中,是一個由緊張到放松,由嚴肅到喜悅的過程。
年前擔心舊的不去,所以要采取多種措施進行驅趕,并設定了許多禁忌,進行身心防備。防備的主要方式就是家族的老小團聚,用集體的力量,抗拒威脅。爆竹、火、紅色門聯等起初都有巫術的意義。年后則是慶祝新生,互相祝賀。
春節是農耕社會時間節奏的產物,符合中國人“平靜的激情”之性格,超常而世俗,喧鬧而溫情。
近代以后,中國社會逐漸發生變化,西方的時間體系進入中國,春節是在公歷元月1 日被定名為元旦之后而得名的,古代的年節本來就叫正旦、元日。傳統年節名稱的改易,雖因立春節氣的貼近與傳統習俗的延續而不顯突兀,但現代時間體系對傳統的沖擊已經開始。
但這次沖擊來自外部的強制,是觀念的灌輸,歷史記憶的慣性很難靠外力在一瞬間滌蕩干凈。因此只要外部環境稍稍放松,歷史的記憶就會復蘇。改革開放初期,春節傳統的復興就是如此。
隨著中國社會由傳統進入現代進程的加快,春節終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真正沖擊,這次沖擊來源于社會結構內部。
傳統農業社會賦予春節的種種實際的文化效用,在現代工業社會與信息社會中出現了弱化與傳承的困難。同時伴隨著西方物質文明進入中國的是西洋的生活方式,洋節流行,一些時尚青年可以送圣誕禮物,但卻吝嗇春節的祝福。雖然這其中大多是時尚好奇,不一定形成為民俗,但的確在消解著傳統的春節民俗心理。
在當代社會,我們對待傳統的態度經常處在彷徨之中,回歸? 告別? 還是在回歸中告別? 在告別中回歸? 我們的社會是矛盾的,我們的心情是復雜的,我們能否找到一條適合民族文化的中庸之道,真的令人費盡心思。
春節關聯著我們的民族情感,春節成為我們文化的胎記。我們進入現代社會,享受科技進步的便利,并不一定要以拋棄傳統,特別是以主動拋棄傳統為代價。傳統與現代并不天然為敵,傳統的智慧與情感反而可以作為現代社會建設的文化資源。傳統雖然作為整體的文化體系終究會被打破,但其中仍有許多有價值的文化片段,可以作為我們連綴當代精神生活與社會生活的金縷玉片。尤其是如春節這樣的民族文化節日,它有著獨特的時間優勢,在冬盡春來這樣一個自然時節,人們就著天時的便利,舉行各種年節的儀式,重溫著家庭親情,協調著人際關系,放松身心,脫離緊張忙碌的現代生活節奏,回歸傳統的悠閑。春節傳統內涵的傳承與擴展,對于現代社會來說不僅在文化建設上具有正向與健康的意義,就是從經濟社會角度考量,也是難得的商機,旅游業、交通運輸業、商業、娛樂業等都充分利用了春節人們的消費心理,取得了良好的收益。
當然,春節傳統中也有需要調整更新的因素,祈求神靈的意識應該淡化,繁瑣而耗費資財的祭神儀式以及鋪張浪費應該減少,但春節中禮拜祖先與團聚親人、休閑娛樂與聯系鄉誼的傳統習俗卻應該保持與傳承。家族文化是中國倫理文化的基礎,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傳遞的重要空間,年節期間,家人團聚,交流親情,回首過去,籌劃未來,這樣的節日氣氛,這樣的節日文化,對于整個社會的安定和諧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現代社會時間機器的操縱之下,人們的日常生活匆忙而功利,人們的精神焦慮而孤獨,我們不妨在民族節日中對禮儀的、象征性的、細微而溫情的文化事項中多加強調與提倡——即使你的這一年過得平淡和無趣,還有春節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