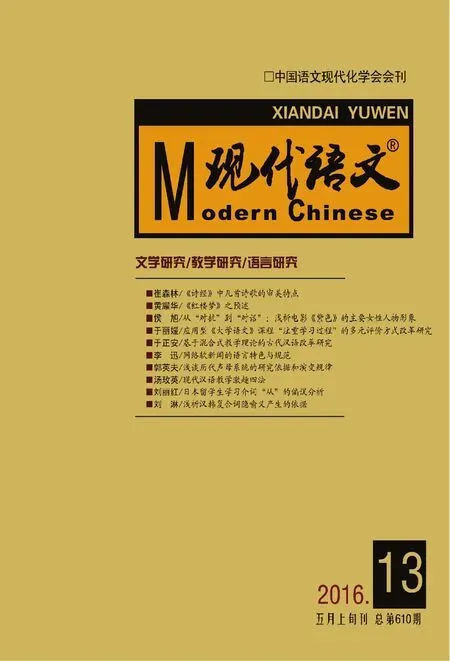從映照現實到揭示存在
——論嚴歌苓《床畔》的英雄敘事
○陳琳琳
從映照現實到揭示存在
——論嚴歌苓《床畔》的英雄敘事
○陳琳琳
嚴歌苓新作《床畔》延續了她軍旅題材小說中的英雄敘事,以象征主義手法復寫了《雌性的草地》中英雄理想幻滅的主題。嚴歌苓試圖通過展示英雄在時代變遷中被樹立、被崇拜、被誤讀、被遺忘的過程,呼喚英雄的回歸,卻又深感時移世易,無力挽回,因而小說又帶有一定的存在主義意味。《床畔》是對嚴歌苓英雄敘事的一次回望與總結,在呼喚英雄主義的同時,回避了對英雄內涵的構建與反思,體現出作家對英雄價值觀念與當代語境的疏離。
嚴歌苓 《床畔》 英雄敘事 存在主義
嚴歌苓2015年的長篇新作《床畔》(首次發表時名為《護士萬紅》)講述了一個“不識時務”的護士萬紅的故事。護士萬紅主動請纓照顧已是植物人的英雄張谷雨,她在細致入微的觀察護理中與張谷雨產生了心靈感應般的精神溝通,半生守護在病房床畔,遭受著他人的質疑與不解。小說以高度象征的方式展示了當代英雄被樹立、被崇拜、被誤讀、被遺忘的過程,呼喚英雄的回歸,也表達了個人的無力感,因而具有某種存在主義意味。
英雄敘事是嚴歌苓創作伊始便存在的主題,帶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和強烈的個人印記。她創作的一系列軍旅題材小說,形成了尋找英雄、否定英雄、反思英雄的完整主題序列。嚴歌苓這樣解釋《床畔》的創作動機:“《護士萬紅》并不是我采集來的一個故事,而是我在脫下軍裝二十多年后一直想表達的一種軍人精神。軍人精神的核心無疑是英雄主義。”[1]因此這可以看作是她對英雄敘事的回望與總結。
與古希臘羅馬神話傳說中個性豐滿、有著七情六欲的英雄人物不同,“十七年”文學英雄形象往往與日常生活極端疏離,被抹去了人的正常情感和欲望,呈現出“純粹化”和“神圣化”特質,為迎合主流話語的要求而帶有傳奇或夸張色彩。尤其是“文革”文學“三突出”原則要求“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來;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來;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即中心人物來。”[2]樣板戲和樣板小說中的英雄人物被提純成為政治符號,成為無懈可擊、完美無缺的典范。改革開放后,作家們以“人性”為切入點對英雄和英雄主義進行反思,打破了神化英雄的寫作理念,“在70至80年代轉型期乃至整個80年代,圍繞著‘人性’‘主體’等問題的人道主義表述,無疑構成了最為醒目且持續時間最長的一組話語形態。這些在不同的領域和不同的話語脈絡上展開的表述,分享著共同的中心化主體的想象,即在普泛意義上將‘個人’視為絕對的價值主體,強調其不受階級關系、社會歷史限定的自我創造屬性。”[3]與同時代的人本主義思潮相呼應,嚴歌苓以書寫和平年代部隊生活的“軍旅三部曲”步入文壇,開啟了對英雄主義的探尋。
嚴歌苓“軍旅三部曲”側重表現集體主義與個體價值的沖突,展現英雄人物身上感情的糾葛與人性的復歸。“不論以個體存在的英雄或以群體出現的英雄,其思想性格中既有集體主義觀念也有個性主義意識,雖然兩者偶爾也會有沖突,但它們互為統一才構成了英雄的整體精神風貌。”[4]《綠血》和《一個女兵的悄悄話》塑造了英勇仗義的楊燹、成熟理性的王掖生等青年軍人,通過女主人公的自白,肯定了他們“標準軍人”的身份,表現了他們身上集體意識與個性意識的沖突與磨合。《雌性的草地》中以沈紅霞為代表的牧馬班女戰士,在政治理想的指引下消耗著青春年華,在荒僻險惡的草原上執行放牧軍馬的荒誕任務,被解散后竟陷入了無所適從的心理處境,集中表現了集體意志對于個體價值的抹殺。楊燹、沈紅霞都是內心理念的堅定追隨者,甘愿舍棄個人欲望甚至生命來踐行理想,他們身上的神性超過了人性、超我壓抑了自我和本我,延續了十七年時期發端的“理念英雄”形象。王掖生舍命救下陶小童的壯舉,則摻雜著對陶小童的愛戀,不再純粹是犧牲奉獻精神的產物。而在女子牧馬班指導員“叔叔”身上,已經看不到太多意識形態的影子,其行事方式遵從于生存的自然法則,突破了秩序對于情欲的禁錮,是一個充滿原初本真力量的自然人,也是草原真正的主人,在他的身上集中體現了“人性英雄”的審美觀念。
1990年代初期,一批描寫和平年代軍人世俗生活的“大院小說”紛紛涌現,集中展現了市場經濟浪潮對軍營生活的影響,將軍人拉下神壇,還原了他們作為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在權勢或情欲的驅動與誘惑下,他們或振作或清醒,或頹唐或沉醉。才華因此而變質,人格因此而萎縮,個性因此而扭曲。”[5]此時已赴美留學的嚴歌苓,也開始將經典的戰爭英雄置于和平背景下,從對英雄精神的建構轉向了反思與批判。在1992年的《草鞋權貴》中,開國元勛程在光戰功卓越、躋身權貴,在和平年代延續著首長的專斷作風,把程家大院變成了一個黑暗壓抑的封閉牢籠;他以老前輩的姿態向小保姆霜降施加威權,在教她書法時伺機猥褻,甚至赤身裸體把她叫到浴室,打著革命傳統教育的幌子講解自己的傷疤。權力和欲望的膨脹,徹底顛覆了程在光的英雄身份,揭開了遮蔽在神圣光環下的凡人肉胎,他的意志不再是崇高價值和意識形態的代表,而是蛻變為肆意張揚的世俗欲望。
在完成解構英雄的“弒神工程”之后,嚴歌苓似乎停止了對英雄的直接關注,轉而向移民故事、文革歷史、社會現實等題材開疆辟土。此后以抗戰為背景創作的《第九個寡婦》《金陵十三釵》和《寄居者》等作品,雖然也塑造了公正仁義的孫懷清、壯烈赴死的金陵妓女、滿懷人道主義精神的杰克布等人物形象,延續著對英雄主題的書寫,但這種新歷史主義的書寫顯然不是她的創作重點。直到《床畔》,嚴歌苓才又重新開啟了她的英雄敘事,用這個自1994年就開始構思的故事接續了早期作品中的英雄主題。不過,與此前頗具現實性的英雄敘事相比,《床畔》更像是一種符號化的理念思考,帶有一定的存在主義意味。
以薩特為代表人物的存在主義哲學,從反對本質主義的基點出發,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質”的命題,主張“人可以做任何選擇,但只是在自由承擔責任的高水準上。”[6]1980年代,存在主義進入中國大陸,“為當時的先鋒作家和文藝理論提出‘人學’的問題形成了一個有力的思想參照系。”[7]在存在主義以個人精神為核心的價值取向影響下,“個人性的境遇與價值開始代替啟蒙主義的‘社會正義’與‘公眾真理’而成為人們思考問題的新的基點。”[8]雖然嚴歌苓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存在主義思想的影響難以證實,但是她偏愛在極端環境中展現人性可能呈現出的極致面目,與存在主義文學的創作主張不謀而合;她將文學作為探索人類生存的方法,通過關心具體人在各種生存境遇下的種種體驗,呈現人性無限豐富的可能性。作為其英雄敘事作品的總結之作,《床畔》無論是在主題還是形式上,都與存在主義的文學觀念有著某種契合。
一、側重揭示荒誕的生存境遇
《床畔》不僅是一部呼喚英雄主義的回望之作,更是一部關于英雄處境的現代寓言。張谷雨是一個舍己救人的經典英雄,得到了官方話語的認可與推崇,卻以植物人的身份呈現,不僅失去了行動能力,更失去了表達自我的話語權,幾乎完全是一個概念式的存在。人們敬仰他、贊美他、利用他,把他當作一筆巨大的政治遺產,獲得了豐厚的利益回報,但從來不承認他身上表現出來的心理活動和情感反應,或者說拒絕承認他真正的人性。萬紅試圖證明張谷雨不是植物人,卻始終被周圍的人視為笑談。二人同樣不被理解和認同,只能在精神上依靠彼此對抗孤獨,成為了社會環境荒誕面目的見證者和承受者。
這種荒誕感集中體現在二人英雄身份的“命名”中。張谷雨是通過體制機制的追認獲得的英雄身份,萬紅成為英雄則是因為陳記者的報告文學引發的社會反響。在這個過程中,英雄概念的所指與能指發生了錯位與置換,英雄身份僭越了其所代表的理想精神本質,代替它發揮了各種各樣的政治功能,其背后是權力機制與宣傳話語的合謀。二人英雄人格中本應被弘揚的部分,只能得到政治話語形式上的認可;萬紅將為張谷雨正名的希望寄托在陳記者身上,也只能是一廂情愿。政治命名對二人英雄身份的肯定,并非對其真實存在狀態的認可,換句話說,決定他們是否存在、怎樣存在的不是個體的真實狀態,而是社會話語先入為主認定的現實,這就構成了關于存在主義思想中“存在”與“本質”關系的隱喻。因此,張谷雨和萬紅的處境不僅是經典英雄在新時代中的處境,也是人在基于本質主義的社會話語中無法確認真實存在狀態時的處境,反證了“存在先于本質”的命題。
二、著力表現英雄個體的自由選擇
存在主義認為,人在本質上是自由的,人通過自己的選擇才能不斷造就自我的本質。“但事實上,客觀現實往往不容許人有絕對的自由,不容許人超越自己生存的環境。這就意味著人必須為自己的選擇承擔一切責任。”[9]萬紅因為堅信張谷雨仍具有普通人的感知與情感,不斷為他爭取更好的醫護條件,并為此放棄了深造的機會和個人的婚姻幸福,顯露出處處“不合時宜”的偏執與擔當。甚至在張谷雨因轉院的波折停止呼吸之后,她仍延續著自己的執著,主動請纓照顧另一個植物人戰士,甘愿成為醫院遺址中的“最后一個嬤嬤”。從常理上看,萬紅幾乎是陷入了自己內心的魔障而不得自由,但是從存在主義哲學的角度看,這種近乎偏執的堅守恰恰是她自主選擇的結果,是其個人自由意志的表現。這種在艱難處境中自主選擇承擔責任的行為,表達著絕望者的希望,使得生命獲得了意義。
《床畔》續寫了《雌性的草地》中英雄理想幻滅的主題,同時為萬紅這種悲壯而孤獨的堅守保留了一份呵護與包容。嚴歌苓讓萬紅擔當起傳遞理想信念的旗手,幾乎把她寫成了《雌性的草地》中沈紅霞的翻版。萬紅拒絕放棄張谷雨的意識體征,一如沈紅霞拒絕相信鐵姑娘牧馬班被解散的命運;萬紅在張谷雨身邊輕聲的呢喃,與沈紅霞同草原深處女紅軍孤魂的邂逅如出一轍,都是內心理念的一種外在投射。二人的主觀意志在反復的自我強化中,產生了強大的內驅力,推動她們奔向理想信念,成為理念上的英雄人物。感情、欲望、痛苦、性別差異等人性的基本面,都在這個宗教般的“凈化”過程中被抹去。不過相比而言,沈紅霞的信念主要是來自意識形態的宏大話語,客觀上呈現出對現實的反思與批判;萬紅的信念則是對經典價值觀的追溯與堅持,代表著永恒意義上的英雄精神。在《雌性的草地》里,作家以女子牧馬班的解散直接宣告了沈紅霞理想的荒誕與破滅,并且讓敘事人跳出敘事話語,注視著沈紅霞的徘徊與迷惘,呈現出理性批判的立場。《床畔》卻對萬紅執著與堅守的邏輯基礎不予置評,所有關于張谷雨的生理心理反映的描述都出自萬紅的主觀視角,對張谷雨是不是真的植物人,則產生了信則有、不信則無的多義性,更加突出了萬紅“自由選擇”的積極意義。
三、將文學作為思想理念的表達
出于“存在先于本質”的基本立場,存在主義文學對傳統文學的“反映論”提出質疑,透露出鮮明的哲理探索傾向。“它否定藝術的認識作用,認為藝術家的目的僅僅是創造自己的世界,表達自己的哲學思想和自己的感受,而不是藝術地再現客觀世界。”[10]這就導致作品人物成為思維推演中的邏輯符號,其自身性格的典型性和行為邏輯的客觀真實性都不再是關注的重點。《床畔》同樣采用了這種高度符號化的寫作方式,嚴歌苓自己就說,“這是一部象征主義的小說,年輕女護士堅信英雄活著,象征她堅信英雄價值觀的不死。”[11]為了直接表達這一命題,嚴歌苓簡化了人物的身份性格,通過特點鮮明的扁形人物設置戲劇沖突,快節奏地推進敘事過程,使讀者在跌宕緊湊的情節發展中直奔主題、抓住要旨。這部小說也因此在邏輯上抽象、細節上真實,雖有長篇小說的篇幅,情節卻只相當于中篇小說的容量。
“堅守信念”這一行動,幾乎可以概括《床畔》的全部情節。萬紅以巨大的犧牲奉獻和力排眾議的堅持,為自己贏得了一種夸父逐日、愚公移山般的壯美。實際上,苦難并不直接產生價值,但自虐般的磨礪確實能夠讓人得到一種崇高感,甚至是精神上的優越感。在經典革命敘事中,這種壯美往往被意識形態宣傳放大,通過集體話語的認可,達到一種非理性的狂熱,沈紅霞便是這樣的例子,她曾經的自我懷疑被宏大的集體話語裹挾,阻止了對信念本身更加深入的思考,導致了不計成本、不惜代價的付出。《床畔》則試圖為萬紅的堅守尋找情感上的邏輯支撐,萬紅在護理張谷雨時產生了一種近似愛戀的情愫,其中摻雜著對英雄品格的傾慕、對職業道德的堅守,以及對男性知己的依戀,這種感情符合嚴歌苓的軍人情結,也是她早期作品中女主人公對英雄軍人的感情,是對她心中那個“營長夢”的一次回望和總結。不過,如此歸因也使得《床畔》避開了價值層面的深入探討,一方面通過突出“信念”的情節功能營造出一種悲壯感,一方面在發掘“英雄價值觀”具體內涵的命題上止步不前,僅僅成為了一個指向鮮明、邏輯簡單、情節緊湊的寓言故事。
嚴歌苓創造了萬紅這一理念英雄的當代符號,卻回避了對其英雄理念內涵的深入發掘。即便她在《床畔》后記中闡明了自己對英雄的理解,但單就作品文本來說,這種英雄精神并沒有得到合乎邏輯的展現,使得作品發表后引起了一些批評者的質疑。不少評論者注意到作品中“人物身份與角色功能的錯位”[12],指出其人物性格的失真,便可以看作是基于現實主義反映論的“誤讀”。不過如果從存在主義文學的角度看,無論張谷雨是不是真正的植物人,萬紅對堅守的選擇都不必受到“典型論”下人物性格發展邏輯的牽絆,在作家創作意圖的強力干涉下便可以自圓其說。
從“軍旅三部曲”到《床畔》,嚴歌苓對英雄的書寫由反映人與現實的關系出發,漸漸傾向于抽象理念的表達,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從生動描繪變為簡筆刻畫,暗合了存在主義文學的一些基本主張,其背后則是社會語境的復雜變遷。21世紀以來的中國社會,已經脫離了啟蒙話語下的二元對立思維,呈現出繁復紛雜的多元價值取向。與之相應,對英雄內涵的理解也早已不存在標準答案,無論是“十七年”文學中的紅色英雄,還是啟蒙話語中的人性英雄,都在價值觀的層面遭到冷遇。幻滅的英雄理想,使得嚴歌苓筆下的傳統英雄最后大都處于無處安葬的僵死狀態:沈紅霞變成了草原上的又一個孤魂,指導員叔叔被狼群吞噬,徹底消失,程在光、張谷雨則以植物人的方式延續生命。而作家本人也由對英雄人物進行建構性塑造、宣揚某種特定的英雄精神,退守到“呼喚英雄主義”的簡單命題上。“萬紅并不否認應運而生的其他種種英雄價值觀,但她永遠不放棄以張連長為代表的舍己救人的英雄價值觀。”[13]這種消極自由的態度,實際上是作家無法正面回應當下社會多元價值話語的結果。嚴歌苓長期旅居國外,與三十多年以來的中國社會相對疏離,她近幾年來當代題材的創作,主要是以某個社會事件為基礎加上個人的想象與演繹,同時通過體驗生活來充實細節。這使得她難以把握更加復雜的社會圖景,因此只能在關于存在的理念探討中,劍走偏鋒劃出一道鋒利的創口,一再提醒人們注意到英雄末路的刺痛。
注釋:
[1]嚴歌苓:《〈床畔〉后記》,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2015年版,第264頁。
[2]于會泳:《讓文藝舞臺永遠成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陣地》,文匯報,1968年5月23日。
[3]賀桂梅:《“十九世紀的幽靈”——80年代人道主義思潮重讀》,上海文學,2009年,第01期,第88頁。
[4]朱德發:《革命文學群己對立英雄觀辨析》,河北學刊,2005年,第06期,第77頁。
[5]朱向前:《軍旅人生小說》序,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頁。
[6]周煦良,湯永寬譯,[法]薩特:《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頁。
[7]錢翰:《存在主義的中國之旅》,法國研究,2011年,第03期,第22頁。
[8]張清華:《從啟蒙主義到存在主義——當代中國先鋒文學思潮論》,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06期,第137頁。
[9]何勝莉:《世界的荒謬與個人的孤獨——淺析存在主義文學觀》,成都電子機械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6年,第04期,第100頁。
[10]何勝莉:《世界的荒謬與個人的孤獨——淺析存在主義文學觀》,成都電子機械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6年,第04期,第98頁。
[11]嚴歌苓:《床畔》后記,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2015年版,第267頁。
[12]歐陽光明:《嚴歌苓還要在寫作的歧路上狂奔多久——從〈護士萬紅〉說開去》,南方文壇,2015年,第04期,第22頁。
[13]嚴歌苓:《床畔》后記,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2015年版,第267頁。
(陳琳琳 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 273165;濟寧市委統戰部 27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