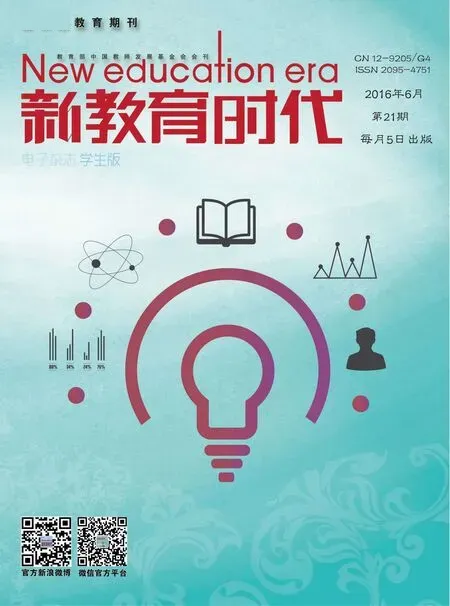生態批評視域下楊利民戲劇創作探討
劉春艷
(公主嶺市戲劇創編室 吉林公主嶺 136100)
生態批評視域下楊利民戲劇創作探討
劉春艷
(公主嶺市戲劇創編室 吉林公主嶺 136100)
生態意識是維護社會發展的基礎,強調其整體運動規律和對人的綜合價值效應,要求把人對自然的改造限制在地球生態條件所容許的限度內,反對片面強調人對自然的統治,反對無止境地追求物質享樂的盲目傾向。楊利民出生在黑土地上,黑土情結給了他陽光、空氣、力量、動力,他把這稱為“自己的陽光和空氣”。一定的地域環境和自己的生活經歷,加上西方兩位著名戲劇家的影響,使他的劇作中不斷出現自然風情、生命本真、詩意之美,并逐漸引起關注。
生態批評 視域 楊利民戲劇創作
引言
楊利民這個新時期極具有影響力的劇作家,憑借著他對石油大地的滿腔熱愛,憑借著他內心的淳樸與本真,憑借著他對這個時代特有的敏感,寫出一部部引人深思的優秀劇作。究其話劇的成就,其中之一就在于對荒原、風雪及月亮意象的運用上。劇中常常通過意象渲染氣氛、勾勒外部環境、表現劇作深刻的主題,進而表達悲劇意義,表現人物的精神品質,引發讀者思考。[1]
一、楊利民生態戲劇的審美表現
1.物我交融的意境
在楊利民的戲劇作品中荒原意象的運用與作品主題相契合,人們眼中的荒原是寂寥、痛苦的,長期在這樣的環境下生存會給人們的心靈造成嚴重的傷害。在荒原中,物質匱乏、交通閉塞、生存環境惡劣等一些列問題隨之而來,人們只能通過盲目的工作、一味的妥協來度過生活。在楊利民的戲劇作品中,往往通過荒原意象的運用使得人們由失望變成希望。[2]
話劇《大荒野》非常善于將天然風景襯托人物心靈,天然美與人主體的心靈美融為一爐,情景相融。這四幕劇是以四季的順序為線索進行的。每一幕各以春夏秋冬構成其獨特的自然景觀:
春:動物從冬眠中醒來,小草從土地中鉆出來,藍天、白云、青山一切都是充滿生機,一片和諧,春意盎然。
夏:色彩紛呈、生命在此勃發,朝氣蓬勃。
秋:秋高氣爽、碩果累累。生命走向成熟,輝煌。
冬:藍藍的天空、白皚皚的雪,寒氣凜冽,萬木蕭瑟。生命走向盡頭。
春天,生機勃勃。大荒野上在生命即將走到盡頭的兩位老人相遇了。他們由于對彼此的相互關心、對生活的獨特體驗、對生命的共同認識,他們之間便擦出了愛情的火花。夏天,絢麗多彩。此刻,人的生命,人的情感與“夏”的生命律動和諧共振。生命與自然同在,情與景相生。不知是老梁頭與牧牛婆的情愛點燃了夏的靈性,還是夏的靈性孕育了這美妙而深沉的愛情。[3]
秋天,金光閃耀。所有在春天與夏天收獲到的東西在秋天將會做一個篩選,是去是留,哪些東西應該舍去,都是要考慮的問題。老梁頭與牧牛婆經過夏天風雨的洗禮,兩顆心被擾亂了,再也無法安定下來,他們互相牽掛,互相期盼,他們也曾幻想過,然而終究因為傳統倫理道德的樊籬,他們像老酒一樣醇美的感情未能越過夏的深沉,在深秋時節分手了。
冬天,白雪皚皚。老梁頭還想和牧牛婆在一起,于是他帶著對荒野深深的眷戀,帶著給自己定的清規戒律,離開了他度過大半輩子的大荒野。他沒有成名,也沒有受過一次表揚,他沒有實現自己的愿望,就走了。但是他走的并不悲傷,而是走的坦蕩,走的磊落,雖死猶生。老梁頭的精神與大荒野同在。就像冬天一樣,雖然萬物沉寂,但是,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4]
老梁頭的生命價值還會在春之聲中生根發芽,在夏之光中怒放,在秋之韻中結果。自然生生不息,生命還在延續,精神代代相傳,這就是春夏秋冬的抒情。
2.質樸與靈性的語言表達
楊利民的劇作十分注重對戲劇氛圍的烘托。他常在劇作中增加一些獨特的地域歌謠烘托戲劇氛圍,歌謠是每個地方所特有的一種語言表達方式,每個地方有獨特的表達方式,在東北,歌謠與博大、蒼涼的景觀融合在一起,達到情景交融的戲劇效果。
《黑草垛》中則是用歌謠的手法為我們營造了悲涼的氣氛。老瞎子雖然不是這部戲劇中描寫的一個人物,但是卻通過從他的側面描述奠定了該劇的情感基調,老瞎子的妻子和兒子被土匪給殺害,現在孤苦伶仃,只有兒媳婦與他相依為命,他是讓人同情的,他也注定孤獨,但是他孤獨的時候會唱一些歌謠來排遣:“老來難啊老來難,人到老時惹人煩。從前看著別人老,而今輪到我面前。耳聾眼花難分辨,生生死死兩可間。老年喪子多凄慘,臨終喪妻最孤單。”
當他發現兒媳婦香草有事隱瞞他的時候,他就想到自己孤身一人,妻子和兒子也被土匪殺害,種種慘狀浮現在腦海中,他不禁悲痛起來,又唱起了《老來難》。這首歌謠突出了他的苦痛與悲傷絕望。當他得知香草和小山東都被官兵所包圍,在大火中死去的消息后,老瞎子孤苦無依,用一曲古老歌謠表達了他凄涼無助的心境。
語言的描寫是評價劇本好壞的重要因素,劇本的語言如果平平淡淡,沒有特色,那他不能稱之為好劇本,好的劇本中作者會對其語言下很大的功夫,其中有一點就是風趣幽默,這種語言的運用會使觀眾、讀者、作者、作品這四者融為一體,達到觀賞的效果。而想要達到風趣幽默,就要使語言具有機趣性。所謂“機趣性”則是所描寫的語言側重于修辭方面的表現,即:化俗為雅,雅中帶俗,語言尖新,詩意情趣。楊利民創作的話劇吸取了戲曲的化俗為雅、雅中帶俗的特點,語言尖新,在詩意情趣方面頗有特色,使其語言生動、幽默機趣,頗有東北地域風格。
結語
從楊利民的戲劇作品中我們能夠感受到作者對于大自然與黑土地的熱愛,“人出于自然而又回歸自然”,自然養育了我們,自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讓人敬畏的,人只有與自然和諧共生才能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正是出于對黑土地的熱愛,楊利民在他的作品中有許多表現自然的主題,在生態危機日益嚴重的今天,楊利民緊跟時代的腳步,追隨著社會的發展,他的作品里展示了當代社會進程中自然生態失衡的重大問題,表現了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人與自我、人與自然之間嚴重失衡的問題,表達出想要回歸自然、救贖人類的崇高理想。
[1]楊利民.楊利民劇作集上冊[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
[2]楊利民.楊利民劇作集下冊[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
[3]伊波利特·丹納.藝術哲學[M].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9.
[4]劉文良.范疇與方法生態批評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