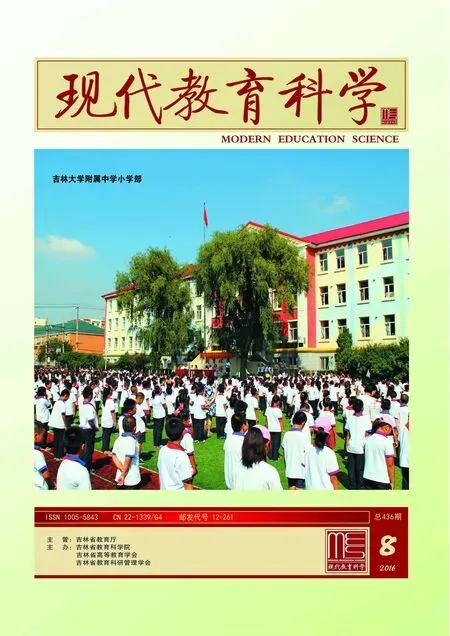高校教師跨學科研究:學科文化的阻力分析
顧沈靜
(浙江師范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浙江 金華 321004)
?
高校教師跨學科研究:學科文化的阻力分析
顧沈靜
(浙江師范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浙江 金華 321004)
跨學科研究是當代社會問題日益復雜化催生的產物,對于解決疑難問題、創新科學知識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以單一學科建制為主的學科文化,由于學科語言的獨特性、學科價值觀的差異以及學科研究方法的差異,削弱了高校教師參與跨學科研究的積極性。究其原因,高校教師對跨學科研究的必要性缺乏認識、傳統的院系制、過于明晰的學科邊界以及單一的評價方式等方面,通過厘清不同學科文化之間的關系、創設交流平臺、引導教師樹立正確的學科文化融合觀以及促進評價方式多樣化來減少跨學科文化中的學科文化阻力。
高校教師 跨學科研究 學科文化 阻力
文化對人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學科文化對于高校教師的影響更為深遠。學科文化的概念中包括學科語言、學科價值觀、學科研究方式、學科評價方式等基本要素。高校教師在獲得這一身份之前,已接受了很多年有關某一學科的語言、思維方式、研究范式等內容的訓練,對于特定的學科文化有較深的認同感。目前在高校流行的以單一學科建制為主的學科文化的形成,使高校教師對其他學科文化產生不同程度的排斥感,從而導致學科文化限制了高校教師跨學科研究的積極性、主動性以及可行性。
一、學科文化對高校教師參與跨學科研究的阻力表現
跨學科意味著“兩門或者兩門以上不同學科之間的相互聯系,從思想的簡單交流到較大領域內教育與研究的概念、方法、程序、認識論、術語、數據以及組織之間的相互聯系”[1]。因而,跨學科研究是一種集合多種學科的研究,目前以單一學科建制為基本單位的院系制對高校教師參與跨學科研究存在著重重阻礙。
(一)學科語言的獨特性使不同學科教師溝通交流困難
語言是人與人進行溝通的基礎。學科語言主要包括兩層含義:學科術語與學科措辭[2]。學科語言是形成學科邊界的重要一步,同一領域的學科或同一學科的語言對于本學科領域內的教師認同有著重要影響。通常情況下,不同學科的專業用語是不同的,例如物理學領域內的“道爾頓定律、范德華方程”、化學領域內的“同離子效應”“價鍵理論”、哲學領域內的“易謬主義”“第二世界”、心理學領域內的“解離認同失常”“紋理遞變度”等,對不屬于這一學科領域的高校教師來說,很難理解其他學科的專業術語,異質程度越大的學科,教師越難理解對方領域內的學科語言。
這種語言隔離可以歸因于學科規訓制度。學科規訓制度是為了維護其學科文化和學科地位,并通過傳播學科價值觀使得一部分人追隨和繼承這種規訓。高校學科教師是受過了一系列專門的正規的學科訓練,才成為某一領域內的教學者。正如萊喬恩夫伍德描述的那樣:“年輕的經濟學家,或‘畢業生’,直到他制造出一個‘模型’,展示了一定程度的‘技藝’,為他當學徒所在學科的長輩們認可,他才被承認進入該學科。”[3]高校專業教師能夠成為這一門學科的教授者是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專業訓練的,因此對本學科的認同感會較高,而對于其他學科則就容易產生排斥感,進而也排斥其他的學科進入本學科內或與本學科融合。因而,面對難以理解的學科話語,高校教師對跨學科的研究往往是望而卻步。
(二)學科價值觀的差異易導致不同學科教師的沖突
價值觀作為一種觀念,其實質是一種價值評判和價值選擇的標準[4]。學科的價值取向則決定了有關學科主體的行為目標和活動范圍,即決定了高校教師在學術領域內的行為目標和活動的領域,來自不同學科領域的教師對于學科應持有的價值傾向有時有著較大的差異。正如斯諾在其著作《兩種文化》中提出,西方社會的智力生活分裂了人文學者和科學家。兩種文化之間缺乏理解性,甚至存在著一定的敵對意識。人文知識分子認為科學家過于樂觀,沒有真正意識到人處境的艱難性;而科學家則批評人文學者僅僅滿足于自我欣賞,漠視存在的現實問題[5]。不同學科的教師受到不同學科價值觀的指引,相互之間的不理解增加,甚至出現敵對的狀態,與跨學科所研究希望的不同學科的相互融合、教師之間的交往與溝通完全背道而馳,必然會引發不同學科教師之間的沖突,對高校教師參與跨學科研究帶來了阻力。
(三)學科研究方法的差異性使高校教師難以進行跨學科研究
學科研究是指基于有關學科的觀點或視角來解決學科所涉及到的問題的研究過程,不同學科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有很大差異。目前學科主要劃分為5大領域:自然科學域、工程技術域、醫學科學域、農業科學域和人文與社會科學域。在不同學科域內交叉的就是異域交叉,如生物醫學;在同一領域內交叉的學科則為同域跨學科,如物理化學[6]。即使在同一領域或相近領域的跨學科研究方式也有可能存在巨大的差距。如心理學與哲學,心理學慣常進行實驗室試驗,通過實證研究的方法得出相關的結論,而哲學則更傾向于思辨型的研究方式,思辨者對于定量類研究方式無法掌握,而習慣于采取實證研究的教師對于理論層面的東西難以把握。
正如伯頓·克拉克曾說:“數學的基本風格是優雅與精確相結合,數學家不同于大多數其它學科的科學家,尤其不同于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定性學科的思維和交流方式,其書面交流的方式是簡短的,多半只是幾頁以數學符號表達的高度濃縮的知識……但是,對于歷史學家而言,歷史家的文章開頭不會少于三頁紙。其他人可能需要一張桌子,一個房間和一個堆滿書籍的圖書館。”[7]學科研究方式也成為阻礙教師參與跨學研究的另一道障礙。
二、學科文化對高校教師參與跨學科研究產生阻力的原因分析
當一門學科正式建立、獲得認可時,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學科邊界的形成。學科邊界對于區分自身學科與其他學科,促進教師對本學科的認同,從而致力于本學科的進一步發展有著重要意義。但跨學科研究是由多門學科融合在一起的研究,過于清晰的學科邊界影響了教師對其他學科的認識與理解,不利于教師參與跨學科研究,其更不利于學科的創新與突破。
(一)單一學科文化過于濃厚,使高校教師對跨學科研究的必要性缺乏認識
學科信念如同一種學科文化的粘合劑,把同類學科成員聯接在一起并形成對學科的認同感、歸屬感與忠誠感等,正是高校教師對自身學科的信念使得其更追求本身學科的精細化。但隨著各種問題的日益復雜化,問題所涉及的學科知識日益多樣化與整合化,單一的學科研究已經滿足不了問題的解決,特定學科文化反而一種枷鎖,阻礙各學科教師的交往與合作。同時,高校教師對于自身所屬學科研究的高度投入也造成了他們的個人主義傾向[8]。在個人主義情緒的影響下,高校教師往往傾向于認同自己的學科與自身所做出的成就,特別是科研成果往往需要同行評議,而跨學科的科研成果往往受不到認可或者歸屬并不明確,影響教師自身的發展。因而,從美國的終身教職制度到中國職稱評定中重學科科研成果,都限制教師參與跨學科的研究,更甚者從理念上潛移默化地引導著高校教師尋求學科歸屬,狹隘了教師研究的視野。
學科是連接不同學科專家的專門化的組織方式,并由此推動名領域內知識專門化。學科信念則是一名“扳道工”,其作用在于確定由利益所推動的活動的路線[9]。高校教師對單一學科的信念與忠誠,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對其他學科的忽視與不理解,從而導致不愿意合作、不參與合作,從根本上說就是缺乏對學科融合必要性的認知,缺少對跨學科的一種信念。
(二)學科范式阻礙了高校教師對其他學科的認識與理解
庫恩的范式理論認為科學研究的基礎是科學共同體,這個科學共同體是由共同主題、受過相似的教育與專業訓練、能夠充分交流以及專業判斷一致的一組工作者所組成。科學的革命是一種變革的方式,轉變發生在共同體內部而不是來自外部,不同團體之間的專業交流存在著一定困難,甚至可能導致誤解與重大分歧[10]。目前在高校中仍廣泛采取以學科為中心的建制,學科是整個高校的中心,高校的運作以學科為基礎,整個學科共同體是封閉的,但是跨學科中的共同體追求的是學科邊界的開放性,通過不同學科之間的融合來解決相應的問題。傳統以學科為中心的院系制其實質就是對學科范式的重視與強調,阻礙了學科邊界的開放,不同學科教師之間在學術上缺乏必要的溝通與交流,對其他學科缺乏認識與理解,抑制了高校教師參與跨學科研究的積極性。
(三)過于明晰的學科邊界影響了高校教師之間的關系
學科邊界明確了本學科與其他學科之分,對于學科范式、學科規訓以及的強調,都加深了不同學科之間邊界的明確性。不同學科教師的使命與工作是不同的,克拉克將學者分為三種類型,分別表現為:“把自己關進實驗室的入迷的科學家;鄙棄專業化而致力于教書的教學先生;花大量時間在校外從事咨詢工作、只是由于按新規則不得不花一定時間回校的商業教授、教育教授和工科教授。”[11]學科文化對學者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其本身對問題的研究和批判也是“內斂式”的,即主要指向科學內容本身的自我超越與評述,一旦質疑超出某一學科體系的范疇,恐慌和不適應就會接踵而至,質疑其他學科領域似乎少了一份合法性的支撐[12]。因而這種恐慌使高校教師在參與跨學科研究中必然有一方處于相對輔助的位置,多門學科之間并非有完全平等的地位,由此造成的跨學科研究中一部分教師話語權的缺失,這對跨學科研究實現創新、獲得新發現等非常不利。
(四)單一的學科評價方式阻礙了高校教師參與的積極性
目前的跨學科研究大多仍采用同行評議的方式,但由于不同學科文化之間的差異性,使得評價結果往往失真,跨學科成果往往不能得到公正認可。正如阿蘭·L·波特等人的研究表明:“跨學科研究申請常常在評審中被低估了水平。從個人水平上分析,評審者往往會贊成一個來自他所熟悉的研究領域的申請,因為他更易于理解研究計劃,知道最前沿的研究水平與學術權威,對于做出推薦也更有把握與安全感。”[13]教師參與跨學科研究對自身的晉升沒有很大的效用,從而不利于調動教師參與的積極性。從總體情況來看,同行評議對教師學者們的評審具有導向性和規整性的作用,使他們不敢越學科邊界半步,生怕成果難以得到承認而被邊緣化。
三、減少高校教師參與跨學科研究的學科文化阻力的路徑選擇
(一)厘清跨學科研究中主學科文化與附屬學科文化之間的關系,形成不同學科文化合力從而促進跨學科研究的發展
在跨學科研究中,對于任意參與跨學科研究的教師來說,都存在主學科和附屬學科之分。主學科通常是指在教師參與到跨學科研究中前的所在專業,附屬學科是指在跨學科研究中所涉及的其他學科。建構主義提出,對學生的教育要從學生原有的知識經驗出發,通過原有的認識結構更好地促進新知識的獲取。在跨學科研究中也是如此,主學科文化是高校教師認知結構的基礎,憑借這一基礎可以更好地促進教師對跨學科研究中其他學科更好的認知。通過厘清主學科文化與附屬學科文化之間的關聯性,更好地理解附屬學科文化的意義,從而將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豐富教師認知結構,推動跨學科研究的開展。
(二)完善不同學科教師之間的交流平臺,促使高校教師更好地理解彼此學科文化
跨學科研究的意義表明知識存在著內在一致性,不同的知識之間存在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只有當研究者充分理解研究中所涉及的不同學科文化,才能真正實現跨學科研究。為了更好地讓高校教師參與跨學科的研究,首要的就是創建一個溝通平臺,方便不同學科之間教師的交流。皮特·加里森將跨學科研究中學科文化的交流比作 “貿易區”,在這個“貿易區內”存在著共同的目標,即將不同學科文化的學者集合在一起,首先通過各自的學科語言進行暫時的交流,在一定范圍內形成協調機制。隨著交流程度的不斷加深,最終將會形成新的語言體系,研究也因此獲得新的身份[14]。這一過程實質就是通過不同學科文化的熏陶,使教師在潛移默化中增加對不同學科的認同,而跨學科研究交流平臺正是為這種認同的實現提供了現實基礎。
(三)引導高校教師正確認識跨學科研究對不同學科文化的需求,打破嚴格的學科邊界促進不同學科文化之間的融合
跨學科研究的意義在于通過不同學科之間的融合實現創新,從而解決復雜問題或形成新的發展動力。因為跨學科本身就要求集多種學科文化于一體,在其研究過程中需要不同學科文化之間的融合。皮徹曾指出,學科及其知識生產的邊界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在科學知識的生產過程中,知識的邊界在不斷地重新界定[15]。因而,高校教師首先應該樹立學科邊界開放性的意識,用廣闊的視野來看待不同學科文化的地位,認識不同學科文化融合的重要性。通過模糊學科邊界,促進同學科文化之間的融合,找到新的研究視點、基礎、方法等,從而推動跨學科研究的不斷深化與拓展。
(四)強化教師對其他學科文化的了解與理解,促進評價方式的多樣化
在同行評議過程中,評審專家總是喜歡用他們所熟悉的學科文化視角審視整個跨學科研究的內容。無論是哪個領域的專家,都不能提供對跨學科項目整體研究情況的評議。對跨學科研究來說,尋找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同行,即精通所涉及的各個領域的研究專家是最困難的。因此,要求教師增強對其他學科文化的了解與理解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優化同行評議專家隊伍結構。在跨學科研究中的同行評議隊伍,要充分發揮好不同年齡層次的優勢,結合青年學者對問題的敏銳度高、對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強,加之年長專家豐厚的理論與實踐經驗,對跨學科研究進行科學、合理的評定。另一方面要設置評價者與被評價者之間有效的溝通機制。在現有的評價中,評價者與被評價者兩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完全隔離的。作為評價者的同行專家需要面對嶄新的論題,憑借自身已有的學科文化知識進行評判,但這種文化知識體系常常單一的,即使對有關選題有疑惑但并不能得到及時解答,只能憑自己的經驗進行判斷,因而難免產生誤判。而另一方面對被評價者,即對項目申請人而言,在此過程中無法與專家交流、解答專家的疑惑并提出自己對科研項目的看法,而只是在最后才會收到“判決書”。斯特芬·赫杉里(Stefan Hirschaue)認為對文章初稿的同行評議過程是需要由作者、評議人員和編輯的聯合參與,最后使文章達到可以出版的水平[16]。
學科文化作為高校文化的一種形式,影響著整個高校學術的發展。雖然單一學科的文化阻礙了高校教師參與跨學科研究的積極性,但是學科文化所擁有的語言、價值觀、研究方法使高校教師產生的認同感、歸屬感與忠誠感對促進高校教師參與跨學科研究有著重要的啟發意義。面對日益復雜化的社會問題,跨學科研究有必要成為高校內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如何促進高校教師參與跨學科研究的積極性,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與思考。
[1]OECD. Interdisciplinary: Problems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universities[M].Paris: OECD Publications,1972:25.
[2]徐燕.跨學科研究生的學科身份認同研究-以N大學教育學研究生為例[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33.
[3]A.Leijonhufvud. Life among the Econ[J].Western Economic Journal,1973(3):327-337.
[4]金盛華,鄭建君,辛志勇. 當代中國人價值觀的結構與特點[J]. 心理學報,2009(10):1000-1013.
[5]徐晴. C.P.斯諾兩種文化分裂命題的現代分析[J].復旦大學論壇,2004(5):76-78.
[6]金吾倫.學科研究引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11.
[7] [9][11][美]伯頓·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統——學術組織的跨國研究[M].徐輝等譯.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88-99.
[8]于汝霜. 高校教師跨學科交往特點分析[J].江蘇高教,2012(4):74-76.
[10][美]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第四版)[M]. 金吾倫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37.
[12][14]童蕊.大學跨學科學術組織的沖突問題研究[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107-118.
[13]Alan.L. Poter, Frederick A. Rossini.Peer Review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roposals[J].Science Ethnology & Human Values,1985(03):33-38.
[15]童蕊.大學跨學科學術組織的學科文化沖突分析——基于組織分析的新制度主義視角[J].2011(Z1):82-88.
[16]劉明.同行評議芻議[J].科學學研究.2003(06):574-580.
(責任編輯:劉宇)
Teacher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he Resistance Analysis of Discipline Culture
GU Shenjing
(InstituteofEducationScience,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Zhejiang321004,China)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s a product of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social problem,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solving problems and the innov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t present, the discipline culture with a single discipline system as the main weaken teachers' enthusiasm about participating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because of the uniqueness of language, the difference of subject language and the values of heterogeneous and research methods, which was leaded by college and universities' teachers who is lack of necessary understanding about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e traditional system of faculty and so clear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The resistance of discipline culture can be reduced through sorting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ciplinary cultures, creating the communication platform and leading teachers to set up the correct concept.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discipline culture; resistance
2016-03-27
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教育學重點研究基地課題“我國研究型大學交叉學科機構成員的組織認同研究”(項目編號:JXYSSS026)。
顧沈靜(1992-),女,江蘇蘇州人,浙江師范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學。
G640
A
1005-5843(2016)08-0116-05
10.13980/j.cnki.xdjykx.2016.08.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