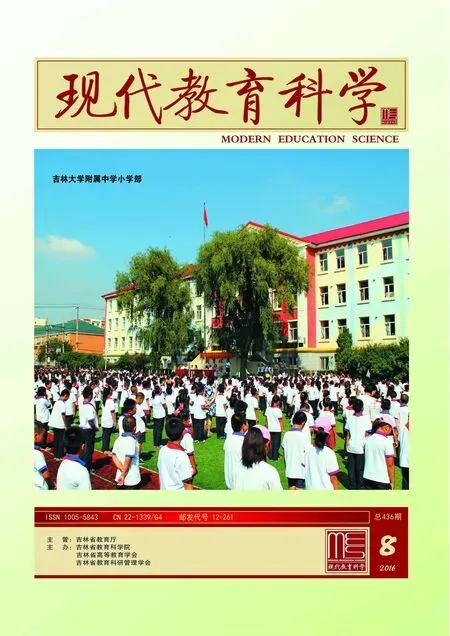我國幼兒教師培養孕育及萌芽的歷史基礎探析
田茂
(1東北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吉林 長春,130117;2東北師范大學,吉林 長春,130000)
?
我國幼兒教師培養孕育及萌芽的歷史基礎探析
田茂1,2
(1東北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吉林 長春,130117;2東北師范大學,吉林 長春,130000)
自原始社會起,學前教育和幼兒教師就在生活和生產中出現了,歷經先秦保傅制度、秦漢宮廷幼兒教育制度、隋唐宋元三師制度、明清社學、蒙館的發展,從無到有,從宮廷到民間,從家庭教育逐步轉向社會機構式教育,幼兒教師也從以家長為主要教育者發展到專職幼教人員。作為學前教育發展的推動者和見證者,總結學前教育師資發展和學前教育事業發展間的關系,探尋經驗與教訓,可以為當代學前教師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提供歷史啟示。
幼兒教師 歷史基礎 古代社會
教育是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產生的,迄今走過了百萬年的歷程,一方面在人類創造歷史文明的過程中不斷培養接續文明的締造者,另一方面也作為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熠熠生輝。學前教育作為學校教育的“前奏”,有的時候以家庭教育的形式存在,有的時候以機構式教育的形式存在,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填補了學校教育的不足。
一、原始社會學前教育及幼兒師資的出現
170萬年前,在云南元謀縣上那蚌村,當元謀人第一次使用工具狩獵、采集,用火烤食物的那天起,出于對撫養后代的天性的認知,教育就在這生活和生產中萌芽了。在漫長的原始社會時期,為了抵抗惡劣的自然環境,人類以“抱團取暖”的方式生存,所以學前教育作為人類文明的一部分,也是在這樣的團體中進行的。《禮記·禮運》篇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1]這是對原始社會幼兒公有公育的描述,“天下為公”,故“不獨子其子”,乃是“幼有所長”,氏族里的長者或能者須向幼兒傳授基本的生活、生產技能和常識,傳遞氏族的道德規范和宗教禮儀以及歌舞、繪畫等。
待原始社會末期,教育從社會生活和生產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社會部門——學校。這為《禮記·王制》篇言:“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2]“庠”除了承擔養老的功能外,還要對氏族里的兒童進行保育和教養,成為最早的學前教育機構,也出現了最早的學前教育專職人員,即“庠”里的長者。除此之外,《尚書·堯典》篇記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3]夔被舜帝任命為樂事之官,負責教導未成年人。先賢在創建人類文明之初就已意識到對教導幼兒的重要性,設置了從事幼兒教導的人員和機構。
二、夏商周時期“三公”“三母”等保傅制度的出現,推進了幼兒師資在實踐中的發展
至夏商周時期,這種設立機構來教養幼兒的做法仍然被效法,《禮記·文王世子》篇載,周天子要求公、侯、伯、子和地方官吏“反養老幼于東序”[4],設立“東序”,用以養育老人和幼兒。
除此,周王室為了更好地培養下一代,還在王宮內設置專門教養幼兒的機構,即孺子室。孺子室作為一種特殊的幼兒教育機構,承擔的是養育和教導國家統治者和管理者的責任,所以在師資的選擇和管理上極其嚴苛。《禮記·內則》篇記載:“異為孺子室于宮中,擇于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5]書中所記載的就是孺子室的三母制度,分別是子師、慈母和保母。子師一般在后宮中挑選那些心性寬裕、慈惠、溫良、恭敬、謹慎寡言的女子擔任,“師教以善道者”,負責王室幼兒的品德教育;慈母“審其欲惡者”,負責道德行為教化;保母“安其寢處者”,照顧飲食起居,還挑選品行良好、身體健康的乳母養育幼小的王室成員。
除了以保育為主責的三母制度外,為了培養王室子弟從事政治活動的道德品質和文化知識,還設立了保傅制度,這也是宮廷學前教育區別于只有家庭教育充當學前教育的平民教育的主要特點。《禮記·文王世子》篇記載:“《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6]疑、丞、輔、弼即四輔,疑乃為幼兒解釋疑問,丞專司記事,輔主責糾正過失,弼司表揚之責;太師、太保、太傅為三公,太師“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通過具體的事件讓幼兒知曉道義,是文化知識和統治經驗的教育,太保“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保護幼兒身體康健,生活舉止規律且合符禮儀,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進行的是父子君臣道義的教育,是道德教育。三公最主要的職責是培養未來的君王,對其進行德、智、體等多方面的影響和教育,所以只有那些德才兼備、忠厚賢能的人才能擔任。擔負王室幼兒保教任務的人員除了三母和三公,還有三少——少保、少傅、少師,常年陪伴在側,施以積極和正面的影響。
可見,先秦時期,我國的學前教育主要還是以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為主,但是在王室已經出現了機構式幼教的形式,教育內容也有了相對穩定的發展,雖無對從教人員的系統培養,但是對從教人員的選拔已經有了嚴苛的標準,這對學前教育師資的選拔和培養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三、秦漢南北朝時期幼兒師資在實踐中的發展
秦漢時期的幼兒教育主要還是以家庭教育為主,但也出現了兼具幼兒教育性質的機構,如宗學和書館,教師則由宗師或書師擔任,宗師和書師皆由蒙學舉辦者出資聘請有學問者擔任。對幼兒教育較為重視的仍然是秦漢時期的宮廷幼兒教育,延續了先秦時期的保傅制度,對從事教育皇室接班人的教師委以重任,尊為國家官吏,對皇室幼兒進行道德品行、學識、政治素質、騎射等軍事和身體健康的教育。這一時期的思想家賈誼對早期教育有諸多論著,賈誼曾做過八年太傅,對為師之道頗有見地。他認為只有“賢者”才能擔當教師之職,且對教師應怎樣教學也提出詳細的辦法,《新書·容經》載有他的精彩論述:“故師傅之道,既美其施,又慎其齊,適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圣人之化也。”[7]可以看做是對教師的教學方法進行指導的早期思想,影響深遠。
魏晉南北朝時期并無專門的幼兒教育機構,主要附屬于其他類型的學校,并無突出的特點。這一時期的皇室幼兒教育同樣是師保傅制度,強調尊師重道,從教者一般位高官重,也有學者對師、保、傅的素質有精辟的論述,如西晉閻纘提出應選擇那些“寒門孤臣、以學行自立者,及涉履艱難、名行素立者,使與游處。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但道古今孝子事親、忠臣事君,及思想改過,皆聞善道,庶幾可全”[8]。出身寒門、清廉正直、學問卓然自立等成為師資備選的重要條件。北魏歷史學家李彪也指出只有那些“天下賢才”,“孝悌博聞有道術者”才能擔此重任,唯此,皇室子弟才能“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9]。這些關于師者要求的見解對后世擇優錄取幼兒教師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古代的幼兒教育一直以家庭教育為主,世人一直比較注重家庭教育,其中的佼佼者當屬北齊的顏之推,他撰寫的《顏氏家訓》一直被推崇為中國家訓的始祖。顏之推認為家庭是人的第一所學校,父母、師傅等就是人的第一任教師,所以父母等養育者必須以身作則,曰之“風化”,“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婦不順也”[10]。這是對為人父母或為師者行為的要求,除此,還對具體的教育方法提出及早施教、嚴慈有節、一視同仁等真知灼見,這也是今天的幼兒教師在施教過程中必須遵守的原則。
四、隋唐宋元時期幼兒師資的發展
隋唐五代受到重視的仍然是皇室貴族幼兒教育。這一時期的皇宮幼兒教育除了繼承北齊的做法外,還設置皇太子賓客和詹事,禮遇厚待,配合“三師”對皇室子弟施以教育和影響。其他學前教育則由官辦小學(京師的小學只有皇室和功臣之后可入學,普通民眾子弟只可入地方州縣舉辦的小學)、家學、鄉學和家庭教育承擔,家學或鄉學一般聘請小知識分子或迫于生計的學術大師擔任,其學識水平與皇室幼兒教育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及至宋元,為了更好地培養王位繼承人,師保傅制度和宮廷學校都得到了較好地發展,并十分重視對“神童”的選拔和教育,宋朝特設“童子科”用以選撥和重用有才華的幼兒。普通民眾也十分重視幼兒的教育,這一時期還有眾多的學者對幼兒教育進行了闡釋,比如程頤就特別提到要慎選乳母教師,要聘請那些德行高雅的人擔任教師一職;朱熹則詳細論述了怎么培養幼兒的道德觀念,并將之轉化為道德行為,并親自編寫童蒙教材《童蒙須知》,還對主要負責幼兒養育的乳母提出了具體的要求:“乳母之教,所系尤切”[11],須選擇那些“寬容、慈、惠、溫、良、恭、敬”[12]的人擔任此職。除此,還要慎擇師友,曾勸誡帝王應當效仿古代賢王教子的方法,在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中擇其優秀者為太子師友。這也是對幼兒教師應該具備什么素質的論述,因為朱熹相信“習與正則正,習與邪則邪”[13]。
五、明清時期現代幼兒師資培養的萌芽
明清時期的幼兒教育一方面由中央官學、地方官學和私學承辦,國子學就曾向幼兒開放,收剛離開襁褓的幼兒,明朝時曾建立武學,招收幼兒,教導其武技;國子監也曾委派學識淵博、德高望重的伴讀、教授等對官員子弟進行教育,如選擇知識淵博、德行高尚的官員專門教導世家子弟,嚴格教育;地方官學,特別是社學招聘有學識的人擔任教師,教育童蒙;此外,私人興辦的蒙館也大量招收幼兒,但是大多數幼兒的早期教育還是以家庭教育為主。可見,在明朝,一些賢者已經意識到在幼時教以禮儀,成人時方不背禮教的重要性,所以大量的私塾、社學、蒙館和中央官學等機構承擔了一部分幼兒教育的任務。在這個過程中也必然催生著對從事幼兒教育人員的需求,但是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幼兒教師一直附著在諸如塾師、官員等身份上,并沒有獲得獨立的地位和重視。
清朝承襲明朝的諸多做法,中央官學,如八旗官學、咸安宮宮學、長房官學等招收幼兒。由專職人員教授幼兒。這些中央官學主要招收官吏后代,在官員中擇優那些文能安邦武能治國的優秀人才充任教導幼兒的教師,教之以滿文、漢學、算學、騎射等科目;地方學校特別是地方義學,私人興辦的學館、私塾等也承擔幼兒教育的任務。這一時期的一些學者也對幼兒教師的選拔等有過論述,清朝學者唐彪在論作《父師善誘法》中指出只有“品端學優,而又勤且嚴者”才能“不克勝任”,對幼兒教師的辛苦工作、工作的重要性等做了總結,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培養、任用幼兒教師絕不可輕視之。
梳理幼兒教育發展的歷程可以發現,原始社會的幼兒教育和今天的機構式幼兒教育如幼兒園有頗多相似之處,地點、時間、專職人員、教授內容等有數處共同之處。自夏商至明清,幼兒教育雖然得到一定發展,但是機構式的幼兒教育一般是依附于其他學校(宮廷幼兒教育相對獨立一些)或者是以家庭教育的形式存在的,并不成體系。但是自宋朝起,有一種幼兒教育機構和今天的幼兒園倒有頗多相似之處,即為收養棄嬰孤兒設置的慈幼機構,明清兩朝也一直延續此制度。
宋朝的慈幼機構主要有慈幼局、社倉、舉子倉、育嬰社、廣惠倉等,由朝廷撥款興建和維持,失親的嬰兒可在這些慈幼院接受乳母喂養,慈幼院還聘請有經驗的老年婦女幫助養育。宋朝的慈幼局、舉子倉等“為貧而棄子者設”,可能是中國最早的專門養育幼兒的機構。但宋朝的慈幼院僅是恤孤性質,到明清兩代,慈幼院發展為育嬰堂、養濟院、漏澤園。明清的育嬰堂、育嬰所等機構及人員的設置和管理較之宋代相對嚴格和全面,具體的工作人員有負責育嬰堂全面管理的首事,還有書役、醫生、門役、巡役、廚夫、看護、乳婦等,除此之外,還對具體須負責的工作進行了分配,如誰負責幼孩寢食、衣服浣沐、疾病休假等事。
清代還有民間興辦的諸如及幼堂等。如唐鑒在貴州創辦的及幼堂不僅供幼兒吃住,還教幼兒讀書寫字或其他謀生技能,將保育和教育合為一體。這種育嬰堂雖然在當時并沒有得到大力推廣,但是其在保幼結合幼教之路的探索上卻寫下重要的一筆,對清末新式學前教育機構的興盛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特別是對育嬰堂從事幼兒教育的專職人員如“節婦”“乳媼”的選擇與培養,打開了新的篇章。
晚清至民國時期,我國學前教育從無到有,學前教育師資也從最開始的業余的“乳媼”“節婦”到國立幼稚師范學校培養專業的幼兒師資,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歷程。幼兒師資的發展為促進學前教育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最基礎的力量,可以說,一部中國學前教育發展的歷史其實就是學前教育師資發展的歷史。學前師資的發展是學前教育事業發展的“見證者”和“推動者”,所以了解我國學前教育師資隊伍從產生到發展的歷史軌跡,以史為鑒,可以為今天的學前教育事業發展尋找歷史支撐點,總結晚清至民國我國學前教育師資發展和學前教育事業發展間的關系,探尋經驗與教訓,“察古思今,述往思來”,可以為當代學前教師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提供歷史借鑒。
[1][4][5][6][清]阮元.十三經注疏(下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0:1416,1410,1416,1407.
[2] [清]阮元.十三經注疏(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0:1346.
[3] 王世舜.尚書譯注[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8.
[7] [漢]賈誼.賈誼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145.
[8] [唐]趙蕤著,李孝國.長短經[M].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13:536.
[9] [北齊]魏收.魏書·李彪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4:1384.
[10]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8.
[11] [12][清]張伯行.小學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5:3,18.
[13] [宋]朱熹.朱文正公集(卷11)[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6.
(責任編輯:劉宇)
Historical Basic Analysis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Training and Germination in China
TIAN Mao1,2
(1CollegeofHumanities&Sciencesof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17,China;
(2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17,China)
Since the primitive society,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kindergarten teachers have appeared in life and production, it gone through the pre Qin dynasty’s Fu system, Qin and Han’s court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ystem, Dynasties’ three division system from Sui, Tang to Song, Yuan, Ming and Qing’s elementary school, it grow out of nothing and developed from the court to the folk, from family education to social organization education. The preschool teachers developed from parents to full-time preschool workers. As the promoters and witnesse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development, summing u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chool teachers’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exploring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can provide a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reschool teacher education.
kindergarten teachers; historical basis; ancient society
2016-02-23
吉林省教育科學2015年度“十二五”規劃課題“晚清自民國時期我國幼兒教師培養模式研究”(項目編號:GH150759)。
田茂(1982-),女,四川瀘州人,東北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博士研究生,東北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學前教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國教育史。
G615
A
1005-5843(2016)08-0129-04
10.13980/j.cnki.xdjykx.2016.08.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