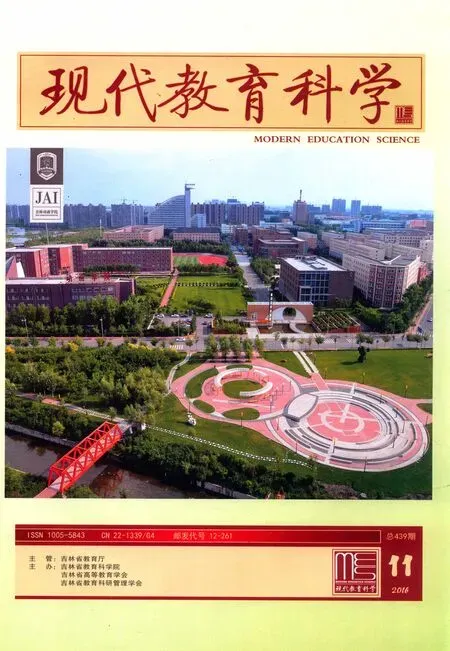大學章程:歷史、現(xiàn)狀與未來
魏志榮
(濟南大學政法學院,山東 濟南 250022)
?
大學章程:歷史、現(xiàn)狀與未來
魏志榮
(濟南大學政法學院,山東 濟南 250022)
大學章程與大學相伴而生,起源于中世紀晚期的歐洲,由特許狀演化而來。由于歷史原因,中國的大學章程建設(shè)一度中斷。當前,中國大學章程建設(shè)存在著章程性質(zhì)不明確、內(nèi)容同質(zhì)化、制定的被動性和執(zhí)行力的有限等問題。要切實發(fā)揮大學章程的作用,明確大學章程的“軟法”性質(zhì),以“雙一流”為抓手突出大學特色發(fā)展,形成建立現(xiàn)代大學制度的共識,依法依章治校,推進大學治理的現(xiàn)代化。
大學章程 同質(zhì)化 軟法 現(xiàn)代大學制度
一、大學章程的發(fā)展歷史
(一)國外的大學章程
大學章程與大學相伴而生,起源于中世紀晚期的歐洲,由特許狀演化而來。11-13世紀,隨著歐洲新興城市的出現(xiàn),社會的教育需求日益強烈。然而,曾經(jīng)發(fā)揮過教育機構(gòu)作用的修道院、神學院卻更加重視懺悔、祈禱和隱修等宗教教育形式的作用。新興城市中的知識分子群體則以行會組織為參照,組建了大學行會,大學得以發(fā)展起來。學術(shù)功能的定位和學術(shù)權(quán)力的輻射,使大學的影響力逐步增強。教皇和國王為了擴大各自的勢力,爭相為大學頒發(fā)特許狀,賦予大學一定的自治權(quán),如大學可以自主開設(shè)課程、錄取學生、授予學位、聘任教師、實施內(nèi)部管理等。此時,特許狀起到了大學章程的作用。在教權(quán)與王權(quán)的爭奪過程中,大學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權(quán)利。但大學成立的前提條件是獲得特許狀,因此,特許狀具有法律效力。隨著歐洲殖民主義的擴張,特許狀也被頒發(fā)給殖民地大學,如美國的耶魯大學就是一所殖民地時期建立并獲得特許狀的大學。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使王權(quán)取代了教會并加強了對大學的影響,政府的改革方案和教育立法削減了大學的自治權(quán),但社會組織的介入使政府不再是大學唯一的經(jīng)費來源,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政府對大學的控制。
美國獨立后,其大學的設(shè)立和運作不再需要英國的特許,新成立的大學需要遵照美國聯(lián)邦或州的教育法律法規(guī)制定章程。董事會是美國大學的最高決策和權(quán)力機構(gòu),是大學章程的制定主體。如加利福尼亞大學、麻省理工大學、康奈爾大學、伊利諾伊大學、威斯康星大學等大學的章程,均源于聯(lián)邦法律。二戰(zhàn)后,英國政府通過教育立法使大學進入了全新的發(fā)展階段,其在1988年通過的《教育改革法》更是開啟了多元主體共治的大學治理模式,大學章程的內(nèi)容也隨之發(fā)生了變化。
在英文中,大學章程有四種表述:Statue、Ordinance、Charter、Bylaw,由此也體現(xiàn)了各大學章程的不同側(cè)重點。按不同的標準,可以將大學章程劃分為特許章程或授權(quán)章程、法律性章程或規(guī)范性章程等。從宏觀來看,英美法系的國家,如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其大學章程賦予了利益相關(guān)者參與權(quán),強調(diào)決策權(quán)、執(zhí)行權(quán)和監(jiān)督權(quán)的分離制衡,具有規(guī)范大學同政府關(guān)系的特點。大陸法系的國家,如德國、法國、日本等,其大學章程具有強調(diào)政府參與的優(yōu)先權(quán),決策權(quán)、執(zhí)行權(quán)和監(jiān)督權(quán)的三權(quán)合一,重視基層學術(shù)組織的自治權(quán)等特點。
(二)中國的大學章程
關(guān)于中國大學章程的起源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大學章程是由古代書院的“院規(guī)”或“訓示”演變而來的,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國的大學章程始于1895年盛宣懷起草的《擬設(shè)天津中西學堂章程稟》,第三種觀點認為中國的大學章程源于1898年梁啟超起草的《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筆者贊同第三種觀點。
1898年,在參考西方大學制度的基礎(chǔ)上,梁啟超起草了《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得到光緒帝的批準,京師大學堂誕生。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綜合大學。1901年,時任山東巡撫袁世凱組織起草了《山東試辦大學堂暫行章程》,創(chuàng)辦了山東大學堂。這是中國最早的省立大學堂。此后,各省多以山東大學堂為樣板,參照其章程辦理。1920年,在借鑒德國柏林大學制度的基礎(chǔ)上,蔡元培主持制定了《國立北京大學現(xiàn)行章程》。這是民國時期第一部由大學自行起草、評議會通過、教育部備案的國立大學章程。該章程共分七章,分別為“學制”“校長”“評議會”“教務(wù)會議”“行政會議”“教務(wù)處”和“事務(wù)”,體現(xiàn)了校長治校、教授治學、民主管理等原則。隨后,《東南大學組織大綱》(1921)、《清華學校組織大綱》(1927)相繼頒布。此后,無論是成立國立大學還是私立大學,均制定大學章程,為中國大學的發(fā)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新中國成立后,實行的是計劃經(jīng)濟體制,大學的發(fā)展要根據(jù)國家的計劃進行,大學的一切事務(wù)由政府規(guī)劃。在這種情況下,大學對自身的發(fā)展和管理失去了自主權(quán),沒有制定章程,其施行的規(guī)章制度是對國家教育政策的具體執(zhí)行。文化大革命時期,大學高度政治化,成為了政治斗爭的舞臺,發(fā)展出現(xiàn)了停滯甚至倒退,大學章程更是無從談起。
改革開放以后,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亟需大量人才,而大學的管理體制和培養(yǎng)模式卻無法與之相適應(yīng)。1985年,中共中央通過的《關(guān)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簡政放權(quán),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quán)”,中國的教育改革由此開啟。1995年頒布的《教育法》規(guī)定:“章程是設(shè)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gòu)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1998年頒布的《高等教育法》規(guī)定:“申請設(shè)立高等學校的,應(yīng)當向?qū)徟鷻C關(guān)提交章程。”2010年印發(fā)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提出:“完善中國特色現(xiàn)代大學制度;各類高校應(yīng)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規(guī)定管理學校。”2011年印發(fā)的《高等學校章程制定暫行辦法》(下文簡稱“《暫行辦法》”)規(guī)定了大學章程的內(nèi)容、制定程序、核準與監(jiān)督等,為大學章程的制定提供了規(guī)范。2012年,教育部印發(fā)的《全面推進依法治校實施綱要》提出:“加強章程建設(shè),健全學校依法辦學自主管理的制度體系;到2015年,全面形成一校一章程的格局;經(jīng)過核準的章程,應(yīng)當成為學校改革發(fā)展、實現(xiàn)依法治校的基本依據(jù)。”《教育法》實施之前成立的大學相繼開始補擬章程。當前,很多普通高校都完成了大學章程的制定工作,但如何使其在現(xiàn)代大學治理中切實發(fā)揮作用,則有待進一步探索。
二、中國大學章程的實施現(xiàn)狀
根據(jù)《全國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的數(shù)據(jù),2015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有2 560所,共招生737.85萬人,在校生校均規(guī)模達10 197人,有教職工236.93萬人。如此龐大的體系如何有效運轉(zhuǎn)?如何適應(yīng)內(nèi)外環(huán)境的變化?《暫行辦法》指出:“高等學校應(yīng)當以章程為依據(jù),制定內(nèi)部管理制度及規(guī)范性文件、實施辦學和管理活動、開展社會合作。”地方政府舉辦的大學所制定的章程由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核準,部屬大學所制定的章程由教育部核準。根據(jù)教育部網(wǎng)站的信息,截至2016年6月,教育部共核準了92所部屬大學的章程,其中2013年核準6部大學章程,2014年核準41部,2015年核準37部,2016年上半年核準8部。與此同時,地方大學也開始制定各自的章程。我國大學章程的制定邁出了現(xiàn)代大學制度建設(shè)重要的一步,但由于大學章程近幾年才重新被提上議程,而此時中國大學正面臨著從規(guī)模發(fā)展向質(zhì)量提升、從管理向治理的轉(zhuǎn)變,因此,在大學章程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
(一)大學章程的性質(zhì)不明確
關(guān)于大學章程的性質(zhì)和法律地位,學界有不同的觀點:第一種是契約說或合同說,認為大學章程是舉辦者與辦學者及師生之間在溝通協(xié)商的基礎(chǔ)上,就大學的辦學原則、組織結(jié)構(gòu)、運作模式、經(jīng)費資產(chǎn)等方面達成的合意,一經(jīng)核準備案便具有約束力。或者說,大學章程是舉辦者與辦學者之間達成的格式合同,只要按照合同條款執(zhí)行就會減少摩擦、提高效率,進而實現(xiàn)合同目標。第二種是自治法說,認為大學章程是大學依據(jù)國家法律法規(guī)授權(quán)而制定的自主管理的自治法,對其內(nèi)部成員具有效力。《暫行辦法》規(guī)定:“教育行政部門對章程中自主確定的不違反法律和國家政策強制性規(guī)定的辦學形式、管理辦法等,應(yīng)當予以認可。”第三種是行政法說,認為大學章程具有行政法律效力,當行政相對人認為大學的行為違背了大學章程而侵犯其合法權(quán)益時,可以提起行政訴訟。劉燕文就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未授予其博士學位提起行政訴訟一案,經(jīng)常被作為此觀點的例證。國外大學章程發(fā)展比較成熟的國家,如美國,其大學章程經(jīng)所在州議會批準后可以成為州法律的一部分。那么,中國大學章程到底是哪種性質(zhì)呢?《暫行辦法》將其定位為“基本準則”,這一定位是比較模糊的,將會影響大學章程效力的發(fā)揮。
(二)大學章程的內(nèi)容同質(zhì)化
從已經(jīng)公開的我國大學章程文本來看,其框架結(jié)構(gòu)基本相似:前兩部分是序言和總則,后三部分是資產(chǎn)財務(wù)、學校標識和附則,中間部分涉及組織結(jié)構(gòu)、管理體制、教職員工、學生等內(nèi)容。從具體內(nèi)容來看:對學校的領(lǐng)導體制和決策機制表述基本相同,占很大篇幅的大學黨委和校長的職責、教師和學生的權(quán)利與義務(wù)部分差別不大;基本都設(shè)有學術(shù)委員會、學位評定委員會、教職工代表大會、校務(wù)委員會,有的還設(shè)有教學委員會(如清華大學、南京大學)、人才培養(yǎng)委員會(如中山大學)、董事會/理事會(如中國人民大學、山東大學)等。各大學章程的內(nèi)容為什么會同質(zhì)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暫行辦法》詳細規(guī)定了大學章程應(yīng)該體現(xiàn)的內(nèi)容,從而限定了章程的框架;另一方面是因為大學的趨同化導致了章程的同質(zhì)化。長期以來,“985”“211”工程大學能夠獲得更多的政策和資金支持,發(fā)展較快,其制度設(shè)計、組織規(guī)劃等成為了其他大學模仿的標桿;教育行政部門對大學采取同一的評估指標,進一步塑造了趨同的大學。大學章程本應(yīng)“反映學校的辦學特色”,如果都一樣或相似,那就失去了各自制定的必要,同時會加劇大學之間的競爭,無法滿足社會對人才培養(yǎng)的多元化需求,進而使大學教育失去活力。
(三)大學章程制定的被動性
長期以來,我國多數(shù)大學都是根據(jù)教育法規(guī)政策和內(nèi)部規(guī)章制度運轉(zhuǎn),直到《暫行辦法》出臺后大學章程的制定才重新提上議程。其初衷是進一步賦予大學依章治校的自主權(quán),政府給大學“松綁”,這應(yīng)該是大學制定章程的內(nèi)在動力。但事實上,各大學的積極性并不高,大學章程制定進程緩慢。如《復旦大學章程》《東南大學章程》都是歷時4年才出臺,《北京大學章程》從2006年獲準籌建到2014年核準頒布,更是歷時長達8年之久。截至目前,仍有很多大學沒有發(fā)布章程。此種狀況反映了大學章程制定的被動性。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呢?一方面,大學章程的制定是由教育行政部門發(fā)起和推動的,是強制性的制度變遷,不是大學的自主行為。同時,《暫行辦法》對章程內(nèi)容的規(guī)定又過于具體,留給大學自主發(fā)揮的空間有限,自主權(quán)無法得到彰顯。另一方面,大學的黨政領(lǐng)導、內(nèi)部各部門及師生對現(xiàn)代大學制度建設(shè)缺乏足夠的認識,有的認為制定大學章程是在完成任務(wù),應(yīng)付了事;有的認為是形式主義,閉門造車。這些錯誤的思想和行為是亟需糾正的。
(四)大學章程執(zhí)行力的有限性
大學章程的執(zhí)行力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執(zhí)行大學章程的能力,二是執(zhí)行大學章程的效力。再好的制度設(shè)計,如果不去執(zhí)行,或者執(zhí)行不到位,都不會產(chǎn)生應(yīng)有的效力。從當前的情況來看,大學章程的執(zhí)行力有限,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兩方面:一是執(zhí)行能力有限。大學章程為大學內(nèi)部治理和處理外部關(guān)系提供了依據(jù)。從內(nèi)部來看,現(xiàn)代大學治理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意味著打破原有的權(quán)力和利益格局,大學章程要明確黨委領(lǐng)導與校長治校的關(guān)系、平衡行政權(quán)力與學術(shù)權(quán)力的關(guān)系、規(guī)范大學與師生之間的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從外部來看,大學章程要界定大學與政府、社會之間的關(guān)系。但在已經(jīng)頒布的大學章程中,對“舉辦者與學校”的關(guān)系進行說明的卻很少。如果不能理順內(nèi)外關(guān)系,必將掣肘大學執(zhí)行章程的能力。二是執(zhí)行效力有限。大學章程的制定與執(zhí)行出現(xiàn)了脫節(jié)的現(xiàn)象,制定之后便束之高閣,執(zhí)行情況沒有得到有效的監(jiān)督。在實踐中,有的大學或者二級學院并沒有按照章程進行管理,出現(xiàn)了“一把手治理”現(xiàn)象。《暫行辦法》規(guī)定,大學“應(yīng)當指定專門機構(gòu)監(jiān)督章程的執(zhí)行情況”。這樣的規(guī)定較為模糊,多數(shù)大學都沒有這樣的專門機構(gòu),同時自己監(jiān)督自己也很難產(chǎn)生應(yīng)有的效果。此外,章程內(nèi)容的可操作性也影響了執(zhí)行的效力。
三、大學章程的未來發(fā)展
中國的大學正從管理走向治理,要實現(xiàn)大學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xiàn)代化,制度建設(shè)是關(guān)鍵,而制度建設(shè)的核心就是大學章程建設(shè)。針對中國大學章程建設(shè)中存在的問題,未來要使大學章程切實發(fā)揮作用,首先應(yīng)當明確大學章程的性質(zhì)與法律地位,同時,以“雙一流”為抓手突出大學特色,形成建立現(xiàn)代大學制度的共識,依法依章治校,推進大學治理的現(xiàn)代化。
(一)“軟法”:大學章程的合理定位
在不同的情況下,大學章程兼具契約合同、自治法、行政法的某些特征,但又不完全相同。由于不是平等主體,所以不符合契約合同的訂立要求;大學有一定的辦學自主權(quán),但還沒有實現(xiàn)自治;行政法是由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在中國,大學章程顯然不是行政法。因此,筆者認為,大學章程更合理的定位應(yīng)該是軟法。何為軟法?“軟法的出現(xiàn)與社會秩序?qū)崿F(xiàn)方式從統(tǒng)治向治理的轉(zhuǎn)變緊密相關(guān),統(tǒng)治形式下的法律通常是‘硬’的,是國家機關(guān)制定或認可、體現(xiàn)國家意志并由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規(guī)則體系,而治理形式下的法律是‘軟’的,即不直接依賴于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但事實上存在的可以有效約束人們行動的行為規(guī)則”[1]。軟法的存在可以是政黨組織、政協(xié)組織、事業(yè)單位、社會團體、行業(yè)協(xié)會等的章程、公約、規(guī)范、綱要、決定等多種形式。大學章程是由大學治理共同體成員協(xié)商制定的、不受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約束共同體成員行為的準則規(guī)范,是一種軟法。
軟法的實施主要“依靠組織和共同體自身的力量或者社會輿論、成員自律、利益引導等柔性手段”[2]。雖然軟法不直接依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但“并不排斥司法適用,有時會以證據(jù)的身份進入司法程序”[3]。也就是說,違反了大學章程一般不會被提起訴訟,但它仍然會以自身獨特的方式發(fā)揮著法律效力。在我國大學章程發(fā)展的起步階段,將其定位為硬法顯然是不合時宜的,也是不現(xiàn)實的。硬法具有一定的穩(wěn)定性,軟法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將大學章程定位為軟法,將有利于其在實踐中不斷完善,為最終的法制化奠定基礎(chǔ)。
(二)“雙一流”:推進大學特色發(fā)展
如前文所述,大學章程的同質(zhì)化與大學的趨同化有很大關(guān)系。2012年,教育部出臺的《關(guān)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zhì)量的若干意見》(又稱“高教30條”)第二條“促進高校辦出特色”中指出:“探索建立高校分類體系,制定分類管理辦法,克服同質(zhì)化傾向;根據(jù)辦學歷史、區(qū)位優(yōu)勢和資源條件等,確定特色鮮明的辦學定位、發(fā)展規(guī)劃、人才培養(yǎng)規(guī)格和學科專業(yè)設(shè)置。”2015年5月,教育部發(fā)布的《關(guān)于深入推進教育管辦評分離,促進政府職能轉(zhuǎn)變的若干意見》提出:“健全多元化評價標準;建立與學校辦學定位、目標、責任相適應(yīng)的評價體系,充分反映學校辦學的努力程度和進步情況,促進學校特色建設(shè)、個性發(fā)展。”在此基礎(chǔ)上,2015年8月,國務(wù)院印發(fā)了《統(tǒng)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shè)總體方案》。2016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十三五規(guī)劃”進一步明確指出:“全面提高高校創(chuàng)新能力,統(tǒng)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shè)。”同時,各省屬高校也開始了世界一流、國內(nèi)一流大學和學科的建設(shè)。由此,中國各大學已經(jīng)全面進入了質(zhì)量提升、內(nèi)涵建設(shè)、特色發(fā)展的階段。
各大學應(yīng)以“雙一流”建設(shè)為契機和抓手,形成自身的優(yōu)勢和特色。《耶魯大學章程》提出的辦學理念是“致力于知識與文化的保護、傳授、推進及豐富;學校要為國家和世界培養(yǎng)杰出領(lǐng)袖”,中國各大學的發(fā)展定位、辦學方向、培養(yǎng)目標等也應(yīng)突出各自不同的特色。“雙一流”建設(shè)必將推動大學章程的不斷完善,使大學在實踐中發(fā)掘自身優(yōu)勢,形成自身特色,而大學章程的制定、完善也將為“雙一流”建設(shè)提供制度保障。兩者相互促進,共同推動著大學的發(fā)展。
(三)形成共識:建設(shè)現(xiàn)代大學制度
2010年印發(fā)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要“完善中國特色現(xiàn)代大學制度”,包括完善治理結(jié)構(gòu)、加強章程建設(shè)、擴大社會合作、推進專業(yè)評價等方面。可見,章程建設(shè)是中國特色現(xiàn)代大學制度的重要內(nèi)容。認識是行動的先導,要使大學章程行使喚醒大學“沉睡”的權(quán)利,政府與大學、大學內(nèi)部必須就章程建設(shè)達成共識,充分認識到其在現(xiàn)代大學制度建設(shè)中的重要性。首先,政府與大學應(yīng)就各自的權(quán)力邊界達成共識,并在章程中予以體現(xiàn)。2012年印發(fā)的《全面推進依法治校實施綱要》提出:“教育行政部門要切實轉(zhuǎn)變管理學校的方式、手段,從具體的行政管理轉(zhuǎn)向依法監(jiān)管、提供服務(wù);切實落實和尊重學校辦學自主權(quán),減少過多、過細的直接管理活動。”當前,應(yīng)進一步深化教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推行清單管理方式,建立教育行政權(quán)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制度,同時引入負面清單。凡是列入政府權(quán)力清單的事項,政府必須嚴格執(zhí)法;凡是權(quán)力清單以外的事項,大學可以自主決定,政府不得直接干預(yù)[4]。清單管理模式可以劃定政府與大學之間的權(quán)力邊界,也意味著大學辦學自主權(quán)的擴大。雙方應(yīng)就此達成共識,并在大學章程中予以明確,才能使大學章程具有實質(zhì)性的意義。其次,大學的黨政領(lǐng)導、各部門、廣大師生應(yīng)提高對大學章程的認識,并在溝通協(xié)商的基礎(chǔ)上,就章程內(nèi)容達成共識。章程規(guī)范著大學的權(quán)力運行和內(nèi)部治理,因此應(yīng)當遵循民主公開的原則,充分反映各方意見,進而理順政治權(quán)力、行政權(quán)力和學術(shù)權(quán)力之間的關(guān)系,使章程的制定過程“成為學校凝聚共識、促進管理、增進和諧的過程”。
(四)依章治校:推進治理的現(xiàn)代化
2012年教育部發(fā)布的《全面推進依法治校實施綱要》指出:“推進依法治校,是學校適應(yīng)加快建設(shè)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要求,發(fā)揮法治在學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學校治理法治化、科學化水平的客觀需要;是深化教育體制改革,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構(gòu)建政府、學校、社會之間新型關(guān)系,建設(shè)現(xiàn)代學校制度的內(nèi)在要求;是適應(yīng)教育發(fā)展新形勢,提高管理水平與效益,維護學校、教師、學生各方合法權(quán)益,全面提高人才培養(yǎng)質(zhì)量,實現(xiàn)教育現(xiàn)代化的重要保障。”大學的治理首先要遵守國家憲法和法律法規(guī),同時,還要依章治校,因為大學章程是在“以憲法、法律法規(guī)為依據(jù),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遵循高等教育規(guī)律”的基礎(chǔ)上制定的軟法。
大學應(yīng)增強法治意識和主體意識,擺脫對政府的路徑依賴,在實踐中要依法治校、依章治校,切實提高大學章程的執(zhí)行力。《暫行辦法》規(guī)定:“大學應(yīng)當指定專門機構(gòu)監(jiān)督章程的執(zhí)行情況,受理對違反章程的管理行為、辦學活動的舉報和投訴;教育行政部門對大學履行章程情況進行指導和監(jiān)督,對不執(zhí)行章程的情況或者違反章程規(guī)定自行實施的管理行為,應(yīng)當責令限期改正。”大學章程應(yīng)彰顯高校的辦學自主權(quán)和辦學特色,但同時也應(yīng)具有嚴謹性和可操作性。在大學章程向社會公開的基礎(chǔ)上,應(yīng)完善多元主體參與的監(jiān)督機制。大學章程既承接國家法律法規(guī),是國家法律法規(guī)的延伸,又統(tǒng)領(lǐng)著校內(nèi)各種規(guī)章制度,進而形成大學治理的制度體系。提高大學章程的執(zhí)行力必將有利于推動大學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xiàn)代化。
[1]陳立鵬,楊陽.大學章程法律地位的厘清與實施機制探討:基于軟法的視角[J].中國高教研究,2015(2):25-29.
[2]羅豪才,湛中樂.行政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13.
[3]羅豪才,宋功德.軟法亦法:公共治理呼喚軟法之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374.
[4]周光禮.實現(xiàn)三大轉(zhuǎn)變推進中國大學治理現(xiàn)代化[J].教育研究,2015(11):40-42.
(責任編輯:劉新才)
University Charter:History,Situation and Future
WEI Zhirong
(CollegeofPoliticsandLaw,JinanUniversity,Jinan,Shandong250022,China)
University charters are accompanied?with universities, they are originated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of Europe and evolved from charter. Due to the historical reasons, university charter construction of China was suspended. At present,university charter construction of China express some problems,such as the nature of charter undefined,the content homogeneous,formulated passively and execution limited. To make university charter work effectively in the future,“soft law”nature of university charter should be definite,put the first class university and first class discipline as the starting point,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versity, get consensus with construction of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governance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law and charter and promote university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university charter;content homogeneity;soft law;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2016-07-29
魏志榮(1981-),女,黑龍江龍江縣人,管理學博士、政治學博士后,濟南大學政法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政府管理、公共政策。
G647
A
1005-5843(2016)11-0006-05
10.13980/j.cnki.xdjykx.2016.1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