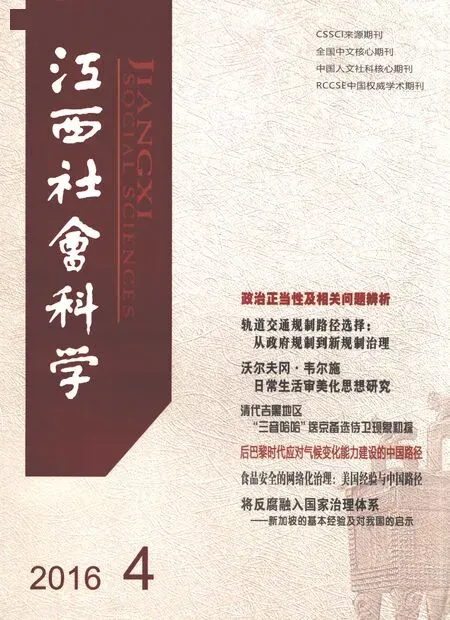客家歌謠女性書寫的當代價值
■閆淑惠 徐林祥
客家歌謠女性書寫的當代價值
■閆淑惠 徐林祥
女性在具有鮮明地域和族群特色之客家歌謠的創作、傳播過程中發揮著主體作用,客家歌謠呈現出女性書寫與書寫女性交相輝映的狀態。客家歌謠中的女性書寫與客家傳統社會的地理狀況、民風民俗、經濟發展等因素直接相關。它集中展現了傳統社會客家女性的生活、情感和精神世界的多樣風貌。同時,客家歌謠中的女性書寫為族群與地域文化研究提供了樣本,對深化客家學研究、開拓當代女性研究視野、促進客家文化傳承與創新等具有現實意義與當代價值。
客家歌謠;女性書寫;族群;地域文化
閆淑惠,揚州大學文學院博士生,贛南師范大學客家研究中心講師;
徐林祥,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江蘇揚州 225002)
以贛南、閩西、粵東北交界地帶為中心的區域廣泛分布著漢民族的一支重要支系——客家。據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的考證,客家先民的祖先系中原士族后裔。因戰亂等原因,他們自晉至宋元經過多次遷徙、輾轉來到贛閩粵邊區。這些地區土地貧瘠、交通閉塞、瘴癘盛行,自然環境惡劣。客家族群雖不斷遷徙,卻始終銘記中原古風,同時不斷適應改造當地地理自然環境和畬、瑤等土著民族文化風俗,經過長期的融合,形成了具有鮮明地域和族群特色的客家文化。而以客家山歌為代表的客家歌謠是客家文化的基本要素,其形成是確定客家文化乃至客家民系成型的標志之一。[1](P361)
客家歌謠以客家方言為主,輔以曲調加以表現。客家歌謠是反映客家生活的一面鏡子,舉凡勞動生活、人情風俗、愛情婚姻、人生遭遇、游戲娛樂等都在客家歌謠中一一呈現,從內容題材、曲調、功用等角度,可以有多種分類。如同其他歌謠“多半是由婦女們造成的”、“多半是討論婦女問題的”[2](P77-94)一樣,客家歌謠記錄了客家婦女的生活形態、思想狀態,其中的女性書寫與書寫女性交相輝映,異彩紛呈。
一、客家歌謠女性書寫的歷史與特點
客家歌謠大多是由女性創作的,黃遵憲稱其為“婦人女子矢口而成”。這與客家所處的自然環境和社會傳統有直接聯系。客家人所到之處膏腴之地多已被土著占據,他們只能在貧瘠的土地上耕種。不利的自然條件決定了客家人不能再延續中國傳統社會“男耕女織”的經濟形態。為了謀生,客家男子多遠離家鄉,遠渡重洋,有的幾年才回去一次,有的可能到年老才會回家鄉。因此,與其他地方的女性相比,客家婦女就必須承擔更多的家庭和社會的責任。一方面,客家女性要履行傳統女性“主內”的角色;另一方面,由于男性的“不在場”,本應由男性承擔的農事一類的粗重活也落到了客家女性身上。再加上,受程朱理學婦女觀等思想的影響,傳統社會客家地區形成對女性的歧視和壓制。面對生活的種種重壓,吟唱歌謠則成為傳統社會客家女性排解勞累、抒發情懷的一種重要方式。
客家婦女自小便生活在女性長輩的歌謠聲中,長大后她們也模仿長輩延續歌謠的傳送和創作。歌謠中眾多的愛情山歌直接驗證著客家婦女的創作實踐,在大量的勞動歌、愛情歌、戰斗歌中處處顯露著女性的才思。在客家歌謠的傳播過程中,客家婦女不僅充當創作者角色,還是重要的演唱者和傳承者。
因此,客家歌謠的女性書寫有著鮮明的族群性和地域性的特征。首先,客家歌謠是用客家方言創作和吟誦的。客家方言是客家族群的身份標志。客家人雖屢次遷徙,但堅持“不忘祖宗言”。“山歌每以方言設喻,或以作韻,茍不諳土俗,即不知其妙。筆之于書,殊不易耳”[3](P56)。客家人善于將客家地區常見的自然景象融入歌謠中,如“山、樹纏藤、藤纏樹”,使得客家歌謠的地域性色彩濃厚,客家特有的方言詞匯、方言語音熔鑄了客家女性對于祖先和族群的敬仰,客家歌謠在女性的創作與延續中已演變成為客家族群文化認同的符號。其次,客家歌謠有自己獨特的藝術表現形式。客家歌謠不甚講究雅馴,只求順口,一般句尾押韻,注意字音的聲調搭配,注意整個句子的和諧、抑揚頓挫,因此,客家歌謠明白易懂、朗朗上口,便于吟誦。客家歌謠常常將客家民俗、典故、客家典型意象融于歌謠當中。在客家童謠中,就有很多“觀音”、“讀書郎”等客家人熟悉的意象。這些意象內蘊含著客家人的信仰和文化心態,其運用增強了客家歌謠的藝術表演力。
二、客家歌謠中的婦女風貌
(一)客家婦女的生活世界
客家地區是典型的農耕社會,自然條件艱苦,交通閉塞,經濟結構單一。客家人歷來崇文重教。客家人主張耕讀傳家,設立“學田”資助本族貧寒子弟讀書,通過族學、義學教授族人,建立書院、私塾等形式組織客家子弟讀書求學。客家子弟勤奮刻苦,人才輩出,黃遵憲、李金發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古人云:子不教,父之過。然而,客家地區則由于受“膽大飄洋過海、膽小死守家門”、“寧愿出門做到死,不愿在家吃老米”的思想影響和當地生活境遇的局限,客家男子大多終年在外謀生,生活勞作的重擔主要由女性承擔。客家地區“女子役男子役”成為普遍現象。《客家哺娘》生動描述了客家婦女家庭“四頭四尾”的生活場景,也是傳統社會客家婦女生活世界的真實寫照。
同時,教育的責任理所當然地落在婦女的身上。客家婦女從小就被教唱 “月光光、秀才娘”,歌謠中“秀才娘”的種種美好際遇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中扎根。他們深知知書達禮的價值,讀書為貴的思想自他們出生就一直存在,在結婚生子之后,他們更把相夫教子作為人生最重要的功課,即使生活再清苦,也要支持丈夫和子女讀書。“討食也要叫子女讀書”、“喉嚨省出叫子讀,只望孩兒美名揚”,這些客家地區流行的民諺,也是客家人崇文重教民風的明證。客家婦女在這樣的民風之下,堅守內心的向往、艱苦勞動,執著支持丈夫和子女讀書向學。
客家婦女從小就通過童謠等形式教育子女要多讀書。以《月光光》為代表的客家童謠為例,“月光光,秀才郎,騎白馬,過蓮塘……種田怕稅重,不如去讀書。讀書有官做,大家都歡喜。”證明了讀書人被客家人喜愛和尊重,童謠通過對讀書人各種生活情境的描繪表達客家人的崇文重教思想。客家婦女還通過歌謠教育子女在讀書求學的過程中要勤學好問、自強不息。“不學唔知,不問唔曉”,“讀書肯用功,茅寮屋里出相公”,“秀才不怕破衫,最怕肚中無貨”,“家有千金,不如藏書萬卷”,“子弟不讀書,好比沒目珠”。客家婦女通過樸素的歌謠民諺傳遞教育理念,身體力行,竭盡所能創造教育條件。
(二)客家婦女的情感世界
在客家歌謠里,有大量表現客家人情愛的內容。正如客家山歌所唱“一陣日頭一陣陰,一陣狂風吹竹林,狂風吹斷嫩竹筍,山歌打動老妹心,涯請山歌做媒人。”在山林間,在勞動中,客家男女以歌謠為媒介傳情達意。畬、瑤等少數民族受封建禮教束縛較少,客家人南遷后與長期與這些少數民族雜居,受到影響也是自然的。音樂學家藍雪霏和歷史學家謝重光分別從音樂和歷史的角度論述過畬瑤與客家的關系,認為其淵源應共同追溯到唐代連畬民的音樂傳統。[4](P84-86)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少數民族對于客家的影響。
在客地,客家姑娘用日常生活常見的事物入歌,通過歌謠表達愛意。著名詩人李金發《嶺南戀歌序》中提到:“客家有些聰明女子,可隨口唱歌,恰合她所表示的情思,如七言詩的入韻,其詞句組成的妙麗…有時是大詩人所不及的。”“新做煙卷一條龍,老妹唔怕哥哥窮,取你人好心腸好,取你人窮志不窮。”“高山做屋蓋杉皮,有心有意來戀你,哥哥情義有咁好,煮菜煮粥也愿意。米果放糖莫放鹽,織網用繩莫用線,哥妹兩人來相愛,講情講義莫講錢。”在這些歌謠中,“煙卷”、“杉樹皮”等都是常見的物品。客家姑娘隨手拈來,表達她們質樸的愛情觀。
情投意合的愛情自然是最好不過的。但是,傳統客家社會,“等郎妹”、“童養媳”、“隔山妻”等畸形婚戀大量存在,給客家婦女帶來巨大痛苦。畸形婚戀現象在傳統客家落后地區表現尤為突出,這與客家地區的民風、民俗、經濟發展等因素有直接的聯系。在客家傳統社會嚴格的宗族觀念和制度的約束下,客家女性不可能用類似離婚等實際行動去反抗這些不幸的婚姻。她們能做的唯有以歌謠為媒介,排解內心的痛苦。童養媳董四金在家受苦受累,在外能唱唱山歌就覺得輕松多了,“唱了山歌不高興的事就忘了”[5](P164)。在落后、閉塞的傳統社會里,歌謠儼然成為客家女性生活中重要的情感寄托,調解和慰藉著煩悶的情感生活,支撐著她們堅韌地存活。
(三)客家婦女的精神世界
客家婦女除了承擔家庭的日常生活瑣事外,還肩負著維系家庭和諧氛圍的重任。在家庭生活的諸多方面,客家婦女表現得識大體、明大義。客家婦女深知家和萬事興,在對待家庭成員方面,他們孝敬父母,關愛小輩,與同輩相處融洽。“打開竹板唱開腔,人生百歲念爺娘,尊敬父母愛(要)做到,父母年老愛贍養,低頭飲水念高崗。”歌謠反映了客家婦女的孝心,他們對父母的養育之情感恩戴德。客家婦女的“孝”以孝敬父母為起點,推廣為睦姻睦族,進而為民族盡大孝,為國家盡全忠。
在丈夫要出遠門時,客家婦女也表現出大局意識,“一囑我郎放開心,莫把妹子掛在心,妹子好比油燭樣,油燭總是一條心。二囑我郎心莫灰,總愛勤儉做家財,游手好閑么了日,大小生意做等來。”在異族入侵、家國不寧之際,客家女性更表現出大義凜然、保家衛國的剛強氣概。南宋末年,江西吉安客家人文天祥起兵勤王、毀家紓難,所率隊伍多是贛閩粵交界地的客家人,客家婦女也不甘落后,積極投入抗元斗爭。許夫人、洪宣嬌、邱二嫂等是客家婦女反抗黑暗統治、追求進步的代表。近代革命史上,“《送郎當紅軍》、《十送紅軍》等都是客家婦女心懷國家的心聲,客家婦女和著歌聲將自己的丈夫、兒子送往前線。在國家危難關頭,客家婦女舍小家為大家,涌現出許多母送子、妹送哥、妻送夫的動人場面。客家女性不僅支持家中男子參加革命,自身也積極追求進步,參與革命斗爭中。“妹送郎當紅軍,臨別贈言記在心,郎在前方打勝仗,妹在家中搞婦運”,客家婦女在家“搞婦運”既是對男子的支持,更是另一種形式的戰斗。“阿妹送哥當紅軍,同心協力打敵人;郎拿駁殼打地主,妹拿大刀殺豪紳。你莫笑耕田嬤,紅軍妹子頂呱呱,又會打槍打白狗,又對耕田駛犁耙”。這首歌謠充分表現出客家妹子的驍勇善戰,表達了客家婦女渴求解放和堅信勝利的信念。伴著客家山歌的悠揚旋律和鏗鏘節奏,客家姑娘的追求進步獨立、民族解放的英雄氣概一覽無余。
三、客家歌謠女性書寫的當代意義
(一)提供族群與地域文化的研究樣本
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范圍內興起了地域文化研究潮流。美國、日本相繼以立法的形式保護和推動地域民俗文化研究。客家文化以其對文化的堅守性著稱于世。以歌謠為切入口,以歌謠與婦女生活為線索,是我們了解地域社會的一條途徑。“性別是社會分層的一種主要形式,也是建構個人和群體所面對的基于和生活類型的決定性因素,并強烈地影響著個人和群體在社會結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族群文化與地域社會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6](P82)客家女性在世界女性形象中獨樹一幟,有人曾評價說是“最偉大的女性”。傳統社會中的客家女性雖整日辛苦勞作卻極少怨言,即使身心受到折磨卻從不丟棄希望。在艱苦的歲月中,她們用歌謠慰藉心靈,啟迪孩童,振作精神;在國家和民族危難之際,她們挺身而出。客家婦女的功績彪炳于客家發展史上。沒有哪一個族群的婦女,能如客家婦女一般,成為這個族群和地域的文化代表之一。
客家童養媳、等郎妹歌謠都是特定歷史時期下的產物。客家歌謠內容與形式的變革,體現了歌謠的發展,展現了客家女性命運的轉變。歌謠映射了客家女性的思想、生活與情感世界,女性也通過歌謠表達她們對于外部世界以及自我世界的認識與感悟。客家歌謠中的女性書寫反映了女性與客家族群、客家地域社會的關系。有關客家歌謠女性書寫的研究為族群和地域文化研究提供了一個樣本。
(二)開拓女性研究視野
女性主義的先驅西蒙·波伏娃說:“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客家歌謠塑造了客家女性。客家歌謠源于民間,是對客家地域社會最為原汁原味的記錄,其中展現了諸多最為真實、自然的客家婦女及其風貌。客家歌謠中的女性書寫為與客家婦女相關的文化、歷史地位變遷等的研究提供了事實的積淀。立足客家歌謠,關照客家婦女,有助于我們在豐富原始素材的基礎上進行分析和判斷。
女性的書寫經歷一直伴隨文明的進程,女性主體身份的流動性特點一直處于不斷建構的過程,永遠不會呈現完成狀態[7],對于客家歌謠的研究,女性主義是一個常談常新的視角。歌謠塑造了客家女性,客家女性也在不斷地重塑客家歌謠。女性意識的覺醒與發展推動著客家社會的變化與歌謠的變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歌謠之于女性,二者是相輔相成的,二者在不斷地“書寫-被書寫-再書寫”的過程中實現著彼此的深化與升華。而二者之間的深層角色關系是當代客家研究和女性研究的關注點,還需要進一步挖掘。
(三)深化多學科融合的客家學研究
自20世紀30年代羅香林開啟現代意義上的客家學術研究以來,客家學研究已逐漸成為一門顯學,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經過80多年的發展,這門學科還并不完善。客家女性社會是客家學研究中一個較少有人關注的領域,是客家學研究中最為薄弱的環節之一。[6](P35-36)客家歌謠女性書寫研究本身涉及面廣,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很多,其本身也需要多種學科的介入與學科的整合。音樂學、語言學、舞蹈學、人類學等學科知識對于我們深入研究客家歌謠女性書寫書寫的淵源、特征、藝術價值等很有幫助。反過來,客家歌謠女性書寫研究也為多學科交融研究提供實踐舞臺。田野調查、訪談、問卷統計,歷史學、社會學等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能夠從不同層面搜集客家歌謠、審視其女性書寫的內容與價值,有利于形成對這一研究的全面認識。
客家歌謠女性書寫研究能夠促進學科交融,深化客家學研究。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可以發現客家歌謠女性書寫的多種研究意義和價值:從其發展歷程來看,有歷史學的意義;從其內容上看,則有民間文學意義;從其收集、整理的過程來看則具有民俗學和社會學的意義。客家歌謠中反映的有關客家婚姻形態、家庭關系等都可以成為客家歷史、客家社會研究的佐證;以陳賢英為代表的客家女歌手、客家婦女的個人成長史本身也是客家社會發展的縮影。以客家歌謠女性書寫研究為中心的客家婦女生命史、客家婦女社會活動史、客家社會網絡研究等,都可以為客家學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四)促進客家文化傳承發展
客家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客家歌謠又是客家文化的分支。客家歌謠以客音表達,既是客家族群特征的表現,也是客家族群邊界的符號。它已成為客家文化的代表,維系客家族群認同感的精神支柱和邊界符號。客家歌謠中的女性書寫直接記載女性的心路歷程,反映了時代和社會的變遷,是客家鄉民重要的集體記憶,更是客家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客家女性、客家傳統社會的價值觀念通過歌謠這一載體進行沉淀和積累,千百年來,歌謠對客家文化的傳承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在現代文明和大眾流行文化的沖擊下,客家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危機重重:會說客家話的客家后代越來越少,傳統的客家手藝后繼無人……。這種情勢下,客家歌謠需要在形式方面借鑒其他藝術形式,內容上增加富有時代氣息的內容,空間上逐漸從山野進入城鎮,才能不斷煥發新的藝術活力。客家歌謠中的女性書寫更是責任重大,一方面要完善保持客家歌謠健康質樸的文化韻味和文化傳統;一方面要積極采用靈活的形式,加快傳播和影響。發揮客家歌謠女性書寫的易記易誦、便于教育的優勢,綜合利用現代技術手段,提高客家歌謠女性書寫的現代性水平,積極發揮其在現代語境中對于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的媒介作用。
[1]謝重光.客家文化論述[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2]苑利.二十世紀中國民俗學經典·史詩歌謠卷[M].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3]鐘俊坤.客家山歌文化研究[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9.
[4]謝重光.客家文化與婦女生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高小康.客家山歌的當代傳播與影響[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6]劉大可.田野中的地域社會與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7]劉巖.女性書寫的“主體(性)”悖論[J].文藝研究, 2012,(5).
【責任編輯:田 鑫】
G122
A
1004-518X(2016)04-0247-05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客家文化研究”(12&ZD132)、江西省2011“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資助項目(KD201504)、江西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語言文化與族群認同研究——以客家族群為例”(15SH14)、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客家方言與族群認同”(JC1504)、贛南師范學院社科重點招標課題“贛南客家歌謠語言文化特征研究”(14zb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