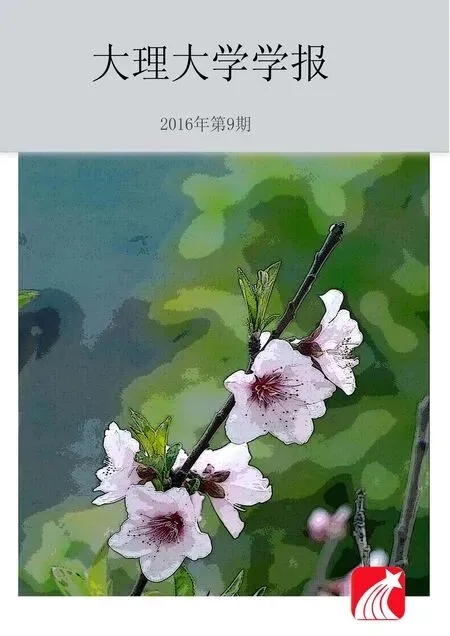論《春秋大義述》“經世致用”的時代特色和個人特色
肖 峰
(1.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長沙410081;2.銅仁學院文學院,貴州銅仁554300)
論《春秋大義述》“經世致用”的時代特色和個人特色
肖峰1,2
(1.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長沙410081;2.銅仁學院文學院,貴州銅仁554300)
楊樹達著《春秋大義述》目的是激發抗日敵愾,打擊漢奸和倭寇,有很強的時代特色。他在著述中述而不作、不事考據,原因在于他的幾個恩師在《春秋》義理的闡發上爭論不休,這既迥異于歷代各家對《春秋》義理的闡發,也迥異于他本人其他著作的撰寫風格,個人特色鮮明。綜觀他的其他著作,他對《春秋》義理的闡發還是述而有作的。
春秋大義述;經世致用;時代特色;個人特色
[DOI]10.3969/j.issn.2096-2266.2016.09.012
楊樹達(1885-1956),湖南長沙人,近現代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和史學家,近代湘學代表人物。在中國慘遭日本侵略,國土淪喪,民族危亡之際,他慨然作《春秋大義述》一書,書中倡“復仇”“攘夷”,誅討“叛盜”等內容,在當時對打擊侵略者和漢奸的囂張氣焰,弘揚抗日正義,有著重要的輿論導向作用,體現了他治經以治世的學術追求。而該書不事考據,“一以大義為主,考訂之說概不錄入”〔1〕8的撰述方法,既有異于楊氏的其他著述,也迥異于《春秋》學其他學者的撰述方法。深入探討這些問題,不僅具有社會現實意義,也有助于我們從不同視角了解楊氏的治學特點。
一、《春秋大義述》撰述的學術背景和時代背景
楊樹達的語言文字學研究私淑段、王,相關著作如《積微居金文說》等皖、浙學風濃厚。而作為近代湘學的代表人物,《春秋大義述》一書則有著非常濃厚的湘學特色。所謂湘學,源于朱熹所稱的“湖湘學”,是一個有特定內涵和時空范圍的學術思想史概念。從內涵上看,它是中國傳統學術即國學的一部分,具體說是中國儒學、宋明理學的一部分,有別于閩學、洛學等其他地域學術派別〔2〕,不僅有自身特有的地域特色,更具有鮮明的思想內容和價值取向。內容包括濂溪學、船山學、湖湘學和近代湘學,其特征在于具有強烈的原道意識,強調經世致用,高揚民族主義,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從時間上看,其源頭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的楚文化,而具比較嚴格意義的學理和學術傳承意義的湘學,始于南宋時期胡安國父子。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湘學的上限斷自北宋的周敦頤,下限為清末民初之際〔3〕。湘學的學術根基在于經學,其治學特色則在于經世致用,《春秋大義述》在特殊的歷史時期下撰述而成,既是對經世致用這一湘學傳統的稟承,也是對《春秋》作為經學服務政治功能的弘揚,有著深厚的學術背景。
《春秋》一經,經世致用是它的本來之義。魯國史官在記錄史實過程中,這種寫作意圖就已經深含其中,孔子修《春秋》,是為了存周道,這種政治目的就更加顯白無疑了。此后,在不同時代,不同學者對該經經義從不同角度作出過闡發,這對保持當時社會穩定和推動社會進步方面起到了相當的作用。董仲舒闡發經義,為大一統奠定了思想基礎;而清末的維新變法則通過該經的經義闡發來尋求變法的理論依據;楊氏撰述《春秋大義述》,目的在于激發族人抗日敵愾,其書所承載的現實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
楊樹達自小生活在湖湘文化中心的長沙,由于家庭教育的原因,自小就接觸到很多當時名重一時的湘學大師,湘學的學術傳統深入到他的每一根神經,并深刻影響楊氏治學的價值取向。在治經與治世的關系上,他認為治經的目的就是用以治世,經籍所承載的義理道德可以施行于世事,“通經本所以致用,經義大可以治事”,而對世人認為治經于世事無用的觀點提出嚴厲批評,“世人目經術為迂疏無用者,固大謬也”〔1〕9。曾運乾曾稱贊《春秋大義述》“上契圣心,近符國策”,有存“撥亂反正之道”和明“通經致用之方”的功用〔1〕4-5。由于各自面對的社會環境不同,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也不同,在經義的闡發上,其側重點也就有差異,對于當時的楊樹達來說,他所面對的就是如何打擊日寇的侵略,因而表現出了鮮明的時代特色。
首先,他對日寇給中國帶來的深重災難有著深刻認識。作者從小飽受日本的侵華之辱,中日甲午之戰,他親睹祖父及父兄的憤慨之情,國恥深埋于心。后游學日本,對日本的狂妄自大、狼子野心有了更切近的認識,而晚年日本在中國本土上犯下的種種罪行,使他不僅肩負起了傳統知識分子因外族入侵所應有的國仇,也使他深深懷有日寇入侵中國楊家遭到破壞的切膚之痛的家恨,如1938年4月初,敵機炸岳麓山,湖大圖書館被毀,死三人,當時楊氏“以大人營葬事清晨入城,免于當場驚悸,為萬幸矣”〔4〕141。1939年4月底,“敵機炸辰溪城”,其所居“前檐屋瓦皆墜”“室中塵土滿地”“鄰彈相距不過十丈許。脫稍偏,妻子四人成齏粉”〔4〕150。其次,他對我族人士抗日的凜然正氣有著深切共鳴。面對倭寇的野蠻和兇殘,我族上下奮起抗爭,其間所彰顯出來的勇氣和節操令楊氏十分欽敬。如1939年5月初聞錢玄同病逝于北京,對錢身陷寇患仍能堅守操守十分贊賞,“周作人為其友,錢稻孫為其侄,皆已附逆。玄同獨不受污,志節皎然,尤為可敬”〔4〕150。1939年6月中,聞好友劉弘度的學生苗可秀抗日獻身,即賦詩:“無端狂寇掠三邊,殺賊終軍正少年。縱有貔貅師百萬,漢家終見服柔然。猶有門人作鬼雄,幼安無負客遼東。浮云蔽日須臾事,夕照從來分外紅”〔4〕151。這些人在抗日中凸顯出來的高風亮節與《春秋》所彰明的大義相合,兩者交相輝映,相得益彰。因此,他本著繼承《春秋》“善善惡惡”的經學傳統來撰寫《春秋大義述》。該書撰寫始自1939年7月底,“近日憤于國難,治《公羊春秋》,欲撰述條例,《春秋大義述》始此”〔4〕152。所謂“國難”,就是指日寇對中國本土的侵略。楊氏所面對的現實問題就是當時中國如何聚全民族之力乃至全世界之力,盡快將日寇驅出中國。作為一個傳統知識分子,一方面深以“荏染書生,迫於衰暮,不能執戈衛國”〔1〕6為憾,但著書立說,闡明抗日大義,鼓舞我族士氣是楊氏的長處,教諭國人“嚴夷夏之防,切復仇之志,明義利之辨,知治己之方”〔1〕7,同樣可以起到打擊敵人的作用。
鑒于這種時代背景,他在撰寫該書時對經義的取舍主要以是否利于抗日為標準。“《春秋》一經,其微言大義,經董仲舒闡發,其最著者即‘大一統’”“要實現大一統,必須‘尊王攘夷’”〔5〕。但書中并未將“大一統”和“尊王”單立一個義類,只將“攘夷”獨立出來,因為當時將夷即日寇攘斥國門之外是中國最重要的任務,因此舍“大一統”與“尊王”而獨取“攘夷”一義,其意圖是不言自明的。治《春秋》,探討“微言大義”是一個無法回避的話題,從一些學者看來,經中除了大義,更多的是碎義,楊氏撰此書時,最初定為《春秋述指》,“取《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之義也”。這數千之義,多半大概是碎義。楊氏認為,“大義”,就是“碎義之反也”,如“說《春秋》者矜持‘三世’之說,毛舉日月之例”即是。除此之外董仲舒《春秋繁露》提到的“陰陽五行”、何休的“牽強穿鑿之說”、康有為在變法中提出的“新王改制”“通三統”等也應該歸于“碎義”之例。上述義理,由于與當時的社會時事實在沒有太大關系,楊氏都棄而不錄。因此,可以說楊氏的意圖就是要將回歸到魯史官撰寫和孔子修治《春秋》時的本來面貌,在“遵圣意”的前提下,為抗日提供強大的輿論支持作為該書撰述的學術使命,從而實現治經以治世、救世為急務的最高價值追求。
《春秋大義述》由于緊貼時代脈搏而在當時引起廣泛共鳴,影響巨大,具有很高的社會價值。該書1944年1月出版,4月底就售出近800本,“戎馬倉黃之日,經術迂疏之書,得此銷數,頗為意外”。究其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說“蓋以復仇攘夷之說頗合國人心理故耳”〔4〕214。同樣,該著述能夠推陳出新,顯示出了楊氏鮮明的個人特色,因而也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二、《春秋大義述》推陳出新與個人特色
《春秋大義述》是“樸學家經世之作”,“與乾嘉漢學家可謂全然異轍”,就在近代湘學中,該書也卓然有異,“對于《春秋》大義的內容,與默深(即魏源)之見自有出入。”從他個人撰述風格來看,“《大義述》編撰之法”即是“以傳證經”“前此的《周易古義》即用此法”“《老子古義》亦相類似”,但是還是“有進于此”,主要表現在“廣采兩漢君臣論事涉及《春秋》大義者”〔6〕。與他同時期語言文字學相關著作比較,不事考據也是一個很大的轉向。因此,無論跟前人有關《春秋》義理闡發的著述相比,還是跟他本人相類似的著述相比,都有很大突破,個人特色鮮明。
《春秋大義述》富于個人特色與作者豐富的求學經歷和深厚的學術積累有關。這突出表現在他能廣參他書,但又不囿于他書,無門戶之見。他的老師中,或在經學上深有研究,如胡元儀是當時名重一時的經學大師;或對《左傳》深有研究,比如他的父親。更重要的不少是《公羊春秋》的研究大家:楊氏在時務學堂學習時梁啟超教“以《孟子》和《公羊春秋》”;葉德輝和蘇輿是《翼教叢編》的重要參與者,該書探討的就是《春秋》義理;不僅如此,蘇輿還是清末《公羊春秋》研究的大家,著有《春秋繁露義證》,楊氏向他求學時挾該書“時時晉謁”,而蘇輿“頗以書中要義相指示”〔5〕。這些豐富的求學經歷,為該書的撰寫提供了重要的借鑒。此外,他在該書著述期間,也參考了清代康有為、陳立、孔廣森、劉逢祿和皮錫瑞等人的著述,通過各家的比照,各有趨取:陳立《公羊義疏》“搜羅甚富”,孔廣森《公羊通義》“針對《徐疏》立說,實較精彩”,皮錫瑞《春秋通論》“大體平實”,而劉逢祿書“實無可取也”。這些廣博的涉獵既能使他體悟到《春秋》經中的精微之處,也能對各家優劣體察入微。因此他在著書立說時能左右逢源,結論自然確不可易。
從內容上看,第一卷是該書最重要的部分,最能體現作者的寫作意圖和價值取向,主要闡發“榮復仇”“攘夷”“貴死義”“誅叛盜”和“貴仁義”等五方面內容。雖然“攘夷”義理的闡發貫穿整個《春秋》經義研究的始終,并且有很強的繼承關系,但在各個時期,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從論述的內容上看,在湖湘學派里,對《春秋》夷夏問題的探討“胡安國雖以禮義分辨華夷關系,卻沒有為夷狄確立進退的標準”,“蘇輿既強調華夷之防,也指出夷狄可進至華夏”〔7〕。楊氏繼承了他的老師蘇輿夷狄與華夏的關系轉換理論,也賦予了更豐富的內涵:以前的學者往往重在尊王、重在夷夏之辨或夷夏之變,楊氏針對時事,在攘夷一編里,其論述重心還是落在對“夷”的打擊上,如果我們對照第一篇“榮復仇”來看,就更加清楚楊氏攘夷的意圖。其次該書在義理的闡發上將“誅叛盜”裒舉出來,單獨立為一編,這是以往學者所沒有提及的,可以說是他的一個創舉。這一方面是“一九四一年接受正中書局的建議增補”,聲討“憑藉異族之勢力以脅父母之邦”〔1〕299的漢奸汪精衛之流,另一方面也是他在平時的學術積累并深感于時世的妙手偶得。其他各卷內容相對雜蕪,難以用一個主題來全面統紀,除末卷外,大部分是圍繞抗日和經世來闡發。如楊氏談到“貴有辭”一篇的目的時,認為“國必求與國自助,故折沖樽俎者尚矣”。當時中國要想取得抗日勝利,得到友國的幫助是必不可少的。
跟楊氏很多著作一樣,他很注意將自己的研究成果拿到教學中去驗證,而在教學中獲得的心得又用之于自己的學術研究中。羅常培先生評價他說,“每開一門課程就有這門的著述”“遇夫先生是有目的地結合著教學實踐來讀書的,通過教學實踐又使他的研究更深入一步”〔8〕。該書就是其中的一個典范。1939年秋季,經過兩個月的撰訂,“乃取以教授諸生”〔1〕291,在教授過程中,“每習一章,即明一義”〔1〕7,教學對該書的逐步修訂和完善起到促進作用,這些義理的教授對傳播抗日思想和堅定抗日信念也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這也可以看作是楊氏學術研究所體現出來的“經世致用”推陳出新的一個注腳。
在楊氏一生的治學過程中,始終堅守乾嘉時期的樸學風格,私淑段、王,撰述重證據,信奉無征不信,強調述有己意,并以“述而有作”自得。唯獨著述該書時他一再強調“非萬不得已,則不下己意”〔1〕292,他在“凡例”上明確指出:“一以大義為主,考訂之說概不錄入,遵圣意也”〔1〕8。也就是說,該書只是為了闡明魯史官和孔子的大義,只作義理的歸納和總結,不作深入挖掘和進一步演繹。楊氏的這種“述而不作”主要源于一段學術公案。清末康有為引導的“戊戌變法”,其政治理論基礎是“新王改制”“通三統”等,這些都是從《春秋公羊傳》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的相關義理中演繹出來的。當時變法在湖南推行得轟轟烈烈,但同樣也遭到了以王先謙為首的當地鄉紳也是學術領袖的強烈反對,對他的“新王改制”“通三統”進行了猛烈抨擊,蘇輿是王氏的得意門生,是這次對抗的中流砥柱。正如方克立所描述的“湘學的經世取向使一部分湖湘士人具有了通變精神而成為著名的維新派,而同樣由湖湘學統培育出來的那些守舊派經學家卻頑固地反對新學、新政。湘學的這種兩重影響,使湖南在近代經常成為維新與反維新、革命與反革命激烈搏斗的戰場”〔9〕。這種對抗由變法時政治對抗演變成學術對抗,而這種學術對抗也并未因變法失敗而消失,從相關資料可以看出,這種對抗直到1920年依然延續。由于早年楊氏入時務學堂,梁啟超曾親授過他的《春秋公羊傳》,深受他的教育,1920年以后上北京謀職,又與自己的恩師同在清華大學共事,關系非同一般。這時王先謙與蘇輿均已過世,但他的另一位恩師葉德輝健在,并依然對維新派說解《公羊春秋》的義理頗有微詞。如葉德輝給楊氏的信中即有“令兄兩師,一湘綺,一梁卓如,皆為鄙人平日最攻擊者”〔10〕之句,并十分尖銳地指出“流為康、梁,已成亡國之禍”〔10〕。除了湖湘學派與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存在門戶之爭和很深的學術積怨,就是湖湘內部,也有不和的聲音,葉德輝批評湖湘碩儒也算是楊氏的恩師王闿運“以今文欺人”“六朝文士,不足當經學大師”“名為尊經,實則誣圣”〔10〕。王闿運、蘇輿、葉德輝和梁啟超既是當時名重一時的經學大家,又是楊氏最尊敬的授業恩師。由于種種原因,他們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學術恩怨,而這些恩怨又都牽涉到《春秋》經義理的闡發,這讓楊氏在這一問題上諱莫如深。基于“為尊者諱”的傳統,他在義理的闡發和歸納上不得不小心謹慎。
總之,由于楊氏廣采眾說,自成一家之言,其著述既有非常濃厚的經世致用的湘學特色,也不難看出其無征不信的乾嘉樸學路子。這不僅是對前人《春秋》學研究的一種超越,也是對他個人經學和史學研究的一種超越。
三、《春秋大義述》內容框架與“述而不作”的反思
楊樹達將《春秋》中的大義歸納為29類,每類立為一篇,即上文所述“每習一章,即明一義”,如榮復仇、貴得眾等。每篇之間在內容上也存在一定的邏輯關系,“當時舉國抗戰,‘復仇’之義被置于最重要的地位”〔5〕,因此,以復仇和攘夷為首。復仇和攘夷需要赴死疆場,貴死義自然應該置于重要位置。所立29篇又以5卷統紀,楊氏對這5卷未標題目,亦未在《凡例》中說明分卷的緣由。細繹該書內容,每卷的內容都有一個相對集中的主題:卷一主要針對時事立意,即全國上下同仇敵愾,抗擊日本的侵略,“榮復仇”“攘夷”“貴死義”和“誅叛盜”即是,唯“貴仁義”與時事似乎關系稍遠,不過從義理上亦說得過去,“夷虜不知禮義,忘吾先民卵翼教誨之恩,尋戈于上國”,日寇侵我中土,行的是忘恩負義、不仁不義之事。我族“秉政因國人之怒,起率南北健兒以與夷虜周旋,伸其撻伐”〔1〕6,這是率義師以伸張正義。孔子修《春秋》時往往以一字寓褒貶,其目的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在中間穿針引線的是禮與仁義。筆伐外侵的不仁不義,宣揚抗擊外夷入侵的正義性,激發我族斗志是《春秋大義述》撰述的最重要意圖,這既是對《春秋》傳統的繼承,也體現“湘學”一貫奉行的“經世致用”的學術追求,體現該書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因此,“貴仁義”自然可以與“榮復仇”“攘夷”等大義相提并論了。卷二主要事關修身,“貴正己”“貴誠信”“貴讓”“貴豫”“譏慢”等篇都與個人的修養有關,“貴變改”與“貴有辭”雖與個人修養也有一定關系,主要還是事關治國和外交。卷三主要闡明治國方略。“明權”“重民”“惡戰伐”“重守備”和“貴得眾”皆涉及家國治理,謹始篇多涉“何以書”的問題、重意篇多涉“如何書”,少部分涉及“何以書”,置于治國方略大致可行。卷四多與齊家有關,如“尊尊”“親親”和“重妃匹”,“錄正諫”與“大受命”于義稍隔,似乎放到卷三治國卷相對妥帖。卷五主要對《春秋》“微言大義”條例的抽繹。如“諱辭”“言序”則有關“春秋筆法”中的“如何書”的問題,而“錄內”篇則有關“何以書”的問題。“尚別”與“正繼嗣”篇當置于卷四的齊家卷在內容上似乎更符合。因此,如果從內容上作出統一的話,除卷一不作調整外,卷二至卷五的內容可以作如下相應調整:卷二括“貴正己”“貴誠信”“貴讓”“貴豫”“譏慢”,主要講個人修身方面的內容;卷三括“明權”“重民”“惡戰伐”“重守備”“貴得眾”“貴變改”“貴有辭”“錄正諫”和“大受命”,主要講治國方略;卷四括“尊尊”“親親”“重妃匹”“尚別”和“正繼嗣”,主要講齊家方面的內容;卷五括“諱辭”“言序”“錄內”“謹始”和“重意”,主要對“春秋筆法”的條例進行歸納。這樣一來,每卷內容相對有一個比較明確的主題,不至于蕪雜。不過其他各卷均為五篇,卷三所轄內容則有九篇,差不多是其他各卷的兩倍,為了平衡,該卷可以分卷上和卷下。
對于《春秋》義理的闡發,雖然他在《春秋大義述》一書中是“述而不作”,在其他著作中,還是“述而有作”的,這主要表現在通過金文來考證春秋時代的歷史史實。對于春秋歷史的研究,除了傳世文獻外,在20世紀初,越來越多的學者結合地下出土文物來進行考證,這就是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楊氏素來敬重王國維的學問,這方法在楊氏治學中,也得到很好的貫徹。不過這些考證不集中,只是散見在《積微居金文說》的相關跋文里,經過歸納,楊氏對《春秋大義述》義理上作進一步考證的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對前人的義理提出質疑。如在《春秋大義述·言序第二十九》:對經文“隕石于宋五”“六鹢退飛而過宋都”進行了評價,“記聞則先隕而后石,記見則先六而后鹢”。肯定了經文語序對義理的表達功能,并引用《公羊傳》《谷梁傳》以論證這一觀點。但在《積微居金文說·函皇?跋》中,對這一說法提出了一定的懷疑:
按此銘“自豕鼎降十,又?八,兩鑘、兩壺”,鼎、?后數,鑘、壺先數,與《春秋》經“石五”、“六鹢”相類。《谷梁傳》后數散辭、先數聚辭之別,極見用心,惟經文石、鹢異類:隕石屬聞,鹢飛屬見,先數后數,或當如傳文所說。若此文鼎、?、鑘、壺,同屬器名,又同屬記事之辭,無聞見之別,數字或先或后,殆古人行文變化以求美,不必有深意于其間。如必以傳義說之,則鑿矣〔11〕219-220。
二是通過金文內容來證成或敷暢《春秋》的義理,以補《春秋大義述》之闕。《春秋大義述》以義理為綱,按其內容對事例進行歸類,搜羅備至。如《叔夷鐘再跋》有“丕顯穆公之孫”一語,楊氏在肯定孫詒讓所考證的“叔夷既為成湯之后,宋為商后,此穆公自謂宋穆公”。指出“宋穆公有傳國與弟之高行,銘文特舉其人,蓋以此與”〔11〕76。這可以看作是對《春秋大義述·貴讓》一章的補充。
三是通過金文內容探討古代社會生活,以補《春秋》之不備。《春秋》之所謂仁義,主要指仁慈、愛人、誠信。而楊氏認為《春秋》之所謂仁義除了以上方面之外,還有文化卓犖的內容。他在《積微居金文說·王孫遺諸鐘跋》一文中,通過分析銘文字體后,斷定為徐器。綜合銘文的用韻等方面,而推斷“徐之文治殆欲跨越中原諸國而上之”。然后進一步指出:“傳記每言徐偃王行仁義而楚滅之,以余觀之,所謂行仁義者,實敷揚文治,文化卓犖之謂耳”〔11〕62-63。
此外,他在《積微居小學述林》里,就《公羊春秋》里的義理撰專文進行考訂,如《公羊傳諾已解》《駁公羊傳京師說》《公羊傳君不使乎大夫解》等,由于大多屬于“碎義”,不屬“大義”,在此不作展開。
四、結語
楊樹達作為傳統知識分子,身負對學術傳統和道德傳統的傳播和發揚的重任,有感于倭寇入侵,慨然以作《春秋大義述》,以此筆伐丑類,彰明大義,很有現實意義。該書雖然在“裒取大義”時,態度相當謹慎,“非萬不得已,則不下己意”,即“述而不作”,但綜合楊氏的其他著述,對《春秋》一經,無論在義理上還是名物制度上都作過考訂,其實是“述而有作”的。深究其因,主要在于他的幾位恩師素有積怨,在《公羊春秋》上爭論不休,這使得他不得不語出謹慎,不下己意,這應該看作是對各位恩師的尊重,“為尊者諱”。反觀該書各編的內容,雖然內在邏輯嚴密,但如果從本文的角度來觀照,更能明確該書的主旨所在。
該文得到蔡夢麒師悉心指導,謹致謝!
〔1〕楊樹達.春秋大義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張齊政.湖湘文化筆談:湖湘文化與湖湘學〔J〕.衡陽師范學院學報,2016(1):171-172.
〔3〕王國宇,張衢.湘學研究述評〔J〕.船山學刊,2014(2):56-63.
〔4〕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5〕楊逢彬.楊樹達的《春秋大義述》及其相關未刊稿〔J〕.中國典籍與文化,2002(3):56-61.
〔6〕嚴壽澄.百年中國學術表微〔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222-225.
〔7〕盧鳴東.蘇輿《春秋繁露義證》以禮經世述考〔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18(4):22-30.
〔8〕湖南師范大學學報.楊樹達誕辰百周年紀念集〔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255.
〔9〕方克立.“湘學精神”與“湖南人精神”〔J〕.文史哲,2005(1):17-19.
〔10〕張晶萍,李長林.葉德輝致楊樹達書札四通〔J〕.文獻,2008(4):101-106.
〔11〕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Abstract〕The purpose of Yang Shuda's Chun Qiu Da Yi Shu is for appealing to anti-Japanese and fighting against the traitor ans Japanese pirates with obvious era characteristics.Because his teachers had argument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Yang's work only elaborates the facts and the theories without any personal thinking and evidence,which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scholars' explanation and his other works.With the special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mong all the other works,his explanation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can be considered to be creative.
〔Key words〕Chun Qiu Da Yi Shu;statecraft ideology;era characteristics;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責任編輯黨紅梅)
On the Era an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Statecraft Ideology"in Chun Qiu Da Yi Shu
Xiao Feng1,2
(1.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Humanitie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2.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Humanities,Tongren,Guizhou 554300,China)
G256
A
2096-2266(2016)09-0058-06
貴州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14GZYB51);銅仁學院博士啟動基金項目(TRXYDH1305)
2016-04-26
2016-07-12
肖峰,副教授,湖南師范大學博士后流動站在站,主要從事古文字學與訓詁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