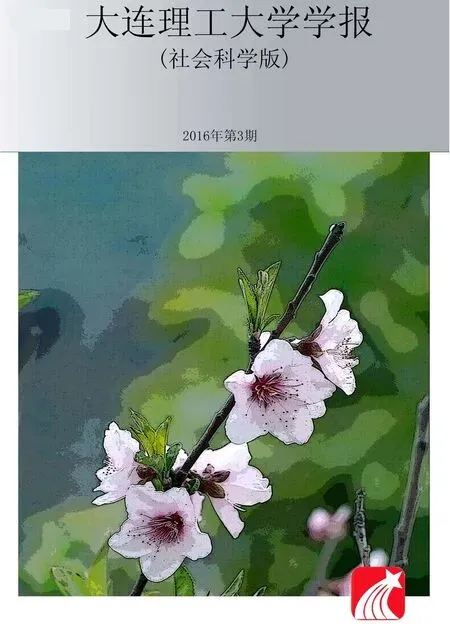論侵權責任減免中的親屬身份考量
艾 圍 利
(上海師范大學 法政學院, 上海 200234)
?
論侵權責任減免中的親屬身份考量
艾 圍 利
(上海師范大學 法政學院, 上海 200234)
摘要:在親屬之間侵權、第三人侵害親屬一方和親屬一方侵害第三人等情形下,親屬身份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為責任減免事由。親屬身份主要通過阻卻違法性、損害、過錯(注意義務)等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來減免責任,以及通過綜合考量情誼因素、親疏有別、和諧安寧的家庭整體利益、家庭的人類繁衍功能等政策性因素來阻卻責任。親屬身份的責任減免功能主要通過立法、構成要件理論等理論運用、法律解釋等法學方法論和法官自由裁量權四種途徑來實現。
關鍵詞:親屬身份;免責事由;情誼因素;構成要件
在刑法上,國內外立法或理論在一定程度上都認可“親親相隱”的合理性,這對于以“倫理的人”為邏輯起點的民法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我國《侵權責任法》專列一章對不承擔責任和減輕責任事由進行了規定,這之中并不包括親屬身份。親屬身份是否可作為減輕或免除責任的事由以及在哪些方面、通過哪些途徑可作為減輕或免除責任的事由,本文擬就此展開研究。
一、我國侵權責任法免責理論之檢討
1.當前免責理論的不足
《侵權責任法》第三章專門規定了不承擔責任和減輕責任的情形,學者對將其稱為“免責事由”或“抗辯事由”存在爭論,本文在此不做討論,統一采用侵權法傳統習慣概念“免責事由”。目前我國侵權法上免責的理論基礎主要包括兩部分:侵權責任不成立而免責和侵權責任成立但予以免除。
目前的侵權責任免責理論在邏輯上存在缺陷。首先,就侵權責任不成立而免責的情形而言,免責事由與不具備侵權責任構成要件形成了這樣一種邏輯關系:免責事由?不符合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侵權責任免責理論完全沒有必要存在,通過責任構成要件理論即可實現免責。其次,我國《侵權責任法》第三章列舉的免責事由基本上是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不成立的事由,而不是侵權責任成立但予以免除的情形。再者,我國司法實踐中認定侵權責任的邏輯結構是,先認定侵權責任構成要件是否滿足,然后檢查是否存在免責事由,這與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理論形成路徑相反。
在減輕責任事由上,我國侵權責任法主要規定了受害人過錯。但受害人過錯與其說是減輕侵權人責任的事由,不如說是侵權人承擔其應當承擔的那部分責任。我國《侵權責任法》第26條規定的減責事由,實際上類似于刑法上的“罪責相當”,可以稱之為“責過相當”或“責因相當”。
2.侵權責任免責理論框架之重構
基于目前侵權責任免責理論的缺陷,有必要建立新的侵權責任免責理論框架。在新的侵權責任免責理論框架下,侵害嫌疑人以免責為常態,只要不存在“特別干預的理由”,侵害人均免責。據此,本文的侵權免責理論框架如下:以免責理論統領構成要件理論,侵權構成要件只是免責理論內部損失移轉的條件,具備完整的侵權責任構成要件則損失由“被擊中者”轉移至侵害人,不具備則損失“停留在其發生之處”,即侵害人免責。同時損失的移轉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損失雖移轉至侵害人,但基于政策考量或利益再衡平損害可能會反向再次移轉至“被擊中者”。這主要是因為侵權責任的承擔實際上是一個利益的再平衡過程,而由于整個社會利益的牽連性,在利益的再平衡過程中,有些案件不僅僅只涉及侵權關系雙方當事人的利益,可能還會涉及其他人的利益。因此損失移轉的過程中有時會基于公共利益、第三人利益的考量而使得本應發生的移轉仍停留在原地,這就是所謂的政策考量。
在這一理論框架下,凡是使得“損失停留在其發生之處”,阻卻其向侵權人移轉的事由,包括損失移轉后使之發生反移轉而回復至損失發生之處的事由,都可以稱之為免責事由,使損失部分停留在其發生之處的事由稱之為減責事由。因此,免責事由主要是指構成要件阻卻事由和使得損失停留在發生之處的政策性因素,減責事由主要是使得損失部分停留在發生之處的政策性因素。其中基于政策考量進行的責任減免是在符合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基礎上根據利益衡平進行的責任減免,可以稱之為責任阻卻事由。
二、親屬間侵權責任減免的身份關系考量
1.親屬間身份關系及民事活動的特征
親屬身份作為身份的一種,具有身份的一般屬性。徐國棟教授認為身份應該是人在社會關系中與他人進行比較而所處的有利、不利以及平等的地位或狀態;張俊浩教授則認為身份是自然人在群體中所處的據之適用特別規范的地位。
親屬身份除了具有身份的一般屬性外,還具有其獨有的特征。第一,親屬身份關系具有濃厚的倫理性和社會性。“夫妻、親子等相互之間的關系,倫理的色彩特別濃厚,親屬法之規定,須以合于倫理的規范為適宜,而且有其必要。”[1](p5)從自然法的角度來說,倫理是一種自然法則,是有關人類關系(尤其以姻親關系為重心)的自然法則,因此即使親屬間的倫理規范沒有上升到法律的地位,其作為公序良俗的一部分對于我們的行為仍然具有約束力。另外,親屬身份權“不獨為了權利人之利益,同時為受其行使之相對人利益而存在”[1](p35),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來說也是為社會公共利益而存在[2],更宏大的意義上來說,家庭仍然是人類繁衍的基礎;第二,家庭成員之間存在著分工合作,家庭成員之間往往具有特別的信賴關系。如貝克爾所言,家庭之所以亙古已有、綿延長存,其原因在于家庭以明確、精致的分工協作為基礎,同時家庭成員之間彼此了解、相互信賴,這極大地減少了監督和管理費用,因此家庭是一個有效率的經濟單位[3](p4);第三,親屬之間的大多數行為都不構成法律行為,而是一種情感行為或情誼行為。所謂情誼行為,“是指行為人以建立、維持或者增進與他人的相互關切、愛護的感情為目的,不具有受法律拘束意思的,后果直接無償利他的行為”[4],當事人間構成“施惠者”與“受惠者”的關系。在家庭領域絕大多數的行為都是為了增進感情的無償行為,不具有使自己受到法律拘束的效果意思,屬于情誼行為而非法律行為。
2.親屬身份對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阻卻
國內外對于特定身份的親屬之間是否可以構成侵權一直存在爭論,本文認為在人格獨立、平等的背景下,特定身份的親屬之間可以構成侵權,因此本文所謂親屬身份關系對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阻卻,不是指在任何侵權類型中親屬之間均不構成侵權,而是指在特定情形下親屬身份對于構成要件形成的阻卻。
(1)親屬身份對違法性和損害要件的阻卻
我國學者對于侵權責任構成要件是否包括“違法性”存在爭議,但是從否定構成要件的角度來說,對違法性的阻卻仍具有意義,因為即便違法性要件為過錯或損害所吸納,對違法性的阻卻也可以認為是對過錯或損害的阻卻。損害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行為人行為的違法,因此本文將違法性和損害在此一起探討。由于親屬身份會導致親屬之間形成特定權利義務關系,親屬身份對于親屬個體的財產權和人格權形成了極大的限制,因此親屬間的某些行為即便侵入了對方的權利范圍領域,往往也不具有違法性,不構成損害,相反,對于對方或社會而言這些行為甚至是有益的。
①親屬身份對人格權的限制
首先,親屬間在評價性人格權上具有牽連性,這是親屬關系的固有社會屬性,很難說是親屬主動追求的結果,因此基于牽連性而“連累”他方的往往不具有違法性。雖然基于牽連性,親屬一方的名譽會因他方而受到影響,但在以下情形下不能認為構成損害或具有違法性。第一,親屬間由于一方社會評價降低牽連影響他方社會評價降低的。雖然是一方引起他方名譽受損,但這并不具有違法性,因為侵害名譽權的行為要求是積極的作為[5](p116),而在這里他方名譽受損主要是由于社會基于聯想性評價導致的。因此在所謂“養不教,父之過”中,父母并不能因此主張子女對其名譽構成侵害;第二,親屬一方導致他方在家庭范圍內評價降低的,不具有違法性或不構成損害。“名譽不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評價,也不是一種自我評價,而是公眾對特定人的評價”[6]。由于家庭在很大程度上被社會當作一個共同體來看待,因此家庭成員內部的評價不構成名譽權的侵害;第三,普通民事主體間構成侮辱、誹謗的行為,在特定親屬之間并不一定構成侮辱、誹謗。如強行與他人接吻、擁抱,將糞便、垃圾涂抹或散播于他人的建筑、門前、庭內等行為一般在刑法上構成暴力侮辱行為[5](p118)。由于特定親屬之間需要在“同一個屋檐下”共同生活,親吻、擁抱也是表達、增進情感的方式,因此在特定親屬間的這些行為不具有違法性。
其次,親屬身份對于自由性人格權形成了限制。自由性人格權除了受到法律的限制外,親屬身份對其構成全方位的限制。基于配偶權之同居義務致使夫或妻的遷徙自由等行動自由受到限制。父母對于子女而言往往有居所的決定權。家庭成員間的隱私權也因為身份關系而受到極大的限制。不僅在夫妻之間,在整個家庭內部往往是作為一個整體來共享一些秘密的,隱私在家庭內部只具有相對意義。甚至有學者認為家庭成員之間通過相互 “侵犯隱私”,可以減少家庭成員彼此之間的利益沖突[3](p41)。就婚姻自主權而言,雖然夫或妻都享有離婚的自由,但在離婚之前夫或妻都不享有再次結婚的自由,否則構成重婚。而就性自主權而言,其本意是指自然人有權自主支配自己的性利益,每個人都有權決定自己與什么樣的異性交往,以什么樣的方式交往。但已婚夫妻,基于配偶之間的忠實義務,性對象只能限制為配偶。另外夫妻雖可侵害性自主權而構成婚內侵權,但夫妻之間很難構成性騷擾。很顯然,上述限制雖然在一般意義上構成對一個人自由性人格權的某種損害,但從法律上來看,這些都是基于親屬身份關系而應當盡到的容忍義務,因此不具有違法性。
最后,在標表性人格權方面親屬身份也會對其產生重要影響。就姓名權而言,雖然法律規定自然人有決定、使用、變更其姓名的權利,但一般來說姓隨父或隨母,名往往也在出生時由長輩決定,在成年之前父母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進行變更。父母子女之間、夫妻之間互相使用對方姓名、肖像的情形也十分普遍,但往往是家庭生活所必須的。這些都反映出在很大程度上,親屬之間在特定情形下決定、使用、變更他方姓名和使用對方肖像的行為不具有違法性。另外,隨著標表性人格權的商品化,對于姓名、肖像等標表性人格權的侵害也主要體現為利用他人姓名、肖像等獲取財產利益,但由于家庭成員采取財產共有制,因此特定親屬間利用對方姓名、肖像獲利也不具有違法性,不構成損害。
從實務來看,親屬之間人格權侵權主要是對身體、健康等物質性人格權的侵害,主要體現為虐待、人身傷害等侵權行為方式。
②親屬身份對財產權的限制
在財產權方面,我國婚姻法原則上采取的是夫妻財產共同共有制,對于家庭財產我國立法上未做明確規定,但在理論和實務上,家庭成員未分家析產之前,家庭財產也是采取共同共有制[7]。在共同共有制下,各共有人因日常生活需要對于一般的共有財產可以平等的、不分份額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只有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對比較重大的財產作出重大的處分行為時,才需要全體共有人同意。這在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17條有明確的規定:“婚姻法第十七條關于‘夫或妻對夫妻共同所有的財產,有平等的處理權’的規定,應當理解為:(一)夫或妻在處理夫妻共同財產上的權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處理夫妻共同財產的,任何一方均有權決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對夫妻共同財產做重要處理決定,夫妻雙方應當平等協商,取得一致意見。”即便是婚姻法上認定為個人財產的那部分財產,也主要是在涉及財產處分以及離婚時才強調其歸屬性。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一方對他方個人財產占有、使用、收益行為,一般也不構成侵權,否則共同的家庭生活必須處處設防,時時留心。可見在特定的親屬之間,對財產權的侵害主要是指對財產處分權的侵害,具體來說,是指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對比較重大的共同財產未經協商單方作出重大的處分行為和個人財產的處分行為。普通民事主體之間存在的針對財產的占有、使用、收益、決定等實施的侵害行為,在特定親屬之間是法律所允許的合法行為。當然嚴重違反“平等原則”的占有、使用、收益、決定等仍可構成侵權。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對比不具有親屬身份關系的一般民事主體而言,由于親屬身份關系的作用,特定親屬之間在很多領域即便侵入對方的某些權利領域也不具有違法性,無所謂損害,而是基于親屬身份關系形成的特定權利義務關系中,另一方必須盡到的容忍義務。
(2)親屬身份作為注意義務阻卻事由
無論在英美法系還是在大陸法系,注意義務都是過失判定的基準。《牛津法律大辭典》對注意義務的解釋是:“一種為了避免造成損害而加以合理注意的法定責任。在侵權法中,行為人無需因疏忽而承擔責任,除非其造成損害的行為或疏忽違反了應對原告承擔的注意義務。如果一個人能夠合理地預見到其行為可能對其他人造成人身上的傷害或財產上的損害,那么,在多數情況下他應對可能受其影響的人負有注意義務。”[8]從這一定義來看,注意義務可以分為“注意”和“義務”兩方面,一方面注意義務是一種“義務”或“法定責任”,另一方面注意義務要求行為達到一定程度的謹慎,即要求達到一定的注意程度。與此相對應,對注意義務的阻卻也包括兩方面,第一,否定該項“義務”,即特定情形下行為人不負有或不再負有該項注意義務。第二,行為人達到了特定的注意程度標準。
從否定注意義務的層面來看,刑法上主要有被允許的危險和信賴原則兩項注意義務阻卻事由,本文認為刑法上的信賴原則對于侵權責任法具有借鑒意義。信賴原則由德國在1935年通過判例首創,德國理論及實務部門確立信賴原則之后,相繼得到瑞士、澳大利亞、日本等國判例和學術的支持,并突破交通肇事領域,在過失犯罪領域占據重要地位。超越交通肇事領域的信賴原則是指,當行為人實施某種行為時,如果可以信賴被害人或者第三人能夠采取相應的適當行為的場合,由于被害人或者第三人不適當的行為而導致結果發生的,行為人對此不承擔過失責任的原則[9]。信賴原則是根據人的相互信任情感、共同責任心以及“社會連帶感”產生的。它強調,既然人們共同生活于一個社會空間,那么,為了維持社會生活的和諧和有序,每個人都應當承擔一些注意義務,而不能把注意義務只加于某一些人,而且人們還應當彼此信任[10]。因此,行為人雖然預見到有損害結果發生的可能性,但是只要對方做出合法或適當行為損害結果就可以避免時,行為人由于信賴對方會做出合法或適當行為,而對方未做出合法或適當行為導致損害結果發生的,該損害結果由未做出合法或適當行為的一方承擔,行為人免責。而如上文所言,家庭之所以長存并使得人類得以延續,其原因在于家庭以明確、精致的分工協作為基礎,正所謂“你耕田來我織布,你挑水來我澆園”,家庭成員彼此之間存在信賴關系。因此在需要相互配合、協作方可完成某項事情的家庭生活中,注意義務應當在彼此之間合理分配,而不是完全由一人承擔。在親屬一方做出一定的行為后,相信對方會做出適當的、合法的配合行為而對方未做出并導致自身損害發生時,信賴方因注意義務阻卻而免責。
從行為人行為達到了特定注意程度標準層面來看,又可以分為兩種情形。第一種,規定行為人與一般人同樣的注意程度標準,并且行為人達到了這一標準;第二種,規定行為人在特定情形下比一般人更低的注意程度標準或者較高的過錯程度要件。考察國外法律規定和實務可以發現,特定親屬之間的很多民事活動注意程度標準往往較普通人之間要低,往往只需盡到與處理自己事務同樣的注意即可。或者有些國家規定夫妻之間、父母子女之間只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才構成侵權。如日本民法規定:“行使親權者,應以與為自己同一之注意行使其管理。”[1](p682)德國民法典第1664條第1款規定:“父母在進行照顧時,只需就在自己的事務中通常所盡的注意向子女負責。”[11]再比如在《美國侵權法重述·第二次》第895F條的評論h中有如下舉例:如果夫妻中的一方在脫衣服的時候把鞋遺留在了某個地方而另一方因此在黑暗中絆倒或者夫妻一方把咖啡弄到在另一方的身上而此時夫妻雙方仍然困倦時,這往往視為沒有過失[12](p374)。另外雖然美國的很多州逐漸廢除了家長豁免權和配偶豁免權,但是其發展趨勢仍然是一般過失不可訴,對于故意侵權才可以提起訴訟[13]。
(3)親屬身份關系作為一種政策考量因素
按照矯正正義的理論,侵權責任的承擔實際上是在侵權人與被侵權人之間進行利益的再平衡。但從宏觀上來說家庭親屬關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某種公序良俗和社會公共利益,甚至是人類繁衍的基礎。因此如果特定親屬之間構成侵權,利益的再平衡不能僅在特定親屬之間展開,而應當同時考量整個家庭甚至社會的利益。本文在此僅探討情誼因素和親屬豁免權的問題。
①情誼因素
德國學者拉倫茨和沃爾夫認為,情誼關系存在于社交領域,是法律之外的關系。可見情誼行為是指行為人以建立、維持或者增進相互的感情為目的而作出的行為,這些行為屬于日常生活、社交領域,行為人不具有受法律拘束的意思,這些行為一般不屬于法律管轄的范圍,并非民事法律行為。情誼行為雖然不屬于民事法律行為,但不能簡單地說不產生任何法律效果,在實務中已經存在情誼行為構成侵權的案例。家庭親屬間的大量行為都屬于情誼行為,好心辦壞事構成侵權的當然也不在少數,但情誼因素能否作為侵權責任的減免事由值得探討。
本文認為在家庭內部基于情誼行為而構成侵權時,情誼因素應當作為責任減免事由,這主要是由情誼行為的特征決定的。首先,情誼行為旨在建立、維持或者增進相互的感情,基于該目的性,情誼行為應當是社會所鼓勵的行為。家不僅僅只是冰冷的法律關系,更是“心靈的港灣”和“情感的寄托”,這需要精心地呵護和情感的投入。因此特定親屬為了增進感情而作出的情誼行為,即使構成侵權也應當考慮其良好的初衷和目的性而予以減免。另外,情誼行為具有無償性和無私性[14]。無償性是指受惠者獲得好處不需要支付對價,往往是單純獲益;無私性是指施惠者主觀上不追求經濟利益的回報,客觀上也未獲得經濟回報。這體現了一種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是施惠者對受惠者作出的單方向利益輸送,因此在施惠者承擔侵權責任而進行利益的再平衡時,應當向施惠者適當傾斜,否則有違公平。德國學者梅迪庫斯也認為既然在很多無償的法律關系中責任都可以得到減輕,在侵權責任中無償的情誼行為應當作為責任減輕事由[15]。這一點也得到了我國司法實踐的支持,在“盧元明訴林福春損害賠償案”(“(2002)龍泉民初字第1057號”)中,法院即認為“施惠者長期無償搭載受惠者上下班可以作為減輕施惠者侵權責任的裁量情形”。
②配偶豁免權和家長豁免權的存廢之爭
配偶豁免權和家長豁免權(spousal immunity and parental immunity)是傳統美國法上的兩種豁免權。其基本含義是考慮到維護家庭和睦的必要,禁止配偶之間的侵權訴訟和子女對父母的侵權訴訟。美國現在大多數的州已經廢除了配偶豁免權和家長豁免權,但仍有很多州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圍內保留了配偶豁免權和家長豁免權[13]。
本文認為家庭有其固有的功能和價值,這是在探討配偶豁免權和家長豁免權存留時不得不考量的因素。劉引玲教授認為,親屬身份權行使的目的是追求幸福,美滿的婚姻和享受天倫之樂是親屬身份關系的價值取向[16]。個人利益無疑需要保障,但美滿的婚姻、和諧安寧的家庭、天倫之樂等家庭整體利益同樣重要。因此本文認為在安寧和諧的整體家庭氛圍下發生的偶然的夫妻間侵權,配偶應當享有豁免權。美國一些州甚至不允許對僅存在單純的經濟損失不伴隨人身傷害的案件提起訴訟,一些州則建立了這樣的規則:只有不存在和諧安寧的家庭氛圍需要維護的前提下才取消配偶豁免權。例如,配偶一方已經死亡、故意或粗暴的侵權行為等。就親權而言,親權在德語中表述為elterliche gewslt,在英語中表述為parental power,都含有權力的意思。這是因為親權最核心的內容是父母對于未成年子女的哺育、監護和教育,在這一目的和前提下,各國都一定程度上賦予父母使用合理的武力懲戒其未成年子女的特權。因此即便父母對未成年子女構成侵權但只要這些做法是從未成年子女利益角度出發的,是作為哺育、監護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手段使用,且程度在社會一般可接受范圍內的,本文認為父母應當享有豁免權。
三、非親屬間侵權責任減免之親屬身份考量
1.親屬身份在對外上的特征
親屬身份對于親屬身份關系之外的人而言,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親疏有別。親屬身份關系是一種長期的倫理的結合,不是一種短期的基于利益的結合,雖然姻親和擬制血親并非不可變動的,但在目的上其仍然是以長期穩定的結合為目標。而基于血緣形成的血親更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在出生之前就形成一種固定的事實,這使得親屬之間比沒有親屬身份關系的人之間在心理、情感等方面更加靠近;第二,家庭對外往往被作為一個整體看待。雖然現代社會已經采取了“夫妻別體主義”,子女有獨立的人格。但在很大程度上家庭仍然被當作一個共同體來看待,如《瑞士民法典》規定:“妻為日常需要之處理,與夫同樣代表婚姻共同體”,“夫為共同生活的代表,也可以妻為代表”。
2.親屬一方對第三人侵權時基于親屬身份的責任減免
親屬一方侵害親屬身份關系以外他人權益的,至少在以下兩種情形下可以基于親屬身份關系而減免責任。
第一種,親屬之間傳播對他人具有誹謗性的事項。美國法和英國法都認為夫妻之間的交流、陳述是絕對特權[12](p716),屬于完全抗辯事由。因此即使夫妻之間傳播對他人具有誹謗性的事項也可以免除責任,張新寶教授則進一步將該范圍擴大至親屬之間[5](p161)。本文認為這種免責源于親屬身份關系的對外屬性,該屬性既可阻卻構成要件,又可作為政策考量。由于家庭對外往往被作為一體看待,因此家庭成員間的傳播不符合“公開”向“公眾”傳播標準,不會影響他人的“社會評價”,不構成誹謗行為。而且“如果法律鼓勵或容許一個親屬作證證明另一個親屬具有此項侵權行為,勢必在親屬之間造成矛盾,其結果是即使在親屬之間的談話,人們也不得不有所顧忌,這是不利于良好的親屬人情關系之建立和維系的。”[5](p162)換言之,從家庭成員情感的角度出發,因疏而廢親,有違人常。
第二種,為了親屬的生命、身體和自由利益,采取緊急避險,保全的法益等于損害的法益,構成避險過當的情形。我國學者一般認為緊急避險中“必要的限度”是指損害的利益小于保全的利益,如果損害的利益大于或等于保全的利益則構成“超過必要的限度”[17]。可見在我國保全的法益等于損害的法益,構成避險過當,避險人需要承擔侵權責任。而學者一般認為所謂緊急避險是指為了避免自己或第三人生命、身體、自由以及財產上的急迫危險,不得已而實施的加害他人的行為。但我國緊急避險理論和立法中的“第三人”未區分“親屬”和其他第三人,這似有不妥之處。德國刑法將緊急避險分為阻卻違法性的緊急避險和阻卻責任的緊急避險,分別規定在德國刑法的第34條和35條,兩者規定了不同的構成要件。德國刑法典第35條1款第1段規定:“為使自己、親屬或者其他與自己關系密切者的生命、身體或自由免受正在發生的危險,不得以而采取的違法行為不負刑事責任。”[18]我國刑法學者認為德國刑法第35條規定的緊急避險與第34條比較有以下特別要求:第一,只能針對生命、身體和自由三項重大的法益實施緊急避險;第二,并非本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遭遇緊急情況都可適用該條,只能是家庭成員和其他親近的人[19];第三,保全的法益等于損害的法益,即按照一般的緊急避險理論構成避險過當[20]。一般認為該法條的理論基礎是“可期待性理論”,即行為人具有可非難性,除了故意或過失之外,還必須要求行為人有實施合法行為的可能性卻沒有實施,行為人的行為才值得非難。學者認為這是“對人性弱點的考慮”,充滿了人性的光輝。本文認為德國刑法上關于緊急避險的區別立法值得我國侵權責任法借鑒,因為它反映了親疏有別的基本人性。在涉及親屬的生命、身體和自由這些最重要的法益時,避險人的急迫心情可想而知,此時不應期待避險人權衡所有利弊并采取完全恰當的避險措施,因此保全的法益等于損害的法益的也應減輕或免除責任。
3.第三人對親屬一方侵權時基于親屬身份的責任減免
在第三人對親屬一方侵權時,親屬他方的過錯可否作為侵權人的侵權責任的減免事由。換言之,我國侵權責任法第26條規定的被侵權人過失,是否僅指狹義的受害當事人過失,還是應當擴大至“受害者方”過失。從國外有關判例來看,特定情形下親屬他方的過失可以減免侵權人的侵權責任。
(1)未盡到監護義務的父母與侵權人過失相抵
日本通過判例認為“民法第722條第2款規定的受害人的過失是指,包含了廣義的受害人方的過失,因他人的侵權行為導致幼兒死亡,在父母一方對事故的發生上存在監護上的過失時,對于雙方的請求可以酌情考慮上述過失。”[21](最判昭和44年[1969]·2·28民集23卷 2號525頁)但并非任何有監護義務的人未盡到監護義務的都可以減輕侵權人責任。在“幼女軋死案”判決中法院對“受害方”進行了限制,在該案中保育士雖然受幼兒父母委托而負有監護義務,但保育士未盡到監護義務并不適用過失相抵原則。法院認為只有“像受害者的監護人的父母或者被用者的家庭使用人等那樣,受害者的身份或者生活關系上成為一體的相關人員”(最判昭和42年6月27日民集21卷 6號1507頁)的過失才可以與侵權人進行過失相抵[22]。
可見這些判決中監護人與侵權人過失相抵的理論依據正是家庭共同體理論,只有父母或者其他在身份或生活上與受害者成為一體者才可看作受害方,其過失方可與侵權人過失相抵。
(2)機動車交通事故中家庭成員駕駛者與侵權人過失相抵
通過判例日本也認可了妻子和孩子搭乘丈夫駕駛的機動車,因丈夫的過失和相對車駕駛者的過失導致發生了碰撞事故,妻子和孩子向相對車的駕駛者請求損害賠償時,對方駕駛者可以丈夫的過失為由主張過失相抵。(最判昭和 51[1976]·3·25民集30卷2號160頁)該判決的理論基礎同樣認為妻子和丈夫在身份上、生活關系上是一體的,關系沒有破裂的夫妻間“錢包一體”[22](p221),而不具有身份上、生活關系上一體性的同事關系(最判昭56[1981]·2·17判時996號65頁)、戀愛關系(最判平9[1997]·9·9判時1618號63頁)等關系中,法院都否定家庭成員駕駛者的過失與對方駕駛者過失相抵。
四、結語
以上關于親屬身份在侵權責任減免中的作用雖然是在各種具體的案例和特定的情形下來闡述的,但是也可以總結出親屬身份作為責任減免事由的四種途徑。第一種,是根據法律的直接規定來免責,如德國刑法典第35條、“臺灣民法典”第1053條關于夫妻間宥恕的規定和美國尚未完全廢除家長豁免權和配偶豁免權的州立法和判例等;第二種,是通過法學方法論上法律解釋方法、類推適用方法等來實現免責。可通過對現有法律進行擴大性解釋來實現免責,如日本將“受害人的過錯”擴大解釋為“受害方的過錯”。還可通過類推適用來實現免責,如將現有法律關于無償行為責任減免的有關規定類推適用于親屬間的情誼行為;第三種,通過與侵權法、婚姻家庭法等相關理論結合在實務中實現免責,如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理論、注意義務合理分配理論、過失相抵理論、家庭共同體理論或 “夫妻錢包一體”理論等;第四種,通過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作為酌定免責事由適用。這主要是指在各種政策考量下的情形,如對情誼因素的考量、對家庭整體利益的考量等。當然這四種途徑也可以結合發揮作用,如上文日本“夫妻同乘案”中結合了法律解釋方法、過失相抵理論和“夫妻錢包一體”理論等。
參考文獻:
[1] 史尚寬. 親屬法論[M].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2] 張繼承. 親屬身份權研究[M]. 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2.42.
[3] 加里·斯坦利·貝克爾. 家庭論[M]. 王獻生,王寧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4] 王雷. 論情誼行為與民事法律行為的區分[J]. 清華法學,2013,7(6):157-172.
[5] 張新寶. 名譽權的法律保護[M].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6] 王利明,楊立新. 人格權與新聞侵權[M]. 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1995.328.
[7] 梁慧星,陳華彬. 物權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43.
[8] 戴維·M·沃克. 牛津法律大辭典[M]. 北京社會與發展研究所譯. 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137.
[9] 林亞剛. 犯罪過失研究[M].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192.
[10] 周光權. 注意義務研究[M].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159.
[11] 陳衛佐譯注. 德國民法典[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516.
[12] 小詹姆斯·A·亨德森. 美國侵權法:實體與程序[M]. 王竹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13] 文森特·R·約翰遜. 美國侵權法[M]. 趙秀文等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244.
[14] 王雷.情誼行為基礎理論研究[J]. 法學評論,2014,32(3):57-66.
[15] 迪特爾·梅迪庫斯. 德國民法總論[M]. 邵建東譯.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51.
[16] 劉引玲. 親屬身份權與救濟制度研究[M]. 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11.100.
[17] 王利明. 侵權責任法研究(上卷)[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453.
[18] 徐久生,莊敬華. 德國刑法典[M]. 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13.
[19] 劉艷紅. 調節性刑罰恕免事由:期待可能性理論的功能定位[J]. 中國法學,2009,150(4):112-121.
[20] 馬克昌. 德、日刑法理論中的期待可能性[J]. 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55(1):5-11.
[21] 平野裕之. 免責事由、責任的減輕(過失相抵、減輕因素等)[J]. 趙莉譯. 金陵法律評論,2009,18(2):28-31.
[22] 圓谷峻. 判例形成的日本新侵權行為法[M]. 趙莉譯.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收稿日期:2015-11-07;修回日期:2016-01-26
作者簡介:艾圍利(1981-),男,湖北天門人,講師,博士,主要從事民法、知識產權法研究,E-mail:keaton2004@163.com。
中圖分類號:D9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07X(2016)03-0130-07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Domestic Relation in the Reduction of Tort Reliability
AI Weili
( Law and Politics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
Abstract:The domestic relation can be to a certain extent a reasonable excuse for non-responsibility in infringement act between kinsfolk, the third party infringement relatives and relatives’ infringement the third party. The domestic relation mainly exonerates the infringer through blocking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and remits liability after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s about emotive factor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elatives and strangers, the harmony of the family unit, the human reproductive function of the family unit and so on. The domestic relation is an exemption by four ways: legislation, theories such as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methodology of jurisprudence such as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judge’s discretionary power.
Key words:domestic relation; exemptions; emotive factors;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