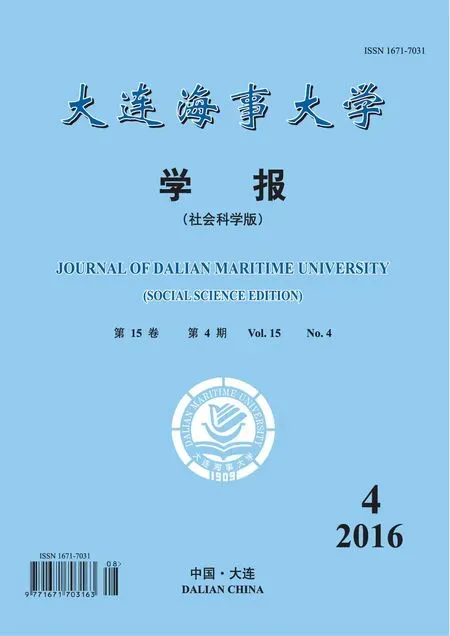“不合作”中的“合作”
——合作原則視域下《京華煙云》中的“中國表達(dá)”
馮智強(qiáng),李 濤
(1.天津工業(yè)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天津 300387; 2.朝陽師范專科學(xué)校外語系,遼寧朝陽 122000)
?
“不合作”中的“合作”
——合作原則視域下《京華煙云》中的“中國表達(dá)”
馮智強(qiáng)1,李濤2
(1.天津工業(yè)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天津300387; 2.朝陽師范專科學(xué)校外語系,遼寧朝陽122000)
合作原則是保證人物會(huì)話順利進(jìn)行所應(yīng)當(dāng)遵循的基本原則,但為了達(dá)到特定的交際效果和交際目的,會(huì)話雙方很可能會(huì)故意違背合作原則進(jìn)行對(duì)話,這在林語堂小說MomentinPeking(《京華煙云》)的人物對(duì)話中也時(shí)有體現(xiàn)。分析林語堂在運(yùn)用英語進(jìn)行創(chuàng)作時(shí)如何巧妙地使用帶有中國特色的翻譯表達(dá),最大限度地保留漢語及中國文化的特點(diǎn),從而使這些表面上違背合作原則的帶有中國語言文化特征的表達(dá),成功地達(dá)到了傳播中國文化的目的。
《京華煙云》;合作原則;中國文化;中國表達(dá)
一、引 言
話語交際是一種雙邊或多邊的語言行為,為保證交際的順利進(jìn)行,交際者必須共同遵守一些基本原則。話語交際原則中最重要的是由哲學(xué)家格萊斯提出的會(huì)話合作原則(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以下簡稱為合作原則),認(rèn)為言語交際雙方在使用語言時(shí)要遵守合作原則的四個(gè)準(zhǔn)則:數(shù)量準(zhǔn)則、質(zhì)量準(zhǔn)則、關(guān)系準(zhǔn)則及方式準(zhǔn)則,而其中的每一條準(zhǔn)則都有相應(yīng)的要求。[1]這四條準(zhǔn)則看起來很有道理,但人們平時(shí)說話時(shí)并不一定總是亦步亦趨地完全遵守,這可能產(chǎn)生三種結(jié)果:第一,使話語交際不能順利進(jìn)行甚至中斷;第二,使聽話人上當(dāng)受騙;第三,產(chǎn)生特殊的交際含義。[2]文學(xué)作品中通過故意違背合作原則而產(chǎn)生特殊的蘊(yùn)含(implicature)和交際含義,需要讀者根據(jù)語境中或隱或現(xiàn)的線索來推導(dǎo)其字面以外的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的現(xiàn)象是十分普遍的。如果說質(zhì)和量的準(zhǔn)則相當(dāng)于傳統(tǒng)翻譯標(biāo)準(zhǔn)中的“忠實(shí)”(信),關(guān)系和方式準(zhǔn)則相當(dāng)于“通順”(達(dá)),那么“美”(雅)的標(biāo)準(zhǔn)則主要體現(xiàn)在蘊(yùn)含之中。[3]40
林語堂的英文著譯作品是中國文化在西方傳播的典范,其中融入了許多具有中國文化內(nèi)涵和漢語語言特色的“中國表達(dá)”,真實(shí)地再現(xiàn)了中國語言文化從表層結(jié)構(gòu)、思維習(xí)慣到文化心理等諸多特質(zhì),忠實(shí)地傳播了源語文化的特點(diǎn)和源語語言的“差異性”特征。林語堂小說代表作MomentinPeking即《京華煙云》中的人物對(duì)話就是對(duì)中國文化背景下人們?nèi)粘=涣鞯恼鎸?shí)再現(xiàn),其中包括大量具有中國特色的表達(dá)方式,同時(shí)對(duì)話中就有很多看似違反合作原則但卻能夠反映中國文化的地方。由于中國文化的獨(dú)特性,使得許多人物語言背后都包含著深層的文化內(nèi)涵,而這些文化因素通常無法在有限的人物對(duì)話中得到充分解釋,在語篇意義連貫方面往往會(huì)產(chǎn)生斷層,因而違反了合作原則。林語堂巧妙地利用具有濃厚中國特色的表達(dá)方式對(duì)其進(jìn)行翻譯和創(chuàng)作,在人物對(duì)話中采用具有中國特色的表達(dá)方式,使譯文組織依然體現(xiàn)漢語的表達(dá)特征和行文風(fēng)格,從而達(dá)到了傳播中國文化的交際效果。由此在譯文的語言層面產(chǎn)生的看似語義斷層、信息不適量、信息不真實(shí)以及語言歧義等現(xiàn)象,對(duì)于不熟悉中國文化的西方讀者來說理解起來會(huì)有一定的難度,甚至?xí)徽J(rèn)為是違反了合作原則,但這樣恰恰產(chǎn)生了一種特殊的文學(xué)性和美學(xué)效果,從而最大限度地向世界展現(xiàn)了中國文化的魅力和中國語言的特色。本文從林語堂小說MomentinPeking中違背合作原則中的關(guān)系準(zhǔn)則、質(zhì)量準(zhǔn)則、數(shù)量準(zhǔn)則或方式準(zhǔn)則的人物對(duì)話入手,論證其中違反合作原則但卻用中國化的表達(dá)方式成功傳播了中國文化和語言特征的諸多情況。
二、違反“關(guān)系準(zhǔn)則”的中國表達(dá)
關(guān)系準(zhǔn)則是指說出的話應(yīng)切合話題,要求會(huì)話當(dāng)中聽話人的話語要和說話人的話語相互關(guān)聯(lián)。例如當(dāng)甲提出問題時(shí),乙不能問而不答或者答非所問。若會(huì)話違反了關(guān)系準(zhǔn)則,可能是因?yàn)槠渲兴a(chǎn)生的特殊會(huì)話含義和交際意義。有學(xué)者指出,譯者碰到有會(huì)話含義的語句時(shí),一般只需譯出其語義意義,其語用意義留給讀者去推理和體會(huì),譯者無須代勞。如果不顧及原文語境,將語用意義也譯出,反而會(huì)弄巧成拙。[4]因此,在翻譯實(shí)踐中應(yīng)多考慮采用適當(dāng)?shù)姆绞椒g和傳達(dá)原文的語用意義。MomentinPeking中就有許多因?yàn)橹袊幕奶厥庑远鴮?dǎo)致的違反關(guān)系準(zhǔn)則的會(huì)話。例如曼妮在將要嫁給平亞沖喜之前曾向蔣太醫(yī)問起平亞的病情,蔣太醫(yī)由于不知道曼妮就是平亞的未婚妻,于是將平亞的實(shí)情告訴了曼妮。兩人之間的對(duì)話如下:
“How is he and will he get well?” Mannia went on.
“He is making good progress. Probably he will recover now.”
“Do you think so?” asked Mannia, and her voice quivered. Such a concern about the sick boy was not exactly good form. The doctor liked talking to a pretty face, and he said, with the idea of testing her, “A case like this half depends on men and half depends on Heaven. It half depends on the power of medicine and half upon the patient’s vitality. He has been sick for so long.”[5]159
語言不僅是文化的載體,更是價(jià)值觀的載體,因此,不同民族的世界觀同樣可以通過語言反映出來,這一點(diǎn)可以從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方面很直觀地顯現(xiàn)出來。在人類發(fā)展歷史上,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人們總是愿意去相信世間有一種超自然的神的力量在主宰著宇宙中的一切,萬事萬物存在的規(guī)律和法則都是由超自然的神在掌控著。與西方人信奉的上帝(God)不同,中國人則信奉天帝(King of the Heaven),因此百姓們也對(duì)天帝有“老天爺”、“上天”、“玉皇大帝”等多種稱呼。在中華文化中,玉皇大帝(即天帝)堪稱是超越三界之外的最高統(tǒng)治者,掌管著天地萬物的興衰發(fā)展與消長變化,無論各方神圣、妖魔鬼怪均在其掌控之中,因此,他在中國人心目中有著神圣而至高無上的絕對(duì)信仰地位,對(duì)人間之事更是有著絕對(duì)的權(quán)威和能力。此處蔣太醫(yī)的話也是想要表達(dá)平亞的病情已經(jīng)十分嚴(yán)重,到了單靠高明的醫(yī)術(shù)也無能為力的地步,只能在服藥的基礎(chǔ)上看上天的安排了。這里對(duì)于“上天”的翻譯若采用歸化方法翻譯成“God”,則很容易讓西方讀者產(chǎn)生誤解,以為中國人也普遍信奉基督教。林語堂則比較高明,使用“Heaven”一詞避免了這一可能,但同時(shí)這一中國化的表達(dá)方法也會(huì)讓不懂中國人精神信仰的西方讀者感到不解:平亞的病情康復(fù)為何要一半靠藥效一半靠天空,這其中又有怎樣的關(guān)聯(lián)。因此,畫線部分若按照西方讀者的角度理解的確違背了關(guān)系準(zhǔn)則,但若聯(lián)系中國文化語境,這卻真實(shí)地反映出中國人精神信仰的狀況。
其他違背關(guān)系準(zhǔn)則卻反映出中國文化的情況還有很多。例如曼妮剛剛來到曾家時(shí),恰逢為自己的父親守孝時(shí)期未滿,當(dāng)平亞問起曼妮為何遲遲不來探望他時(shí),他和桂姐有這樣的一段對(duì)話:
Pingya still had high fever and smiled feebly, and closed his eyes, then opened them again and said, “Is she really here? You are not deceiving me? Why does she not come in to see me?”
“You are impatient,” said Cassia. “They have just arrived. She is in mourning and can not come into the sickroom as she is.”[5]117
在中國文化中,自古以來人們將對(duì)父母“生養(yǎng)死葬”的態(tài)度,視為衡量“孝”的普遍標(biāo)準(zhǔn)。父母亡故了,子女要守孝三年,服孝期間不走親戚,不訪友,不集會(huì),不拜年,尤其不能到病人家去,以免給他人帶來不幸。俗語有“身穿熱孝,不登鄰宅”。中國人認(rèn)為戴孝的人不能進(jìn)病人的房間,因?yàn)檫@樣比較晦氣,不利于病人病情康復(fù),所以這里隱含著中國守孝文化的規(guī)約。桂姐的回答正好傳達(dá)了中國這樣的喪葬習(xí)俗,但林語堂并未對(duì)其背后的原因做過多所謂“明晰化”與“合理化”的解釋,這對(duì)于不了解中國文化的英語讀者而言,很可能會(huì)不理解為何為死者哀悼的人不能進(jìn)病房探望病人以及兩者究竟有何關(guān)系。因此這里的守孝與探望病人兩者表面上并無關(guān)聯(lián),違背了關(guān)系準(zhǔn)則,但這卻是對(duì)中國喪葬守孝文化的真實(shí)描述,是對(duì)中國文化的客觀傳達(dá)和再現(xiàn)。
三、違反“數(shù)量準(zhǔn)則”的中國表達(dá)
數(shù)量準(zhǔn)則是指話語應(yīng)包含需要的信息,即要求會(huì)話雙方應(yīng)讓自己的話語提供當(dāng)時(shí)所需的適量的信息,且不要提供超出所需的過量信息。由于人們常常因?yàn)樘囟ǖ慕浑H目的而違背交際原則展開對(duì)話,于是格萊斯在提出合作原則時(shí)也聲稱人們?cè)谡f話時(shí)并不是分毫不差地遵循這些準(zhǔn)則,他曾經(jīng)在其著作中提到:若一段話語表達(dá)在字面意義上違背了合作原則里的某一準(zhǔn)則,或者在更深層意義上選擇故意違反它,或者與其中若干準(zhǔn)則的規(guī)定相違背,那么聽話人就應(yīng)該自我構(gòu)建會(huì)話含義使其符合合作原則。[6]也就是說,人們?cè)诖蠖鄶?shù)情況下會(huì)盡量地遵循這些準(zhǔn)則,但是當(dāng)談話沒有按預(yù)期進(jìn)行時(shí),即當(dāng)說話人看似違背了其中的某一條或多條準(zhǔn)則時(shí),聽者也并不會(huì)放棄解讀說話人的意圖,而是會(huì)努力依據(jù)固有知識(shí)或常識(shí)對(duì)話語意義進(jìn)行自我聯(lián)想和闡釋,在理解話語的過程中添加失落的背景信息,以便讓話語從文化層面上講仍遵循合作原則,從而使得說話人的話語在特定的語境中具有獨(dú)特的交際效果。MomentinPeking中就存在這樣的話語信息量過多或不足而違反數(shù)量準(zhǔn)則的情況,但作者的意圖是為了凸顯中國文化特殊的交際含義。例如其中有一段情節(jié)是說曼妮的母親孫太太帶著曼妮和眾丫鬟到北京的親戚曾家后,叮囑所有人說話辦事要處處仔細(xì)小心,不能讓人家看笑話,她的話是這么說的:
“Now we are in Peking and in this big house and garden,” said Mrs. Sun, “you should be careful what you say. When people ask you things, think before you reply, and don’t talk too much. Say half of what you want to say, and swallow the other half. It isn’t like the country, you know. Observe others and try to learn the manners and rulers.”[5]126
【譯文】孫太太說:“現(xiàn)在咱們是在北京城,在一個(gè)有花園兒的大公館里頭,你說話要小心。有人問你話,要想想再開口,不要多說話。話要說一半兒,咽下去一半兒。要知道,不像在鄉(xiāng)下了。睜眼看別人,跟人家學(xué)禮貌,學(xué)規(guī)矩。”[7]
冗余信息是言語交際過程中信息差導(dǎo)致的表現(xiàn)之一,從語義內(nèi)容與語言形式的矛盾以及語言發(fā)展的規(guī)律來看,冗余的產(chǎn)生不但不可能避免,而且也不必要完全避免。如果沒有冗余,語言反而缺少豐富性,就難以擔(dān)負(fù)傳遞社會(huì)信息的使命。非語言性語境下的冗余是會(huì)話中十分常見的現(xiàn)象,其作用通常不在言內(nèi),而在言外。[8]其實(shí)原文中孫太太說這么多話只表達(dá)了一層意思,就是叮囑大家要謹(jǐn)言慎行,但是文中用了三個(gè)句子來表達(dá)這一層意思,并且每句話都是包含有各自分句的長句,信息量略顯冗余和重復(fù),表面上違背了合作原則中的數(shù)量原則,但是若從漢語語句屬于意合結(jié)構(gòu)的角度出發(fā)就不難理解了。例如我們看到張振玉的漢語譯文里的語義就并不顯得那么多余和重復(fù),這是由于漢語重整體思維,漢語的一個(gè)典型語言現(xiàn)象是周遍性重復(fù),一個(gè)意思本來講一次就已足夠,但漢語常不厭其煩地一再加以重復(fù),有時(shí)是別的語言(例如英語)很難容忍的。[9]因此,這里的英文原文在語言結(jié)構(gòu)上體現(xiàn)了漢語的意合以及重整體思維的特點(diǎn),是一種帶有濃厚漢語特征的中國化表達(dá)。
相反,還可以從中找到一些人物會(huì)話中語言所含信息量較少的例子。例如當(dāng)曼妮和平亞訂婚之后結(jié)婚之前,恰逢曼妮的父親去世,平亞作為未來的女婿自愿和曼妮一起為父親守靈。偶然兩人在守靈時(shí)得以有獨(dú)處的機(jī)會(huì),在曼妮拿自己的玉墜兒給平亞看時(shí),平亞想趁機(jī)拉住曼妮的手,曼妮不好意思地縮了回去,兩人之間發(fā)生了這樣的對(duì)話:
As Pingya received the jade he took the occasion to hold her hand, but Mannia quickly withdrew it, so that the jade almost fell to the ground.
“You shouldn’t do that,” she chided quite flushed.
“You let me hold your hand that day of the cricket match, when my cricket was killed,” he protested.
“Then was then and now is now,” said Mannia.
“Why is it different?”
“We are grown-up. I should not hold hands with you now.”[5]126
首先平亞想攥住曼妮的手,曼妮躲開時(shí)說“Then was then and now is now”,這是漢語的慣用語“此一時(shí),彼一時(shí)”的直譯,是典型的中國表達(dá)。那么讀者理解原文時(shí)會(huì)產(chǎn)生像“此一時(shí)如何,彼一時(shí)又如何”的疑問,雖然讀者可以根據(jù)上下文推斷出“此一時(shí)”是他們倆已經(jīng)長大,“彼一時(shí)”是他們小時(shí)候,那么為何他們只有小時(shí)候可以拉手而長大了就不行了?這對(duì)于思想開放的西方讀者來說讀起來是費(fèi)解的,而林語堂并未就此闡明原因。因此,這是一種信息量不足的話語,違背了合作原則的數(shù)量準(zhǔn)則。了解中國文化的人會(huì)知道這是跟中國舊社會(huì)“男女授受不親”的思想分不開的,當(dāng)時(shí)成年男女是不允許有身體接觸的,即使是一對(duì)訂了婚的成年男女在結(jié)婚之前也是不允許的。更有甚者,古時(shí)還有“沾衣裸袖便為失節(jié)”的說法,但未成年的小孩子兩小無猜,就不必講究這一點(diǎn)。這些都是一種典型的中國社會(huì)文化規(guī)約,而“Then was then and now is now”這個(gè)說法本身就是漢語“此一時(shí),彼一時(shí)”的直譯,英語中并沒有這樣的說法,其對(duì)應(yīng)的表達(dá)應(yīng)該是“The time has changed.”或是“The situations are different.”因此林語堂的這種“中國表達(dá)”不僅在文字表達(dá)方面模仿了漢語的表達(dá)方式,而且也反映了漢語語篇以意合為主,主要憑借詞語、句子之間內(nèi)在的邏輯聯(lián)系而形成語篇連貫的特點(diǎn)。
四、違反“質(zhì)量準(zhǔn)則”的中國表達(dá)
質(zhì)量準(zhǔn)則是指會(huì)話當(dāng)中要盡量說真實(shí)的話語,不說自己認(rèn)為是錯(cuò)誤的話,不說自己缺乏足夠證據(jù)的話。質(zhì)量準(zhǔn)則要求話語內(nèi)容是真實(shí)的,不是虛假或缺乏足夠證據(jù)的。說話人一旦違背了質(zhì)量準(zhǔn)則,那么同樣可能會(huì)產(chǎn)生一定特殊的會(huì)話含義和交際意義。翻譯此類具有會(huì)話含義的語篇時(shí),譯者可根據(jù)原文,采用含義對(duì)含義的對(duì)應(yīng)模式,即原文中違背合作原則的地方,譯文也應(yīng)違背合作原則,其含義由譯文讀者自己去體會(huì)和推導(dǎo),以獲得類似于原文讀者的感受。[10]小說MomentinPeking中就有一些人物對(duì)話貌似違反了質(zhì)量準(zhǔn)則而產(chǎn)生了一定的會(huì)話含義,其中帶有夸張手法的例子很能說明這個(gè)問題。例如曼妮到了曾家后頭一次和木蘭見面時(shí),兩人久別重逢,四目相對(duì),都猶豫了一下,接著木蘭說的頭一句話是這樣的:
After a wavering moment Mulan burst out: “You predetermined enemy, I almost died thinking of you and waiting for you.”[5]147
原文中的“I almost died thinking of you and waiting for you.”是由漢語的“我快想死你了”直譯而來的,這種表達(dá)是獨(dú)特的中國化的表達(dá),類似的漢語表達(dá)不勝枚舉,例如“我快累死了”,“我快渴死了”,“惡心死我了”等。這只是一種夸張手法,僅僅說明說話人當(dāng)時(shí)的某種切身感受的程度之深,已經(jīng)達(dá)到了無法忍受或者無以復(fù)加的地步,而并沒有真的達(dá)到“死了”狀態(tài),這樣語言所包含的信息實(shí)際上是不真實(shí)的,所以這是違背合作原則中的質(zhì)量準(zhǔn)則的。但林語堂采用這種包含著中國文化的中國表達(dá)直接進(jìn)行翻譯,卻從語言表層展現(xiàn)了漢語表達(dá)特點(diǎn)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使讀者回味無窮。
接著再看另外一例。曼妮見到病中的平亞后問起桂姐平時(shí)夜里有誰在平亞身邊伺候時(shí),桂姐說了如下的話:
“Who keeps him company at night?” asked Mannia, while Snow Blossom was inside.
“Oh, it’s not certain,” said Cassia. “Taitaiand I take turns at night to keep him company until he goes to sleep, but several days ago when he was not so well, we all sat up the whole night and went to sleep by turns. Sometimes Muskrose comes to relieve Snow Blossom, or sometimes, it is the maid Phoenix, and they sleep in the western room. We rely most upon Snow Blossom and she has never stolen an hour of idleness throughout his sickness.”[5]144
原文中的詞組“steal idleness”也是由漢語的“偷懶”一詞直譯而來的,但英語中并不存在這樣的表達(dá),是一種很典型的中國化的表達(dá),英語中的對(duì)等表達(dá)應(yīng)該為“always keep herself busy”或者“never stop working for even one moment”等。一般說來,譯者應(yīng)在翻譯實(shí)踐中保持了解和熟悉“慣用法意識(shí)”,并處處有意遵循目的語的習(xí)慣用法,包括動(dòng)詞和其他詞語的搭配用法、習(xí)語的用法、語言詞匯中豐富的表達(dá)方式等。[11]漢語中類似于“偷懶”這樣的慣用法很多,例如“看病”、“烤火”、“曬太陽”等,這些動(dòng)賓短語的真正意義并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而是要取其抽象的深層意義才講得通,這同時(shí)也充分體現(xiàn)了漢語的意合特點(diǎn)。林語堂并沒有采用英語中的慣用表達(dá)進(jìn)行對(duì)等翻譯,而是采用慣用的中國表達(dá)對(duì)“偷懶”一詞進(jìn)行了直接翻譯,這可能會(huì)令西方讀者感到疑惑:“懶惰”怎么可能會(huì)用“偷”來形容呢?從而認(rèn)為這屬于虛假信息。這表面上確實(shí)違背了質(zhì)量原則,但這種中國化的表達(dá)卻體現(xiàn)了漢語的意合特征和中國人形象化的思維方式,讓西方讀者在理解原文意義的基礎(chǔ)上感受到中國文化的新異與神奇。
五、違反“方式準(zhǔn)則”的中國表達(dá)
方式準(zhǔn)則是指人物會(huì)話中應(yīng)該說清楚明白的話,避免表達(dá)含混和歧義,力求簡短,力求有序。違反方式準(zhǔn)則可能造成語言歧義或者無法理解,但是在一定的情況下這樣恰恰能反映出說話人在該語境下的特殊含義和作者所表達(dá)的特殊的交際效果。例如林語堂的小說MomentinPeking中有這樣一個(gè)片段:曾家二兒子經(jīng)亞小時(shí)候十分淘氣,有一次為了尋開心他騙姚家的女兒木蘭上樹,而后木蘭不小心失足從樹上摔下來暈了過去。父親曾老爺聽說這件事之后十分生氣,準(zhǔn)備命人把經(jīng)亞抓來狠狠教訓(xùn)一頓。他在全家在場的情況下與桂姐有如下對(duì)話;
“The little ‘bad-goods’!” snorted Mr. Tseng.
Cassia was greatly concerned at what her child had said.
“Don’t listen entirely to what the child says. It may or may not be true.”
“Bring me thechiafa!” was Mr. Tseng’s answer. Thechiafa, meaning “family discipline”, was a birch rod.
Silence fell in the room.[5]76
當(dāng)桂姐勸說不要聽信孩子的話,她們的話也許不對(duì)后,曾文伯并沒有接著她的話講,而是吩咐“Bring me thechiafa!”即拿“家法”來。這里的“家法”就不僅僅是指抽象的家庭法則或家庭條例,而是指具體的藤子棍,意思是他要用藤子棍來抽打經(jīng)亞,對(duì)其惹出的事端進(jìn)行懲罰。在中國舊時(shí)的家庭文化當(dāng)中,家庭中的長輩在家庭管理和威望地位上享有最高的權(quán)力,當(dāng)晚輩犯了錯(cuò)誤以后,長輩會(huì)用“家法”來對(duì)晚輩進(jìn)行批評(píng)教育,即通常會(huì)使用像藤子棍這樣的工具來拷打晚輩以示懲戒,避免晚輩以后再次犯錯(cuò)。“chiafa”是威妥瑪拼音拼出的“家法”,這樣直接音譯成英語的詞匯是早期對(duì)中國文化專有項(xiàng)慣用的翻譯方式,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音譯法,可能會(huì)使不懂“家法”文化內(nèi)涵的西方讀者不知所云,但若聯(lián)系下文林語堂的解釋,便會(huì)將“家法”和藤子棍兩者聯(lián)系起來,猜測出其可能是一種懲戒工具。
這種典型的中國表達(dá)背后蘊(yùn)含的是中國的家庭文化,而這樣的隱含文化是很難在有限的人物對(duì)話中完全解釋清楚的。因此,這種背景文化的缺失會(huì)導(dǎo)致其在表面上違背了合作原則中的關(guān)系準(zhǔn)則,即便如此,林語堂仍大膽地采用了音譯的中國化表達(dá),給讀者留下思考與想象的空間,從而間接地傳播了中國的家庭文化。因?yàn)榇祟悓S忻~是具有闡釋意義的文化符號(hào),如果譯文將其內(nèi)涵意義全部意譯出來而一覽無余,鎖定一種解讀而排斥其他解讀,便束縛了讀者想象力,也違背了文學(xué)作品“陌生化”的特質(zhì)。
再看小說MomentinPeking中的另外一例:曾家大兒子平亞得了場大病,就在平亞病情越來越嚴(yán)重的時(shí)候,曾家無奈請(qǐng)來和平亞從小定下娃娃親的曼妮姑娘,準(zhǔn)備讓兩人盡快結(jié)婚沖喜,使平亞能得到康復(fù)。但曾家一直擔(dān)心曼妮知道了平亞的病情后會(huì)不愿意拿自己的終身大事來完成沖喜,可是就在桂姐告訴曼妮有關(guān)平亞的實(shí)情后,曼妮非但沒有一點(diǎn)怨言,反而堅(jiān)決同意要嫁給平亞。其中桂姐和曼妮兩人有如下的對(duì)話:
“Anything, anything that will help him to get well!” said Mannia, sobbing.
“If something unfortunate should happen, I would shave my head and enter a convent,” she said, after a moment.
“Don’t talk nonsense,” said Cassia. “Things are not as bad as that, and besides, the parents would not let you and there is your mother. You are indeed already a Tseng family person and as far as I can see, your destiny and Pingya’s are tied up together. We shall wait and see-who can tell but next yearLaoyehandTaitaiwill carry a grandchild and we shall eat red eggs?”
“Now you are making fun of me again,” said Mannia with a sigh and rose and turned aside.[5]134
詞義的模糊與不完全對(duì)應(yīng)通常會(huì)導(dǎo)致跨文化交際中的元信息混淆,而中國文化中的一些文化負(fù)載詞在用英語直接描述時(shí)通常會(huì)失去漢語中原有的文化信息底蘊(yùn),變得語義模糊。上述語篇中桂姐的話是說若平亞和經(jīng)亞結(jié)婚了,說不定明年會(huì)生一個(gè)孩子,老爺和太太可能會(huì)抱上孫子或者孫女,這樣她和家里的其他人也可以跟著吃滿月酒拿彩蛋,表示祝賀的同時(shí)沾沾喜氣。其中的“who can tell but next yearLaoyehandTaitaiwill carry a grandchild and we shall eat red eggs?”這一句中提到了“red egg”這個(gè)意象,就是代表吃滿月酒的意思,這對(duì)于不太了解中國習(xí)俗的西方讀者來說是無法理解的,是違背合作原則的方式準(zhǔn)則的。在中國文化中,孩子降生后滿一個(gè)月要舉行儀式表示慶祝,通常孩子的父母會(huì)邀請(qǐng)親朋好友聚在一起舉辦一個(gè)宴會(huì),而客人通常會(huì)給所生的兒子紅包,給所生的女兒贈(zèng)送首飾等,而客人在宴會(huì)結(jié)束之后也不會(huì)空手而歸,他們會(huì)得到主人回贈(zèng)的涂成紅色或彩色的雞蛋以示幸福好運(yùn)之意。在這個(gè)宴會(huì)上還有一項(xiàng)講究,就是孩子的生母度過了產(chǎn)后一個(gè)月身體最虛弱的時(shí)期,此時(shí)通常會(huì)服用一碗有豬蹄、醋、雞蛋、生姜等熬成的營養(yǎng)湯粥來補(bǔ)補(bǔ)身子。正是因?yàn)檫@樣的宴會(huì)與紅雞蛋和生姜有關(guān),于是這個(gè)宴會(huì)的英文名字就是“Red egg and ginger parties”,即中國人所說的滿月酒宴。作者林語堂此處直接用了“red egg”一詞而并未對(duì)該詞做過多解釋,雖然對(duì)西方讀者可能會(huì)造成一定理解難度,違背了方式準(zhǔn)則所要求的說話應(yīng)表意清晰明了而避免表達(dá)含混和歧義,但是這種典型的中國表達(dá),會(huì)激發(fā)讀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從而進(jìn)一步去了解相關(guān)的中國文化。
其他的例子還有很多,例如當(dāng)曼妮到曾家后第一次見到病中的平亞時(shí),桂姐打發(fā)其他人都出去,只留曼妮在平亞身邊照顧,平亞讓曼妮幫他擦臉,她和平亞身子離得很近,曼妮說了這樣的話:
Cassia held Pingya’s head up and the three heads were very close together. Mannia lightly whispered, “Is anybody outside? What would this look like?”[5]134
英語中“What would this look like?”一般是指物體的外形樣貌,回答一般是客觀描述,或是一種比喻,比喻物體所相像的喻體。原文中的該句話并不是真正指這看起來像什么,而是害怕她和平亞行為過于親密,若被其他人看見會(huì)被嘲笑指責(zé)未婚男女之間行為的不檢點(diǎn),看起來不雅。這也是與前面提到的中國文化中“男女授受不親”的規(guī)約相一致的。林語堂所寫的這句話很明顯是從漢語的“這叫別人看見像什么”一句直譯成英語的。若不理解中國文化中這樣的背景,那么原文的這句話很可能引起語義歧義,從而認(rèn)為違背了方式準(zhǔn)則。但這種表達(dá)卻展現(xiàn)了特定文化語境下漢語的表達(dá)方式和思維習(xí)慣。
六、結(jié) 語
合作原則的四條準(zhǔn)則是具體化了的合作原則,人物會(huì)話當(dāng)中需要遵守合作原則來保證會(huì)話的順利進(jìn)行,但在現(xiàn)實(shí)的人際語言交流中,人們往往根據(jù)特定的語境故意違反合作原則中的某一準(zhǔn)則或者多個(gè)準(zhǔn)則,使話語按照自己的意向產(chǎn)生特定的隱含意義,從而達(dá)到既定的交際目的和文學(xué)效果。而故意違反合作原則一般與其本土的社會(huì)政治文化因素緊密相關(guān),具有社會(huì)語用價(jià)值與社會(huì)學(xué)意義。同時(shí),說話人或聽話人往往皆知說話人的話語最終勢必會(huì)遵循合作原則,也就是說,“合作”是說話人通過違反準(zhǔn)則產(chǎn)生會(huì)話含義的大前提。[12]這在林語堂的英文小說MomentinPeking中得到充分體現(xiàn)。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京華煙云》的會(huì)話中,存在很多表面上違反合作準(zhǔn)則的話語現(xiàn)象,但若從深層的文化背景或者特定的語境進(jìn)行分析,它們說到底還是遵守了會(huì)話原則,只不過違反準(zhǔn)則也是遵守合作原則的一種方式和表現(xiàn)形式,是一種“不合作”中的“合作”,這也為研究《京華煙云》的對(duì)話提供了新的視角。
通過分析違背關(guān)系準(zhǔn)則、質(zhì)量準(zhǔn)則、數(shù)量準(zhǔn)則以及方式準(zhǔn)則等合作原則而產(chǎn)生特殊交際含義的人物會(huì)話發(fā)現(xiàn),林語堂運(yùn)用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表達(dá)”向西方目的語讀者最大限度地展現(xiàn)了中國文化和語言的特征。這些“中國表達(dá)”雖然對(duì)于不了解中國文化的西方讀者來說理解起來可能會(huì)產(chǎn)生一定障礙,但事實(shí)證明,這種看似違背合作原則的“不合作”中的“合作”,已經(jīng)超越了語言表層的束縛而達(dá)到了語用界面的銜接與連貫,并取得了十分明顯的文學(xué)傳播和文化交流的效果,無處不在地體現(xiàn)出中國文化的獨(dú)特之處,并成為中國文化跨文化傳播的成功范本。誠然,如果文學(xué)作品總是恪守成規(guī),文學(xué)翻譯總是亦步亦趨,不敢越雷池半步,那勢必會(huì)嚴(yán)重影響其文學(xué)性、藝術(shù)性、創(chuàng)造性和可讀性,從而削弱文學(xué)之所以成為文學(xué)的根本特性。當(dāng)然,翻譯作為原作者、譯者與目標(biāo)讀者間的隔空對(duì)話,由于語言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不僅要求譯者要盡量掌握解讀原文語篇的必要知識(shí)和語用前提,把握原文對(duì)合作原則的操縱分寸,而且還要了解目標(biāo)讀者的文學(xué)需求、知識(shí)結(jié)構(gòu)、語言能力、品味格調(diào)和接受反應(yīng)等[3]196-197,只有這樣才能實(shí)現(xiàn)真正意義上的跨文化交流與傳播。
[1]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C]//COLE P, MORGAN J L. Syntax and semantic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307-309.
[2]邢福義.現(xiàn)代漢語[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460.
[3]王東風(fēng).連貫與翻譯[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9.
[4]曾憲才.語義語用與翻譯[J].現(xiàn)代外語,1994(1):23-27.
[5]林語堂. Moment in Peking[M].北京:外語教學(xué)與研究出版社,2009.
[6]GRICE H P.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30.
[7]張振玉.京華煙云[M].北京:萬卷出版公司,2013:81.
[8]邵志洪,邵惟韺.新編英漢語研究與對(duì)比[M].上海:華東理工大學(xué)出版社,2013:322-327.
[9]潘文國.漢英對(duì)比綱要[M].北京:北京語言大學(xué)出版社,2013:372.
[10]陳淑萍.語用等效于歸化翻譯策略[J].中國翻譯,2004(4):43-44.
[11]陳宏薇,李亞丹.新編漢英翻譯教程[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0:13.
[12]何兆熊.新編語用學(xué)概要[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160-161.
2016-05-09
馮智強(qiáng)(1970-),男,博士,副教授;E-mail:1670942099@qq.com
1671-7031(2016)04-0122-07
H030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