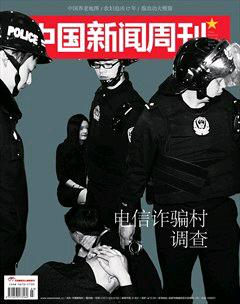漂浮在的的喀喀湖上的家園
張媛

黎明時分的的的喀喀湖。圖片編輯/董潔旭
秘魯的路況大多不好,以坑坑洼洼的土路為主,趕上雨季,滿地泥坑。大巴的座椅沒有扶手,沒有安全帶,每每被顛得整個人快飛起來。當地司機和乘客卻視若無睹,司機只顧狂飆從不減速,乘客自顧自地聊天或睡覺。
大巴上,只有一位秘魯人會說英語。她叫朱莉,是一名醫務工作者,原本在秘魯首都利馬工作,7年前來到普諾,再也沒離開。簡單生活、淳樸民風和原生態文化,是她對這座城市的概括。她向我們保證:“你們一定會愛上這里的。”
安第斯山縱貫南北,將秘魯劃分成了三個地理區域:西部沿海狹長的平原、東北部氣候濕潤的亞馬遜森林和南部海拔僅次于青藏高原的阿爾蒂普拉諾高原。普諾就位于阿爾蒂普拉諾高原之上。
普諾市依山而建,密密麻麻的房屋聚集在較平坦的山谷間。市中心是一個20米見方的中央廣場,這是普諾市舉辦年度大型活動的場所,也是游客聚集之地。筆直的道路向廣場四周延伸,從高檔餐廳、繁華的市場、干凈的賓館到外圍簡陋原始的民居。
普諾農貿市場面積比中央廣場還大。秘魯傳統服飾和藝術品以色彩鮮明聞名,無論商販身上的傳統服飾、售賣的羊駝毛披肩和針織制品,還是作為紀念品的玩偶和擺設,都有著獨特的花紋和鮮艷的色彩。
以色彩取勝的還有水果蔬菜區。駐足一個水果攤,滿滿的全是熱帶水果,從地面直至一人多高,竟有一半從未見過。老板是位中年女子,坐在水果攤后面,只有起身才能露出頭。語言不通,只能沖我們微笑表示歡迎。我將沒見過的水果一一搜羅到塑料袋中,從兜里抓出一把硬幣,任由她拿。
秘魯的餐飲可以用簡單粗暴概括。比人臉大幾倍的面包、一只手只能抓下十來粒的爆米花、高掛的豬頭和羊頭……但就那一碗只加入少許調味料的荷包蛋肉絲湯面讓我找到了媽媽的味道。正如普諾給人的感覺一樣,簡單質樸卻幸福滿滿。
普諾被稱為秘魯與南美的民俗之都。作為印加文化的發祥地,普諾每年都會舉辦“民俗節”,以紀念印加帝國的創建者曼科·卡帕克。節日期間,廣場被裝飾得十分古樸,人們也都身著古代印加服飾。置身其中,仿佛穿越回印加時期。
印加帝國主要信仰太陽神因蒂。傳說太陽神將一對兒女送到普諾旁邊的的的喀喀湖中的的的喀喀島上,曼科·卡帕克便是太陽神的后裔。從此,這座小島被印加人視為圣地。曼科·卡帕克在島上修建了富麗堂皇的太陽神廟,每年供奉大量的金銀珠寶以感謝太陽神的恩賜。神廟的建造技巧令人贊嘆,重達數噸的一塊塊大石頭嚴絲合縫,連匕首都無法插入。這座太陽神廟成為印加文化的代表建筑之一,也賦予了的的喀喀湖圣湖神秘的色彩。
海拔3860米的的的喀喀湖上留存著一個奇觀,那就是烏魯族人的漂浮島。作為少數族裔的烏魯族人曾經受印加人侵略,于是在的的喀喀湖中建造了與世隔絕、便于移動的漂浮島,并至今居住在島上。
漂浮島距普諾港有半小時左右的船程。從普諾港出發,乘游船漂蕩在的的喀喀湖上。這是南美洲最大的淡水湖,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可以通行大船的高原湖,被秘魯人稱作“母親湖”。湖面碧藍,有一種令人生畏的深邃感,仿佛是神靈在向世人昭示著什么。向導是土生土長的普諾人,英文流利,對的的喀喀湖的故事一路如數家珍。
烏魯族人身著鮮艷的傳統服飾,早早地站在島邊等候著,用悠遠、宏亮的歌聲把我們迎下船。一個三四歲的烏魯族小朋友更是熱情,急切地伸出小手與我們相握,生怕自己被人忽略。
這座漂浮島僅有6戶人家,20多個居民。雖然稱為漂浮島,走在上面并沒有漂蕩的感覺。的的喀喀湖常年風平浪靜,令烏魯族人感恩。
我們走進了其中一家。茅草屋僅有一個入口,門梁低矮,需要彎下身子才能進入。茅屋內只有一張及膝高的茅草鋪,墻壁上掛著家人的照片,再沒有其他裝飾。主人并不太會說英語,只能指指點點帶我們參觀,向我們展示手工制作的藝術品。兩歲的小男孩流著鼻涕趴在地上玩耍,見到我們羞澀地笑著,憨態可掬。這種純真的笑容,我們在每位烏魯族人臉上都曾見到。
的的喀喀湖至今依然完好地保存著40多個漂浮島,面積在60-100平方米之間。曾經隨湖水漂流的漂浮島如今通過錨固定在湖床上,并通過結實的繩索相互連接。由于河水的侵蝕,連接島嶼的繩索每三年都需要更換一次。
漂浮島的制作是烏魯族人獨有的工藝。每年雨季,他們將蘆葦草根部的土壤切割成一米見方的立方體,再將多個立方體連接成長方形的平臺,縱橫交錯地鋪上水草葉子,再用水草搭建房屋。向導介紹,制作漂浮島必須在雨季,若是旱季切割蘆葦草根部,土壤就不能漂浮起來。
蘆葦草是烏魯族人賴以生存的植物。除了建造島嶼、茅草屋、船只,它還是烏魯族人的主要食物之一,且有清潔牙齒、解暑降溫等藥用價值。
烏魯族人的生活是忙碌而艱辛的。蘆葦草在湖水的浸泡下很容易發霉腐爛,每年都需要花大量時間重修漂浮島,在島上鋪蓋新鮮的蘆葦葉。船只的底部半年左右需要更新一次。隨著社會的進步,烏魯族人學會了使用電動船只,旅游業也增加了其收入,但他們依然選擇在島上居住,因為這是他們的家。